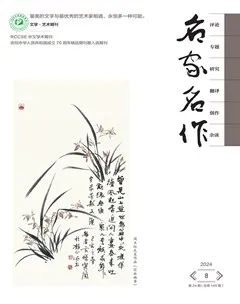儒學倫理觀下的“親親相隱”及現代啟示
[摘 要] “親親相隱”是中國儒家思想體系架構的“副產品”,在現代環境中飽含爭議,但這不代表它沒有意義和價值。首先,從根源出發看,作為中國主要哲學的以宗族血緣關系為根基進行架構的儒家倫理學,為了維護和保障其體系的正當性,必然會開出“親親相隱”的思想;其次,隨著個人的主體性地位提升,以“親親相隱”為代表的傳統倫理學遇到困境;最后,在今天,親緣關系依舊是人與人之間無法割舍的存在,因此今天應在保障正義的基礎之上正視人的情感需求。
[關 鍵 詞] “親親相隱”;儒家思想;倫理學;現代啟示
自劉清平教授發表的《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有關舜的兩個案例》一文起,關于“親親相隱”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問題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事實上,整個人類社會都無法脫離人際關系的窠臼,人無法離開社會而獨立存在。因而,社會關系既是在古代中國社會倫理架構得以維系的重要手段,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的理論內容,更是當今社會法治建設值得借鑒的重要思想。因而,現實要求我們必須以開放和前進的態度,運用深入和合理的方式,在傳統儒學的社會體系中尋找現代價值,使其在適應時代要求的基礎上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親親相隱”是中國傳統儒學倫理體系的部分表現,其形成和延續離不開儒家倫理系統的支持。隨著個人價值得到弘揚和發展,正義原則從家族的正義下降到個人的正義,因此有人開始反對“親親相隱”等損害個體利益的行為。但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家國觀念不會很快被淡化,直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儒家倫理學的宗族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與集體主義具有一定的契合之處,“親親相隱”也就具有了在新土壤中萌發生機的可能性。
一、儒家傳統倫理建構與“親親相隱”的關系
儒家傳統倫理體系的建構從孔子開始及至宋明理學,其思想體系一步步完善,最終形成了一座堅不可摧的理論大廈,“親親相隱”也逐漸由倫理道德上升到法律制度,這說明“親親相隱”制度是儒家倫理不可避免的衍生品。
先秦時期,儒家倫理學屬于初步構建階段,這一時期屬于從奴隸制向封建制度轉型的階段,但二者都以宗族血緣為紐帶構建社會等級秩序,因而其倫理學的建構也就以此為核心。孔孟思想在這一階段起主要作用。
孔子將“仁”定義為其思想的核心,而將“愛人”作為“仁”的來源,能夠將個人從親屬那里習得的愛推而廣之施行到所有人身上就是仁。這種愛是從親人身上生發延伸至他人的愛,因此它是有差等的。以親緣關系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仁愛,既滿足了孔子以仁為核心實現社會和諧的愿望,又導致他的仁愛關系理論體現在現實世界,沒有超脫以往以血緣氏族關系為基礎構建社會秩序的局限。正是由于以“愛人”之“仁”為核心,“全德之仁”關注的一大重點便是“孝悌”,甚至將其放在根本性的地位,“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顯然,親緣關系在他的倫理觀架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正因親緣關系在其倫理體系中的重要性,儒家從一開始在面對親緣與法律的沖突時就選擇提高親緣關系的地位。因此,在《論語》記載的“直躬證父”故事中,孔子持“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的態度。一方面,這種做法維護了儒家有差等的倫理基礎;另一方面,也為封建時期的等級尊卑制度提供了合理性。
孟子將以仁義為核心的倫理價值與政治原則相結合的這套系統發揮得更加完善。首先,孟子對孔子以仁為核心的體系給出了根源性依據,即人之性為其根本。孔子雖然提出了人性問題,但并未明確表示人性本原是善是惡。孟子明確提出,人之本性為善,人先天具有“不忍人之心”,他所謂的人之本性,是人不同于禽獸的某種特殊本質。人天生具有與禽獸相區別的“善端”,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四個善端正是人之四德的來源。正因為人之性善,人才自然地根據親屬之愛推而廣之到所有人身上踐行仁。從這一方面說,親緣關系是人天生具有的情感,是人類特有的本能,“親親相隱”是維護這種本能的決定,而反對“親親相隱”才是在破壞人的本性,是“不正直的決定”。其次,根據性善論的指導,孟子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會道德規范系統。有關這些道德規范,孔子和子思已有所涉獵,但孟子豐富和完善了其內容。第一,孟子以仁貫穿道德倫理和政治系Hn2rcc9wp6xJ6ThfyLGNJHtBOH3qS9/+XOJwSi+qdhs=統,形成了由仁義到仁政的思想體系。因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君王既具有社會的最高地位,又具備最高的道德標準,所以君王的不忍人之心是最為強烈的。因此,君王會實行“仁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既然君王具有仁愛之心,那他施行仁政就是自然而然的。因此為了彰顯仁義,在制度上更應該體現人文關懷,所以“親親相隱”具有實行的合理性。第二,孟子還將封建道德與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等級制度相結合,把以仁義禮智為代表的德行貫穿到“五倫”中,說明尊卑上下的等級從屬關系。而五倫中最重要的是“君臣”“父子”兩倫。①他指出:“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作為家庭道德的“孝悌”延伸至社會層面便是“忠君”思想。如此,他便將仁、義與孝順父母、忠誠君主緊密相連,視智、禮為對仁、義的踐行,從家庭父子關系出發形成的等級制度也就與倫理道德緊密聯系起來,倫理道德成為鞏固封建等級的證明。
孔、孟的倫理學說以“仁”為出發點,董仲舒的倫理學說則延續了西周時期天人合一的特點,將“天”作為倫理思想的出發點。他從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推出同類相動,進而說明“天人合一”,最后得出天人感應。董仲舒借助《易傳》描繪了以天地之氣、陰陽、四時、五行、萬物為運轉規律的宇宙,宇宙萬物種類中同類的事物能相互感應,如此形成了他的同類相動說。董仲舒進一步分析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發現人是萬物中最優秀的存在,稟受了天地之氣最為精粹的部分。這樣一來,要想找到能與天為“同類”的存在,也只能是人了,這也就推出了他的天人合一的理論,又根據同類相動,天人感應也就成立了。因為天人感應,董仲舒又根據《易傳》斷言陰與陽是陽尊陰卑的關系,所以天意落實到人事上也要奉行這一道理。董仲舒提出了“三綱”思想,由此,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等級從屬關系也就嚴格確立了,在森嚴的等級秩序之下,各種社會關系得到規范,宗法倫理思想成為社會正統。至此,“親親相隱”由倫理道德上升為法律制度,而這正是當時倫理的直接體現。自此之后,“親親相隱”一直作為社會法律制度存在。
宋明時期,理學家們著重從本體論的意義上對倫理道德展開深入探討,將封建倫理道德看作天然之理,此時的關注重點轉移到本體論以及理欲關系上,“親親相隱”作為公認的標準已經較少有人討論。朱熹在《論語集注》的《子路第十三》中對“直躬攘羊”的故事進行評注:“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于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于直不直,何暇計哉?’”②朱熹將父子相隱視為天理統攝下的人情之至,父子相隱是正直的體現,正直的做法是順應天理的,而天理蘊含在個人順應自然情感流露而做出的合乎情理的舉動之中。顯然,朱熹承認“親親相隱”具有合理性和價值,這是合乎個人情感和價值的行為。
總之,從儒家倫理思想的開始,對于“親親相隱”就具有了理論支持,這種理論支持是與其體系架構密切相關的,是由宗族血緣關系延伸至社會關系的理論思想決定的。這種思想只是把人作為構成宗族倫理道德的分子,顯然具有個人價值的消解的因素,但這也說明它并不忽視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中的人的情感體驗和倫理需求,因而體現了儒家的“德治”思想。
二、傳統儒家體系的近代困境
近代以來,個人的價值逐漸得到重視,“我”逐漸取代“宗族國家”成為倫理構建的主流。以宗族血緣關系為紐帶建立社會關系的儒家倫理制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理論困境。
近代傳入的西方思想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思想,其倫理價值體系與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結構全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第一,自古希臘羅馬時代,西方便以法律為規范個人行為的工具。自先秦時期,中國便以道德作為規訓個人行為的工具,后期的法律也依道德而建,因此中國古代的第一行為準則是道德。第二,自啟蒙運動興起,西方民主就注重個體價值的發揚與個人權利的維護,而近代中國仍然以宗族家庭作為其倫理體系的細胞,個人并不作為獨立的因素被重視。因而近代時期,中國經濟在被動工業化的同時,傳統文化也難以適應新情況并出現新問題,因而中國傳統思想也處于弱勢地位,尤其是“三綱五常”制度成為當時一些知識分子抨擊的對象,而作為與儒家倫理學伴生的“親親相隱”也隱沒于歷史之中。
近代知識分子尤其深受西方思想熏陶的知識分子對儒家“親親相隱”展開了猛烈的抨擊,認為“親親相隱”是導致不平等的根源。因而學者就“親親相隱”展開激烈爭論。但是,無論如何辯駁,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那就是儒家倫理架構已經存在于中國土壤中數百上千年,且即使到今天,中國人的骨血中仍然容納著儒家傳統的倫理內容。此外,導致不平等的原因必然是多樣的,這樣一來便出現了矛盾,那就是“親親相隱”即使到今天也是可以解釋的存在,但當今的法律制度也無法為“親親相隱”安排恰當的位置。簡言之,即是當代法律與家庭倫理之情的沖突。然而實際上,“親親相隱”在現代社會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倫理的融合方面,還是在現代社會法律的建構方面,抑或是在家庭情感的考量方面,仍然具有可以改造發展的可能性。
三、現代倫理體系的建構與“親親相隱”的改造
現代倫理體系主要依賴馬克思主義建立起來,馬克思把人定義為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而儒家的親緣關系與馬克思主義社會關系中的人的定義有一定聯系,因而從馬克思主義的倫理架構出發可以與“親親相隱”的適配度展開探索,最后根據現代社會的需要對“親親相隱”進行社會化改造,使其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
馬克思對人的定義展開了深入的探討。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前人關于“人”的定義的各種缺陷。對鮑威爾“自我意識”附屬品的思想,他們指出“德國哲學仍處于束之于天國之內而未曾降至人間的困境中”①;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批判了費爾巴哈對人的定義:費爾巴哈只在感性范疇內承認“現實的、單個的、肉體的人”②;對施蒂納“唯一者”的思想,他們認為那仍是純粹思想的存在,“他認為歷史的進程必定只是騎士、強盜和幽靈的歷史,他當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擺脫這種歷史的幻覺而得救”③。其次,他們提出了真正人的定義的具體內容。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是現實的個人,是自然的人,是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的人,是處于社會關系之中的人,是在歷史中不斷發展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是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表述:“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④,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其進行了更深層次的探討,得出了“現實的個人”是處于社會關系之中的人的結論。
儒家倫理體系中的人與之有一定的相似性,儒家倫理體系中的人也是處于社會關系之中,但二者有極大不同。首先,儒家倫理體系中的人是以宗族血緣為社會關系中的人,而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人則是以物質生產為社會關系中的人。其次,儒家倫理體系中的宗族觀念消解了個人價值,隱匿了獨立的個人的存在。但馬克思主義則不然,馬克思主義是在肯定個人價值的基礎上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進而發展出社會關系。再次,儒家倫理體系就人與人的關系強調尊卑等級的社會秩序,而馬克思主義以物質生產勞動為基點構建的社會關系則注重強調人人平等。總而言之,儒家倫理體系中的人與馬克思主義對人的定義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又有極大不同,要想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對儒家傳統倫理觀進行改造,就需要對此問題進一步探索。
既然人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那么人就不可避免對較為親密的社會成員有豐富的情感,而這也使得他們面對客觀事實會產生偏袒、維護等行為。在現代社會中,倫理體系和法律制度的建設既要依賴公平,也要考慮人類情感的體諒。因此,“親親相隱”的改造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要維護社會公平,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要考慮加害者家屬的心理感受。這既是相關制度的完善,也是中國自古以來一以貫之的“德治”的體現。
四、結束語
“親親相隱”是儒家倫理體系建構的一大產物,是儒家以親緣關系為主題建構社會封建倫理系統的證明。盡管這種倫理制度已經過時,但其關于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體諒既是中國一以貫之的“德治”的彰顯,也是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親親相隱”從歷史角度體現了社會的人文關懷,促進了儒家“王道”思想的發展;從現實角度契合了馬克思主義對人的定義,維護了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的穩定性。因此,“親親相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造是既有歷史意義又有現實意義的一項課題。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
作者簡介:尚雙(1999—) , 女,漢族,山東泰安人, 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