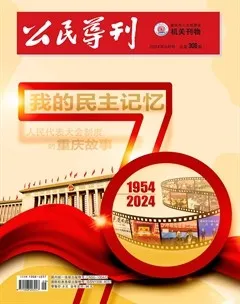陪診師,這個“臨時家屬”需正名

去哪里掛號、在哪里就診、到什么地方繳費……面對迷宮一般的醫院和復雜的就診流程,你是否會感到不知所措?對于一些人來說,獨自看病不僅僅孤獨,更多是無助。
近年來,我國職業陪診服務需求日益旺盛,陪診服務在提升患者就醫體驗、緩解醫療資源緊張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
但因陪診師的從業資質、服務流程、收費標準等缺乏明確界定,以及由此帶來的服務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讓這一新興職業在逐漸進入大眾視野的同時,也伴隨了越來越多諸如“臨時家人”“換湯不換藥的黃牛”等爭議。
作為潛力巨大的就業方向,陪診師為何會存在諸多亂象?行業未來該如何發展?
8月26日,人在貴州省遵義市的李平預約了西南醫院的中醫與風濕免疫科專家號。
就診當天,李平通過社交平臺購買了“代問診”服務,全天服務價格為399元。誰知在他付款后對方又表示,如果需要代取報告、代郵寄,則要另行加收服務費。
為了不讓前期投入的費用“打水漂”,李平只能按照陪診師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加錢,以確保自己能夠順利就診。
“感覺自己被套路了!”李平在社交平臺上表示。
李平的遭遇并不是個例。
今年5月,家住重慶市沙坪壩區的王女士預約了新橋醫院的無痛腸胃鏡體檢,并通過社交平臺聯系到一位陪診人員。
然而,支付完100元定金,她卻被對方直接拉黑,只得獨自前往醫院就診……
作為近年來的新興職業,陪診師被視作有效緩解獨居老人、行動不便患者、異地就醫患者等群體就醫困境的有效補充。
但現實并沒有設想的那么美好。
陪診服務宛如“開盲盒”
為了給年邁的母親尋找一名靠譜的陪診員,陳玉潘傷透了腦筋。
陳玉潘是家中獨女,在上海從事外貿工作,很難照顧到獨自在重慶生活的母親。
前幾年,疾病接二連三地襲擊了陳玉潘的家庭。
2021年冬天,陳玉潘的父親在一場高燒之后,因并發癥去世。緊接著,陳玉潘的母親又在上樓梯的時候突然摔倒,送醫后被查出患有輕微腦梗。
陳玉潘本想接自己的母親去上海生活,但其母親因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同等現實因素,仍獨自留在重慶。
“我前幾天打電話回家,聽到她一直在咳嗽,才曉得她感冒了。”母親身體有恙,讓身處外地的陳玉潘非常緊張,她擔心母親因感冒引起并發癥,堅持要求母親去醫院就診。
但是陳玉潘母親覺得感冒是小病,沒有必要去醫院。在陳玉潘的再三勸說下,她才勉強答應。
考慮到母親患腦梗后行動緩慢,身體也比較虛弱,陳玉潘想找一位陪診師,接送母親到醫院,并協助完成各項檢查。
然而,找一位合適的陪診師,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陪診師主要工作職責包括協助患者辦理就醫手續、陪同患者就診、提供醫療咨詢和建議、協助患者與醫護人員溝通以及關注患者病情變化等。
“我一問才發現,許多陪診師,都是年輕的小姑娘在做兼職。她們要么沒有相關證書,要么不愿意上門接送,要么就是沒有照顧老人的經驗,我擔心老人在看病過程中,遇到需要協助的地方,她們處理不了。”陳玉潘說。
最終,有一位陪診師的條件勉強讓陳玉潘感到滿意。
這位陪診師表示,自己持有護士證,還有急救證,有三年多陪診工作經驗,但是服務費用也增加了許多——半天的服務,需要陳玉潘支付500元。
就在陳玉潘即將下單的時候,這位陪診師表示自己可以幫忙獲取預約已滿的專家號。
這種類似于“黃牛”的行為讓陳玉潘很反感。猶豫再三,她放棄選擇這位陪診師。
“錢只是一方面。最關鍵的是,我發現自己沒辦法僅憑網絡上發過來的護士證和急救證照片,就把老人交給這樣的陌生人。如果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呢?”陳玉潘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記者在小紅書、大眾點評等平臺搜索發現,以個人、機構等名義提供陪診服務的賬號或商家不在少數,但在服務人員資質、定價、內容等方面存在差異。
部分陪診師稱自己是醫學生或護士,但以涉及隱私為由,拒絕提供相關學歷、從業證明。
這就導致消費者在選擇陪診服務時,宛如“開盲盒”:大家并不知道,自己選擇的陪診師是否能夠提供合適的服務。
陪診市場亟待規范
在老齡化趨勢加劇及醫療需求多元化的背景下,職業陪診師行業在重慶市乃至全國范圍內迅速崛起,成為醫療服務領域的一股新興力量。
然而,這一新興行業的快速成長也伴隨著諸多待解問題。
據了解,目前陪診師行業主要遵循中國老年醫學學會發布的《老年陪診服務規范》、中國醫藥教育協會批準發布的《陪診師職業技能規范》等團體標準,專門針對陪診師行業的法律法規體系尚不健全。
另外,陪診師行業的主管部門尚未明確。
衛生健康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以及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參與行業監管與服務指導,管理職責歸屬模糊,多部門共同參與但缺乏統一管理,導致監管效能有限。
此外,相關技能培訓體系也不統一。雖然各地政府部門聯合高校、協會、陪診機構等積極組織小范圍的陪診師職業技能培訓,但覆蓋面和深度仍顯不足。
目前絕大多數陪診師都是在社交平臺上獲得訂單,而游走在互聯網上的陪診師專業素質更是良莠不齊。
消費者最關注的服務價格也缺乏統一標準。一二線城市普遍為半天300元到400元、全天500元到600元,三四線城市一般是半天200元、全天400元。
“缺乏統一標準規范是目前陪診行業的一大痛點。全國統一的行業標準尚未建立,加上通訊工具特別發達,難以杜絕市場亂象。”專業醫療陪護機構“佑倍護診”重慶負責人張丹表示。
“一個男生打算做陪診小程序,于是接單體驗,視頻點贊量有900多。”張丹看得十分難受,“一群外行人來湊熱鬧,把行業攪得很渾。”她注意到,不少陪診小程序并非由有經驗的陪診師管理,“誰都可以開發個平臺,讓各地兼職陪診師入駐。”
張丹表示,自己供職的這家陪診平臺招聘陪診師時,有完整的審核流程,持有護士證的人才可以申請入駐,還要進行筆試、面試考核和陪診培訓。
面對行業現狀,張丹建議,專業的陪診公司應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內部自律,規范陪診師的行為,加強專業化培訓。
立法規范行業發展
“陪診師尚未被正式納入國家職業分類體系,缺乏明確的監管框架和標準,行業亂象頻發,建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根據陪診師行業發展趨勢與從業人員規模,適時推動陪診師職業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確立其法律地位。與此同時,制定專項法律法規,明確主管部門、服務范圍、服務流程、資格要求、收費標準及監管機制,為行業健康發展提供法律保障。”針對目前陪診師行業現狀,市人大代表、上海中聯(重慶)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陳卓建議,應明確陪診師的職業分類與法律地位。
陳卓還建議,相關職能部門加大對非法陪診行為的打擊力度,實施嚴格的監管,建立陪診師實名注冊與持證上崗制度,確保從業者具備必要的專業素質和職業道德。
而針對市場上存在的培訓機構培訓質量參差不齊和虛假宣傳的現象,陳卓表示,可以設立國家級或省級陪診師培訓與認證中心,統一制定培訓大綱和考核標準,并加強對培訓機構的資質審核和教學質量評估,確保培訓內容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同時,引導和鼓勵培訓機構加大在員工培訓方面的投入,提升行業整體服務水平。
可喜的是,一些省份已經開始對規范陪診服務進行探索。
從2020年起,浙江省的浙大二院、浙江醫院等多家醫院先后推出公益陪診服務。
2023年2月,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醫院開通公益陪診服務熱線,組建了一支由醫務社工、醫護人員和基層志愿者聯動的陪診團隊;2023年9月,首屆上海養老服務陪診師培訓啟動,面向各社區為老服務工作人員;2024年3月,上海市首批575名參訓學員經培訓考核合格后,獲得由上海開放大學與上海市養老服務行業協會共同頒發的“上海養老服務陪診師”證書,這標志著上海市首批陪診師已持證上崗。
重慶市二級及以上綜合醫院也在積極開展志愿陪診服務。
有數據顯示,截至目前,重慶市已有129家醫療機構實施了就醫“一站式”服務,該服務集成了咨詢、掛號、繳費、取藥等多個環節,能為患者就醫提供更多便利。
相信在各方力量的努力下,陪診服務會愈加規范,實現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