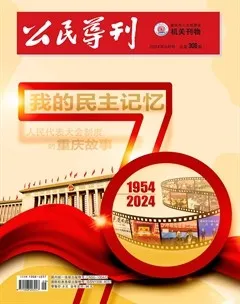網絡立法 時代大潮中的制度變遷
1994年,當中國全功能接入國際互聯網、迎來信息革命浪潮之時,恐怕無人能夠預見,30年后的中國已成為全球網民數量居首、數字經濟規模第二的網絡大國。
從風起云涌的互聯網經濟,到無處不在的數字化生存,深刻影響了政治、經濟、社會生態,也重塑了尋常百姓的生活方式。
具有“雙刃劍”性質的互聯網,創造了時代的紅利,也滋生了莫測的風險。
與傳統治理相比,網絡的虛擬性、開放性、交互性等特質,又使網絡治理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立法作為法治的基礎,更需承擔起揚善止惡的制度功能。
30年前,中國與互聯網初逢之時,幾乎同步出臺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就拉開了網絡立法的大幕。時至今日,網絡領域各層級立法已達150多部,構建起了初步成型、相對完備的網絡立法體系。
網絡立法不斷成熟的演進史,與互聯網波瀾壯闊的發展史共生共長,塑造了一道獨特的時代風景。
30年來,網絡立法,開拓了逐步多維化的方向。
從接入互聯網的初始歲月,到PC互聯網階段,再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網絡風險從早期的黑客攻擊、盜版軟件等問題,逐漸演化出網絡謠言、網絡欺詐、網絡暴力、信息污染、算法濫用等亂象,網絡立法的視野隨之不斷擴展至打擊網絡犯罪、維護網絡安全、規范網絡服務、監管網絡市場、化解網絡糾紛、凈化網絡空間等多維目標。
與此同時,網絡立法形態也從側重刑事立法轉向刑事、民事、行政立法多維齊驅,制度架構亦從側重局部的單向施策日益轉向立足全局的綜合治理。由此彰顯的,正是直面挑戰、全面破題的立法擔當。
30年來,網絡立法留下了不斷精細化的足印。
網絡立法從無到有、由少到多,既有宏觀的新制創設,更有微觀的細節鋪陳,共同孕育了血肉豐滿的立法風貌。
比如,隨著網絡市場的持續壯大、網購等消費形態的日益普及,修改后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確立了網購“七日無理由退貨”等制度,修改后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分別增設了“互聯網專條”和“平臺禁令”。而較低層級的立法,尤其是出臺速度快捷、應急功能強大的部門規章,更是深入了具體至微的治理議題。
從餐飲外賣、網上售藥的安全隱患,到價格欺詐、虛假促銷的網購風險;從“好評返現”“流量造假”的劣質競爭,到“自動續費”“大數據殺熟”的消費陷阱……種種危及市場秩序、侵蝕消費者權益的亂象,無不冒頭不久即遭到網絡立法的有力阻擊。由此彰顯的,正是緊盯焦點、精準治理的立法思維。
30年來,網絡立法,見證了日趨專門化的歷程。
一方面,通過嵌入“制度補丁”的方式,傳統立法持續注入“網絡”因子,諸如民法典對數據和虛擬財產作出原則規定、刑法修改不斷增設網絡犯罪新罪名等等,都標示著傳統立法對接互聯網時代的努力。
另一方面,更多為網絡量身訂做的制度規范,則以專門立法的形式源源產出,且立法位級逐漸提高。
比如,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出臺的“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以“決定”這一特殊立法形式滿足了網絡治理的急迫需求,但也足見彼時網絡專門法律的匱乏。
其后,以2016年為起點,僅僅六年時間,網絡安全法、電子商務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接踵而至,或著力網絡基礎制度,或劍指網絡治理難點,不斷提升著網絡專門立法的高度。
而已經列入立法規劃的數學經濟促進法、網絡犯罪防治法等等,更預示著這一進程方興未艾。由此彰顯的,正是制度升級、系統構建的立法前景。
走過而立之年的網絡立法,已積淀了豐厚的制度成果。但作為新興的立法領域,仍需在填補立法空白、提高立法位級、強化立法前瞻等方面快馬加鞭。尤其是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運用,更是對網絡治理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面對互聯網發展的快速迭代,網絡立法已站到新的歷史起點,只有堅守以人為本的價值立場,力促技術向善的制度變革,并尋找到平衡發展與安全、促進與治理、創新與規范、自由與秩序等深層次問題的最大公約數,才能守護好飛速前行的數字經濟,守護好良性健康的網絡生態,守護好信息時代的公民權利,也才能沿著法治之軌,從網絡大國一步步邁進網絡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