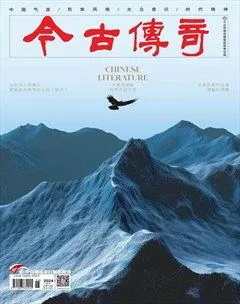天開大冶:對一個千年古縣的文化速寫

江湖之表,山川包絡,形氣涵蓄,寶藏興焉。
——虞集《大冶縣儒學記》
講大冶地區的文明史,通常會從石龍頭遺址說起。但二三十萬年前的遠古時代的“人”是什么樣子,他們能做什么,做過什么,我們并不明了。除了勞動工具,他們沒有留下物質形態的成果,更不用說精神或思想。鑒于此,我們對大冶歷史文化的關照,只上溯到礦冶肇始之際。
《越人歌》與鄂王城
大冶地區誕生的第一件藝術品,竟然是一首歌。
歌曲的作者是一個越族人,歷史上的匆匆過客,只留下聲音,連背影都模糊不清。但是,我們應該感謝他,為大冶早期的歷史增添了浪漫而精彩的一筆。
在大冶金牛鎮鄂王城村的胡彥貴灣,有一處古代城池的殘留,它就是鄂王城遺址,村因此得名。
《史記·楚世家》載:“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春秋時強盛起來的楚國共滅了有封號的小國計五十一國,鄂為其中之一。熊渠滅鄂,并入楚地,他不滿周王對其封爵過低,自立為楚王,并封其次子熊紅(熊摯紅)于鄂,是為鄂王,其都城便是鄂王城。
有論者考證,鄂王城可能一度作為丹陽之后的楚國國都。北宋政和三年(1113),武昌太平湖發現一批青銅器,其中有“楚公逆镈”。這個“楚公逆”,即是楚國國君熊咢(前800—前791年在位)。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夜雨楚公鐘跋》中專有一節關于楚國都城的文字:“夜雨楚公鐘……楚世家言熊繹居丹陽,至文王熊貲始都郢,中間無遷都事。惟言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卒,子熊摯紅立,后六世至熊咢。今熊咢之器出于武昌者,武昌即鄂。蓋熊渠之卒,熊摯紅雖嗣父位,仍居所封之鄂,不居丹陽。越六世至熊咢,猶居于此,故有其遺器,楚之中葉曾居武昌,于史無聞,惟賴是器所出地知之耳。”研究者延伸此說,認為“楚國在鄂王城建都時間大約為89至116年”。楚國遷都至郢后,鄂王城作為鄂君的封都仍存。熊紅是楚之鄂國的第一位國君,時稱“鄂君”,死后被國人作為神供奉,稱“鄂王神”。
由于地緣優勢,在史前和先秦時期,今鄂東地區,特別是今大冶地區為南北陸上通衢、東西黃金水道,故歷來為部落、族屬及諸侯國的匯聚之地。大體說,有原部族文化(或曰土著文化)、三苗文化、揚越文化、中原文化、吳越文化、吳楚文化等聚合融匯共存。
三苗解體以后,此地成為鄂東南揚越的組成部分,人員成為東鄂的先民。他們在繼承石龍頭文化、三苗文化、揚越文化的基礎上向新階段發展。大量商周礦冶遺址、文化遺存反映了之前的本地文化因子。西周初穆王東巡至九江,中原文化的影響就及于該地區,特別是西周熊渠東擴帶來了楚文化,更促進了地區多元文化的融合。
首任鄂王熊紅之后,人們僅知道三位鄂王。一位是前文提及的公元前800年接任楚國國君的熊咢;另兩位,則是春秋時期的鄂君子晳和戰國時期的鄂君啟。前者見于漢朝人的著作,后者因文物出土而知名。
鄂君子晳,又名子晰、公孫黑、黑肱、駟化等,是楚共王(名“審”,前590—前560年在位)的第四個兒子。楚共王無嫡子,只有五個庶子,按長幼順序為:公子招(楚康王)、公子圍(楚靈王)、子比(新楚王)、子晳(令尹)、棄疾(楚平王)。為爭權奪利,楚國王室成員之間展開了血腥殺戮。楚靈王為篡位,將屠刀對準兄長、侄子、侄孫。子比、子晳、棄疾三兄弟后來攜手對抗楚靈王并獲成功。子比成為新國君,子晳為令尹,即僅次于國君的二號人物。
子晳的事跡沉睡于史籍,因他一次偶然出游而誕生的《越人歌》,卻穿越幾千年的歷史風煙,流傳至今。
《越人歌》首見于西漢劉向《說苑》卷十一《善說篇》中莊辛所說的一段話。該篇在敘完《越人歌》的故事后,記云:“鄂君子晳,楚王親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莊辛系楚莊王后裔,因以莊為姓。他曾用計收復淮北之地,得封陽陵君。莊辛在勸說襄成君時,說:“君獨不聞夫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芮芘(兩種草名),張翠蓋,……榜枻越人擁楫而歌。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于是乃招越譯……于是鄂君子晳乃榆修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這首春秋時期的民歌,因對字義的理解不同,致有多種解讀和譯文,以下譯文得到較多認可: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悅君兮君不知。
無論是對大冶而言,還是對中國而言,《越人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從社會學層面考察,它是早期大冶地區社會活動的真實記錄;它反映了越族先民大膽表達感情的民風民俗;它還表明,盡管諸侯國屢屢刀兵相見,但不同民族、普通百姓聚居雜處,也曾和諧共生、友好往來。從文學層面考察,它是我國絢麗多彩的古典文學園圃里的一朵奇葩,是我國最早的文學翻譯作品,是《楚辭》的藝術源頭之一,與《詩經》甚至有相同的語言,如《詩經·唐風·綢繆》:“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梁啟超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中高度贊譽道:“越女棹歌……在中國上古找翻譯的作品,這首歌怕是獨一無二的了。”
如果說,鄂君啟節是研究我國歷史上戰國時期楚國(當然包括大冶)交通、政治、軍事、經濟、地理、賦稅制度、符節制度、楚王與封君的關系等的重要文物文獻依據,那么也可以說,《越人歌》是研究先秦時期大冶地區政治、社會、文化、風俗的重要歷史文獻和藝術品。
東方朔與講堂廟
東方朔在大冶民間具有相當大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漢書》有傳70卷,涉及數百位名公巨卿,其中只有15人單獨立傳,東方朔是其中之一。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引者按:今山東省德州市陵城區)人。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東方朔上書自薦。事實證明,他的確是天下罕見的奇士。
東方朔能言善辯,詼諧百出,常妙言進諫,折服圣上。《史記·滑稽列傳》有西漢褚少孫補寫的東方朔傳,篇幅遠遠少于《漢書·東方朔列傳》(前者1000余字,后者7000余字)。《史記》之朔傳,重性情刻畫而略智諫之事;《漢書》之朔傳,則詳寫其諫阻皇帝之事,人物形象更為豐滿,故事也十分精彩。東方朔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他樹立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諫臣形象。其次,他性格詼諧,機智過人,樹立了一個超級智者的形象。其三,東方朔是西漢有名的文學家之一。第四,東方朔是隱逸文化中“大隱”的發明人和實踐者。
那么,東方朔這樣一個偉大而神奇的人物,怎么與大冶有了關聯呢?
據說“三楚第一山”東方山就是因東方朔而得名。南朝梁代人顧野王《輿地志》六之《山川》一:“東方山在縣北三十里。”這是現今可見的史志中關于東方山的最早記載。王象之成書于南宋中期嘉定、寶慶間(1208—1227)的《輿地紀勝》載:“東方朔讀書堂在大冶縣東方寺。”則是現存史志中將東方朔與大冶聯系起來的最早記載。而最早在文學作品中將東方山與東方朔聯系起來的,是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狀元王十朋,其《題宏化寺》詩曰:
大冶迢迢接武昌,西征逾月到東方。
白蓮智印蟠桃朔,仙佛同歸一道場。
詩中的“白蓮智印”指東方山唐代開山祖師智印和尚及東方山八景之一“白蓮頻開”;“蟠桃朔”則是指東方朔及其成仙后在天庭偷摘蟠桃的故事;東方山既是禮佛之地,又是修仙之地,故稱“仙佛同歸一道場”——這是東方山絕好的宣傳口號。
大冶建縣前,其地分屬永興、武昌二縣,為南唐屬地,自無專志;建縣以后、明代以前志書均已亡佚;明代至清末共十次修志,其中明代四次,清代六次。最早的志書修于明成祖永樂十五年(1417),最晚的修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刻于光緒二十三年。現存舊志中,關于東方朔的記載并不少見。
相傳東方朔曾來大冶游歷,并在此讀書、講學,而且他的兩個兒子靈子、妙子也有讀書堂。明嘉靖《大冶縣志》(嘉靖十九年/1540)之“流寓”類首即東方朔,稱朔“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又說,“然舊志載游寓于此,曰東方山、曼倩山、講堂山。其二子曰靈子、妙子,有書堂,今亦以書堂名山,意者周游方外而隱于此耶?”可知明之前舊志已經將東方朔與東方山等山之得名聯系起來。又載:“東方山,在(大冶)縣治北三十里。世傳東方朔寓此,故名。入《一統志》。”《一統志》指李賢、彭時等纂修、成書于天順五年(1461)的《大明一統志》。這里對東方朔寓居東方山之說,冠以“世傳”二字,未作肯定,亦未作否定。至清康熙大冶縣志關于東方朔的介紹與明代相同,唯添了一句話,“又江夏東山書院為朔讀書處”。這一信息大約是采自《一統志》。東山書院,明成化年間(1465—1487)創辦于武昌黃鵠山東,相傳為東方朔讀書處。關于東方山得名,康熙《大冶縣志》稱:“實為武昌東界,故曰東方。俗傳東方朔隱處,而刊諸石,謬矣。”然而,以地理方位論,東方山在武昌之南而非東方,故此說不確。
大冶一地,與東方朔有關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除東方山之外,還有蓮花山、棲儒橋、講堂廟、靈妙書堂、靈子寺、妙子洞及妙子洞泉。這些景觀,幾乎全集中在離城區不遠的金湖街道境內,而以靈峰山為中心。還有個村莊叫金曼倩,正在靈峰山麓,據說其村民是東方朔后裔。明嘉靖《大冶縣志》載:“東方朔讀書堂詳見‘書院’(見府志)。”又載:“蓮花山,在縣治西南三十五里,世傳東方朔游觀之所。妙子洞,在縣治西三十里,即東方朔之子隱處也。”“書院”條下有“東方朔講書堂”:“縣治西二十里靈峰山。世傳東方朔講書于此,古基存焉。靈妙書堂,縣治西南四十里,世傳東方朔二子曰靈子、妙子,于此讀書,故名其山曰書堂山。”康熙《大冶縣志》“書院”類亦載:“讀書堂,在靈峰山,有石屋焉,云東方朔讀書于此。”
如今,靈峰山仍巍然聳立,棲儒橋老橋幾度興廢(新橋建于1965年,2014年修葺),靈妙書堂、妙子洞之類已失所在,但靈峰山上的讀書堂遺址仍存,講堂還在,而且成為廟,香火仍盛。
講堂廟位于靈峰山東南方的一片平疇沃野——金湖街道優先村講堂畈,其地古屬講堂堡,距靈峰山約兩公里。嘉靖《大冶縣志》載:“講堂廟,在縣治西南二十里,廟之創始不詳何代。”清同治《大冶縣志》載:“明成化七年(1471),知縣常安、鄉官禮部郎中周宗智偕士民捐資重修,鄉官懷寧縣丞胡貢捐金龜山一段,上至頂、下至田,左右塹界。并勒碑殿前,今猶存。”事實上,這塊碑至今仍存于講堂廟中,其正反兩面各有碑文一篇,除個別地方文字剝落,碑石略有損傷,文字幾乎全可辨認。碑文可與同治縣志的說法相互印證。講堂廟屢建屢毀,有據可考的就有6次,可謂多災多難,歷盡滄桑。
大冶民間傳說中的東方朔,與正史中的東方朔有所不同,他是作為一個儒者、智者和文化傳播者活在人們的記憶中。東方朔講書,是大冶教育的最早記錄,開大冶地區民間教育之先河。其開創的講學之風,澤及后世。唐代江水清于其地講學授徒,宋代名儒萬止齋在大冶宮臺山設書堂講學,至清末民初,講堂堡柯隆純捐田一石,于講堂興辦義學。千百年來,大冶斯文不墜,士人輩出,除官辦書院學堂,尚有龍川書院、金湖書院等。棲儒橋、讀書堂、講堂這些地名,反映了老百姓對作為儒士和講師的東方朔的尊敬和認同,和對文化、教育的敬畏。
東方山主體部分,由三座相連的山峰組成,分別名為走馬坪、曼倩垴、覽勝垴,其曼倩垴即以東方朔之字命名。今東方山走馬坪西麓建有東方朔書院,曾為學堂,1957年學堂遷至山下,原址建海會寺,2003年其中一部更名為智圣殿,以紀念東方朔。在東方山的背面山麓(今屬鄂州岳石洪村),建有東方寺。東方朔以這種奇特的形式融入了宗教和教育活動,融入了百姓的精神生活,他對古代大冶地區的文化教育的影響,實在不可等閑視之。
尖山大王與陳九仙
中唐以后,藩鎮坐大,各據一方,互相攻略,兵寇橫行,民不聊生。地方為自保,便在正規軍之外,招募本地百姓為民兵,平時務農,戰時從軍。此即土團,亦稱土團軍。土團軍初為地方民兵武裝,至五代時期,逐漸演變為割據勢力。
黃巢起義軍轉戰江南后,永興(今陽新)百姓紛紛響應。鄂州(治在今武漢)刺史崔紹招募百姓之強雄者,組成土團軍。天祐二年(905),楊行密部將攻克鄂州,后建立吳國,史稱楊吳。楊行密之子楊溥死后,南吳之地,盡為南唐所有,永興、武昌(今鄂州),均為南唐轄地。
幾十年過去,天下大小變亂此伏彼起。永興、武昌邊界地區兩支小規模的土團軍逐漸崛起。他們的頭領雖然不見于正史,卻在民間流傳至今。一支土團軍的頭領名叫王文蔚,祖籍江州都昌縣。王文蔚生長軍中,讀書不多,隨父征戰,慣歷沙場,終成一員驍將,受命鎮守永興北境。其地屬安昌鄉,東西北三面與武昌縣為鄰,四圍群山聳峙,中間為平原沃野,僅有數處峽口出入。古時曾有城,因戰亂而廢,人稱古城里,訛而變成果城里。
王文蔚進駐果城里后,約束部伍,安撫流亡,使地方重現生氣,頗得百姓愛戴。他選中巍峨峭拔的黃茅尖山,勒兵退出村鎮,于山頂安營扎寨。另一支土團軍的首領姓陳,人稱陳九郎,生平不詳,南唐之際割據武昌、永興之交的山區地帶,率土人筑寨自保。經過長年爭奪,永興北部只剩下王文蔚和陳九郎兩支地方武裝。
果城里大致以馬嶺山為界,山南為內果城,山東為外果城。王文蔚據守內果城,以白石巖、屏風峽、黃茅尖山為核心根據地;陳九郎據守外果城,以南山、北山、花楢樹為核心根據地。王文蔚與陳九郎轄地相鄰,時生沖突,互有勝敗。
某日,王文蔚率部巡山,與陳九郎在下馬硔遭遇,雙方發生激戰。陳九郎戰敗,王文蔚窮追不舍。陳九郎藏身大泉洞,饑寒交加,又兼傷重感染,倒斃洞中。其尸體被水沖出,沉于山溪港。適逢兩個漁人捕魚,收網時感覺十分沉重,起網,見陳尸,大驚失色。二人為陳九郎轄下部民,曾受其恩惠,就偷偷將陳尸抬到溪港下游,仍沉于水,希望其隨水沖走。第二日,二人繼續回原地打魚,一網下去,竟然再次撈起陳九郎尸體!二人再次將其運到下游,而且比前一次更遠。奇怪的是,兩天以后,他們又一次在上游撈起了陳九郎。
這詭異的消息不脛而走,土人大嘩,結隊往觀。時逢酷暑,數月無雨,禾稻皆枯,眾人百計求雨,終無響應。有一老者忽發奇想,將陳九郎遺體置于洞口古樹下,率眾焚香禱告:“大王如有靈,請降雨解除旱疫,我等定當設廟,世世祭拜!”翌日,天降大雨,莊稼得救了,民人信守諾言,即以塘泥糊裹陳之遺體,于大泉洞口之側,建一小廟供奉之。其后逢天旱求雨,或無嗣求子,屢有應驗。人們相信,陳九郎生前保衛地方,死后亦護佑百姓,因此尊稱其為陳九郎仙、陳大仙。久之,原陳九郎統轄之民,亦為王文蔚收服,一境初安。朝廷以其有功,封王文蔚為銀青光祿大夫。
宋開寶八年(975),宋軍攻破江寧,南唐滅亡,王文蔚亦隨之歸順,因人心久服,朝廷仍命其鎮守舊地。是時,大小山賊仍存,南蠻余部繼續為害,王文蔚盡心捍御,以次清剿,平定內亂,使得果城里地區維持著相對的安寧,當地百姓為其建生祠,以示感戴。北宋咸平(998—1003)初,王文蔚以老疾終于任所。官府順應民心,挑選一塊背崗臨水之地,作為其長眠之所。
后來,當地百姓集資,在山寨原址修建了一座簡易殿堂,泥塑土主像一尊,一境之人,歲時祭祀。土人稱王文蔚為尖山大王,又稱土主老爺,視為地方保護神。土主崇拜,由敬奉恩人,逐漸演變為既感恩,又許愿。
內果城的百姓記住了尖山大王王文蔚,外果城的百姓則懷念著陳大仙陳九郎。人們將大泉洞口小廟擴建為陳九仙廟,并將大泉洞稱為陳九仙洞,后漸呼為龍泉洞。大仙廟變名為龍泉寺,至今尚在。
春秋代謝,歲月更迭。土主老爺屢次顯靈保佑人民。據說,南宋建炎初,金朝名將兀術率軍南侵,遇土主之神兵阻擊,由興國轉趨洪州,大冶得以保全。此時,土主老爺已經升級成菩薩,與觀音比肩而坐,同受膜拜。果城里逐漸形成一個專為紀念土主的節日,每年接土主下殿、巡游、上殿,案主即山主、六團、十八大姓。土主會與陽新民俗“接大王”、大冶民俗“接太公”既相類似,亦有區別。最大的不同在于參與者的范圍,“接太公”只限一姓同宗,“接大王”只限李、徐、黃、費、何五姓,而參與土主會則多至40余姓,看熱鬧者成千上萬,不可勝數。
我為什么要如此詳盡地述說尖山大王與陳九仙的故事呢?非為獵奇談玄,而是因為,大冶建縣較晚,無論是正史還是野史,關于其宋代以前包括隋唐、五代及更早時期的記載都極少;大冶先民在經年戰亂和天災中所剩無幾,今人之先祖多是明初才遷來,惟果城里原住民稍多;王文蔚和陳九郎的傳說,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南山區的整體社會狀貌和不同族群為人口、田地、水源等資源而博弈、爭斗及分裂、統一的歷程,為豐富大冶的歷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佐證。
青山場與大冶縣
大冶自設立至今,一千余年來,縣名未變,縣治未變,經中國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2017年第二次“千年古縣”專家會議鑒定,確認其為中國地名文化遺產千年古縣。
大冶設縣,在于其具備獨特的資源秉賦。
唐末五代之際為亂世,對兵器的需求量大增,鑄錢亦需大量銅鐵。唐天祐二年(905),武昌軍節度使秦裴在永興縣青山開采鐵礦,并設青山場院,作為專門管理鹽鐵及采煉銅礦的機構,進行大規模的采煉。《九國志·秦裴傳》載其“在治七年,積軍儲二十萬,開青山大冶,公家仰足”。
青山場院是大冶建縣的“基本盤”,可以說,沒有青山場院,就沒有大冶縣。清同治版《大冶縣志》卷之二《山川志》載:“青山,在縣西,距城十里,舊設青山場,故名。”1990年新修《大冶縣志》據此稱:“青山場,在縣城西5公里,銅綠山附近的青山,山呈東北走向,黃色黏質土壤,蘊藏著豐富的銅、鐵礦。昔年山上長滿樹木,一年四季,綠樹成蔭,故名青山。”我們實地考察發現,青山在大冶城區以西5公里左右,包括今大青山、青山、銅綠山等連片丘陵,分布在今金湖街道境內的株林村、銅山村和銅綠山礦社區等地;而青山場院,則在今大冶市區老街,是青山場采冶活動的管理機構。
還有一個問題:為什么是青山場院?李璟建大冶縣,主要原因是青山一帶的銅鐵礦藏十分豐富,可煉銅鑄造錢幣,冶鐵鑄造兵器,此二者都是戰略物資。
據馬令《南唐書》卷三十《建國譜》,南唐國勢在保大十四年(956)因周世宗柴榮武力步步進逼而轉衰。在這之前,937年滅吳(秦裴所創辦的青山場院歸唐所有),945年滅閩,951年滅楚,南唐軍隊一直打進潭州(今長沙)。此時,南唐地跨今江西全省及江蘇、安徽、福建、湖北、湖南的一部分,人口約500萬。青山即春秋時期采礦煉銅之處,其地蘊藏有豐富的銅礦,周邊鐵山、白雉山等地又有豐富的鐵礦。
南唐國主李璟升青山場,并劃武昌縣的三個鄉,新設一縣,取“大興爐冶”之意,定名“大冶”。大冶設四鄉:安昌鄉、四會鄉、宣化鄉、永豐鄉。其中,安昌鄉原為永興縣屬地,包括青山、棲儒橋、果城里等地,四會、宣化、永豐為原屬武昌縣的三個鄉。
關于大冶建縣的時間,也存在二說,一說是宋乾德五年(967),一說是南唐保大十三年(955),我們認為是后者。
1980年代,大冶縣在編纂《大冶縣志》時,重點研討了大冶建縣年代問題,認可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之說,即宋乾德五年(967)建縣。其文獻依據不少。如北宋歐陽忞《輿地廣記》卷二十五載:“大冶縣,皇朝乾德五年以大冶場置,屬鄂州。”《宋史·地理志四》載:“大冶,繁,南唐縣。”明萬歷《湖廣通志》載:“乾德中析武昌地并場置。”當然,保大十三年說的依據也不少。如《讀史方輿紀要》:“南唐保大十三年升為縣。”《十國春秋》載:“保大十三年,分陽新武昌三鄉置大冶縣。”康熙《大冶縣志》載:“保大十三年,時乾德三年也,升青山場并析武昌三鄉置大冶縣。”同治《大冶縣志》載:“保泰十三年,時乾德三年也,升青山場并析武昌三鄉置大冶縣。”《四部備要》載:“南唐保大中升為大冶縣。”
上述記載涉及三國(南唐、后周、北宋)和兩個年代,其中有的紀年有明顯矛盾和錯誤,但它們顯露了一種傾向:明代以前多為乾徳五年說,清代以后則多持保大十三年說。前者為宋太宗年號,時為南唐李煜七年,后周亡于北宋已8年;后者為南唐中主李璟年號,時為后周柴榮顯德二年,北宋尚未建立。認為乾德五年(967)建縣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太平寰宇記》撰寫時間距大冶建縣時間最近,因而最可靠;二是樂史任職黃州太守,距大冶不到百里。
樂史(930—1007)所著《太平寰宇記》是杰出的歷史地理著作,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舛誤。郭沫若談及書中三畤原的地點表述錯誤時,說“此乃樂史妄作聰明而以意改者也”;又譚其驤說其記古居巢城陷為巢湖“完全是一種無稽之談”。太平興國三年(978),李煜被宋太宗趙光義用牽機藥毒死,動因之一是李懷念故國,樂史不會不知道。據《辭海》所載,《太平寰宇記》始撰于李煜之死的次年。樂史為避免不測之禍,將大冶建縣時間延至北宋立國之后就可以理解了。另外,《太平寰宇記》在流傳中缺失8卷,其中有卷113、卷114,永興縣、興國州、大冶縣、通山縣恰在其內。今本中的有關文字,是晚清楊守敬在日本從宋殘本輯出來的,或許存在錯訛。
顧祖禹(1631—1692)隱居不仕,歷三十余年時間,參考二十一史和一百多種地方志,傾力完成《讀史方輿紀要》。《太平寰宇記》和《讀史方輿紀要》關于緊鄰大冶的通山縣設置的記載互有異同。前者載:“本永興縣新豐之一鄉也,淮南偽吳武義中隸羊山鎮征賦,周顯德六年唐國建為通山縣。”后者載:“唐為永興縣之新豐鄉,楊吳武義中置羊山鎮,周顯德六年,南唐始置通山縣。”二者史實相同,僅口吻略異,可以看出顧文采用了樂文,但對大冶設縣的年代,顧文卻擯棄樂文及諸多主乾徳五年的記載而采“保大十三年”之說,必有根據。
《四庫全書》中,宋代無名氏所撰《寶刻類編》卷一《國主二(南唐)》:“李璟《四祖塔院疏》,正書,篆額,蘄。保大十三年正月十日。”可惜文字已亡佚,《全唐文》卷一百二十八和近版《李璟李煜集》里均缺這篇文字,但這似可表明李璟在保大十三年曾巡行鄂東。南宋王象之《輿地碑記目》卷二里的二則記載:“《喬公亭記》,篆,法甚古,保大十三年徐騎省記。”“《周將軍廟碑》,保大十三年徐騎省記。”此載可與《寶刻類編》相互印證。徐騎省即南唐隨侍皇帝左右的重臣徐鉉(916—991),他降宋后官散騎常侍,世稱徐騎省。保大十三年徐鉉亦至鄂東(按:“喬公”即三國大、小喬之父,其籍潛山與黃梅緊鄰)。君臣同時到鄂東,也許游山玩水,李璟信佛,寫四祖塔院,徐鉉是文學家,憑吊英雄美人;但更有可能是處置國事,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臣此行,為南唐保大十三年置大冶縣之說提供了某種文獻依據。
保大十三年建縣說,將大冶建縣時間向前推進了12年,但我們作此辨析的目的不在于此,而在對歷史負責,以取信于后世。
名流與八景
古人喜歡擷取一地之山川風物,列為八景或十景,并邀約騷人墨客,吟詩作賦,以廣令名、留佳話。無論八景或十景,必為一州一縣自然人文之精華所在。大冶八景,正是如此背景下的產物。
說大冶八景,不能不說它的“創始人”趙鼐。趙鼐字鉅夫,別號南峰。云南河陽(今澄江縣)人,明嘉靖四年(1525)鄉試第一。嘉靖十四年(1535)任大冶知縣。“起敝振廢,自學校、公署、橋道、郵舍,罔不悉舉。”大冶的民風在他治理下大變,他離任多年后百姓仍念念不忘。
“千秋疊翠,森列于前;長樂諸山,環擁于后。湋源之水,春夏為湖,則彌漫灝渺,遠接天碧;秋冬為港,則轉旋曲折,而莫見其所從出也。”這是舊志對大冶縣城形勝的描述,不算是夸張。然而,當時武昌府下屬九縣一州,府志中對各縣山川形勝皆有記述,竟獨缺大冶。趙鼐深以為憾。于是在政務之暇,偕一幫文人朋友遍歷山水,摘其流峙之奇者,定為“八景”,分別是:龍角朝暾、鹿頭夕照、金湖湛月、玗洞飛云、鳳嶺松風、雉山煙雨、東方覽勝、西塞懷古。他又帶頭作詩題詠,眾多名士步韻相和,成為一時佳話。后來,縣人又擷取境內名山,將其中的天臺山、云臺山、宮臺山作為“三臺”,與“八景”并稱為“三臺八景”。此文單說“八景”。
八景各有何特色及內涵?以八景之首“龍角朝暾”為例,略作說明。趙鼐詩云:
神龍何代幻形蹤?一角崢嶸插太空。
甲鏡浸開晴霧黯,頷珠光射旭陽紅。
花封景際文明處,寒谷春回煦育中。
歲旱出云作霖雨,茫茫何處覓玄功?
龍角朝暾,意為龍角山頂,旭日初升。同治《大冶縣志》載:“龍角山,在縣南南昌堡,距城二十里。東連(興國)州境,西有仙人橋,下臨絕壁。《通志》:兩山相對,本名龍耳,天寶四年(745)更名。舊志:高峰峻拔,日出,光先見其巔。將雨,則有云起。”龍角山與陽新第一高峰南巖峰、大冶第一高峰太和山相距不遠,海拔786米。因山體如龍,尖峰如角,故趙鼐以此起興,歌詠飛龍在天、撥云布雨之祥瑞。
“龍角朝暾”之所以被列為八景之首,一是因其高峰峻拔,氣勢雄偉;二是將雨則云,有預報天氣之神奇功效;此外,千年名剎龍角寺也為其增色不少。
龍角山與其西側名為“仙人橋”的險絕群峰組成一條巨龍,雙峰恰如龍角。龍角古剎正位于龍角之下,其地背峰面谷,懸崖千仞,云飛泉涌,堪稱勝境。有一首詩專述龍角古剎的傳奇往事:
危巒瘦筱敵風威,遺像千年俯夕暉。
現角空中龍聽法,銜鞋石上鹿當機。
一燈下見諸峰瞑,孤杼寒舂宿霧飛。
鐘落世間疑送雨,云來丈室已沾衣。
此詩題為《龍角山禮慕仙禪師像雨至投宿》,為官撫邦所作。
官撫邦是明楚黨領袖官應震(1568—1635)之子,工詩古文詞,善米元章書法。清順治六年(1649)任大冶訓導,教育人材,賞議雋異,“若父兄之于子弟,惟恐其不克成也。披荊立學,尤為著力”。此詩選自詩集《猗玗詩草》,是他任職大冶時所作。官撫邦入寺禮拜慕仙禪師像,遇雨投宿寺中,因而作詩詠史。
近年大冶將龍角山盤山公路拓寬且延伸至頂峰,“龍角十八拐”成為吸引遠近游客的網紅打卡點,龍角古剎也煥然一新。
趙鼐主持評定的大冶八景得到邑人的認可,其八景詩問世后,一時和者眾多,留傳下來的也不少。
這里將其余七景之詩及其他名流相關詩作稍作介紹。
《鹿頭夕照》:
幻鹿春山何處尋,萋萋芳草襯疏林。
咸池返照浮光躍,昧谷橫霞暮影沉。
退舍揮戈誰壯志,分陰尺壁古人心。
未遑白發催衙鼓,獨對遙岑憶好音。
清同治《大冶縣志》載:“鹿頭山,一名鹿耳山,在縣南馬叫堡,距城七里。山脊與(興國)州分水。下有大泉潭、小泉潭,取水禱雨輒應,日西則光射其巔。”鹿耳山,在金湖街道上馮村上馮灣西南,主峰海拔600余米。山名“鹿頭”“鹿耳”,本以形言,如鹿耳虎頭之類。可能是感覺不太形似,同治縣志加了一句:“山麓有茨結形,四時蒼翠,望之如鹿。”與嘉靖縣志相比,有畫蛇添足之嫌。因此景的關鍵詞是夕照,故詩中多處狀寫太陽及相關意象。
《金湖湛月》:
雨添新水泛湖潴,野渡舟橫漏正初。
萬籟靜排青玉案,一川光映白蟾蜍。
明窗倒浸漣漪影,虛室遙分皎潔馀。
擬欲洗心清俗翳,靈臺侵曉憶居諸。
金湖即今大冶湖,時指大冶湖磊山以西部分。其得名或與“金井”有關。明嘉靖舊志載:“金井,在縣治西五里。水泛沒入湖,水涸坑窟如池。相傳古淘金井也。”此井雖久廢,而地名至今尚存,具體方位,在大冶湖南面原海螺山附近。“金堤”則因金湖而得名。清同治《大冶縣志》載:“金湖,源出宮臺、西陽、云程等里,其湋源河泊漁利雖屬興國,形勝則吾邑可撫而有也。《通志》:金湖在縣南半里,湖南為興國州界。春冬則涸,夏潦盛時,由湋源口入江,夜色尤佳。”此詩狀寫月光下的大冶湖美景。
《玗洞飛云》:
嵸巃山勢傍江潯,巖洞迂回異眾岑。
靈竅天開應有意,蒸云時出本無心。
尋幽臥榻衣裳潤,際會從龍雨露淋。
欲起漫郎問行樂,白云蒼狗幾相尋。
猗玗洞就是黃荊山上的飛云洞。清同治《大冶縣志》載:“在縣東九十里回山之上,唐元結避兵于此。洞有三:上出云,中出風,下出水。嵌巖面江,幽窅幻怪。絕頂異泉流注,飛瀑百丈,下復穹然。三石巖奇怪尤絕,每洞云一縷如絮,土人以為雨征。”
《鳳嶺松風》:
鳳去山空愿未平,龍髯虬角遍森森。
化工久植千年干,靈籟時傳十里聲。
陰散日中擎葆蓋,響遺云外奏簫笙。
何人更葉丁公夢,會見明堂作棟楹。
清同治《大冶縣志》載:“鳳凰山,在鳳凰堡,距城七十里,高百余丈,周三十余里。上有佛石、佛堤池諸景,多靈草、松濤之勝。北界武昌。吳建興中,有鳳集焉,故名。《一統志》:又名鳳棲山。”鳳凰山在今鄂州市鄂城區澤林鎮境內,最高處海拔220米,山間有唐貞觀年間興善寺遺址。
《雉山煙雨》:
獻秀呈奇欲定名,千年越鳥浪儲精。
巖阿氣吐煙籠靄,炎夏威凌雨挹清。
圖壓輞川山出色,吟回漁父路迷津。
可人剩有尋常事,禾黍油油燕歲成。
清同治《大冶縣志》載:“白雉山,在縣北宋皇堡,距城五十里。昔有白雉之祥,故名。山高一百三十丈,周回五十里,最高曰芙蓉峰。峰前獅子巔,峰后金雞石。絕頂(有)石佛像,禱雨者占石,石舉則雨,不雨則舉莫能勝。后石失所在。”
江西萍鄉人吳仁,明萬歷十年(1582)任大冶知縣,建學宮,修邑乘,多所創立。曾作《雉山煙雨》詩云:
下雉何年被爾名,山林佳氣轉醇精。
朝飛厭浥林陰密,麥秀氤氳暑溽清。
嵐重洞天分別界,路迷仙侶共尋津。
坐沾沃壤流膏液,童子馴心愧未成。
東方山,在今黃石市,跨下陸、鐵山兩城區,主峰走馬坪海拔約470米。清同治《大冶縣志》載:“在縣北東方堡,距城三十里,高聳入云,一覽無際。云中多藥草,邑主山也。山勢連亙,至瀕江山鎮,皆其支麓。”東方山有大小寺院20余處,其中以弘化禪寺最為著名。該寺位于攬勝垴與曼倩垴之間,為馬祖道一和尚的高足智印和尚道場。清咸豐年間曾毀于兵燹,歷經重修擴建,其本寺、下院和子孫寺多達二十余處,今為湖北境內最大的寺院群落。
趙鼐《東方覽勝》詩云:
石磴羊腸路幾盤,梵宮捧出翠微端。
地分山水成奇勝,天與詩人縱大觀。
身世不知霄漢際,塵寰擬隔霧云關。
賞心不解東方趣,歸為斜陽興自闌。
其《西塞懷古》詩云:
別障分巒擁碧油,石公磯下系行舟。
天分吳楚舊王業,地失孫權偏霸謀。
白鷺秋空人世事,蒹葭霜老古今愁。
我來欲賦登臨興,云自行空水自流。
清同治《大冶縣志》載:“西塞山在縣東道士堡,距城九十里。高一百六十丈,周三十七里。……”西塞山居吳頭楚尾,是長江中游沿江最險峻的山峰之一,也是黃石最重要的人文勝景。江淹、陶峴、羅隱、皮日休、蘇軾、顧景星等歷代名流先后題詩,盛贊該山的傳奇歷史和奇絕風光,其中尤以“詩豪”劉禹錫之《西塞山懷古》最為膾炙人口。
到過大冶且寫過相關詩文的名人不少,陸游、吳國倫、袁宏道、官撫邦等都是,清代名噪一時的才子詹應甲(1760—1841)也是。道光初年,詹應甲任大冶縣令,縣志稱其“溫和風雅,政以德化;案牘雖煩,行所無事。士類加意培養,每月課論文,一經點竄,多佩教益”。
詹應甲在大冶期間,創作的兩篇賦,在歷代文人墨客歌詠西塞山和鹿頭山的篇章中,堪稱精彩之作。其一為《鹿頭夕照賦》,全文約700字,使用了幾十個與“鹿”有關的典故,狀寫“鹿頭夕照”之美之奇,可謂別出心裁。其二為游西塞山時所作《桃花洞賦》:“盈盈隔水,雨花散到江洲;歷歷回山,瀑布飛來玗洞。一線天通,千盤石走。虎豹當關,蛟龍有藪。”“花開一曲漁歌子,誤認蓬萊即塞山。”極言其險峻壯美,可算是西塞山和桃花洞上佳的推廣語。
“大冶八景”沿襲數百年,直到上世紀50年代區劃調整,西塞山、東方山劃入黃石城區,鳳凰山、白雉山劃入鄂城縣(今鄂州),其實大冶建縣前,鳳凰山、白雉山就在原武昌縣(今鄂州)境內,與其說是劃走,不如說是歸還。但八景變為“四景”,數量偏少,也不符合國人偏愛“八”“九”“十”的傳統。于是,1990年代,大冶一些文人又補充了“銅海飛煙”“太和云霧”等若干景點,湊成“新八景”。老八景易為新八景,反映的不只是行政區劃的變更,還有大冶經濟社會之滄桑巨變。
文起閣與縣學宮
什么最能體現和代表一個地方歷史上的文化狀況和教育水準?是歷史名人、文化遺產、文化景觀、文化事件的質量和數量。那么,大冶歷史上,究竟有多少聞名遠近的文物、景觀和人物呢?
恕我直言,并不多。石龍頭的刮削器,銅綠山的銅斧,鄂王城的城墻,蟹子地的谷粒,都是大冶悠久輝煌歷史的見證,外地出土的鄂君啟節等,也與大冶有著特殊的關聯,但總量不多。歷史景觀除了銅綠山、鄂王城等,其他只在鄂東一隅小有名氣。
那么歷史名人呢?從我搜檢的結果看,大冶歷史名人極少,而且幾乎沒有文化名人。《湖北歷史人物辭典》中的大冶人物,明代以前沒有,明代只有徐祥,清代只有余國柱,二人均不以文名。近代有柯玉山、黃申薌、向海潛三,均為會黨首領。現代只黃赤波、余立新二人。當代稍多,也主要是軍政人物。再看《湖北省志·人物志》,大冶人或與大冶有直接關聯的人物:春秋時期兩人,鄂王熊紅、鄂君子晳;徐祥、余國柱仍然在列;清代多了柯逢時,但他原屬武昌(今鄂州)人;清末民初之際人物,除柯玉山、向海潛外,還有周孚、劉復、柯竺僧,幾乎罕有人知。《湖北文化史》(湖北人民出版社)中,沒有提到一個大冶文化人。《湖北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中,沒有提到一個大冶僧人。《湖北道教史》(荊楚文庫版)只有半個大冶人,即金牛人雷時中,道教天心派混元道法創立者,其道場設在陽新顏子山。
這就是大冶名人被湖北省權威辭典收錄的情況,《中國名人辭典》收錄的就更少了。不說與省內省外的文化大縣相比,就與同屬武昌府的興國州和黃州府的蘄州、黃岡縣、蘄水縣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
考察一個地方歷史上的文化狀況,還有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該地的科舉狀況。以清代為例。湖北省共領10府,1直隸州(歸州),1直隸廳(鶴峰),60縣。清順治三年(1646)第一次舉行進士考試,至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1904)最后一次考試,一共112科,合計1228人考取進士。1228/62=19.8。大冶縣(按當時境域統計)共考取15人(詳見筆者所著《大冶文化簡史》),不及全省平均數。
以上情況表明,歷史上的大冶,在文教方面的表現,并不突出,但俊才杰士,亦代不乏人。文起閣或可稱為大冶文人的淵藪。
大冶城區位于大冶湖(金湖、湋源湖)邊的丘陵地帶,三面環湖,唯北面地勢稍高。湖與長江相通,每當雨季,湖水暴漲,城區東、西、南三面之水連成一片,往往大部被淹,居民深受其害。城區東南約一里許,湖邊有座小丘,一部分延伸至湖中,成為半島。明萬歷二十二年(1594),知縣楊令名決定修長堤,造高閣,以殺水勢,興文運。于是修筑高丈余寬五尺之堤,堤上造三層高閣,供奉文昌帝君。此前大冶連續三十年無人中舉,當年胡基竟然高中,邑人以為文昌閣發揮了作用。此后,清順治、康熙、乾隆年間,屢有增修。乾隆五十八年(1793),知縣陳瞻燧會同士紳募捐,重建兩座樓閣,分別命名為文起、大士,旁造七級佛塔,名曰青云梯,以昌文運。清嘉慶年間,知縣陳桂生增建拜亭。咸豐間,太平軍將閣像盡毀,唯存一塔,后邑人復修如故。
文起閣位于城關,屬邑中名勝,縣衙、學宮陳列其北,鹿頭山、龍角山聳峙其南,“煙嵐萬態,盡入幾席酒杯”;后則金湖大江,“漁蓑短棹,來往如在鏡中”。(胡繩祖《文起閣記》)登斯閣者,興之所至,發為詩文,數量可觀。
胡繩祖,明崇禎十五年(1642)舉人,官潛江知縣,著有《讀史論略》《歸農雜撰》《晚箴錄》等。他是邑中名流,兩次參與縣志修纂。
如果說文起閣是大冶文人的逞才之地,那么學宮和書院則是大冶士子的養成之所。
大冶縣學之建,始于宋代。潘子韶出身于福州詩書大族、科舉世家,曾任大冶縣令,是我們已知的第一個興辦大冶縣學的官員,“賢而有政事文章”,理應受到邑人的尊敬和銘記。
宋元之交,兵禍連綿,大冶縣治屢遭劫難,縣學自難獨免。自元代起,政府官辦的學校稱儒學,又稱學宮。元至正元年十二月(1342),大冶縣尹周鏜重建儒學,并在儒學旁建冶邑先賢萬止齋祠堂。周鏜對大冶教育最大的貢獻,不在于重建儒學,而是將大冶南宋名儒萬止齋樹為典型,使邑人有所遵循。
萬禎,又名人杰,字正淳,號止齋。生活于南宋時期,先后從陸九齡、陸九淵兄弟和朱熹問學。朱熹評價說:“陸子壽兄弟……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盡好,卻是先于情性持守上用力,此意甚好,……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舍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萬禎未獲功名,亦無專著傳世,《朱子語類》中有多處出現萬禎、正淳、人杰之名。萬禎學成歸來,在鄉間授徒,后應聘至崇虛觀講學。縣主簿黃何聞萬禎之名,便延其為縣學儒師,傳授朱陸之學。萬禎去世后一度沉寂無聞,其逸事只在民間流傳。直到元代后期,程朱理學之正統地位復得認可,在周鏜等地方官員的推動下,萬禎得以專享祭祀,其名漸傳漸遠,乃至被今人稱為大冶“千年第一賢”。
明洪武八年(1375),縣儒學毀于災。十二年,知縣王伯時重建。其間又數次興廢。永樂九年(1411),儒學規模格局大定,基本適應教育教學之需。自宋至清同治間,儒學修建近30次。
儒學既是一縣之最高學府,又是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往往與文廟比鄰而建,或者合而為一,作為全縣文化的淵源和象征,受到邑人的普遍尊崇。大冶學宮前的雙石坊,其文先是“臺垣接武”“科第聯芳”,后易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又建“圣域”“賢關”二坊。光緒七年(1881),皇帝御書“斯文在茲”四字,頒行天下學宮。這些坊聯殿額,昭示了儒學的三大功能:一者崇儒祭孔,一者傳播文化,一者作育人才。大冶儒學在文化傳播和人才培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儒學之外,還有書院、社學、義學等,也承擔了相關教育職責。明代大冶民間已有書院,只是規模較小,一般只供族中子弟就學。至清代,政府舉辦有金湖書院。起先建在縣衙后左側,因與后衙近,兼作郵館,頗狹仄。嘉慶年間,移置于東市二鋪河街,一進三重。道光二十八年(1848)、二十九年連續受災,毀于大水。知縣繡麟捐廉籌款,改建于北關外旌陽山后,即將完工,不幸遇兵燹,遭焚毀。同治六年(1867)冬,馬修藩自黃陂移c9ea5f8d9111d4f56f1dfba8b286c59e署大冶,有志重修。舉人黃昺杰之宅適在文廟之側,遂慨然捐出住宅,改建書院。合邑士民,歡欣鼓舞,特請人作記刻石。金湖書院藏書計有:《四書經注集證》20套、《欽定周易折中》12套、《欽定書經傳說匯纂》18套、《史記》40套、《資治通鑒》104套等,共計600余冊,專備住院諸生誦習,外人不得借觀,主講亦不得挾為己有。
社學創自元代,明清相沿,府、州、縣各立社學,每鄉各設一所,擇文義通曉、行誼謹厚者為社師,以朝廷律令、經史歷算等教化青少年,相當于后來的掃盲教育,入學者可免差役。大冶社學原在縣衙之左二十步,系租賃民居而設。義學,相當于官辦免費學校。大冶義學,向在縣治東西市各一,以兵亂停辦。同治四年,知縣易振元捐資復設。后知縣胡復初以小學最關緊要,增捐修金,重立兩塾分課。知縣馬修藩重建書院時,在其側修建東市義學,又將西市二鋪一所,改為西市義學。光緒七年,署任知縣朱榮椿捐金,于保安、黃石港兩鎮借公所各設義學一所。
嘉靖十四年(1535)六月,新任知縣趙鼐遍行鄉坊,勸諭民人送子就學,“或家塾,或寺觀,隨處立館,延明師以教之”。行之三年,家知向學,形成了良好的讀書風氣。四年后,提學使田頊到大冶開展歲考,選拔33名童生為秀才。在此之前,大冶很長一段時間無人考取秀才。書院、社學之類機構,對一地文化教育的影響,于茲可見。
窮不丟豬,富不丟書。當時民間小戶,鮮有能送子入學者,而世家大族則能自辦學校,教養子弟。私辦義學通常稱為義塾,一般只供宗族子弟就讀。大冶歷史上著名的文化家族主要有章山里周氏、鯚魚地余氏、換絳橋胡氏、流水里丁氏、章山里向氏,幾乎都有自辦的學堂,其中胡氏家族所出人才尤多。胡希瑗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中舉。在此之前,大冶縣連續二十年無人中舉。明隆慶元年(1567),胡應辰考取舉人,距其父親胡希瑗考取舉人時隔整三十年,距大冶人上一次中舉時隔十五年。可見考取舉人有多難,至于進士就更不必說了。一些家族因族中無人中進士,只能退而求其次,以“鄉進士”(舉人)、“歲進士”(貢生)之類牌匾懸于宗祠,雖不能夸飾外人,卻可激勵族中子弟刻苦向學,以圖進取。
文起閣消失了,但文峰塔還在,而體量龐大且風格各異的學校,成為大冶城區的新亮點。
銅綠山與新大冶
1994年,大冶撤縣建市。
2001年10月,在大冶青銅文化研究會上,楚文化專家張正明斷言:“沒有銅綠山,就沒有楚文化!”這話是否妥當,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沒有銅綠山,就沒有大冶縣,當然也就沒有今天的大冶市了。
不過,與大多數人的認知相反,在相當長的歲月里,銅綠山對大冶的影響并不大,有時甚至幾近于無。
銅綠山,大冶建縣之時稱“青山”。如前文所述,此青山并非泛稱,而是有明確指向的實體,而銅綠山礦區則比青山、銅綠山范圍更大,包括銅綠山、仙人座、大青山、小青山等約20座小山。礦區面積10平方公里,礦床面積3.5平方公里,最深至負720米標高。那里曾經長年有大批的工人在采礦、冶煉,聲勢浩大,場面壯觀,可以用“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來形容。清初大冶人胡率祖有《道邊鐵爐》詩云:“辛苦耕耘盡納輸,村村為活賴洪爐。夏王大有銅山帳,可只三千六百無?”當時地方百姓終年辛苦耕種,出產的糧食卻剛夠交納糧賦,只有靠自辦小礦采冶銅鐵掙點活錢。人們循著銅草花的指引,以此確定礦藏所在。《山海經》稱,天下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二者相加四千余,而大冶一地就有眾多銅鐵礦山,可知其資源稟賦之富厚。
南宋人洪咨夔曾游歷江西饒州等地,為東楚之地礦藏之富饒所震撼,創作了一篇奇文,名曰《大冶賦》。其《平齋文集》三十二卷,而《大冶賦》為其開卷之作,可見他本人對這篇作品的重視。《大冶賦》以賦體創作,述及歷代礦冶源流、采冶機構、礦藏分布、管理制度、金屬采選、造幣工藝、儲藏運輸等。賦文自開天辟地講起,講山岳湖海之形成,歷述金屬礦藏之來歷,統治者對金屬的重視,至唐宋開采的歷程。《大冶賦》之“大冶”,不是指大冶縣,而是形容礦藏采冶之盛,其中記述了采冶場所和機構的名稱,這些冶場之名,在其他文獻中只有零星記載,因而顯得尤其珍貴。大冶亦屬東楚,且富銅鐵,作者不會不知道,因而此文自然涉及大冶,如“然或鐵山之孕銅,或銅坑之懷金”,即將鐵山、銅坑并列而言。
正因大冶銅鐵礦藏豐富,才獨立設縣,宋朝廷才在其地設置富民錢監和磁湖鐵務,這兩種機構,承擔著冶鑄、經營錢鐵的重要職責,是維持帝國運轉必不可少的重要機構,這也體現了大冶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
但是銅綠山曾經陷入長久的沉寂。清同治《大冶縣志》卷二《山川志》對銅綠山的記載卻只有寥寥數筆:“銅綠山,在縣西馬叫堡,距城五里。山頂高平,巨石對峙。每驟雨過,時有銅綠如雪花小豆點綴土石之上,故名。綿延數嶂,土色紫赤,皆官山也。或云古出銅之所,居民掘取鐵子石,頗傷山骨。”同治《大冶縣志》卷一《疆域志·沿革》又載:“舊志考工云:冶氏為鐵邑之名,權輿青山場之鐵冶,夫非五金之謂矣,無論金井銀爐,湮滅已久……銅灶雖存遺跡,亦莫詳其年代興廢與鼓鑄之方也。”100多年前縣志的編纂者,弄不清銅綠山的開采及冶煉情形,于是在撰寫時大發慨嘆。由此可見,在清代,銅綠山無人開采,全然廢棄。其實,據舊志所載可知,自元末天下動亂,礦工散亡,銅綠山的采礦業就幾乎停滯,安田爐等管理銅鐵采冶的機構也先后廢罷,所謂“熊熊爐火三千年不熄”,未免過于夸張。
1965年,大冶有色金屬公司在銅綠山礦的建設過程中,不斷發現古代采礦和冶煉的遺跡和遺物。放眼望去,礦區漫山遍野堆積著古代的煉銅爐渣,覆蓋面積約14萬平方米,原堆積層有3米多,總量在50萬噸以上。人們開始追溯歷史,但所獲無多。進入20世紀70年代,銅綠山再次引起世人矚目。1973年6月至10月,銅綠山礦在南露天采場北端剝離距地表40余米的銅礦富集帶時,在一片古代采礦井巷中,先后發現銅斧(每件重3.7公斤)、銅錛及木槌、木鏟、陶罐等器物。礦山負責人迅速向上級報告,中國歷史博物館派人現場調查,認定這是春秋戰國時期一處大型采冶遺址,具有重大歷史、科學價值。
1980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召開的中國古代青銅器學術會上做了題為《銅綠山銅礦的發掘》的演講,銅綠山古銅礦遺址自此聞名世界。1982年,國務院批準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4年在決定永久保留的遺址一號發掘點建立“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1984年12月落成并對外開放,成為繼半坡、秦始皇兵馬俑之后,我國第三個古文化遺址博物館。參觀者稱其為“曠世奇觀”,學術界列其為“世界第九大奇跡”。有的說“這是世界冶金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有的說,“我們在這里看到了在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東西,這在我們一生中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從銅綠山遺址被發現之日起,國務院和湖北省政府就一直強調要好好保護,但是,由于遺址位于某大型國企的開采區,遺址之下貯藏著價值連城的金屬礦物,有關部門和單位主張將遺址搬遷。1989年11月,在黃石海觀山賓館召開遺址“保護方案”論證會,奇怪的是,論證會的組織者竟然是礦冶機構,主持人卻是中國國家文物局某副局長。包括副局長本人在內,絕大多數專家主張搬遷,只有省文化廳退休的孫副廳長、黃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瑞云和黃石博物館館長周保權等人堅決反對。反對無效,方案獲得通過。會后,黃瑞云立即撰寫《銅綠山古遺址不應搬遷》的長文寄給新華社,又將刊發該文的新華社內參寄給湖北省省長黃知真。黃省長高度重視,明確要求就地保護。這樣,“世界第九大奇跡”才得以幸存。
銅綠山遺址201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工業遺產名單,2021年入選全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成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后,它的使命不再是貢獻礦藏,而是展示大冶悠久的采冶歷史及文化。
銅綠山古銅礦遺址的考古發掘仍在深入。1985年,經碳十四測年等綜合研究,初步確定銅綠山井巷采礦年代早到商代晚期。2011年以后銅綠山的發掘和研究逐步深入,每一次發現,似乎都將銅綠山的采掘時間向前推進。據2024年的媒體報道,新的發現將“銅綠山采冶的肇始年代向前再推進1000年”。
2023年,銅綠山古銅礦遺址博物館完成改擴建并開館迎賓,與1984年的舊館相比,無論是建筑規模、建設水準,還是館藏內容,都實現了巨大的跨越和提升。事實上,2023年的大冶,與1980年代的大冶相比,無論是經濟體量、生活質量還是文明水準,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跨越和提升;與建縣之初的社會狀貌、物質生活、文明程度相比,更不啻霄壤之別了。
2024年是大冶撤縣建市30周年。
銅綠山已不是當年的銅綠山,大冶也不再是當年的大冶。大冶正從以采冶為主的資源型城市逐漸轉型為以綠色生態為底色的現代化城市,大冶的全域人口從當年的不足十萬到如今的接近百萬,城區從墈頭、將軍山向大冶湖東岸和南岸跨越,城區人口從當年的數千人發展到30多萬。2012年,大冶成功進入全國縣域經濟“百強”,排名第97位。此后,大冶的排名逐年提升(2023年升至第56名),顯示出其在經濟發展和綜合實力方面的持續進步。2018年2月,黃石大冶湖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升級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與之相適應,大冶的文化和教育也在發力。勁牌公司公益助學20年,累計捐贈助學金4.7億余元,幫助4.2萬余名青少年圓夢大學。小學教師陳彥珍,一生儉樸,退休后籌資開辦加油站,以其盈利出資七百余萬元設立助學基金會、建造慈善大樓,長年堅持慈善助學……勁牌公司和陳彥珍作為企業和市民的代表,體現了大冶人對文教事業的關注和重視。大冶先后獲得國家園林城市、中國詩詞之鄉、中國楹聯文化城市等“招牌”。2017年大冶獲評全國文明城市,這表明其城市整體文明水平得到了國家層面的認可。
如果說銅綠山是大冶的根基,代表著曾經的輝煌,那么決定大冶未來遠景的,則是文化和教育。
(特邀編輯 丁逸楓 278317698@qq.com)
- 今古傳奇·當代文學的其它文章
- 影響力人物——張曉亮
- 楊公堤
- 芭茅草
- 暮色中的深情呼喊
-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 把人物丟到漩渦里熬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