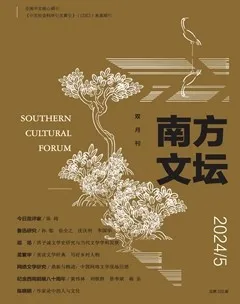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中的“洪氏話語”
忽然想到了這個(gè)詞,似乎可以給我們將要談到的主人公一個(gè)概念,一個(gè)說法。
世紀(jì)之交以前,雖然洪子誠教授也曾參著多部文學(xué)史,但直到他1999年獨(dú)立出版《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才算是真正從幕后走到了臺(tái)前。再到2002年出版《問題與方法: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研究講稿》(以下簡稱《問題與方法》),他的地位再次躍升,變成了“作為學(xué)科的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奠基者。之所以如此說,是因?yàn)樵诖藭鴨柺乐埃瑢W(xué)界雖有了多部有影響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出版,但那些似乎還都不是以“個(gè)人主體”為本位的寫作。也就是說,那些文學(xué)史中說話人的身份是非常模糊的,他們是一種混合的“集體的發(fā)聲”,所代表的是國家制度、文藝界、某種莫名的文化權(quán)力,其述史的主體性是“非個(gè)人”的,尚不存在一個(gè)“個(gè)體人格”的敘述者主體。
當(dāng)然,更重要的是,那些述史者也從未在內(nèi)容和方法的意義上,對(duì)這些建構(gòu)起來的敘述進(jìn)行過有“間離性”的討論,不會(huì)對(duì)自己“述史何為”或“何以言說”有什么自我的分析與懷疑。
只有到了洪子誠先生這里,一切才進(jìn)入了一個(gè)“主體性反思”的階段。
這馬上就涉及了一個(gè)最根本的問題——洪子誠最重要的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即是首先對(duì)學(xué)科進(jìn)行的“本體論的思考”。猶如布萊希特的“間離理論”一樣,洪子誠教授在言說和言說者之間,建立了一種頗為新鮮的疏離感,因而也產(chǎn)生了鮮明的“陌生化”效果。即,“不要完全相信說話人”,“我說的不一定是完全對(duì)的”,“我只是在不得不述說的意義上講述這些”,“你還需要審慎思考”……在《問題與方法》中,甚至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中,他創(chuàng)建了這樣一種話語方式和說話角色。千萬不要小看這一發(fā)明,正是它凸顯了“作者”在當(dāng)代文學(xué)述史工作中的個(gè)人身份,正是這個(gè)身份才使得這些敘述獲得了“可反思性”,具有了與司馬遷的“太史公曰”,或蒲松齡的“異史氏曰”相近的意義,即“歷史”和“敘述”之間的分離——猶如“角色”與“演員”之間的分離一樣。這種分離的意義與作用,無論怎樣強(qiáng)調(diào)都是不過分的。甚至在洪子誠先生那里,是通過在課堂上與學(xué)生的對(duì)話和自嘲式的玩笑來實(shí)現(xiàn)和強(qiáng)化的。
一旦建立這種距離,關(guān)于文學(xué)史的“對(duì)象”是什么,“講述者”是誰,“如何通過講述來抵達(dá)對(duì)象”等問題,便可一一被凸顯出來。很顯然,正是從《問題與方法》一書開始,學(xué)界之前從未正式談?wù)撨^的,關(guān)于當(dāng)代文學(xué)學(xué)科的內(nèi)涵、構(gòu)成、研究方法、文學(xué)環(huán)境的演化、文學(xué)史寫作、經(jīng)典化、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資源等問題,才從學(xué)術(shù)構(gòu)建的角度得到了系統(tǒng)的反思,關(guān)于這門48N8eePxLeQWHJBo20izhDyHDjwzozCHSs0M/K1HeWM=學(xué)科的許多基本問題,才真正浮出了水面。“當(dāng)代文學(xué)”也才從一些“制度化的知識(shí)”,轉(zhuǎn)變?yōu)橐婚T可以與“古典文學(xué)”“現(xiàn)代文學(xué)”“外國文學(xué)”相提并論的“學(xué)科”。
顯然,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中的“洪氏話語”,首先是由“間離性”所導(dǎo)致的反思性話語,這種話語也導(dǎo)致了“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元寫作”效果——就是在文學(xué)史的寫作中,“敞開”了這種寫作本身,使其變成了一個(gè)并非絕對(duì)和終極的“歷史的敘述”。可以說,迄今為止洪子誠先生的所有著作,都是以《問題與方法》為引論的,如果把其全部著作看作是一個(gè)整體,那么作為“總綱”的,就是《問題與方法》。而“洪氏話語”正是通過這部書而得以彰顯,并作為一條線、一種方法、一種述史話語,貫穿在其全部著作之中的。
其實(shí),“洪氏話語”在更早先出版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中就已經(jīng)顯形了,它顯形的效果,便是“使個(gè)人的話語進(jìn)入了歷史的話語”,同時(shí)又表明了“個(gè)人話語與歷史話語之間的差異性”。比如在該書的“前言”中他說:
在50年代初,文學(xué)界的權(quán)威者認(rèn)為“目前中國文學(xué),就整個(gè)說來,還不完全是社會(huì)主義的文學(xué),而是在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指導(dǎo)之下社會(huì)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文學(xué)”,但又指出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xué)已經(jīng)開始走上了社會(huì)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道路”。“建國以來”的文學(xué)與以前的文學(xué)性質(zhì)的區(qū)別,以及“建國以來”文學(xué)是一個(gè)更高的文學(xué)階段的判斷,在50年代已成為不容置疑的觀點(diǎn)。①
這是典型的“洪氏表述”,此段話中至少包含了三個(gè)層次的話語:首先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表述,即現(xiàn)階段中國的文化,“是以無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主義文化思想為領(lǐng)導(dǎo)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②這是原始的理論出處;其次是文學(xué)界的“權(quán)威論述”依據(jù)上述政治經(jīng)典所演繹出來的表述,“目前中國文學(xué)……”其語言邏輯與語氣亦完全仿照前者;最后才是說話人,以“史家轉(zhuǎn)述”的口吻所進(jìn)行的敘述。這樣,原先人們習(xí)慣的“歷史”本身,就轉(zhuǎn)換為“關(guān)于歷史的知識(shí)”,或“關(guān)于歷史的敘述”,其原先似乎不言自明的真實(shí)性或正當(dāng)性,便置于“被審視或被討論”的位置,而不再是“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shí)本身”。
這就是“洪氏話語”在述史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這使得他的文學(xué)史敘述中,始終存在著一個(gè)講述者的聲音,一個(gè)時(shí)時(shí)將講述“懸置”或“敞開”的角色。如同戴衛(wèi)·赫爾曼在《新敘事學(xué)》中征引羅蘭·巴爾特的觀點(diǎn)所說,“巴爾特1967年的文章《歷史的話語》是一個(gè)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點(diǎn)。巴爾特取消了歷史話語的指示物和所指,認(rèn)為歷史像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一樣,產(chǎn)生的不是真實(shí),而是一些真實(shí)的效果,為類似海登·懷特在《元?dú)v史》里闡發(fā)的理論方法搭起了舞臺(tái)。這類方法突出一個(gè)雙重等式,即‘情節(jié)結(jié)構(gòu)=文學(xué)操作=虛構(gòu)杜撰’,也可以表示為‘歷史敘事=文學(xué)敘述=虛構(gòu)敘事’”③。洪子誠的文學(xué)史話語,正是標(biāo)識(shí)出了“文學(xué)歷史本身”與“關(guān)于文學(xué)歷史的講述”之間的差異性,它其實(shí)是一個(gè)“被講述之物”。在他的講述中,“歷史話語”終于可以讓“個(gè)人話語”得以“容身其間”,歷史不再由一個(gè)不容置疑的權(quán)威角色來宣告,或者甚至“自動(dòng)發(fā)聲”,而是變成了一個(gè)沉默者,僅由個(gè)人依據(jù)有限的材料來說出。這樣的“當(dāng)代文學(xué)”或“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才算是回到了其基本的存在形態(tài)。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洪子誠《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之所以能夠成為“認(rèn)同度最高”的文學(xué)史的原因。因?yàn)樗鼮槲覀兲峁┝艘环N更可信任的范式——即便是在受到各種因素強(qiáng)力干預(yù)的當(dāng)代文學(xué)中,也有著某種歷史的客觀性的存在。
其次,“洪氏話語”還試圖生成為一種具有“實(shí)證”功能的“科學(xué)話語”,這使得“文學(xué)研究”本身,可以在“史學(xué)”的意義上建立起精細(xì)考據(jù)的模型與范式。
這里僅舉一例,就是他在《材料與注釋》一書中的第一篇:《1957年毛澤東在頤年堂的講話》。這是1967年春洪子誠先生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huì)看到的一份記錄稿,手寫且無記錄人姓名。這樣一份“并不正式”的記錄稿,通常不會(huì)得到重視,但其中所包含的大量時(shí)代和政治信息,卻被敏銳的洪子誠捕捉到,且在多年后他更意識(shí)到了其“知識(shí)考古學(xué)的意義”。某種程度上,只有看到這樣的文字,才會(huì)真正理解那個(gè)時(shí)代“到底發(fā)生了什么”,意識(shí)到文學(xué)在領(lǐng)導(dǎo)者思維中的性質(zhì),其所處的地位,領(lǐng)導(dǎo)者如何看待作家,其對(duì)作品的態(tài)度與理解方法,意識(shí)到我們之所以經(jīng)歷了那樣一個(gè)“文學(xué)的時(shí)代”,其背后的真正原因。
在這篇奇特的文字中,我們看到了作者對(duì)于原稿的完全性的“實(shí)錄”,那些文字中奇特的斷句,時(shí)而完整時(shí)而中斷的語勢,其字里行間的意義,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話中有話,其口語習(xí)慣,個(gè)人腔調(diào),欲言又止等,都有言不及義和言難盡意處,但洪子誠先生卻能夠?qū)⑵洹翱p隙”中可資闡釋的信息一一發(fā)掘出來,供我們這些跨越了巨大時(shí)間溝壑的人,來品鑒和咂摸其中的滋味。經(jīng)過他的注釋之后,這段文字就具有了濃厚的“春秋筆法”的意味。讓我們透過實(shí)錄,去感受歷史中豐富的潛臺(tái)詞。
某種意義上,《材料與注釋》一書的“文本體例”,是洪子誠先生的一個(gè)首創(chuàng),它以事件和人為中心,以原始材料加“證據(jù)鏈?zhǔn)降淖⑨尅钡姆绞剑噲D為我們廓清當(dāng)代文學(xué)歷史中發(fā)生的幾個(gè)重大事件背后的故事,在這其中,對(duì)于同一個(gè)事件,不同歷史人物的態(tài)度或看法各有差異,作者讓他們在歷史中展開了“對(duì)話”,而并不是提供一個(gè)獨(dú)斷式的敘述。關(guān)于1957年中國作協(xié)連續(xù)召開的黨組系列擴(kuò)大會(huì)議背后的暗流,關(guān)于1962年在大連召開的“農(nóng)村題材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會(huì)議”,關(guān)于1962年紀(jì)念“講話”的社論,還有1966年林默涵的檢討書,等等,都有非常富于戲劇感的呈現(xiàn)。其中林默涵的檢討書《我的罪行》竟然是全文照錄的。這些特定史料的獲得肯定有某些偶然性,但作者“嘗試以材料編排為主要方式的文學(xué)史敘述的可能性”的意圖,“盡可能讓材料說話……以展現(xiàn)歷史的多面性和復(fù)雜性”的表述方式,正是“洪氏話語”的一個(gè)重要特征。
而且,首篇文字中洪子誠先生似乎是專門為了做一個(gè)示范,在注釋部分中,將眾多的材料如《郭小川日記》、黎之《文壇風(fēng)云錄》等進(jìn)行精細(xì)對(duì)讀,作為旁證,甄別校正了這次會(huì)議的日期等信息。最后還不忘對(duì)自己在《1956:百花時(shí)代》一書中所記的此次會(huì)議的時(shí)間作了訂正,從“1967年3月16日”改寫為“17日”。這種史家的認(rèn)真與較真,可以說樹立了治學(xué)的典范,也堅(jiān)定地標(biāo)識(shí)了“洪氏話語”的史學(xué)品質(zhì)與歷史態(tài)度。
最后,從述史實(shí)踐的角度,至遲在1980年代之初,文藝界就已發(fā)育出比較系統(tǒng)的“異質(zhì)性”力量,而且,這一力量在不久之后便占據(jù)了文學(xué)的正統(tǒng)和核心位置,這便是從“新詩潮”到“尋根小說”再到“先鋒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新變革。很顯然,在“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總體性”中,出現(xiàn)了并不統(tǒng)一且很難整合的“斷代”現(xiàn)象。“前二十七年”和后來的“八九十年代”,有著非常不同的文學(xué)景觀和思想性質(zhì)。那么,如何將前后兩個(gè)階段的文學(xué)歷史在敘述中整合起來,便需要?jiǎng)?chuàng)建一種間離敘述和“中性角色”,才能將其統(tǒng)一起來。洪子誠《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通篇采用了這種“局外人式的敘述”方式,敘述者既不是上一個(gè)時(shí)代的傳聲筒,也不是下一個(gè)時(shí)代的代言人,兩個(gè)時(shí)代都不屬于他。具體表現(xiàn)是,在大量的文學(xué)現(xiàn)象的名稱上加上“引號(hào)”,使其在敘述中“升級(jí)”且“懸置”(這種作用與“元敘事”的作用是近似的),比如他發(fā)明的“百花文學(xué)”一詞,就將原本因?yàn)椤半p百方針”頒布而形成的活躍局面,大量“干預(yù)生活”和進(jìn)行“人性探索”的作品,以及在稍后遭到了批判等這一復(fù)雜的歷史情境,悉數(shù)裝入到這一詞語之中,使其具有了“歷史的客觀性”和“令人疑慮的待解說性”。也就是說,在早期的文學(xué)史寫作實(shí)踐中,洪子誠先生就已經(jīng)建立了這種特殊的文學(xué)史話語。
這在以往的文學(xué)史敘述中,都是很難做到的。作者總是“與歷史站在一起”,因而也就獲得了一個(gè)“正確地位”,“歷史正確的制高點(diǎn)”,然后有了語勢滔滔的雄辯和指點(diǎn)江山的權(quán)威。這種敘述就像前文中洪子誠著作所引述的周揚(yáng)的話語“目前中國文學(xué)……”一樣,是一種不容置疑的判斷。這并非個(gè)例,即便是在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jì)文學(xué)主流》這樣的著作中我們也能夠看出,作者與他所講述的那些作家與文學(xué)現(xiàn)象是完全站在一起的,他們是應(yīng)了歷史的感召,為了一個(gè)共同的使命匯聚在一起的。“這些互相影響、互相闡釋的思想界杰出人物形成了一些自然的集團(tuán)。我準(zhǔn)備描繪的是一個(gè)帶有戲劇的形式與特征的歷史運(yùn)動(dòng)。我……把他們看作是構(gòu)成一部大戲的六個(gè)場景。”④在勃蘭兌斯的文學(xué)史敘述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就在文學(xué)現(xiàn)場”的,所以他是時(shí)時(shí)以目擊者、親歷者的語態(tài)來進(jìn)行表述的,其褒貶和臧否的態(tài)度亦是一無保留的。而洪子誠先生的文學(xué)史敘述,卻總是以一個(gè)“遲疑”的審慎角色出現(xiàn),以中性或接近中性的話語來推演的。
很顯然,洪子誠先生強(qiáng)化了一種“能述則不論”的敘述語體,這與以往“論從史出”的研究方法構(gòu)成了明顯的區(qū)別。而且他的“述”總是從材料出發(fā),試圖獲得與事實(shí)最近、信息量最大,在文字上更可信的效果。另外,他刻意平實(shí)的風(fēng)格也使得其文字更好讀,更具史家筆法,比如他還通過“重新發(fā)明歷史”,如“一體化”“百花時(shí)代”“文學(xué)資源”“進(jìn)化的文學(xué)觀”等一系列詞語,將歷史“再客體化”,這都從根本上改變了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敘述方式,也根本上改變了當(dāng)代文學(xué)原有的學(xué)科話語體系。
在此文即將結(jié)尾的時(shí)候,忽然想起洪子誠先生數(shù)年前的一篇奇文,名字記不太清了,大概是《與音樂相遇》之類,是談?wù)撔に顾凭S奇、拉赫瑪尼諾夫、馬勒等幾位古典音樂家作品的文章,遂知道洪子誠老師居然還是一位古典音樂的發(fā)燒友。音樂我不太懂,但從中分明感受到了洪老師那顆通常不會(huì)激揚(yáng)澎湃的心,它在平靜的外表下跳蕩著,讓我感到了那個(gè)不同于史家的洪先生,靈魂燃燒,靜水流深,讀之不免夜不成寐,幾乎完全改變了原先對(duì)他的看法——并非只有一個(gè)清冷而瘦削的學(xué)問家的洪老師,這世界上還有一個(gè)有著柔軟內(nèi)心和琴弦般敏感神經(jīng)的洪老師。他真切地面對(duì)著歷史,感受和記憶著那些曾經(jīng)的苦難,并且在沉穩(wěn)而平靜的文字中記錄下它們,仿佛把一個(gè)個(gè)相似而又不同的精神樣本,悉心地收納進(jìn)歷史的博物館。
這大概也是他“洪氏話語”的一部分了。
我甚至產(chǎn)生了這樣的想象:洪先生的肉身是用以做學(xué)術(shù)的,偏瘦而謙卑;但洪老師的靈魂是用來感受偉大藝術(shù)作品和追求人類正義的,這靈魂非常豐腴且高貴。
【注釋】
①洪子誠:《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前言》,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第2頁。所引周揚(yáng)的話,出自《周揚(yáng)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5,第186、191頁。
②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第699頁(見洪子誠先生原注)。
③戴衛(wèi)·赫爾曼:《新敘事學(xué)》,馬海良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2,第20頁。
④勃蘭兌斯:《十九世紀(jì)文學(xué)主流·第一分冊·流亡文學(xué)》,張道真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0,第1、3頁。
(張清華,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