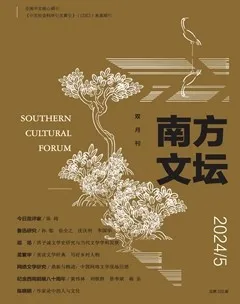中國雕塑的本土化:文化策略與當代實踐
一、何為雕塑“本土化”?
“本土化”的英文為“indigenization”(名詞),“indigenize”(動詞),其含義非常寬泛,相較于“全球化”而言具有“國產(chǎn)化”“本地化”“在地化”或“民族化”等含義。針對“拿來”或“進口”的現(xiàn)當代中國雕塑而言,具有“中國特色”的雕塑是其目標指向,因為社會的驅(qū)動力不僅僅要滿足對西方文化“嫁接”或“移植”,更重要的是要滿足不斷“創(chuàng)新”與“創(chuàng)造”的終極訴求。因此,“本土化”與“全球化”應該是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統(tǒng)一,也應當是與“現(xiàn)代化”“科學化”“先進化”“國際化”的統(tǒng)一,是民族“獨立性”與他者“移植性”的統(tǒng)一。
從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視角來看,“本土化”不僅僅是雕塑所面臨的課題,而是涉及各個學科門類的宏大課題。當下,“本土化”已經(jīng)成為學術界討論的較為普遍的課題,不同學科領域?qū)Α氨就粱庇兄煌脑忈尅S械膶W者認為“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視野下,對外來先進文化的引進和融合,最終形成以本土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的過程①;有的認為“本土化”是“一種文化重組”,也意味著在本土地域中形成了“具備獨特性的新質(zhì)”②;有的認為“本土化”是民族文化具有的“本土的、個性的或傳統(tǒng)的”特點以及“另指外來文化融入本土”③;有的認為“本土化”是“異域異族異質(zhì)的‘他者’理論在滿足本土化的條件之下,經(jīng)過本土化機制的規(guī)約、融合、內(nèi)化、操作與變革,使外來理論順利引入、借鑒與轉(zhuǎn)化的本土理論與實踐的生成過程”④。還有的學者認為“本土”不同于“地域”,“本土性”不同于“地方性”,“地域”是地理學意義上的,而“本土”是精神性的,它有著文化意義上強大的主體意識,正是因這種主體意識的存在,才形成令人仰望的精神地貌⑤。以上闡述雖對“本土化”的內(nèi)涵側(cè)重不同,但其本質(zhì)是相同的。
再來從全球化經(jīng)濟文化視角下來看“本土化”,“全球化”(glocalization)與“本土化”是相對的概念,“既指視角也指行為,主要關注特殊性和地方性”⑥。早在20世紀80年代,世界經(jīng)濟學界出現(xiàn)了“全球化”這一學術主語,主要是強調(diào)全球化的商品要結(jié)合本土文化才能獲得成功,“麥當勞”的成功就是全球本土化的經(jīng)典案例,遍布全球連鎖店的菜品根據(jù)各地飲食文化而各有不同。《全球化:社會理論與全球文化》的作者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將“全球化”概念帶到了文化領域,為全球化理論拓展了新的維度。他的靈感來源于一個日語單詞“dochakuka”。“這個詞指根據(jù)不同地域狀況而調(diào)整自身耕種技術的一種耕種策略,20世紀80年代,它成了日本企業(yè)中的專業(yè)術語——‘微觀市場營銷’(micro-marketing)策略,指跨國性產(chǎn)品必須根據(jù)不同地域的特殊文化、習俗與特色而做適當?shù)恼{(diào)整,以契合和打入地方市場的一種策略。”⑦他深受啟發(fā),認為詞匯的內(nèi)涵超越了全球化理論中的宏觀與微觀的二元對立論,“一種雙向互動的過程,普遍的特殊化和特殊的普遍化”⑧。由此可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雕塑“本土化”內(nèi)涵也要放到“全球化”的語境中闡釋才能找到相應的坐標。
通過以上的分析能夠基本地揣摩到“本土化”的內(nèi)涵,但是要完整地揭示中國雕塑“本土化”的內(nèi)涵,還要將其放到中國雕塑發(fā)展的歷史維度之中。從中國現(xiàn)代雕塑到當代雕塑的發(fā)展脈絡來劃分,不難看出中國雕塑“本土化”的內(nèi)涵是不斷深化和豐富的。第一個階段,“本土化”內(nèi)涵是引進西方的雕塑方法來做中國主題的內(nèi)容。這一階段的中國雕塑的主要任務是“啟蒙”“強調(diào)科學、理性的精神”,是將西方雕塑“觀念”與“趣味”向大眾灌輸和普及⑨。第二個階段,是經(jīng)過一段時期對西方雕塑的學習與消化,雕塑家在具備扎實的西式雕塑基本功的條件下,將中國古代雕塑的語言和民間藝術的造型樣式與西式雕塑造型相融合的探索過程。這一階段,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民族化”文藝方針到《論十大關系》和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全國文藝界掀起了民族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回歸的浪潮。第三個階段,“本土化”內(nèi)涵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不斷拓展,是傳統(tǒng)造型、傳統(tǒng)文化與物質(zhì)符號、傳統(tǒng)審美、傳統(tǒng)哲學、地域人文與民族精神的全面探索。這一階段可謂是“多元對話”語境,此時的“本土化”內(nèi)涵不僅僅是一百年以前的西學東漸,更多的是代表著一種創(chuàng)新與開拓精神,中國當代雕塑的本土化既是對全球化的抵抗,又是其發(fā)展的產(chǎn)物。這不單純是西方雕塑如何在中國生根結(jié)果與中國雕塑的優(yōu)化和當代化的問題,最重要的終極問題是中國氣派與中國特色的形成與持續(xù)發(fā)展。
綜上,本文探討的中國當代雕塑的“本土化”內(nèi)涵包含上述豐富的內(nèi)容,總結(jié)出兩個特征:一是對異質(zhì)雕塑文化的吸納,二是在吸納異質(zhì)雕塑文化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新的具有民族精神內(nèi)核的中國當代雕塑。這兩點是與全球化博弈與對話的前提,可見,“本土化”的目的就是“全球化”。
二、雕塑本土化的生成邏輯與文化策略
近代的中國遭遇了“數(shù)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從清末到民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浪潮之下,“救亡和啟蒙”便成為時代主題。從魏源倡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王國維提出的“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不難看出對西方科學技術、社會體制、文化思想的向往與效仿,社會意識轉(zhuǎn)型使一大批有識之士堅持不懈地師法西方,中國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程由此而開啟。伴隨而來的還有“民族化”“民族主義”“民族精神”等思想觀念,在激蕩的社會變革與東西方思想文化碰撞的時代背景之下,文化“本土化”的問題開始被世人思考,成為中國學術界共同面臨的重要命題之一。
雕塑的“本土化”及相關的思想觀念彰顯出文化自覺的強大內(nèi)生動力,既是對傳統(tǒng)文化將崩塌彌留之際的拯救與重構(gòu),又是對強勢的西方文化話語的無聲抵抗。中國思想界在20世紀20年代關于“全盤西化論”與“中國文化本位論”的爭論對文藝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爭論之激烈既體現(xiàn)出當時文藝工作的文化焦慮,又反映了他們對民族精神與傳統(tǒng)文化捍衛(wèi)與復興的訴求。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中作的報告《中國共產(chǎn)黨在民族戰(zhàn)爭中的地位》,他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宣傳“民族化”的號召,“創(chuàng)造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939年,延安的宣傳與文化界開展了一場“舊形式的利用”與創(chuàng)作文藝“民族形式”的文化運動,“民族形式問題”在全國范圍內(nèi)獲得了積極響應。1940年毛澤東同志發(fā)表了《新民主主義論》,提出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其內(nèi)容和性質(zhì)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1942年,毛澤東同志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此之后“中國共產(chǎn)黨確立了文藝革命化、大眾化、民族化的方針,其后‘民族化’逐漸成為一種顯性和主流的話語”⑩。1956年,毛澤東同志發(fā)表了具有深遠影響的《論十大關系》和關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講話。這一講話中,他首次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指導方針——“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再一次推動了民族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回歸的進程。2014年,習近平同志發(fā)表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11講話是新時代文藝工作的風向標,再次為文化的“本土化”進程指明了方向。
20世紀初,“雕塑”一詞由日本傳入中國,與此同時西方雕塑體系被留洋學子帶回國內(nèi)。雕塑“本土化”問題成為擺在雕塑家面前的命題。中國雕塑歷經(jīng)百年之變遷發(fā)展至今,經(jīng)過多次藝術觀念的傳入、學習、探索、轉(zhuǎn)型,即是雕塑“本土化”的歷程。1979年改革開放,西方藝術再次涌入,與前幾次不同的是,這次是以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為先導的各種藝術思潮的同時涌入,并且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多樣化的藝術思潮紛紛涌現(xiàn),形成了一種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且多元共生的局面。劉驍純提出“如果說‘五四’以來的中西之爭,以西方古典藝術的中國化和新美術的幾度榮衰為最終成果的話,那么,這一次則以西方現(xiàn)代藝術思潮的涌入為先導,經(jīng)過難以預料的波折起伏,最終將以對古今中外文化成果自由吸取的、多元化的中國當代藝術的振興為輝煌成果”12。孫振華在談論中國雕塑近30年的發(fā)展脈絡時,把1979年以前的中國雕塑總結(jié)出了三個傳統(tǒng):一是“西方古典主義”的雕塑傳統(tǒng);二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雕塑傳統(tǒng);三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雕塑傳統(tǒng)。“在以上三個傳統(tǒng)中,最有張力、最有沖擊性和顛覆性、最富于變革精神的,應該是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雕塑傳統(tǒng)。因為它針對過去而言,代表了一種新的知識形態(tài),對它的關注、研究和實踐,成為當時中國雕塑發(fā)展的重要線索。”13這條重要的線索也是中國雕塑“本土化”的前提條件。
從1979年至今,中國當代雕塑的發(fā)展得到了優(yōu)越的社會環(huán)境與豐富的文化資源的支持。全球化背景下的當代文化交流呈現(xiàn)多元化的發(fā)展特征,各個種族、國家、地區(qū)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整體上呈現(xiàn)融合趨勢,但又帶有文化的對抗與沖突。面對新時代的文化發(fā)展形勢,2014年,習近平發(fā)表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中國文化指明了發(fā)展方向,他提出“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guī)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xiàn)中華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14。中國雕塑“本土化”過程中也要面對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問題,中國雕塑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即是對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轉(zhuǎn)化,就是文中提出的“古為今用”與“洋為中用”。在轉(zhuǎn)化過程中要以自身的文化立場為中心,強調(diào)民族性與時代性。
“古為今用”不能將傳統(tǒng)文化原封不動地拿來,要符合當代價值觀才能為今所用,根據(jù)現(xiàn)當代時代精神與價值追求來取舍,并運用當代文化表現(xiàn)形式來呈現(xiàn),在時代精神的框架下對其內(nèi)涵進行闡釋。“洋為中用”的思想早在100多年前魏源、林則徐等人士就開始提出,西方文化傳入中國也開啟了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洋為中用”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又有新的語境,即以民族性為內(nèi)核。因此,避免崇洋媚外和盲目排外是中國文化發(fā)展的共識。民族性為內(nèi)核是對外來文化的基本態(tài)度,首先,外來文化的融入需要符合中華民族文化自身的表現(xiàn)形式,吸收對自身文化發(fā)展有益且符合社會集體價值取向的部分,去其糟粕;其次,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外來文化,要對其本土化轉(zhuǎn)化,同時要符合傳統(tǒng)文脈的承接與當下社會大眾的精神訴求。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在當今世界的文化發(fā)展中具有強烈的文化指向,既代表了堅定的民族立場,又有著開放的國際視野。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并不是分開的,也不能以靜態(tài)的眼光來對待,它們是以一種動態(tài)的并且面向未來的方式,推進中國文化創(chuàng)新性的持續(xù)發(fā)展。因此,“本土化”并不是讓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適應,它是包含著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在新時代進行創(chuàng)造性可持續(xù)發(fā)展,形成新的中華民族文化的過程。
縱觀歷史,經(jīng)歷了一個多世紀的實踐與探索,中國雕塑已經(jīng)由“外來之物”在本土化的進程中融入了“民族的血液”,初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門類。回望中國雕塑“本土化”發(fā)展,取得了許多成就的同時,也經(jīng)歷了許多挫折。總結(jié)中國雕塑各個時期的“本土化”歷程所呈現(xiàn)的不同特點和轉(zhuǎn)化規(guī)律,并揭示蘊含在中國雕塑本土化過程中的內(nèi)在邏輯與發(fā)展脈絡的深層譜系,研究分析中國雕塑“本土化”的具體面貌的內(nèi)在聯(lián)系與動因,在當下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中國雕塑發(fā)展到今天已然進入了嶄新篇章,過往成就毋庸置疑,但是“本土化”過程中也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與困惑,依舊在何去何從中徘徊。
面對中國雕塑的過往與當下,中西方文化、中西方雕塑體系及當今世界經(jīng)濟文化之格局,這些既構(gòu)成了中國當代雕塑“本土化”和對其研究的統(tǒng)一背景,又是中國當代雕塑實踐與理論研究所面臨的問題與要求。
三、雕塑本土化的創(chuàng)作路徑
民國時期中西方文化進行過激烈地碰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大陸尚未打開國門。滑田友、王臨乙、楊英風、文樓、熊秉明、朱銘為代表的港、臺及留(旅)洋藝術家,他們的作品在本土化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實踐經(jīng)驗,雕塑呈現(xiàn)的創(chuàng)作路徑以及在當代雕塑中的拓展,亦有不可忽視的現(xiàn)實意義。20世紀五六十年代,許多港臺藝術家和身在海外的中國藝術家不約而同地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突破口,將傳統(tǒng)符號作為藝術創(chuàng)作的源泉,希望能創(chuàng)作出帶有濃郁東方神韻并能被西方所理解和接受的現(xiàn)代藝術作品。藝術家追根溯源,在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進而創(chuàng)作出具有東方神韻和現(xiàn)代情懷的佳作。通過比較發(fā)現(xiàn)有幾條重要的本土化的雕塑創(chuàng)作路徑:
(一)傳統(tǒng)雕塑的本體語言的轉(zhuǎn)化
傳統(tǒng)雕塑語言最早的探索者是滑田友與王臨乙。滑田友學習研究西方雕塑的同時把中國傳統(tǒng)畫論中的“六法”融入其中,他發(fā)現(xiàn)中西方藝術作品都是做到了“通體‘貫氣’”15。早在留法期間創(chuàng)作的浮雕《長跪問故夫》已經(jīng)頗具中國之風。之后,他用“氣韻生動”之法創(chuàng)作了《轟炸》《農(nóng)夫》《母愛》,形體上的凝練與漢俑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形式上均以高度概括的手法對雕塑的輪廓及細節(jié)進行歸納,強調(diào)大塊面的形態(tài)轉(zhuǎn)折及人物面部的神韻,達到了整體貫通、氣韻生動的效果。
王臨乙在留法期間并沒有停留在對西方雕塑的研究,而是探索中西方雕塑相通之處。他創(chuàng)作的《供養(yǎng)》《大禹治水》《孔子像》等吸收了漢代畫像石(磚)及漢魏雕塑的表現(xiàn)手法,作品渾厚、有力、簡約、古雅,對整體氣勢和意蘊的追求體現(xiàn)出他對古代雕塑的深刻認知。在作品《五卅運動》中,他并未采用常用的人物分組方式,而是借鑒了北魏浮雕《帝后禮佛圖》的構(gòu)圖精髓,巧妙地運用了平行構(gòu)圖法,營造出一種連綿不絕、橫向流動的視覺效果。這一創(chuàng)新設計使觀者仿佛置身于行進中的工人隊伍之中,感受到他們向畫面外無盡延伸的磅礴氣勢。浮雕中巧妙構(gòu)建人物層次,通過精心組合不同人物,巧妙形成了三個層次分明的空間,為畫面增添了厚重的歷史感。
當代雕塑繼續(xù)對傳統(tǒng)雕塑的本體語言進行學習與探索。例如:邢永川的《楊虎城將軍》汲取了漢代茂陵石刻的“怪”與“野”,以及唐陵石刻的“拙”與“憨”,形成了獨特的雕塑語言;曾成鋼的作品揭示了青銅器中線條的力量感與生命力,他將這些富有動感和節(jié)奏的線條稱為“青銅線”,并巧妙地將這一雕塑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蔡志松的《故國》系列作品獨樹一幟,其融合了兵馬俑的莊重、古埃及的神秘、希臘古風時期的典雅以及瑪雅時期的原始韻味。
(二)傳統(tǒng)哲學的轉(zhuǎn)化
楊英風是中國臺灣20世紀60年代以來具有國際影響的雕塑家之一,他崇尚自然之美,將中國“天人合一”的美學思想作為自己追求的終極目標16。坐落在美國紐約的《東西門》,天圓地方(方形墻面加圓洞),以中國園林的“借景”手法通過不銹鋼材料的反光效果,觀念雖然極為前衛(wèi),“但所依托的仍然是東方庭園中的月門造型。至于細節(jié)處,如墻面轉(zhuǎn)折的地方有意借鑒了中國卷軸畫的裝裱形式……這一切既在形式上與西方極少主義雕塑有別,又在含義上恰好吻合貝聿銘設計的東方海外大廈的環(huán)境”17。楊英風的“太魯閣山水系列”自1969年起孕育而生,歷經(jīng)十數(shù)載,通過山川、水流、田野、晨曦與微風等抽象形式,深刻映射出他對東方哲學的獨到見解。
在當代雕塑中,這條路徑也有不少雕塑家在努力探索。例如:傅中望的作品巧妙展現(xiàn)了傳統(tǒng)榫卯結(jié)構(gòu)的獨特魅力。他深知榫與卯,一凸一凹,恰如中國傳統(tǒng)哲學中的陰陽關系,相互依存、相輔相成;陳輝的《高山流水》系列作品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的深刻詮釋;郅敏作品從形而上的哲學思考出發(fā),對河洛易數(shù)、四神天象,以及二十四節(jié)氣進行抽象表達。
(三)傳統(tǒng)文人審美的轉(zhuǎn)化
文樓是中國香港20世紀60年代以來為數(shù)不多且頗具影響力的雕塑家,他以金屬直接焊接的方式,將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抽象語言與中國傳統(tǒng)文人審美結(jié)合。他的《荷》《竹》系列作品表現(xiàn)出文人風骨之精神。《竹》系列從中國畫中汲取養(yǎng)分,作品以線條的流暢、墨色的層次和空間的布局展示了傳統(tǒng)國畫構(gòu)圖方法,為缺乏傳統(tǒng)西方藝術欣賞基礎的中國人提供了一條新的欣賞雕塑作品的途徑。此外,在《荷》系列作品中,一方面展示了對材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運用;另一方面又充滿了傳統(tǒng)繪畫中文人畫荷的韻味,使得這些作品在展現(xiàn)出金屬雕塑的硬朗與精致的同時,也流露出一種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溫柔與深邃。
這條路徑在當代雕塑中也得到了拓展,例如:霍波洋的作品中多構(gòu)造巨石、枯木、懸崖、孤竹、殘荷、野橋、荒渡等文人精神世界的場域,將人物極簡,隨意組合,人與境交融,盡顯出傳統(tǒng)文人的精神追求;展望的不銹鋼“假山石”挑戰(zhàn)了人們對于“真實”的傳統(tǒng)認知,通過不銹鋼復制的賞石,讓我們重新思考,哪一種山石更能真實地反映當代中國的文化面貌,它們雖非自然之物,卻真實地反映了當代中國的審美觀念和文化趨勢;譚勛的作品通過對日常物品進行文人化改造,讓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這些物品背后的文化意義和價值,同時也讓我們更加關注和反思現(xiàn)代社會中人們的生活狀態(tài)和文化身份。
(四)傳統(tǒng)筆墨與意象的轉(zhuǎn)化
熊秉明的鐵鶴系列雕塑展現(xiàn)了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將中國書法線條的精髓與雕塑的構(gòu)成完美融合。他以書法的思維方式為指引,精心組合鐵條的形態(tài)、彎曲、長短以及位置擺放、比例關系、間架結(jié)構(gòu)等要素,從而創(chuàng)作出富有東方韻味的線條藝術。為了實現(xiàn)雕塑與書法藝術的和諧統(tǒng)一,他選用了方棱的鐵條作為創(chuàng)作材料,這種材料經(jīng)過壓、彎、曲、折等工藝加工后,所形成的形體韻律與中國書法的線條在形態(tài)上高度契合。線條狀的材料使得“東方式”的抽象線條得以更好地展現(xiàn),賦予了雕塑作品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文化內(nèi)涵。鐵鶴系列雕塑不僅展現(xiàn)了雕塑藝術的獨特魅力,也體現(xiàn)了書法藝術的深厚底蘊。
當代雕塑把這種寫意美學往前推動了一步:孫家缽的雕塑充滿了寫意的風采,體現(xiàn)了古代雕塑中的“得意忘象”,同時又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繪畫中的“意筆草草、不求形似”,他在木雕上留下即興的削砍痕跡,與水墨畫中的“斧劈皴”有異曲同工之妙;陳云崗對線的運用是采用中國寫意山水乃至書法的方法,以線入塑,具有一種書寫性,在其作品《老子》中,一道道如漣漪般的線自眉眼處往外延伸,由細變粗,由少變多,正契合老子道生萬物的哲思;吳為山將水墨畫大寫意精神帶入雕塑創(chuàng)作之中,“寫”這一技法充滿了書法筆法的深遠意境,其“雕塑筆觸”如同書法家的筆觸一般揮灑自如。
(五)傳統(tǒng)文化符號的轉(zhuǎn)化
朱銘在青年時期開始練習太極,與太極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太極代表著一種動態(tài)平衡的運動與變化,其中陰陽相互對立、滲透、作用、轉(zhuǎn)化,生生不息。這種哲學體現(xiàn)了宇宙對立統(tǒng)一的規(guī)律,是最原始的古代哲理之一;同時,它也體現(xiàn)了中國哲學的特點,即重視感悟而非論證,既非依附科學亦非依附宗教。太極的哲學深深吸引了朱銘,使他開始創(chuàng)作“太極”系列作品。朱銘在“太極”系列作品中,不僅展示了太極的動態(tài)平衡和陰陽變化,還傳達了宇宙間對立統(tǒng)一的哲學思想。這種獨特傳統(tǒng)符號,使他的作品受到廣泛的贊譽和認可。
當代雕塑利用傳統(tǒng)符號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成為一種趨勢:董書兵的作品《無界》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邃的內(nèi)涵,成功地將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唐代《經(jīng)變畫》的精髓融入現(xiàn)代藝術創(chuàng)作之中,作品所傳達的“無界”理念,也是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之間界限的一種突破和超越;何鎮(zhèn)海的《門閂》《門》《陶木結(jié)合》系列作品都是在尋根傳統(tǒng)文化,運用傳統(tǒng)符號進行結(jié)構(gòu)與重組,喚起強烈的民族集體記憶;劉永剛對漢字進行立體化創(chuàng)作,其作品絕不是簡單嫁接、挪用,每個雕塑形態(tài)都經(jīng)過反復的推敲,抽取文字中線與立的因素,形成了獨一無二的站立的文字。
四、結(jié)語
中國雕塑的“本土化”不僅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和發(fā)揚,更是對西方文化的吸收與轉(zhuǎn)化。它體現(xiàn)了中國藝術家的文化自覺和自信,展現(xiàn)了在新時代背景下,中國雕塑如何與世界藝術對話,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中保持自身的獨特性和創(chuàng)造性。面向未來,中國雕塑的“本土化”將繼續(xù)在探索與實踐中前行,尋求與時代精神相契合的藝術表達,通過不斷地自我革新和開放包容,中國雕塑將在世界藝術舞臺上綻放更加奪目的光彩,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東方與世界的橋梁。
【注釋】
①王麗新:《奧爾夫音樂教學法的本土化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2012,第18頁。
②梁江:《本土化:百年中國油畫的主題詞》,《文藝研究》2005年第8期。
③李國慶、宋國彬:《平面設計及其設計元素的本土化與再造》,《包裝工程》2004年第6期。
④龔孟偉:《當代課程理論本土化探析》,《教育理論與實踐》2010年第7期。
⑤邱正倫:《構(gòu)建,必須從本土立場開始》,《美術觀察》2009年第2期。
⑥安娜貝拉·穆尼、貝琪·埃文斯:《全球化關鍵詞》,王德斌主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81頁。
⑦單波、姜可雨:《“全球本土化”的跨文化悖論及其解決路徑》,《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⑧金惠敏:《文化帝國主義與文化全球化——約翰·湯姆林森教授訪談錄》,《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⑨孫振華:《中國當代雕塑》,河北美術出版社,2009,第4頁。
⑩李竹:《文化自覺與身份認同:重慶雕塑的民族化探索(1940—1960)》,《中國美術》2022年第1期。
1114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
12劉驍純:《解體與重建》,江蘇美術出版社,1993,第293-294頁。
13孫振華:《資源與拓展——近三十年中國雕塑的發(fā)展脈絡》,《文藝研究》2009年第1期。
15滑田友:《談雕塑的組織結(jié)構(gòu)》,《美術》1959年第8期。
16王志剛:《略論楊英風雕塑藝術美學風格》,《西北美術》2002年第2期。
17丁寧:《楊英風:一個有思想的雕塑家》,《中國美術》2012年第2期。
[劉宇航,廣西藝術學院造型藝術學院、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胡筠,通訊作者,廣西藝術學院造型藝術學院。本文系“廣西高等學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師培育計劃”人文社會學科類立項課題“數(shù)字技術植入雕塑創(chuàng)作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21QGRW049;2022年度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礎能力提升項目“傳統(tǒng)語境下的中國當代抽象雕塑研究(1979—2020)”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22KY0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