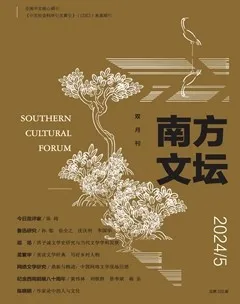海洋書寫的新南方之維
近年來,林森將自己的筆觸轉向了海洋,他有關海洋的作品占了相當的比例,以《海里岸上》《唯水年輕》《島》等為代表的海洋文學作品更是能夠代表林森現階段的關注重點,為讀者和評論者所津津樂道。從《海里岸上》到《唯水年輕》再到《島》,林森對海洋的認知不斷發展:從對“海”“岸”關系的反思到重構一種向海而生的生活方式,再到發掘一種源自海洋的文化底色并以之為契機對海南文化進行反思,海洋已經成為林森創作中的一個視角或者一種方法,借由海水的折射,林森看到了更多有關人類與世界關系的隱喻。
要理解林森的海洋文學創作,則需要將其置于“新南方寫作”的范疇之內。林森是“新南方寫作”作家群中的一員大將,也是這一文學浪潮的重要發起者與實踐者,其本人對此也有著很強的自覺,他將自己的創作稱為“走入南方蓬勃的陌生”①。“新南方”是一個極為豐富的概念,以某種本質性的概念來對其進行總結本身就是不現實的,但是,就林森的文學創作而言,“海洋”的確賦予了他比其他作家更“南方”的精神氣質,“新南方”與“海洋”在林森的創作中融合,形成了他獨特的文學氣質。林森的海洋文學顯示出“更南”的氣質便是源自于此,通過海洋,林森用筆建構著自己的“新南方”,并眺望著更遼遠的“新南方”之南。
一、非建構的新南方之海
“南北之別”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建構,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建構。這一建構大致起源于魏晉時期,直至唐代“南北之別”方成其形②,這一文化格局持續了千年,而到了晚清,“南北之別”有了一定的松動。錢基博稱:“五十年來學風之變,其機發自湘之王闿運,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粵(康有為、梁啟超),而皖(胡適、陳獨秀),以匯合于蜀(吳虞)。”③錢基博所列舉的近代學術譜系則皆在長江之南,這足以證明這種文化建構并非一成不變。“新南方”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對這種文化建構中“南北之別”的反思,“新南方”之“新”,其中本就蘊含著這種非建構性的特質。“新南方”是不證自明的,是自為的,不需要依靠所謂“南北之別”便能夠充分地展示自己。“新南方寫作”有著一種源自于世界視野的開放性,當那些執著于“南北之別”的作家們還在緊盯著地理意義上的界線之時,“新南方寫作”的作家們則越過重洋,將目光投向了與南北無關的遠方。海洋,在此時承載著新南方的意義。
林森的海洋文學創作正是這樣,他寫海,但并不僅僅是寫海岸邊的生活,而是用更多的筆墨去描寫不同身份的人群在海上的生涯,這在很大程度上便避免了在描述海洋時代入一種“陸地心態”。人類是生活在陸地上的生物,漫長的時光已經使“陸地心態”在人類的精神世界里形成一種話語上的霸權,人類總喜歡用陸地上的思維方式和尺度去衡量身邊的一切,使一切成為陸地上的“景觀”。不可否認,這種思維方式在大多數時候是有效的,但是對海洋文學而言,這種心態卻面臨著失語的尷尬。海洋文學所處理的問題很多時候超出了“陸地心態”的經驗范疇,《海里岸上》中寫漁民要“習慣暈船”,《唯水年輕》中寫一家幾代男丁都葬身海中卻又前赴后繼,《島》中寫一個人在孤島上漸漸習慣孤獨皆出自于此。林森筆下的海洋不是景觀式的、固化的意象,而是需要用生命去體驗的情境。
事實上,僅在20世紀中國文學的范疇內,海洋文學的經典作品就不算少,郭沫若在《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中寫到了洶涌澎湃的海,廬隱在《海濱故人》中寫到了浪漫感傷的海,冰心在《繁星》中寫到了平和安寧的海。到了21世紀,海洋文學掀起了一股熱潮,王蒙有《海的夢》,張煒有《黑鯊洋》,舒婷的《惠安女子》更是將海與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了一起。但是,在這些作品中大多存在著一個共性問題,即文本中的海看似在場,實則缺席,也就是說,海洋并未能作為一個主體出現在文本中,而是作為一個被觀察、被凝視的客體,靜靜地、被動地等待著作家的揀選。而在林森“新南方”觀照之下的海洋文學創作中,海洋主動參與到小說劇情的演進當中,不再是一個失卻主動性的、場域性的存在,而是小說的一個主體,是除了敘述主人公之外的另一個主人公。
在林森的海洋文學創作中,人與海洋的關系是平等的、對話性的。在《海里岸上》中,老漁民阿黃一生與海相伴,甚至因為捕魚而疾病纏身,但是,在阿黃對海洋的言語中仍能感受到他對這位相伴一生的朋友與對手的尊重:“大家靠海吃海,但現在沒人祭海了,大家都信儀器,不信儀式。一門心思只想著錢,漁村沒有了……沒有了……”人與海洋之間需要一種互動,需要一種靈魂的直接交流,是有溫度的,而不是通過冰冷冷的所謂“現代”儀器而達成的掠奪。而漁村的存在也正是這種交流后的產物,人與海洋達成了某種共識,雙方互相敬重,互相生成。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沖突是林森在書寫海洋時重點關注的問題,現代科技總以為能通過所謂“理性”來解釋整個世界,然而,它在面對海洋時是無力的,在面對海洋與人在精神維度的對話時是無力的。“大海養人也埋人”,“養人”與“埋人”也是互為表里的,那些被“埋”在海洋之中的靈魂是海的使者,通過各種方式提醒、護佑著后輩向海討生活的人們,而海邊漁民也將海視為自己最終的歸宿,漁民老蘇手抄的《更路經》最后一頁便是“自大潭往正東,直行一更半,我的墳墓”,在那些真正了解海洋的人們心中,海洋與人最終將合二為一。在《島》中,林森將海洋與人的對話關系書寫得更為驚心動魄,他仍是寫現代與傳統的沖突,以“現代”為借口,人們傾覆了海邊的博濟村,傾覆了記載著主人公吳志山一生的“鬼島”,甚至賦予這座荒島以“海星現代城”的名字,可是,就算是建設得再現代、霓虹燈再明亮,也無法還原海洋與人之間的關系。“這不再是一個島,這是一塊被機器橫掃過的工地。這里不再有生命的呼吸;不再有人在這里天天撿起石塊壘積,猶如西西弗斯;同樣,這里不會再有人刻下‘半生心事秋涼春暖愁歲月,永世恩情林秀風清憶海天’這樣的話”,在所謂“現代”的沖突之下,海洋與人之間的關系被人為割裂,從人類的角度出發,海洋失去了主體性,成為被欣賞、凝視的景觀,任人擺布;而從海洋的角度出發,人類也將不再為其所護佑,《島》中寫到了一系列人與海洋之間關系破裂后的異象——豬狗雞鴨的煩躁、魚群的死亡、幻覺中從海底而來的聲音和海怪,而這只不過是預警,更大的災難也許正在路上。
在林森的海洋文學寫作中,“新南方寫作”的視域帶給他更多的思考空間,在他的筆下,海洋因著其非建構性而豐富,也因著人類總想著要“建構”海洋、“賦予”海洋某種自己喜歡的文化景觀而蒼涼。林森書寫著海洋從非建構到被迫受建構的轉變,并呼吁能夠重構人與海洋的關系,但是,林森的海洋文學創作也并不是那種以環境保護為核心的“生態文學”,他所反思的是人,是那些生活在“新南方”的人,他們曾經習慣于被建構,而今,他們需要重新找尋一種能夠自我言說的方式,而這便是新南方之海的重要性,它打破了一種源自于陸地的話語霸權并對其進行反思,提供了一個可以觀察“被建構”過程的樣本,并搭建了一個可以平等對話的平臺。
二、內化的新南方之海
在對“新南方寫作”研究的過程中,很多評論者注意到了普遍存在于其中的“幻想”特質,并稱“他們的文字、故事和意象充斥著潮濕的、陰郁的、魔幻的、混沌的南方氣息”④,而如果深入發掘就會發現這種“幻想”特質的源頭——“新南方”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空間,更是一個無法被本質化思維所言說的文化空間,它的存在不僅僅是一個方位,更是一種集體認同或集體想象。人類喜愛為萬事萬物歸類,這樣方能獲得作為萬物靈長的安全感。近幾百年以來,人們總是習慣于用“科學”去審視身邊的一切,并稱之為“理性”,殊不知,此時的“理性”已經形成了一種話語霸權,它將一切對象化、物質化,但在物質世界之外,尚有“心”這一重空間是所謂“理性”所無法完全駕馭的。“新南方寫作”中的“幻想”特質則來自于此,“新南方”有很強的外向性,但首先它是向內而生的,它扎根于作家與主人公的“心”中。
林森筆下的海洋也正是這樣,這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場域”,而是一個“心域”,所謂“心域”,包含著外部的客觀世界與作家的主觀世界,同時,還包括了作品中人物的內心世界,林森的海洋文學書寫有一種自敘的性質,這并不是單指其小說常以“我”為主人公,更是指其在作品中常會安插一些自我抒懷性的文字。例如在《島》中,上來就是一句“有誰見過夜色蒼茫中,從海上漂浮而起的鬼火嗎?”《唯水年輕》中的“海神……頂天立地的海神……并沒有身軀立起,可海面下不絕的涌動,是不是他在潛游、嘆息和伺機而動?那么多年里,打罵的阻礙和攔截,沒能讓我完全隔絕于那片海”。這樣的敘述方式對很多小說而言是個大忌——能指過于寬泛的抒懷往往會讓讀者有一種漫無邊際的說教感,但是,對林森的海洋文學書寫而言,這種敘述方式卻構成了其藝術特色。在“新南方寫作”的視域下,林森在文本中的抒懷并非空有無限大的能指,相反,它是有著明確的對話對象的,這個對話對象是自己、是海洋也是讀者、是作品中的人物,這四者又在文本中達成了統一,使整部作品沉浸在一種被海洋環繞的氛圍之中。換句話說,在林森的海洋文學書寫中,寫海就是在寫自己。
“新南方”是自足的、非建構的,新南方之海亦然,這也意味著林森筆下的海洋并不是一個已經被概念化、本質化、定型了的景觀,而是一個在不斷運動、不斷更新、不斷突破自身原有形態的活的生命體。那些理性、科學的歸納對這片海洋是失效的,唯有不斷發展的經驗與內心世界的靈感能夠解釋這片海域中發生的故事。在《海里岸上》中,林森寫到了《更路經》的生成過程,與那些一經寫就則一字不易的所謂“經書”不同,《更路經》是伴隨著漁民的每一次出海而不斷成長,它與漁民的生命是緊密相連的。而對《更路經》的增補則更是一個不能用“定量分析”的“現代理性”所框定的過程,它與每一位漁民的一生緊緊相連,并通過捕魚這一行為反作用于漁民的一生。“一位船長,不僅需要掌舵,也是一個記錄者,隨時記下海上發生的一切。航行路線附近的水況、最新發現的魚群位置、島礁的位置……甚至云層也是觀測的對象。云天的變化,很少記錄在《更路經》上,那是出海人一種口口相傳的骨血經驗。白天,可以通過瞭望水面的顏色來判斷海水的深淺,判斷附近是否有礁盤——有礁盤的水要淺一些,日光下,是一種翡翠藍;沒有月亮的夜里,那些經歷了生死的老船長,通過云層的反光來分辨島嶼、珊瑚礁以及水下的魚群。”這些敘述向讀者們證明著經驗的重要,這種經驗并不是群體性的,而是與每一個獨立個體對世界的理解息息相關。甚至可以這樣說,在林森的海洋文學書寫中,每一位小說人物心中都有一片屬于自己的“新南方之海”,而讀者閱讀這些作品的過程其實也正是在尋找自己心中的那片海。
難能可貴的是,林森并未將這種海洋在人心理上的內化看作是一個理所應當的過程,相反的,他在多部作品中都嘗試梳理人與海洋之間密切聯系的脈絡譜系。《唯水年輕》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因為生活在海邊,人們不得不向海而生,由于向海而生,于是有人死于海上。由于有死亡的可能性,父親便一生不敢下海,而在海邊的生活早就把大海的回響印進了父親的生命,使他一生都生活在對海的恐懼與向往之中,最終,父親鼓起勇氣走向了海洋。這一行動線索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洄游,它是非強制性的,同時也是極大的蠱惑和召喚,人們自由地選擇自己與海的關系,但是,如果要真正面對自己、找回自己,則還需要勇敢地面對海洋。人與海洋之間的關系并不是浪漫的、精致的,而是現實的、粗糙的,甚至帶著一點殘酷,而這種殘酷也許正是人生的本相。
在“新南方”的寫作體系中,知識論往往是失效的,對“新南方”世界的理解需要生命來感悟,是需要以肉身作為媒介去體驗、去經歷的。而林森所構建的新南方之海也是如此,事實上,它本身就是建構在經驗與情感之上的,是具有生命的,而生活在海邊的人們通過勞作,將自己的生命與新南方之海緊密相連,經過了千百年的歲月沉淀,早已無法分割,這也是所謂“現代理性”所無法駕馭的。
三、新南方之海的可能性
《島》是林森海洋文學的重要作品,也代表了其對海洋理解的深度。通過“新南方”的視域,林森尋找到了“島”這個可以代表自己對海洋認知的意象。從這個意象出發,林森書寫了一片流動著的海洋,而流動,則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
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其能夠不斷對自己的生存狀態進行反思,隨著20世紀以來現代性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和發展,人對自身生存狀態反思的節奏也越來越急促,當人類目睹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之后,驀然發現“動”和“變”也許才是觀察世界的最合理角度。當20世紀末由“空間”“移動”構成的理論視野方興未艾之時,“流動”“間性”等理論范疇則進一步發展和更新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流動性雖然強調跨界、強調變動,但是它并不是不及物的,跨界和變動需要一個可以承載這種行動的主體,這個主體必然是人或被人格化的事物,同時,它也需要一類可以承載流動本身的主體,它必須能夠承載起流動行為的動因、結果以及其內涵,換句話說,它必須以一種文學意象的姿態承載著流動性,而這一點對林森而言,便是“島”。
在《島》中,島嶼構成了小說中一系列人物行為中流動性的起源,作為獨立于陸地的空間,人在島嶼上的生存方式本身就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政治結構。如果對生存與島上的人進行一番譜系學意義上的考察,不難發現,島嶼生活平淡和傳統的背后,是先祖們對于傳統人倫關系的破碎、想象和重組,而這一文化基因實際上對后世島民生存狀態的影響是深刻的,《島》中的人物向海而生、向海而死,要做“一世祖”等思維方式皆出自其中。尤其是小說中主人公吳志山與故鄉村莊隔海相望卻有著無法抹平隔閡的生存狀態,更是這種流動性的具體表現,人際關系的破碎并不意味著每個人的單子化,正像小說中描寫的場景一樣,在海南島之外還有一個個的小島,而這些小島卻因著看不見的大陸架而與海南島乃至大陸息息相關,沒有人能徹底逃脫。正如《島》這本書的封面上所言,“no man is an island”,這是一句約翰·多恩的詩,“沒有人是一座獨立的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其中一片,就像組成陸地的土塊,如果有哪一顆被海水帶走,整個歐羅巴都會減小”。這也正是“島”作為流動性文學意象的意義,“島”是一個有著很強反合性的存在,看似一個個的孤島,其背后不是與大陸的斷裂,而是與大陸在更深層次上的跨界和彌合,看似生活在“他人即地獄”里的個人,也可以看作是這樣的一座座島嶼,他們互相保持著距離,而在深處卻息息相關。《島》并不僅僅是一部關于海南的題材型小說,也不僅僅是一部反映城鄉轉型期間陣痛的小說,也不僅僅是一部反映個人生存境遇的小說,而是一部通過“島”這個流動性意象來重新探索人類生存方式的小說。而在這個意象的建構過程中,“新南方”是一個重要的視域和立足點。
對林森而言,海洋是其實踐“新南方寫作”的試驗場,他通過寫海洋來將“新南方”之“南”推向了一個極限,并通過建構人與海洋的關系來突破這種“南”的極限,將探索的筆觸伸向了更為遙遠的空間。其實,林森所思考的問題并不是如何去寫海洋,甚至是如何去寫“新南方”,他所關注的是如何將在“現代”侵襲下,被本質化、單一化理解方式所遮蔽的我們的真實生活狀態重新激活,使生活本身重新豐富起來。而在這一過程中,自南方而來的流動性以及其對人際關系與空間關聯的新視角將使讀者在這片現代性的荒蕪中重拾對“人類再生之自信”。
【注釋】
①林森:《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寫作》,《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②劉曉:《唐代南方士人的身份表達與士族認同——兼談中古時期“南北之別”的內涵演變》,《人文雜志》2020年第1期。
③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岳麓書社,1986,第509-510頁。
④梁寶星:《“新南方寫作”以及幻想文學的可能性》,《廣州文藝》2022年第4期。
(曾小娟,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