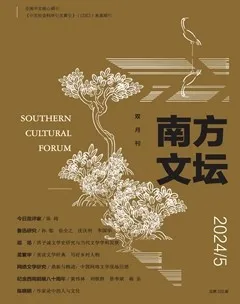我們時代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鄉土”?
近幾年來,關于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研究中的“地方性敘事”的研討逐漸升溫、熱鬧非凡。“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新浙派寫作”等“新區域書寫”,包括“新鄉土敘事”等提法和論述先后登場,不一而足。相關的理論、概念界說、作家和文本分類,成為研討會、論壇和雜志版面的焦點,持續不斷。我曾在《辯證看待地方性寫作風潮的價值》一文中發問,“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新浙派寫作”之“新”究竟落在哪里?它們的寫作及其文本形態、品質當中,有無迥異于以往的敘事理念、審美思維和敘事氣象?在這里,作家作為寫作主體,到底應該在其文本中生發、樹立起怎樣的文學精神?緣何會引發出文學評論界不大不小的陣陣“喧囂”?抑或這里所命名的“新”,就是指的文學“新人”之新嗎?究其根本所討論和命意的范疇,主要集中在不同代際作家之間的差異性比較嗎?“新東北寫作”“新南方寫作”“新浙派寫作”“新鄉土敘事”,會否是某種敘事的重啟?它們能否成為一種對當下寫作的超越性實踐?在這里,一些有關“新鄉土敘事”的理念倡導或“說法”,似乎有意地將其區別于前者。在界定有價值、有意義的“新”概念,進一步討論、認識和確立新的范式的前提,一定基于對當代作家的寫作現狀、寫作發生學、文本闡釋意義,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家和時代關系在內的諸多方面考量,進而從理論層面對新的敘事形態或特征進行深入梳理和界定,這無疑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這種概念的提出尚需要謹慎,而且要看它是否確有既成的、相對可觀的創作實際,在審視其文本實踐對過往寫作的繼承性的同時,尤其還要考量這些“新寫作”的創新性。
在我看來,“新鄉土敘事”與“新東北寫作”、“新南方寫作”、“新浙派寫作”、“新北京寫作”的區別,在于“新鄉土敘事”的“鄉土”相比較“東北”“南方”“浙江”“北京”等“區位”而言,具有溢出“地方知識”、區域歸屬的意味。“鄉土”本身蘊藉著更為豐饒的內涵。“鄉土”具有無與倫比的闊大的敘事空間,蘊蓄其間的人文性力量不可估量,也不可復制。正如弗羅斯特說:“人的個性的一半是地域性。”這無疑是要凸顯地方性、地域性環境、語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烙印,它對于作家的個性形成和塑造至關重要。對于每一位寫作者而言,地域性經驗可能會構成敘事的源頭般的力量。任何一個人從他出生開始直到生命的終結,無不帶有其出生地和成長地的印記,作家的人生“出發地”,往往就是他寫作的“回返地”。對作家而言,地域性早已不僅僅是一個空間的概念,獨特的地理風貌、世情習俗、歷史、現實和文化積淀,都已經成為他的寫作資源。無論是直觀的、隱蔽的,還是緘默的、細微的經歷,尤其那些“舊”經驗,充分地顯現出作家敘事的身份自覺,并且隨時都會激發他們的想象力、虛構沖動的產生。特有的、有記憶的空間感,或者說,那種對曾經擁有的空間的喚醒、頓悟,就是對世界、存在的再度確證、體認,這些無不具有富于個性化的、深層的溫度和氣息。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學敘事的“自傳性”品質不可或缺。所有的敘事框架或結構,都不可避免地鑲嵌著作家精神原鄉的靈魂、情感的絲帶。另外,我們必須注意到地域性、地方性也可能會給文學敘事帶來某種“類型”和局部的“經驗泛化”。因為空間作為地域性的顯現方式,在宿命般地饋贈給作家寫作資源的同時,也常常會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作家的個性優勢和審美獨特性。因為地域的內容,還有更多是社會性的,而且,它對于文學的影響是全方位且具有某種普遍特質。
“地域性”或“地方性”在多大程度上能給予作家自信,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敘事的自由,這也確是一個兩難的悖論性問題。在我看來,“詩人是地域的孩子,也是地域的作品”這種說法,其實也是給作家的某種警示。那么,無論“新南方寫作”“新浙派寫作”,還是“新東北文學”,這些“地方”既可能是屬于“這一個”作家的敘事起點,也可能成為慣性敘述的瓶頸,會使作家沉溺于曾經的、身體的、記憶的或精神的“鄉土”,也可能會讓作家難以進入想象的“自由王國”。越過浮游的高度地方化的藩籬,生成“看不見”具體地方的鄉土長焦遠景,才可能避免成為敘事的“類標本”。這些,都需要我們在對不同作家的具體創作和文本闡釋中獲得文學價值的確認。也就是說,賈平凹有賈平凹的鄉土,莫言有莫言的鄉土,遲子建有遲子建的鄉土。甚至,我們還可以追溯到魯迅、葉圣陶、沈從文和蕭紅,他們的寫作,無不是始終纏繞、盤踞在屬于他們自己的鄉土之上。20世紀初迄今,幾代中國作家念茲在茲、縈繞于懷的“鄉土”情結、鄉土情感和情懷,就是這樣,繁衍不止,生生不息,呈現出不同時代個性化的、別樣的鄉土。
我們在閱讀沈從文的《邊城》、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農村三部曲”時的感受是深刻的,對里面的人物也記憶猶新,它們都是現代文學鄉土敘事的經典之作。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鄉土、鄉村、鄉愁,既是一個地理概念,一種情感、情懷、情境,也是一個生態化的精神空間,文化、心理空間。所以,今天我們面對身處的時代,作家面對我們所處的生活,面對這個時代的各種變局,我們必須清楚我們是在一個什么空間位置上進行思考和敘事,依據什么樣的敘事視角、敘事倫理來書寫今天的鄉土。所以,就像“新東北文學”概念的提出一樣,今天的“新鄉土敘事”究竟應該有怎樣的敘事訴求?它的“新”在哪里?是“新時期”之新,還是較之蕭紅鄉土敘事的時代發生了新的變化?所以它這里面有個邏輯關系,也有一個概念定位的問題。因而,我們現在要探討“新鄉土敘事”,還必須清楚它在百年中國文學的敘事里營構的是一個什么樣的語境。
從新文學史的層面看,“鄉土敘事”的內涵始終在不斷地拓展,賦能作家的創作實踐。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形成了以趙樹理、丁玲、周立波等為代表的鄉土敘事。我們還可以回顧1980年代的“文化尋根”,韓少功的《爸爸爸》等文本,我覺得它們曾經也是鄉土敘事的一個獨特的敘事面向。“文化尋根小說”最初動機是讓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做出一個反駁,這時的鄉土敘事也被認為是文學敘事的根本選擇之一。所以,當時韓少功、阿城、鄭萬隆、李杭育等,他們都是能把敘述需要和愿望指向鄉村、指向鄉土的作家。2021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突出的“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倡導作家要從更廣闊的視野書寫新時代的山鄉巨變,書寫新時代的鄉土故事、鄉村經驗。吳義勤在“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推進會上,特別強調“不要機械、狹隘地理解‘山鄉巨變’。不要僅從字面意義理解‘山鄉’,要從象征層面、寓言層面、哲學層面去認識‘山鄉巨變’。某種意義上,中國大地上正在進行的史詩性實踐都有著‘山鄉巨變’的意義和內涵”,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視野和新時代偉大變革的大視角,深刻認識‘山鄉’,深刻感悟‘巨變’”①。縱觀鄉土敘事的歷史源流,我們現在提出“新鄉土敘事”,既是對既有創作的一次梳理總結,又是對未來新鄉土敘事的一種期待。這是一條視野開闊的闡釋路徑,“新鄉土敘事”提出的初衷不僅是對以往鄉土敘事的梳理,也是一種開放的期待和“鄉土敘事”的重新出發。生活和時代之變,必然敦促鄉土敘事之變。什么是新?什么又是舊?我們現在的“新鄉土敘事”,究竟是否或有何新的元素?我們正在寫作的鄉土書寫范式,是否延展了自“現代文學”以來近百年的鄉土中國語境和情境?說到底,我們現在的寫作,是否提供了時代生活的新內涵?現在所謂的新,是否比肩原來的“舊”?這也是對鄉土敘事倫理的一種讀解。
這里面或許還包括了人物塑造的問題,即“新鄉土敘事”是否給這個時代文學人物畫廊貢獻了新的形象。在此,我們不妨以賈平凹的鄉土敘事作為探討的視點,談論賈平凹《帶燈》的時候,有人曾提出帶燈這個人物是否是“社會主義新人”形象,她對于“新時代”文學鄉土敘事的意義是什么?在這里,我們的確認識到賈平凹著力塑造這個人物的價值所在。那么現在,我們的新鄉土敘事里面找到或者塑造出新人物了嗎?我們都期盼鄉土敘事里面有新的人物出現,這樣的人物應該是我們前所未見的,或者說,他能體現出鄉土敘事新的元素,將其聚焦在以人為核心的人的命運之中。賈平凹的書寫從《浮躁》開始一直到《秦腔》《古爐》《極花》《山本》,都極寫鄉土世界的精神裂變。《極花》,其實就是將中國鄉村作為窗口或視角,完成了百年中國鄉土敘事的這樣一個漫長的路徑。
賈平凹的寫作一開始就表現出鄉土敘事的“本色”“底色”或鄉土敘事的話語自覺。其文本的敘事語言形態和美學風貌,素樸、淳厚且有斑駁的雜色。賈平凹最擅長白描、寫實的手法,令敘事精微、文字綿密,尤其是氛圍和情境的營構獨具意蘊。那時的賈平凹就已然清晰地意識到“鄉土文學”的理念和精神,應該如何在敘事中內在地體現。沈從文文體風格和精神氣質的潛在影響,也在賈平凹文本的字里行間被悄然激活。他早期的小說《滿月兒》《好了歌》《晚唱》《商州》《小月前本》《雞窩洼人家》《臘月·正月》等,都是其自覺地觸及古老鄉村現實的興衰和矛盾,切身地體驗并發現鄉村的心理、精神、倫理和人性的律動的范本,應該說,他就是深切地“懷著真摯的、熱烈的情感”來書寫出鄉村社會的本色“生態”②。賈平凹此后數年內寫作的《秦腔》《古爐》《帶燈》《極花》和《山本》更加凸顯出其對鄉土世界的深深眷戀。特別是長篇小說《帶燈》,他在其間注入了鄉土書寫的諸多新元素,對我們今天的寫作有著重要的啟發。在討論這部小說時,我曾強調,“賈平凹喜歡將小說的結構,深深地植入當代中國的鄉村結構之中,在藝術地呈現當代鄉村生活中的倫理和文化的基礎上,審視人的自然天性和存在形態,進而寫出現實或歷史的沉重,文化的復雜性和迷惘狀態”。“對于自己太熟悉又寫了這么多年的鄉村,他這一次選擇了最貼近現實的追蹤。我們看到,在蕪雜的現實生活中,賈平凹打撈起無數瑣碎的遺落在鄉土中能發聲的和緘默的人與事,面對有血色、有震蕩、有焦灼的燃燒著的當下現實,賈平凹的目光和筆觸,幾乎完全卸掉了以往士大夫沉重的包袱,不再沉醉、悠然于遙遠的古風氣象,發掘民間固有的、隱藏的原始欲望,而是以現代的精神和理念凝視和描摹世相。”③在這里,賈平凹已將地球視為一個村落,將“櫻鎮”這個“地方”視為當代中國鄉村生活、鄉村社會的縮影,并且,將村鎮聚焦為蒼穹下的鄉村、鄉土影像。在其巨大的體內,既有世俗文化的怪影,也有現實中糾結的人性之間的相互沖撞,還有人們的焦慮不安的存在的暗影。直面原生態的現實世界,是一個有擔當的作家的敘事倫理和敘事選擇。它們體現出賈平凹在書寫當代鄉村現實時,竭力發現、發掘這一題材“新視角”的自信。
我們不妨再來看王躍文的《家山》,我認為這是他個人寫作史上迄今最好的作品。十余年來,王躍文悄然地探索鄉村世界中人與社會、人的生態的曖昧而渾然的處境,他對家鄉文化、禮俗的深切關懷,以想象和喚醒的姿態,讓鄉土的過往重新回到個人記憶的母體,敘事沉郁而凝重,通過對故鄉歷史的描摹,再次昭示那些遠逝的時間之流中人性的真實狀況。在這里,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座矗立的生命、宿命的“家山”,極其沉重的“家山”,也看到了一個有傳統、有秩序、有撞擊力并且在沉默和壓抑中抗拒衰朽的蘇醒的“家山”。《家山》這部長篇小說,并沒有像有些“鄉土敘事”那樣,執意地要為歷史和往事作證,而是為大歷史記憶中“曠野的微光”作出遙遠的緬想和述懷。《家山》的敘事語境和情境,不僅氣勢沉穩,重構鄉土世界的格局也極其闊大。作家在涓涓流淌的生活細流中竭力去理解生命、命運及其存在價值,重現歷史、時代的滄桑。可見,王躍文將我們帶入貌似綿長、略顯荒寒的時間向度,也讓我們細膩地咀嚼鄉村、鄉土、鄉情里的生命況味。這些,都深入地體現著王躍文的文學敘事倫理。“無論是大時代背景下鄉村的微瀾,還是鄉土世界的奇詭或人性盲點,都嵌入到《家山》細膩的文字里,同時,讓我們感悟到這個村鎮,以及一個個家族的生生不息的力量,這是一種‘再生性’的記憶與書寫,讓‘家事’重新回到歷史的縱深。”④
在這里,我不禁想起艾青的那句“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我想,這同樣是指向鄉土、鄉愁的難以割舍的情懷和記憶之殤。但是,在“新時代”我們如何再來書寫鄉土,能有什么樣新的視角,能寫出怎樣的新人物,這些都確是令我們非常期待的愿景。當代作家如何才能擺脫焦慮,重述鄉土世界的新狀態,也成為當下“新鄉土敘事”的重要方面。他們在書寫鄉土的時候,其實有一種倫理在里面,說它是一種理念也好,信仰也好,文學觀念也好,它決定著作家的敘事方式、敘事選擇。所以,敘事倫理是一個決定作家及其作品價值、作品成敗的關鍵因素。進一步說,鄉土敘事并不僅僅是一個空間的問題,更是一個如何安放靈魂的問題。
一個作家命定的鄉土可能只有一小塊,但深耕好它,你會獲得文學的廣闊天地。無論你走到哪兒,這一小塊鄉土,就像你名字的徽章,不會被歲月抹去印痕。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熟悉的鄉土,在新世紀像面積逐年縮減的北極冰蓋一樣,悄然發生著改變。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產生了農民工大軍,一批又一批的人離開故土,到城市謀生,他們擺脫了泥土的泥濘,卻也陷入另一種泥濘。鄉土社會的人口結構和感情結構的經緯,不再是我們熟悉的認知。農具漸次退場,茂盛的莊稼地里找不到勞作的人,小城鎮建設讓炊煙成了凋零的花朵,與人和諧勞作的牛馬也逐次退場了。供銷社不復存在,電商讓商品插上了翅膀,直抵家門。這一切的進步,讓舊式田園牧歌的生活成為昨日長風。⑤
如何才能真切地表達當代的鄉土、鄉情、鄉愁形態,給當代作家提出了更高的審美、敘事要求。我們看到,數十年來,遲子建始終沒有離開過對于自己的“故鄉”“鄉土”的回眸與深情呈現,雖然她的書寫不時地會有關于世界冰冷的悲訴和人性、俗世的喟嘆,但總有無盡的溫暖情絲,埋藏于字里行間,款款流溢而出,播散出希望的種子和無限的溫情。盡管用來描述“北中國”的詞語大多是“冷硬”“荒寒”“蒼茫”“蕭瑟”等,但是,在遲子建的敘述里面,我們總能夠體悟到具有充沛人性美的“骨力”“骨氣”“底蘊”的智慧與力量。亦可謂“洞燭世情之幽微”且詩化地再現仁愛、寬厚、溫暖的情感和玄思。遲子建的敘事,直面人生,直面自己堅守的那片“鄉土”,她在解析人性,展現人物性格,探求命運的機變時,令其敘事的“鄉愁”從沉重的鄉土里獲得另一種審美存在的形式。遲子建的鄉土小說敘事中,大量文本的敘事背景、審美觀照視野或視角,往往都不乏大歷史的宏闊和開放性。無論是長篇小說還是中篇小說、短篇小說,遲子建都無法擺脫向大歷史深度開掘的敘事沖動。長篇《偽滿洲國》《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群山之巔》、中短篇《候鳥的勇敢》《燉馬靴》《喝湯的聲音》等,一方面體現出關切大歷史的襟懷,其主題框架潛在地發散出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并且,在看似不經意間將敘事含蓄地拉升至大歷史的維度;另一方面,這些小說又包含對遙遠的歷史或當代現實和生活中小人物的日常書寫。遲子建對大歷史的包容度,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其小說對各種人物日常生活及其情感最個性化、私人化的呈現。因此,我們不妨說遲子建的敘事,大都是以情感為“軸心”或坐標的。對于遲子建小說的精神結構、敘事形態、美學氣質,我更愿意將其文本視為“鄉土”敘事對歷史、當代中國現實和情感的描摹和超越,竭力表達超越時代性經驗的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然,遲子建并不會賦予生活、現實更沉郁的理想化、浪漫化的詩意想象,她只是為鄉土、鄉情、鄉愁這些最神圣的敘事激情和動力驅使,去呈現自己心中的“神圣空間”原貌。從遲子建的小說文本,我們也能感受到她與鄉土、鄉情、鄉愁之間存有絲絲縷縷的“鄉愿”和“鄉怨”,后者或許就是所謂的“震顫中的裂縫”。但是,無論怎樣直面“北中國”大地上精神、情感的“裂縫”,遲子建的文字從未流露出焦慮,也不曾陷入無奈和惘然,她更愿意不斷重返歷史,重回故鄉,在鄉土、鄉情、鄉愁中咀嚼那剛毅而悲涼的骨氣。我感到,這些,才是遲子建最大的鄉土、鄉情和鄉愁。
我們的時代究竟需要書寫怎樣的鄉土?我們在為其賦名、命名的同時,也應當適度重溫并回到“舊時”“舊作”,重返至曾構建起中國鄉土書寫堅實骨骼的經典之作當中,汲取養分,打開個人與世界的視野,打開我們的想象,進一步提升說故事的能力,為那些“準備經典”之作采擷英華。即從鄉土敘事的“新”元素中,探尋、呈現個人與時代、現實與歷史的真實聯系,將寫作主體的個人情感植入社會、時代的脈絡中詠嘆,銘記社會生命的涌動和變化。因此,那經由生命體悟點染過的地方知識方有溫度,一如詩句中有言:“你們永不懂得/那樣的紅玉米/它掛在那兒的姿態/和它的顏色/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兒也不懂得/凡爾哈侖也不懂得。”⑥然而,我們應當懂得,鄉土敘事中潛藏著民族史詩,也懷抱著時代之新中人們情感史的絮語,讓我們的敘事,涵攝抒情、史詩的雙重特征,讓歷史和現實的敘事、書寫成為純然的當代中國的鄉土寫真。
【注釋】
①黃尚恩:《推動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向縱深發展——“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推進會綜述》,《文藝報》2023年7月19日。
②張學昕:《賈平凹論》,《鐘山》2020年第4期。
③張學昕:《帶燈的光芒》,《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3期。
④張學昕:《家山之重,或重于泰山——王躍文長篇小說〈家山〉讀札》,《揚子江文學評論》2023年第4期。
⑤遲子建:《是誰在遙望鄉土時還會滿含熱淚》,《小說評論》2023年第2期。
⑥痖弦:《紅玉米》,載《痖弦詩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第61頁。
(張學昕、李昕澤,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遼寧師范大學中國文學批評研究中心。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當代作家寫作發生與社會主義文學生產關系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2ZD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