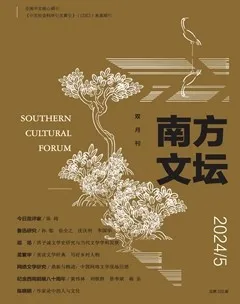新鄉土敘事中的“主體性”問題探析
“新鄉土敘事”抑或“新鄉土文學”并不是當下才出現的新話題,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就有相關討論,但至今卻仍然還是一個“未完成”的、開放的、熱議中的命題。這是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并且仍在持續。這一變化是包含方方面面在內的整體性、結構性、根本性的轉型。尤其是進入新時代后,中國的發展呈現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科技化的進一步深入,召喚著新發展格局的不斷生成與演進,也加速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新山鄉巨變”無疑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鏡像。
一、“新鄉土”與“新主體”的生成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鄉村早已成為現代化轉型中的重要一環。隨著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實踐進一步深化,鄉村的面貌也在不斷產生新變。這一變化是劇烈而深刻的,鄉村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生態等各方面都發生了變革。而“新鄉土”之現實的改變,又不可避免地影響到生活于其間的人們,引起他們在倫理秩序、價值觀念、文化心理、生產方式、情感認同等方面的革命性轉變,而人的變化又能反過來重塑鄉土的格局。因而,“新主體”與“新鄉土”是相伴相生、互為因果、互相建構的關系。
可以說,當下的“新鄉土”是一個巨大的“召喚結構”,沒有固定的形態,并且正在不斷“增殖”。因此,“新鄉土敘事”具有豐富的言說空間、強大的生命力和珍貴的價值意義。它不僅能夠反映當代中國的“新山鄉巨變”,還能以文學的形式提供一份鮮活的鄉土經驗。現實主義的“幽靈”在“新鄉土敘事”中重新獲得棲身之地,并且在作家的敘事中達成與現代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的“合謀”,深化“新鄉土敘事”的時代命題與哲學品格。正如曾攀所說:“‘新鄉土敘事’脫胎于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鄉土文學的多元轉向,尤其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的山鄉巨變背景下,在主體性、實踐性、發展性與時代性四個層面,建構起了自身的藝術理念和意義系統,并且不斷生產出迥異于既往鄉土小說的沿革訴求、主體建構、話語倫理和價值譜系。”①而“主體性”的建構則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為“‘新鄉土’的形成離不開‘主體’的‘實踐’參與以及‘時代’的‘發展意志’”②。質言之,只有準確把握處于大變局之中的新質主體形象,才能夠錨定深入敘寫“新鄉土”之結構變化、思維方式、精神內涵的靶位。
從這個意義而言,“新鄉土”背景下的新質主體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李約熱《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中的李作家、滕貞甫《戰國紅》中的陳放、忽培元《鄉村第一書記》中的白朗、李田野《我是扶貧書記》中的張榮超等。他們有的是大學生村官,有的是駐村第一書記,共同點是都帶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管理方式回到鄉村,從多方面統籌發展,帶領大家擺脫貧困。另一類是喬葉《寶水》中的地青萍、付秀瑩《野望》中的二妞、關仁山《金谷銀山》中的范少山、《九月還鄉》里的九月等。他們返鄉后帶回自己最新的學識、技術以及現代經驗,或投資辦廠或直播帶貨,以多元靈活的方式成為助力鄉村振興的“新人”主體。這兩類主體,一般都在城市中受到過良好的現代教育,有敏銳的商業觸角、知曉法制經營的規則、擁有知識、懂得技術、能夠將互聯網+運用到鄉村發展的實際中,明白現代社會運行流轉的邏輯,可以多維助推鄉村發展。
此外,鬼子暌違18年之久的長篇小說《買話》也貢獻了一個具有典型性的新質主體——劉耳。劉耳是不同于以上兩類的新一類,說劉耳新是因為他并不是經濟意義上將現代科技與新型管理模式、生產關系帶回鄉村的經濟主體、行政主體或新型勞動者,而是指他在“城鄉關系”中的身份與處境,以及他“返鄉”后的遭遇、行為與選擇。重塑“城鄉關系”這一新的歷史“卡夫丁峽谷”并不容易,鬼子以文學的形式進行了一次探索。在《買話》中,城與鄉不是簡單的對立結構,也與以往將小鎮空間作為二者結合的“中間地帶”不同,這次,劉耳這一人物成為鬼子安置城與鄉的矛盾與融合的“裝置”。
總的來說,以上幾類主體形象,不論是因為何種原因而融入“新山鄉巨變”的大潮中而獲得“新質”的主體性質素,都不可逆地彰顯著他們作為現代化主體正在經歷的由內到外、從上到下的嬗變。并且他們的新變正在與大時代的潮流同頻共振。討論他們的主體性如何得以賦形的具體過程,就是對“新鄉土”之豐富樣態與具體“風景”的一次“打開”與“發現”。
二、新質主體的形象賦形
首先,討論“新鄉土敘事”中主體形象的建構問題,必須要處理好“新鄉土”與舊傳統之間的關系。畢竟,任何發展的過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整體呈現出有先有后、有常有變的規律。不能因為一個“新”字,就忽略了所有還留有“鄉土性”的鄉村樣態,這樣反而會造成對“新鄉土”之豐富性與復雜性的遮蔽。需要明確的是,我們所說的“新”絕不是對“舊”的全盤否定。“新鄉土”的“新”與“舊”之間,存在著辯證法。正如李壯所說:“鄉土世界中存在的新與舊文化觀念的交織、碰撞,也使得‘舊鄉土敘事’成為我們創作和闡釋‘新鄉土敘事’時不可能繞開的‘潛文本’‘前文本’。”③在我們言“新”的今天,百年鄉土文學傳統無疑是不可逾越的傳統資源。在一種歷時性的發展對照的眼光中,我們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鄉土”的內涵,由此才能更貼切地闡釋與探賾在這一過程中涌現出的主體。
其次,還需要注意的是孟繁華所指出的“超穩定文化結構”,這是指“在中國鄉村社會一直延續的鄉村的風俗風情、道德倫理、人際關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世風代變,政治文化符號在表面上也流行于農村不同的時段,這些政治文化符號的變化告知著我們時代風云的演變。但我們同樣被告知的還有,無論政治文化怎樣變化,鄉土中國積淀的超穩定文化結構并不因此改變,它依然頑強地緩慢流淌,政治文化沒有取代鄉土文化”④。不能因為要寫“新鄉土”,就完全忽略這些因素,先行預設一個“新”的框架,把敘事套僵套牢。值得欣喜的是,目前的一批優秀作品,都很好地注意到了這些關系。
《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中的李作家,是一名駐村的“第一書記”。最開始,八度屯的村民們并不信任李作家,認為他只是作秀,不能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李作家并沒有因此而急于批判他們,而是以一個傾聽者的身份進入八度屯,在耐心“聽”的過程觀察村民們的精神狀態與現實困境,讓村民們在訴說中減壓、放下防備,繼而逐漸與村民們建立起信任并展開工作。正如李約熱自己所說,《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表達出一位扶貧工作者如何“在一個廢墟上,完成和村民情感的對接”⑤。同時,李約熱也不避諱書寫八度屯村民們性格上莽撞的一面和思想中落后的部分。比如村里的青壯年村民會為了爭取利益,去堵縣政府大門,也會因為土地糾紛和鄰村的村民打架。但同時,李約熱又寫出了對他們的理解:“忠深說,八度的人不像他們說的那樣壞,其實就是想多得些好處。……各家各戶的難處最終都是各家各戶自己解決,也不能全部都靠政府,這點八度屯的每一個人都知道。也不要八度人一提什么要求,就把他當刁民……”⑥這是李作家全方位深入八度屯以后對村民們愛護的理解。也正是在這樣一種現實主義創作的品格下,李作家這一主體獲得了與時代緊密勾連的“當下性”。
歐陽黔森的《莫道君行早》則塑造了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這一扎根鄉村的主體。麻青蒿原本是村里的一名老師,他也曾因為貧窮而想要到城里打拼,但為了孩子,他還是留了下來,隨后憑借自己的踏實負責,當選村主任。他熟悉村里的一切人和事,能夠真正做到為鄉民排憂解難,并且富有犧牲精神。當相關工作威脅到自己的利益時,他沒有動用權力,而是積極配合,最終使得工作順利推行。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他身上的掙扎,但全新的理念已經逐漸成為他這一主體人格的代表面。他是一個不斷求新求變,積極主動學習科學管理并反哺鄉村的新人形象。
關仁山《金谷銀山》中的范少山、《九月還鄉》里的九月,喬葉《寶水》中的地青萍,付秀瑩《野望》中的二妞等人,則是一批克服困難、回鄉創業的主體形象。其中的范少山,原本是一個農民,在北京昌平賣菜,親眼看見在雪災和貧困的威脅下村民老德安的自殺后,大為震顫。從此他毅然回鄉,在一番艱苦的研究和科研力量的支持下,他終于成功引領鄉親們走上脫貧致富的道路。原本即將消失的小村子也因此變為聲名遠揚的旅游觀光村。更為難得的是,他還不止于此,在“新農人”的道路上,他越走越遠,建立萬畝金谷子種植基地,想要讓更多的農民共享新型農業的成果。
從辯證的眼光來思考上述兩類主體的形象,對其主體性之“新質”的產生,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新”的一方面是相對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由魯迅開創的“鄉土文學”而言的,即回鄉主體們不再以“僑寓”的身份和“啟蒙”的姿態自上而下地審視和批判鄉土的凋敝與鄉民的愚昧,而是以平實的眼光、平等的姿態融入鄉村中,近距離地感受轉型期鄉村的現狀,關注鄉民與自我的精神狀態,思索建設鄉村的新途徑,歸來后也不再離去。另一方面是相對于由路遙塑造的高加林、孫少平而言的,新時代、新鄉土背景下的“回鄉”,不是“城市夢”破碎后出于痛苦無奈而被迫的選擇,此時地青萍們懷揣著建設美麗鄉村的新愿景,主動且愉悅地投入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大潮中,并在鄉村中獲得療愈的力量。而在脈絡上,又批判地接續了《創業史》時期梁生寶們的高覺悟,以及20世紀80年代《喬廠長上任記》中改革新人喬光樸的創新精神。總體上呈現出新時代浪潮中,他們對鄉土的新眼光、新態度與新理念。
此外,有學者認為,“新鄉土敘事”中“沒有地方感,這也可能是它最受人詬病的地方”⑦。《買話》《野望》的出現則進一步修正了這一弊病。鬼子在充滿地方性的飲食文化與日常民俗的書寫中,復蘇劉耳對“瓦村”與生俱來的味覺與心靈記憶,同時也勾勒出一個充滿風俗民情,依舊保留著“熟人社會”模式的“瓦村”。在這一體認的基礎上走進“劉耳”,則能更準確地挖掘出他身上的“新質”之所在,從而看到他背后那個作為“異鄉”的“故鄉”世界。于焉,劉耳重返故土之艱難得以言說,并在這種艱難與隱秘中,映射出鄉村的人事倫理、認知結構與情感認同的模式。用兩句話概括他的現實處境與精神狀態就是——“你是村里的人,但你不算是村里的人。”⑧“他的孤獨,城市沒人聽,故鄉沒人懂。”可見,劉耳既是城里人眼里的“鄉下人”,又是瓦村人眼里的“城里人”。事實上,他兩頭的轉化都不徹底,身上既留有瓦村人的習性,又有城里人的生活與行為方式,應當說,他是介于兩者之間的“融合者”抑或是“陰陽人”。至此,城與鄉的對立互嵌在劉耳身上得以實現,他是身處其間一個孤獨而隱秘的“新質”回鄉主體。《野望》題目本身就自帶濃厚的民間鄉土氣息,以及濃郁的傳統文化之脈。而目錄則是以二十四節氣為根莖,以自然主義的筆法緩緩展開橫亙于其間的鄉土日常。“芳村”的日常起居、飲食男女、風俗民情、人情世故……都與遵循農時的節氣有關。也正是在付秀瑩這樣脈脈如流而又熱氣騰騰的敘事中,“芳村”細部那些微小細膩、豐富綿長的“微表情”得以被看見。在細細點染的新與舊、常與變之間,二妞這個念過大學的年輕姑娘逆了母親的意,以青春的熱情和智識投入“芳村”的建設中,成為與母親相向而行的新式主體。
三、具有時代性的精神描摹與人性幽探
最后,要深入討論“新鄉土敘事”中的主體性問題,我們還是需要回到主體所處的時代本身。當下時代的結構性、根本性轉型已經強烈地改變了每個人的生存處境和命運,作為大時代的一分子,我們都身處奔涌的時代洪流中,一方面為向好的嬗變而欣喜不已,一方面也在“加速時代”中難避焦慮。由現代的生活方式而產生的病癥,實際上也是一種現代性的“時代病”。
查爾斯·泰勒指出,現代性是一次“大融合”現象:“‘現代性’指的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融合(amalgam),包括全新的實踐和各種制度形式(科學、技術、工業生產、城市化)全新的生活方式(個人主義、世俗化、工具理性等)以及全新的煩惱(malaise)形式等(異化、無意義、迫在眉睫的社會分裂感等)。”⑨我們現在就正處在這樣一種“大融合”的過渡階段。特別在當下,中國處于“加速”轉型期,在向現代化邁進的征程中,尤其是在要加快鄉村轉型的時代訴求下,考察身處其間的主體之精神狀態與幽微人性,有助于體察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而種種“現代病”的隱喻,則是一把把打開主體深層之精神與人性的鑰匙。《寶水》和《買話》中的病癥,是現代人極具代表性的兩種表征。
喬葉《寶水》中的地青萍患有嚴重的失眠癥,并且還伴有多夢的現象。失眠是一種典型的都市病,暗含人長期處在高壓和深度焦慮的狀態。這一病癥對人的折磨是極其痛苦的,睡不好,意味著人生都失去了活力與動力。失眠癥已經嚴重困擾到她的生活,以至于讓她提出了病退申請。而地青萍的夢,大都是和過往鄉村生活里的人與事相關。或許這就是夢的隱喻,指涉著緩解地青萍失眠癥的方向。果然,在來到寶水村幫朋友經營民宿的過程中,她的病癥得到了療愈并漸漸好轉。鄉土的氣息,甚至是糞便的氣味都使她感到放松與心安。至此,她名字中的“地”終于與夢境中魂牽夢縈的“地”合二為一,她也最終在寶水村落地生根,成為建設寶水文旅特色產業的重要一員。在“新鄉土”的語境下,“寶水”也不再是那個凋敝蕭瑟的“故鄉”,而是具有了精神的治愈與心靈的撫慰之功能的寶地。
鬼子《買話》中的劉耳整天因兒子貪污的事情焦灼不已,遂決定回鄉,逃避一切。他患有前列腺炎,排尿不暢通。“根”的發炎與堵塞不僅是劉耳身體的疾病癥候,也預示著他返鄉尋根之路的不暢通。剛返鄉的劉耳,是被瓦村的話語系統和飲食系統拒斥在外的。而也正是劉耳年輕時的欲望,間接導致竹子失去了生命。暮年時的尿潴留,事實上也是對劉耳的一種懲罰。吊詭的是,瓦村能夠解決這一病癥的人就是老人家(竹子的母親)。她用一根蔥花和一只竹筷,為劉耳治療根部的堵塞。這顯然帶有民間的巫玄色彩,但在文學世界里,無疑也是一種可能和寓言。小說末尾,劉耳說:“可他劉耳還需要壯陽嗎?不要了,不要了,要來干什么呢?只要天天能夠順暢地撒尿吃飯,就謝天謝地了!誰想壯陽就讓他們壯去吧!我劉耳,真的不要了!”⑩不要“壯陽”,是劉耳對人性中欲念的放下,以及與焦灼的過去和解,只求最基本的功能與暢通,實際上也是求心理的暢通。
令人欣喜的是,地青萍、劉耳不再是那個短暫返鄉后感到悲觀、痛心、憤懣后又徹底離鄉的返鄉者,而是一個想從生活與精神上都重新在故土扎根的人。而在《買話》中需要反省與改變的,不是鄉民,而正是劉耳自己。從劉耳返鄉的動因,返鄉后在瓦村人際倫理中的窘境,心靈深處的孤獨與煎熬、反思與自我救贖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幾代人的縮影,還能夠窺見城與鄉在逐步融合的過程中所存在的裂隙,反思如何重建現代人與故鄉的關系。正如丁帆所說的那樣:“《買話》在人性的拷問上更具有時代性,也更有深刻的哲學意蘊,這是一般鄉土小說作家難以企及的境界——思想的烈度足以震撼文壇,且是從形下到形上、再到形下二度循環藝術化抒寫。”11劉耳的孤獨,不是個例,而是一種具有典型性的時代病癥,劉耳的現實處境與精神樣態在離鄉謀發展又返鄉的一批人中是不少見的,甚至可以說勾連著他們內心深處的記憶與生命體驗。相信不少有過相似經驗的人都能從劉耳身上感受到一種心靈的震顫,看到曾經的自己。從這一層面而言,劉耳無疑是具有“新鄉土敘事”中一個具有時代性的人物。
李震曾言:“在新文學史上,鄉村敘事的每一次發展,都是由富有典型意義和時代特征的人物形象的誕生為標志的。如何以鄉村社會第三次文化裂變的文化邏輯,去創造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新型鄉村人物形象,便成為新鄉村敘事的作家們亟待發力的重要敘事支點。”12喬葉、鬼子、付秀瑩、李約熱、關仁山、周大新、滕貞甫等作家正是在這一支點上深入生活、潛心打磨,成功塑造出一個個極具時代性、典型性和闡釋性的“新質”主體形象。他們能不能成為“新鄉土敘事”中被記入文學史的人物,還有待時間來驗證。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確代表了新時代中國“新質”主體的新樣態、新面貌、新質素。并且以其實踐,重塑和推動了“新鄉土”的時代面貌,代表著一代人的心靈史和精神史。
【注釋】
①②曾攀:《新鄉土敘事:主體、實踐與歷史的發展意志》,《小說評論》2023年第3期。
③李壯:《歷史邏輯、題材風格及“縫隙體驗”:關于“新鄉土敘事”》,《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
④孟繁華:《百年中國的主流文學——鄉土文學/農村題材/新鄉土文學的歷史演變》,《天津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⑤李約熱:《我曾穿過“百家衣”——〈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創作手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2年第4期。
⑥李約熱:《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第80頁。
⑦劉文祥:《新時代語境下的“新鄉土寫作”現狀及其未來進路研究》,《云南社會科學》2022年第4期。
⑧⑩鬼子:《買話》,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第208頁。
⑨查爾斯·泰勒:《現代社會想象》,王利譯,載許紀霖主編《公共空間中的知識分子》,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第33頁。
11丁帆:《漂浮在瓦村麥田上空的靈魂》,《文藝報》2024年6月14日。
12李震:《新鄉村敘事及其文化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23年第7期。
(周麗華,廈門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