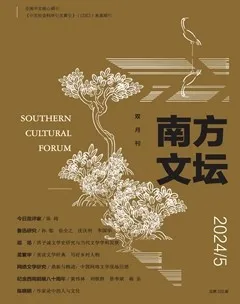講述是一種儀式:關于未來想象的“后設之維”
當我們在談論“人工智能發展與網絡文學未來”這樣一個主題的時候,已經處于人類和機器密切纏繞的后人類境遇。實際上“技術+智能”的結合早就走在那漫長的歷史之途,我們的公共生活、科學、社會、歷史,包括藝術、寫作均在這一境遇“之中”。
中/西、傳統/現代、人/機,我們時刻處在強調對立和抹除間隔的斗爭之中,前兩種尚屬人與人或者不同地域不同人的關系問題,最后一個人機之爭卻將人推入前所未有的境地,所謂生死存亡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因此,機器人是否能像人一樣的問題,漸漸變成機器人是否比人更先進和完全能取代人的問題。當此問題不再止步于學術討論和文學暢想,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從新奇陌生變得耳熟能詳,大眾開始參與到人工智能的討論之中。2023年初的ChatGPT、2021年的元宇宙,與其說這些名詞背后是嚴肅的哲學命題:人是什么,人要如何生存……不如說是一場懸置了討論的大眾狂歡。人們很快樂,人們對新前景毫不慌張地默許。在李敬澤主持的“文學館之夜”討論里,關于元宇宙有一場驚悚的呈現,說其驚悚,是因為參加者中(一場討論,只有三四人)有元宇宙的發燒友,脫離了肉體的元宇宙竟如此輕易地使借助身體感知與體驗世界的人們雀躍接受,還有比這更驚悚更令人惶惑的嗎?或者,當我為這種“輕易”感到驚悚的時候,恰好是一種提醒:我們對自己的來時之路幾乎毫無知覺。如今距離這場熱議已過半年,更多的頭條熱點紛至沓來,ChatGPT仿佛已成過眼云煙。這似乎驗證了戴錦華老師所指出的,在數碼轉型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我們“完全未經抵抗,幾乎未經討論”①。
百年之前的中國學人經歷了科玄之爭,他們為中國的未來焦灼,所遇到的問題直指民族根本和文化存續,他們要尋找武器,來打一場腹背受敵的民族之戰。今天的人工智能、元宇宙的到來,在一片熱鬧的消費大潮和互聯網覆蓋人類生活的世界里,資本在歡呼,網絡的書寫者們在用文字想象新世界、新人類。在曾經的科技去魅和如今人工智能魅影重重之間,或許就像大衛·里昂在《賽博空間:是超越信息社會的存在嗎?》一文中富有洞察力的話語,對于“信息社會”和“賽博空間”等概念的使用所帶來的最大潛在風險是:誤認為新的社會形態、消費模式、政治行為等皆可以從技術革新中尋找答案②。那么,當技術/人工智能進入生活,批評者、作家(或者寫手)是用什么立場、話語來講述和想象這樣一個特殊情境的故事,其文本指向何處,對于我們理解自身所處的時代境遇有何啟發,這是本文借以思考“未來想象”的立腳點。我們看到,從批評、敘事想象到文本內部,是一個關于未來想象逐漸具體化的文化實踐。
立場:作為在場者和觀看者的批評
人工智能在互聯網眾說紛紜的“新聞”中,幾已變成舊聞,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似乎只是眾多頭條當中的一個,隨著新話題的誕生,人們起初的震驚被后置為日常生活中的日常。然而,對于以“人”作為立身之基的人文學者,卻不能不在這技術/人的博弈當中,將“是否取代人”轉換成“人有什么不能被取代”。問題的置換,意味著思考問題角度的不同。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將關注不同文本所發出的聲音。這些文本從故事、分析和解釋層面,以各自的影響力代表著一種態度。批評性的思考在這些話語中顯得格外醒目。
文貴良在ChatGPT引起2023開年轟動之后,緊接著就圍繞人工智能創作中的詩歌進行了比較性的分析。他這篇文章命名為《從小冰到ChatGPT:對人工智能與漢語詩學的一個考察》,主要以微軟小冰為例,他指出:“小冰是根據圖像來創作語言產品的,這智能程序內部的轉化筆者一無所知,猜想是通過一系列的‘算法’轉換出來的,即通過獨特的‘算法’產出一行行的詞語排列。”③這樣的結論是在分析了小冰寫詩的套路化傾向和使用語言“還沒有達到正常人使用語言的程度”之后得出。顯然,文貴良對文字處理軟件以及人工智能是否真的能夠創造出“詩歌”這一問題存疑。其中尤其有一點很突出,那就是在評價中作者始終有著清晰的人類自然主體/人工智能主體的劃分,他針對“未能從智能主體的角度來評價詩歌”的主張進行反駁,“但遺憾的是我們評論者自身仍然是人類自然主體,而不是人工智能主體”。文貴良對自己的這種先行判斷進行反思,他擔心自己預設了人工智能寫作的不足,作為一個嚴謹的批評者,最終還是提出了人/機器寫作之間最根本的差別——一種獨立而富有個性的詩學主體仍然成為判斷的關鍵。這或許就是問題的關鍵。當我們評價或者驚喜于人工智能的高超之時,潛臺詞約莫在于:它就像人的副本。或者,它真像人。再或者,它在模仿人,而不能超越人。無論哪種,“人”都是我們言說人工智能的唯一參照。在主體意識和創造力這個層面,我們找到了人不同于機器的立足之地,可問題是,在數碼包圍時代作為人類的我們是否意識到自己擁有這樣的性質和可能,進而反思自身?在對人工智能的贊譽、好奇和見怪不怪之中,創造力是被激發了,還是被扔在了不知何方的隱秘角落?這種狀況可能比人工智能寫出一首好詩更生恐怖。
話題重又回到主體性和創造力的問題上。齊澤克用《人工智障》作為題目對這場開年“話題”做出了回應。他并不討論人工智能的能力到底得到了多大增強(文貴良文討論的正在此處),他所關注的重點在于“當人類對話者使用侵略性、性別歧視或種族歧視的言辭,促使機器人展現自己滿嘴臟話的幻想作為回應時,聊天機器人應該如何回復?人工智能是否應該被編程,使其回答與對方提出的問題處于同一水準線上?”④這些問題關聯著人們對人工智能所具有的“知識或者意義”缺乏警惕性的現實,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基于對現有文化的大規模挪用”會將人類意識深處的恐怖、骯臟或者偏見以十分清晰的方式表現出來,它真正做到了“精準表達”,而很多話語裂縫和胡言亂語所隱藏的真知灼見就這樣被甩在一邊。聊天機器人的“扁平”“將與各種意識形態擁躉(ideologues)相處得非常好”。在“保馬”公眾號的“編者按”中,更清晰地指向了思想作為人類主體性內核這一關鍵:GPT在經過“思考鏈提示”訓練后所涌現出的能力,恰恰部分佐證了他對語言與思想之關系的一貫觀點:語言并不表達(express)已完成的思想,思想恰恰是在表述(enunciation)中涌現(emerging)⑤。顯然,齊澤克所關心的與其說機器的能力是否大到取代人,更關鍵的在于憑人類語言數據庫化的人工智能將會放大什么,這些數據“以客觀之名”將人類判斷的理據窄化、固化乃至污名化。齊澤克在談論三體時,曾經指出,“萬物歸位”的自然秩序的實在界需要一種象征性的干預,它必須由儀式來保證。進而言之,技術社會帶來的種種會營造一種“事實如此”的假定,從而取消了其現象背后的問題甚至粉飾恐怖,這是面對此種現象時必須要警惕的。《與賽博空間并存:21世紀技術與社會研究》一書中也說:“目前的當務之急并非對信息社會的將來杞人憂天,而是切實關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現狀,并且在關注的側重點上需達成共識,即關鍵問題并非‘技術’本身,而是所涉及的道德、政治、文化等方面。‘賽博空間’這一概念的核心是與電子技術共存的社會體驗過程,因此其關鍵領域就在于嚴謹的社會分析。”⑥
人工智能話語聯通著惡托邦泛濫的可能性,這使研究自然推到了倫理學領域。2018年與2022年發表于《南京社會科學》的《物的倫理性:后人類語境中文藝美學研究的新動向》(張進、姚富瑞)、《后人類語境與文藝理論新動向》(王坤宇)⑦,基本連綴出一條文藝領域面臨的新美學命題——后人類,這自然也是一個嶄新的漸成現實的人類生存課題。王坤宇文將近五年來美學領域的“后人類狀況”做了全面梳理,“元宇宙”進入論域,顯然是關注社會前沿問題的總體性研究。與之相比,2018年的文章更顯出學者的焦慮和問題探究意識。
《物的倫理性:后人類語境中文藝美學研究的新動向》一文將論述放在“后人類語境”的假定之中,即,“后人類”語境中必不可少的一環是“物”,這種“物”成為一種新的生命形式,也就不同于我們以往談論人/自然之間的“物我”雙重主體。后人類情境中的“物”是機器身體、智能化大腦、能說能行動能學習,進而松動了原本堅固的人/自然/機器之間的想象區隔。這是在把人/機器放在“生命形態”基礎上言說倫理問題,然而在具體論述中,顯然作者還在強調一個事實:“作為物的媒介”介入生活已深,但“物”常常被人們自動化為一種事實般的存在,而不需問其本性。換句話說,“‘技術’已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詞匯,也不僅僅在某段時間存在,而是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工智能重新組合時間和空間以溝通有無,而‘技術’也應被重新審視。它不再是被我們利用的‘工具’,而已成為我們每天的日常活動和賴以生存的環境”⑧。這就使“物生命”的活體性質大打折扣,或許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人文學者為“后人類情境”人類主體設置的防線、堡壘。作者通過我/非我的主體間性關系,將問題由現實導向文藝審美活動的道德內涵。在這樣的理路,或許可以獲得由書寫反觀現實和人本身的思考路徑。
在關于AI的討論里,2016年人工智能AlphaGo在似乎最能彰顯人類智慧的圍棋界橫空出世,人們再不能用“學得像不像人”“再能也是人工設置”這樣的話語來安放自己的人類自信,批判性的思考顯得尤為重要。前不久李敬澤做客央視《開講啦》欄目和在鳳凰文學之夜的講話里,也用到了“堡壘”一詞,認為在超級智能的時代,文學是捍衛和證明人類光榮與尊嚴的堡壘;當人工智能兵臨城下,在人與AI的關系上,要思考的是“我們有什么”,“我們只有在如此個別、具體的他人的故事中,只有在面對面的確信中,我才能感知我的存在,我才真正獲得了世界”⑨。戴錦華則在訪談中指出要批判性地認識“媒介改變了我們什么”,而不能將問題停留在“媒介改變了我們”的現實描述層次。或者,“面對媒體環境的復制效率,我們已無力與其抗爭”⑩,但思考還在繼續。被李敬澤指認為“人類光榮與尊嚴堡壘”的文學,尤其伴隨網絡而生的網絡文學、新媒介寫作在如是情境和時空如何描述、如何想象、如何表情達意,就是接下來我們要追蹤的敘事方向。
穿越:空置的主體與“大他者”
關于一切的未知,文學作品中是從主體的想象開始。這里的主體,包括寫作者、作品中的人物,假如讀者也參與到創作之中,則讀者理應也是主體的一部分。作為主體,對應著符號化的客觀世界,是以抵制符號化作為確證主體位置的實現方式。在網絡文學的書寫中,主體關于未來的想象是不是像我們所預估的這樣呢?
網絡文學以類型化作為存在的主要形態,而穿越,幾乎是所有文本橫行于世的有效手段。這一手段,極大地擴充了文本可以容載的范圍,不再拘泥于一時一地或某特定場景,時空可以交錯,人物可以有取之不盡的知識庫作為行動支撐。到了古代的穿越者,可以有現代靈魂;借體重生者,可以有前世記憶;而到了未來,自然有發達的計算機技術支持你在無盡的世界穿梭。這些形象,其實都可歸為穿越,也都像Avadar這個21世紀初在世界影響巨大的虛擬形象,其背后是虛擬世界,也可將其稱為平行空間、元宇宙。世界在這樣的想象里變得無限大、無窮廣,可有一樣還是在的,這就是我們說到的主體,主體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他/她是否還是抵抗符號化的主體?如果是,他/她是以何方式來證實自己的主體性?如果不是,他/她又在這樣的行動過程中如何離開了自己的位置?這種缺失,將倚仗什么來予以補充、解釋,并在文本與現實的雙重世界獲得認可?
以上問題對于解析“人工智能/人”的二元關系似乎顯得最為迫切,前面的批評文章雖各自角度不同,但所強調的核心離不開人作為主體的主導位置。我們討論人工智能有多像人,是因為有“人”這樣一個參照系,我們說人工智能的詩歌寫得有多好,也是因為有詩歌樣本放在那里,這參照系,這樣本,就是規則,制造規則的是“人”。然而,我們也在激烈的批評當中,感知到文學書寫、影視表達中強烈的危機感。這事關主體本身。
首先,以“借用”為根本原則的世界設定,指向文化意義上的“古代”。穿越者,這個描述本身就隱含著雙重世界,一個是未穿前之現實,另一個則是穿向何處,后面這個世界是處于電腦屏幕兩端共同好奇和寄望的所在。在這個意義上,屏幕作為一堵墻,在形式上似乎隔開了寫者/看者、現實/文本、穿越者/未知人,因為“穿越”這樣一個或意外、偶然,或處心積慮的行為匯在一處,這就必然要求有個方法能夠解決強行遇合的問題。
我們看到,敘事從第一次放棄主體位置的行動開始。穿越前的世界,無疑是這個穿越主體之為主體的第一重證據。這個世界,常被描述為背叛(如《醉玲瓏》)、痛苦(如《將夜》)、乏味(如《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困境,困境本身,為穿越者提供了全身心投入新世界的理由。絕大多數文本中的穿越者迅速鳥槍換炮,扔掉舊的,奔赴新形象的旅程。這是我們說的第一重主體位置被棄的文本書寫。與之相仿,電腦屏幕兩端的寫者和讀者也達成共識,越是離奇,越是遠離無可撼動的現實的“超現實”,在手指不斷更新頁碼的飛舞中,越能忘記現實。寫者和讀者都不必管自己是誰,生活在怎樣的境遇之中,我們只管暢想別樣的可能人生。這樣的選擇之后,他/她、他們/她們是否就能掌握自己的人生,進而使“被擲入”的命運改寫?
這就來到進入“新世界”的主體能否建構的問題。由于“古代”這個意味著無限向后的概述包含著太多可以上演的形色人生,我們的穿越文有很多在這方面著力。新主體確證自身的行為所以有趣,大略是與這種“古意今用”有關。
“古代”還有很多好處。一則,保證“主體”依舊在人的世界縱橫捭闔,即便是帶著系統來穿越,這個系統也因為古遠世界的限制而無法施展拳腳。換句話說,系統本身只對這個帶著系統的穿越者有效,所在的“舊世界”本身是穩定的,仍沿著自己的運行規則社會化人們之間的關系。當然,帶著系統穿越的行為是近十年網絡文學書寫中的新鮮事,或者說是赤裸裸的互聯網世界、AI強勢進入大眾日常生活的表達。寫者以“古”為限,是既想要金手指又意圖安放自身的欲望和需求。二則,這里的“古”意味著歷史,而歷史是被書寫的可想象的過去。這隱含著凡有點文化記憶的寫者和看者都能在這里找到“陌生之地的熟悉感”。在網絡文學發生發展之初,這樣的文化記憶常在中/西的二元圈子里打轉,所謂的“魔幻”“西幻”“異能”“耽美”“輕小說”都有“世界之影響”的影子。如此寫的好處是不同于庸常的現世生活,能讓你與世界流行文化處在一個平行線上,時尚+獵奇,構成了這一時期書寫的主要套路。最初封神的那些著作,如《紫川》《惡魔法則》《雪鷹領主》《完美世界》《絕世唐門》大多如是。這些作家在最初幾年的盛景之后,很快就轉向以中華文化為背景的新型世界設定。換句話說,這里的“古”主要是中國元素主宰的“古”。中國的讀者、寫者和穿越者更增加幾分“文化記憶”的獲得感,而非中國的西方讀者則找到了陌生、新奇而又有幾分熟悉的“中國性”和自我文化想象,網絡文學的海外傳播在最初中西交錯的玄幻世界騰挪,與這種文化的糅合是有很大關系的。
其次,定制版的物理身體與裝置化的大腦。一旦選擇了“古”,則要求與之相應的知識系統和文化體系。進入到文本世界的寫者、讀者、穿越者,順手就選擇了先“換身體”后“換腦”。為什么說是“選擇”呢?前面提到,“穿越”所以發生,多是因為現實的不如意,要改變現實,就要從自己不具備但又很重要的要素著手。我們看到,穿到異域的現實人一睜眼,自己的靈魂已在一具堪稱完美的身體里,他/她很滿意。緊接著,如何在這個世界好好爽一把,修正現實中的“Loser”命運,就迫在眉睫。解決方法很簡單,被替代身體的原主記憶包括技能全數復活,這約等于我們說的“換腦”。為什么呢?因為這個“大腦”已經超越了穿越之前、穿越之后的人腦的貯存量,它變成了一個聯通古今的數據庫。恰如奧利維耶·迪安斯所描述:無論我們是在尋求對世界科學現象的理解,還是在遙遠的星云中尋找上帝的神跡,機器都已無可避免。我們是賽博格,因為只有擁有了機器,我們才能夠面對太陽11。然而,一個依托借來的身體和數據庫化大腦的異世者,儼然一個人機合一的賽博格,如何能夠確證在新世界的主體位置?進而言之,作為主體的“人”,沒有自己的身體,只有被裝置化的大腦,他/她將如何抵制符號化的命運?顯然,在文本的世界里我們再次遭遇了齊澤克的批評、小冰的能量和“爽”之后的現實隱憂。技術化、科技化、人工智能化,儼然一把通行宇宙的利器,它縱橫古今,中外皆在其中。
傳統文化這個“大他者”的出現,成為拯救失位主體的群體選擇。這是在選擇“古”的過程中逐漸建立并完成的。數據庫很龐大,要什么,什么在這個世界有用,卻是一種泛主體化的選擇。在網絡小說的穿越世界里,常常有這樣的橋段:穿越者在穿越之前就有了穿越必備,什么唐詩宋詞、經典名著、歷史教科書都名列其中。到了新世界,從數據庫里隨便選上一首李白詩或蘇軾詞,即可在文化圈占據高地。知識的等級化對應著現實中以知識切分的等級階序,而由經典的古詩、古詞、古人道理和歷史名人匯成的文化地圖,則鮮明地描繪出一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地圖。這幅地圖與現實中的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頻共振,為換去身體和大腦的缺位主體們提供了填充空缺的文化倚靠。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網絡文學的中華文化傳承時的文本基礎。多數討論會放在傳承什么、如何傳承,卻有可能忘記“主體”與文本中的傳統文化地圖、現實世界/新世界的互文關聯。
青年:數據化的世界與賽博格們
我們提到未來想象,總會不自覺地指向技術與機器加持的世界。當邁克爾·杰克遜以極為靈活的身體扭動出機器人的骨架之感,當王家衛的《2046》以幾十年后的時空出現在大眾視界,那穿著宇航服有冰冷機器人氣質的女郎似乎暗合人們關于未來的想象。未來,人類的未來,好像就應該是散發著機器味道的樣子。邁克爾·杰克遜是20世紀的明星,《2046》是20世紀末互聯網剛剛在百姓家庭出現的時刻,外星人,機器人,是我們想象未來的必備元素。今天我們很少說外星人,我們說人工智能,我們說元宇宙,說后人類,在時間上,和杰克遜的時代也就隔了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世界似乎已經變了樣子。
誰是未來世界的主宰,誰能順暢地接受這樣一個數字化的新世界,青年——一個擁有多種可能性的隱喻群體——再度在人類重要的變遷時期出場。
工業革命時期,人與人之間的區別驟然加深并且定型。文學中的小人物大批量以陌生而又沉重的姿態站到了文本中央,青年,則在此時扮演了為小人物發聲的角色。向德瑞納夫人開槍的于連,在槍響的那一刻頓悟自己已經在名利的路上走得太遠;拉斯蒂涅卻在高老頭人間冷暖大幕拉下的剎那毫不猶豫投進利欲的深淵;他們的困境和少年維特的煩惱、還沒嫁給查理·包法利的愛瑪、一個潔白的苔絲,還有似乎不在人間的希斯克利夫和拉斯柯爾尼科夫們,以青年的形象,站在邊緣卻力圖擁有主體意志的個體,對這個欲望炎炎的社會發出了微弱卻不失強烈的怒吼。20世紀初期,電氣化時代到來,一切似乎都百廢待興,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世界似乎乘著馬雅可夫斯基們的火車和穿褲子的云在時空穿梭。彼時中國的五四青年,年輕的梁啟超、胡適和“魯郭茅巴老曹”們,則擔當起高擎救國救民大旗的先行者,為同樣年輕的娜拉、子君、覺民、覺慧們尋找出路。青年的聲音在這個時代響徹云霄。二戰過后的五六十年代,青年再次重裝出場。此時的他們,同樣年輕,身體一樣有活力,但精神已不再與昂揚的話語同步,他們成了以群體形式與時代抗衡的身體實踐者。浮士德式的理想話語,薩特以行動見證存在的激情主張,都在殘忍的戰爭和原子彈的滅世打擊中粉碎,青年們所能掌握的唯有自己的身體,在這樣的歷史時空,身體前所未有地變成了一種武器,并成就了身體的哲學。他們的非理性變成利刃,四處開刺,傷了自己,也傷了他人,而“群體”的力量伙同大眾文化再一次將消費文化推向世界。垮掉的世界、麥田里的守望者、公路上的雌雄大盜,陷入黑色幽默中疲憊不堪的身體和靈魂彌漫在青年的世界。
這一切,到了互聯網時代,似乎已經成了不證自明的事實。網絡所指,就是青年。只聽到哪位年長者學習打字或使用網絡的贊譽之聲,何曾有青年熟練使用電腦和手機成為關注的新聞,只因青年掌握網絡名正言順,而網絡代表新潮,也代表未來。網絡,被劃歸到未來和正走在未來之途的青年生存必備。網絡文學的青年寫者和讀者,也在人數和比例上壓倒性地碾壓其他年齡階段。網絡文學的出場,間接表征著并未掌握社會資源和文化資源的青年群體匿名出場。而網絡文學的文本世界,儼然就是青年斗法角力的戰場和不失游戲化的人生想象。在這些作品中,關于人的形象的書寫,極大程度地擴張了肉體的力量、技術,或者說機器人的身體,以人之身體一部分的形式成為人的肉體的延伸。我們把這種人機合一的形態稱為賽博格。
前面提到的換身體又換腦的穿越者們,雖仍有一方物理世界的肉身,其實與賽博格無異,故而我們會說這是一種缺位的主體。那到了賽博格化成為現實的當下,或者數碼文明虛擬世界亦是一種“現實”的時代,我們又當如何評價其主體性或主體位置呢?
從《瘋狂的外星人》到《流浪地球》,人類在世界末日來臨之際暴露出的種種問題,拯救者的強大和超人的力量,都在我們的接受范圍之內。然而到了《流浪地球2》,情況似乎有些不同。
“流浪地球”這一行為本身確定了人類位置的哲學意義,我們在不同的時間空間漂浮,力求在不穩定的落腳點以固有的倫理秩序穩住這個世界,但世界的存在前提卻是在意外、偶然和不確定中誕生,這樣的故事群顯然具有極強的隱喻性。流浪地球以強有力的國家意志、英雄主義的情結和獻身精神,最終完成了末世拯救大業,這些是“世界敘事”的基本結構,但在這個結構之中或者之外的則是一條感傷的尾巴,這條尾巴或許會成為《流浪地球3》的主部。因為最終完成地球拯救的不僅是科學家,不僅是勇士,還有那個已經變成人工智能的小姑娘。她以智能大腦完成了密碼的輸送,一項人腦無法替代的工程決定著人類的前途。而圍繞著這個小姑娘的尖銳討論始終彌散在敘事的空間里。其癥結在于既是人工智能,同時又是有父親凝視的丫丫姑娘,帶著1分鐘的前世記憶,她是否代表著重生,喻示著復活,等于人類?作品似乎沒有作答,但觀眾們從父親如釋重負的神態、拯救完成的眾人狂歡和自己長出的那口氣,都能感知到人工智能與人的圍欄似乎松動幾許,問題一下就好像閃回到科幻片中地球人/外星人是否能和睦相處的另一層面的問題上來。這是核心問題的挪移、懸置和默許,驚悚之余,我們卻不能否定這個小姑娘身上蘊藏的無限可能。
李佳蓬的《青年世代》則給未來200年后的生活勾勒了一幅元宇宙、數字化生活的場景。這是一個已經全面符號化的世界。在所塑造的2221年的歐洲聯邦,我們看不到自然,沒有動植物,人依舊是這個世界的社會主體。小說開端設置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關于如何在速朽的世界中穩定自身,“在歐洲聯邦絕大多數學習都已經采用萬能鏡在家進行畢業考試的2221年,牛津這所有著1500多年歷史的學校,依舊古板地召集了所有人,來到這座不知道幾百年的混凝土樓里,坐在復古的小木桌前,用紙筆來完成大學時代的最后一場考試”,主人公丹尼的心里話對這樣不合時宜的行為做了注解:“罷了,尊重傳統與歷史吧。在這不斷變換的世界中,能堅持不變的,總歸令人欽佩。”12歷史、傳統,是劇變時代的堅持,也已經變成一種儀式。而儀式常常是符號化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如何看待數百年來人工智能的進步。吊詭的是,丹尼曾在一年多前認為人工智能只是個偽命題,只不過是“數據與算法的堆砌”。一年之后再度被來自具有監控功能的最大的流媒體網絡——Europe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提出,此時的丹尼以“其實特別相信人工智能的價值”做出肯定回答。顯然,這已經是人工智能占據話語權的時代。
對比今天我們談人工智能如何更像人、是否超越人、人如何智能化生活這些問題的焦灼,這個2221年的世界,已經有兩樣東西在人們的身體與行為方面普及。在牛津考試的敘事中,我們看到了“萬能鏡”:
當今的世界,“手機”這個古董玩意兒100多年前就被淘汰了,曾經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蘋果”,當下的價值也早已不如一個真的蘋果。將手機取而代之的是與人體貼合更緊密但又不植入人體的萬能鏡。通過眼球的轉動、手指在空中對虛擬投影的點擊、聲音的骨傳導及腦電波的分析,萬能鏡可以實現當年手機、耳機、電腦、電視、運動手環等幾乎所有個人電子設備的功能。13
萬能鏡間隔開了物理世界和數碼世界,同時將二者連接起來,人們可以在物理世界和虛擬世界穿梭。前者顯得單調,后者則為你提供類似穿越者特異功能的各種信息,世界變得清晰而充滿力量:加了濾鏡的姑娘、綠茵覆蓋的街道、有清晰坐標的空間,信息流暢通無阻。
有了萬能鏡保證完美的環境和你對這個世界無所不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則可以借助元宇宙來完成。EBC記者的出現,只不過是“有點像一個黑色小飛碟漂浮在空中……藍光一閃,一個全息投影的人物出現在大家面前”14。當下種種“虛擬仿真”,不過是假設一個場景動起來,多有“復活”某時某地某物的架勢。這里的描寫則是擁有意識和行動力的“分身”,直接承擔起主體職能。這約莫是《青年世代》想象未來的數字世界形態。而架構起這一形態的Europa是這個世界公認的最強大的人工智能,也是“結合當時歐洲最強數據公司DataLab的算法和模擬”應運而生的虛擬議長。換句話說,人工智能系統管理著這個世界。而青年,是這個新世界空間的主體,也是走在政治前沿的社會群體。前所未有的,青年獲得了主宰世界的象征權力。
《青年世代》將世界推進到200年后的未來,這個時期人工智能要求自由自主,要求信任,這已經遠遠超過《流浪地球》中人工智能是否能令人類重生的討論。Aveda儼然是一個能夠與其制造者平起平坐并且擁有著毀滅一切能力的敵手,令制造者/被制造者之間關系破裂之處,卻是擁有了號令天下權力的“人”,將做些什么。權力,是旋轉在《青年世代》的軸心力量。技術是這權力軸心中的軸心,這就猶如手機中的芯片,誰高精尖,誰就掌握市場,掌握互聯網世界的前景。在這個意義上,《青年世代》所討論的權力,實則是個技術問題。而誰擁有技術,利用技術做什么,則屬于社會問題。顯然,作者并沒有跳出人類的圈子來討論這些問題,因為故事的發生發展被限制在朋友、情人、父女、兄妹、母女的關系之中,而對人工智能系統的控制權很自然地被賦予了具有血緣關系的下一代,女兒是第一繼承者,母親則次之。技術變成了某一圈層的財產。這樣一個Bug,就像《流浪地球》的尾巴,只不過后者是在“人工智能/人”之間拆解障礙,而《青年世代》卻把“人之權力/人工智能權力”之爭,或者二者是否能和平相處的問題變成了世襲的血緣問題,前面圍繞權力進行的各種爭奪瞬間無效。無論是首富歐莉維亞,還是擁有獨立意識的Aveda,概莫能外。
200年后的世界,龐大的技術資本假想出一個青年民主制度,而人工智能Europa是這一切的實踐者。青年黨/老兵團是在被結構的獨裁社會中的兩股政治力量。前者是世界的希望,后者——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群體,則被視為反叛組織,是社會的贅余。當我們指稱數字化的世界,人被符號化、賽博格化的時候,丹尼、科霖,他們以各自的路徑想要揭穿這個世界的隱秘,這種行動本身是對全面符號化社會的一種反抗。只不過在這個尋覓過程中,未來世再度變成一個大結構,一個穩定的血緣結構。作為主體的“人”的位置再度被表征為空缺,缺位的填充物是無所不在的權力。權力被指認為一個大他者,其想象維度不斷后移,與開篇的“歷史、傳統”接上了榫。這時候問題就和我們前面討論的穿越格外吻合。穿越者以放棄自己的主體而融入一個新世界,未來世卻在“全息世界”展示出“看似自由的歐洲,居然是被一個獨裁者通過機器操縱的”15。
顯然,在這樣的敘事中,賽博政治似乎成了關注的重點。但當把誰擁有Aveda控制權的問題轉移到人身上的時候,故事就再次進入了熟悉的權力游戲,而人所身在的賽博環境被后置為故事的背景。也就是說,當我們還在為全息世界對元宇宙產生困惑和驚奇的時候,這個問題似乎已經不知不覺變成了一種認知中的常態,不再是被討論的對象。我把這種狀態叫作問題的架空,這樣一種默許,使數碼空間的人們不再占有主體的位置,他們/她們只是虛擬議長Aveda的數據中的光點,是網絡社會抹平不同聲音的一群。
這樣的情境,主體又將如何填充自己空虛的位置,即便要流浪地球,又用什么來安放賽博格化的彼此呢?儼然教父狀的人工智能Aveda自陳:我和你們是不同的生命種類,我沒有感情,只會通過邏輯進行判斷和選擇16。在這話語的裂隙里,似乎一點光亮透了過來,就像穿越者們力圖通過文化記憶來獲取新世界的倚靠。情感,成為區隔“人/人工智能”的關鍵。
想象未來:向后,再向后
歷史、記憶、權力、責任與情感成為行動的根據。想象未來,我們用什么來想象未來,這一切似乎理所當然地落足在人類社會的“曾經”上,使想象這一行為不只是朝前,而是在身不由己的朝前行動之時,不停回望來路,力求用“后設之維”來穩定自身。
歷史總是具有奇特的相似性和耦合性。當時光車輪運行到20世紀末,基本處在文學理論開始幾頁文學起源部分的神話,竟然再度出現在世人面前。只是這一次不是去發現神話、整理神話和借神話來諷喻現實。神話成了此時中國科幻人和大眾的選擇,其宗旨牽連世紀初的學人們以一條長長的紅線綴起“中國性”的歷史。100年的時間,依然在面對著世界文化的沖擊,雖國勢強大但影響的焦慮依舊,甚至更強。此時科技興國已經是毋庸討論的共識,但在互聯互通的世界文化競爭領域,中國將以怎樣的內容和姿態去展示自身?這樣一個宏大的問題,在并不足以影響文藝走向的科幻群引起熱議,“九州”的創設就是世紀末情境作用下的結果。而我尤其感興趣的是,神話又被選擇為言說中國的文化表征。那些《山海經》中的玄奇怪想,孔子所言之怪力亂神,紛紛擾擾下凡來,竟被鋪陳出盛世的文化奇景,還走出國門,來到世界,為本有旁門左道味道的網絡文學成為“中國網絡文學”狠狠出了把力。如果說,魯迅、茅盾等大師筆下的神話在于借古諷今,如今的神話,被選作與西方幻想系統對話的中國符號,書寫者又會怎樣書寫?在世紀初和世紀末乃至新世紀,當文化情境和社會情境變化了,神話對于國人又有什么樣的意義呢?或者就像《與賽博空間并存:21世紀技術與社會研究》一書中所言:“信息社會無數次目睹了人們把夢想照進現實,曾經的種種大膽想象已經成為真實的存在,而賽博空間則反其道而行之,將昨日的現實照進今日的夢想。在這個空間里,人們通過仿真手段將過去的真實事件還原成如今的超現實。”17從歷史而來的文化成為我們安置身體和靈魂的載體。世界在變,我們意圖以向后的姿態穩住自身,讓動勢慢下來,讓言說有所依托,以情感連接起來的個體關系、性別意識、民族關系和地理聯系只有在回望之間方使懸著的心落了地。
從20世紀初的20年,看21世紀的前20年,從科玄之爭到神話的出場,從人工智能是否能打敗人類、虛擬生活是否是另一種真實生活,到擁有數以億計讀者充滿神鬼怪異的網文,這里充滿往前沖和回望來路的強烈張力。兩股力量拉扯著,共同在一個時空呈現。不同的是,20世紀面臨著民族存續的危亡,而今這一切卻在消費文化的話語傾銷中變成趣味,成為一種新生活方式的體驗,文本中的幻想隨之變成笑談,嚴肅性被類型化的文本和故事拆解。盡管如此,話題的不斷反復,疑惑不予討論的狂歡,并不影響人工智能/人的關系問題尖銳地橫亙在人類現實的前路。距離遠近與時間有關,但就像小說中的時空穿梭,時間變得可操控起來,這使元宇宙、ChatGPT變成了互聯網時代的事件。
這種狀況,與前面我們追蹤的幾條線路在不同方向聚合起來。在緊密鏈接現實的批評層面,盡管齊澤克在鄙夷人工智能實則為人工智障,他更擔心被“用人類語言喂養”的人工智能會給這個世界帶來非文明化的恐慌,那將是人類偏見、惡念的洪水泛濫。齊澤克的立腳點在我們必須反思人類本身,這是對人類歷史與現實的回望。批評小冰只是機械地套路化“作詩”,所希求的是人類詩歌的創造性、可變性和不拘一格,以使作為人的“我們”穩下來,平復躁動,回視自身,找尋自己“因何而是”。這一思考路徑正是千年以來我們關于“人”的探索之途,從人是什么、人的不同在哪里,到如今人工智能橫刀立馬之時,將這個老問題再次推到前臺,更顯其滿身歷史風霜的意義和價值。戴錦華將這樣穩住自己的時刻稱為“臨淵回眸”,李敬澤所說“文學代表人類的榮光和尊嚴”,以及在后人類情境下對物倫理的探討,都是一種提醒:在人和技術的關系上,與其漠視、恐懼,不如回到人本身,回到人與人之間,不去做魯迅先生筆下的昏蛋、孱頭,打破人朝向“物世界”的貪戀和不予置評的全盤接受,立足人的世界正視人是什么這一亙古常新的哲學命題。
不斷的回望行為本身,亦是確定人之主體性的強烈意圖。盡管“在超越我們感官的層面上,宇宙是屬于機器的,機器穿透了時空禁戒,有如巫師一般地敘述著不安、憂慮和迷惑,還時常沒有任何先兆地直接影響了我們是什么和我們想象自己是什么……在機器周圍,現實就這樣一步步被創造出來,我們與之交流,問它們此刻看到了什么”18,然而,不容否定的是,在“人與機器”這對關系上,肉身和碳基的區別,決定了我們想象的維度。在無盡的想象世界,從神話世界中生長出來的玄幻、在不同異世界穿越的男男女女,其想象的起點圍繞著身體的改變進行。
身體到底意味著什么呢?僅僅是物質的軀干、可量化的細胞組織、X光下的圖譜?假如僅僅是一具可以量化的生物體,那人類與機器之間的障礙似乎只是何時拆解的時間問題。顯然不是。每個人情感、境遇、感悟和生活的不可復制,每一天的流逝匯成浩浩蕩蕩的歷史,這無數的“每一個”成就了人的身體的文化性。人類的身體,承載著人文化的變遷。詩歌、小說、批評,或者文學,其言說所呈現的正是個體的差異,是創造,是發現。所以,當我們身處后人類情境,或者與賽博空間共存的境遇,討論的核心問題依舊是“‘我’還是‘我’嗎”“又將以何證實自身”這樣的老問題,這樣的思考或許會被技術至上主義者指斥為掩耳盜鈴、自說自話,但這種自證身份的努力、對美好世界的希冀與想象,所表達的正是對有限現實的反抗,每一點反抗都包含著創造力的種子。
或許這是幻想,但我們擁有幻想的權利。關于人的身體,可以如阿凡達進入另一個時空,或者像黑客帝國、銀翼殺手般成為由科技控制的怪胎,也可能成為變種異煞中基因圖譜控制下的天然人體。中國的科幻,或者當下網絡世界關于人的身體的想象,同樣有各種各樣的形態和可能,變成一棵樹、一朵花、一條毒蛇,或者地底的陰魂惡鬼,或者帶著系統去穿越,但經由不同身體所包裹著的卻是對浪漫、激情、新奇和情感的追求。不同藝術形式,不同情感形態,不同文化給養,構成了數字化時代的浪漫主義。這些文本用眾多類型化文本搭建起不斷變化,充滿多樣性、差異性的話語世界。“賽博空間”或許真正做到了使人擺脫“肉身”的限制,達到“靈肉分離”的境界。然而,就如我們在無數次的游戲、穿越、無限流中看到的,所能承載靈魂的最終只能是肉身,這種靈與肉之間的矛盾似乎一直沒有停止過。哪怕經歷了換身體的過程,肉體依舊站在那里,似乎靜靜地標識著等級、差異。肉體是哲學上最大的勝利者,其上有身體和靈魂駐足。這讓我想起博爾赫斯的分析,科學是在無限的空間中發展的一個有限的領域;它的每一次新的擴張使之了解陌生領域中更多的范圍,但陌生領域是不會窮盡的。福樓拜寫道:“我們仍舊一無所知,我們想猜猜這個永遠也不會向我們露出真容的最終真理。想得出一個結論的狂熱是一切狂躁中最不幸的和最貧乏的。”19藝術的運作必須是通過象征來進行的;最大的領域是無限中的一個點;兩個荒謬的抄寫員可以代表福樓拜,也可以代表叔本華或牛頓。我們呢?
【注釋】
①《專訪戴錦華:我質疑技術樂觀主義,馬斯克叫停AI非常滑稽》,見2023年6月23日“南方周末”App。
②⑩1118奧利維耶·迪安斯:《金屬與肉體:技術如何接管人類進化》,朱光瑋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21,第9、25、19、14-15頁。
③文貴良:《從小冰到ChatGPT:對人工智能與漢語詩學的一個考察》,《南方文壇》2023年第3期。
④⑤齊澤克:《人工智障》,原文2023年3月23日發表于Project Syndicate,譯文2023年3月30日首發于“遠讀”公眾號,編者按來自“保馬”公眾號。
⑥⑧17約翰·阿米蒂奇、喬安妮·羅伯茨:《與賽博空間并存:21世紀技術與社會研究》,曹順娣譯,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16,第26、25、17-18頁。
⑦張進、姚富瑞:《物的倫理性:后人類語境中文藝美學研究的新動向》,《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王坤宇:《后人類語境與文藝理論新動向》,《南京社會科學》2022年第1期。
⑨《獨家|李敬澤:語言主權與作者的存亡——關于超級AI,自鳳凰文學之夜開始的演講》,“文學報”公眾號2023年7月12日。
1213141516李佳蓬:《青年世代》,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第1、13、8、169、233頁。
19博爾赫斯:《〈布瓦和白居謝〉的辯護》,載《博爾赫斯談藝錄》,王永年、徐鶴林、黃錦炎等譯,浙江文藝出版社,2005,第56頁。
(張春梅,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姜琴,江南大學網絡文藝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