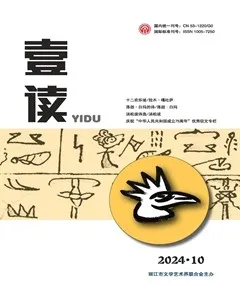垂直下落的雪
開頭已是結局,人生不過倏忽而已。
——題記
一
倒計時,從十默念到一。大約又過了四五秒的樣子,電腦屏幕右下方的數字才從59變成00,11月12日,新的一天開始了。我將電腦息屏,站起來走到窗邊,心里對自己說:生日快樂。
長春的夜晚,大雪漫無邊際地下著,寒風把窗子拍打得噼啪作響。透過水霧彌漫的玻璃看去,外面昏黃路燈下的雪花四散飛射,像粗鹽,一粒粒狂亂著,相互碰撞,或打在一些樹、公寓樓、地面、車輛之類的物體上,使它們遭遇成倍的風雪摧殘,風中不時傳來“咔嚓”的斷裂聲,有時是“咣”的倒地聲。風稍靜些,雪也下得柔和了,像下面條一樣,簌簌往十樓底下的地面癱軟下去。其中有一捧雪很大,掉落的速度也更快,也許是更重的緣故,它還包裹著其他東西,可能是樹枝、瓦片,或窗木什么的,我看得模模糊糊。那么一大團雪直直往下墜落,只聽“嘭”的一聲,雪團就砸在了堅硬、結冰凍僵的地面,散開了。
我不禁打了個哆嗦,想起尚未完成的論文,心里就直犯冷。按照我的預算,大概還有一兩萬字才能寫完初稿,一個碩士論文,八九萬字已經綽綽有余。現在,是徹底寫不下去了,緊繃的線終于斷了,我不停嘆息,心跳就沒有正常過,盡管是凌晨,頭腦昏昏沉沉,但就是睡不著。我沒敢打擾導師,實際上,我已經兩個月沒有聯系他了,按慣例,只要我不主動聯系他,他就不會想起還有我這個學生。
我真想推開窗子跳下去。想起江學長曾對我說的這句話,那時他正為他近三十萬字的博士畢業論文而焦躁不安,我坐在他對面,將夾起正要往嘴里送的土豆片停在嘴前,一臉詫異地看著他。按我對他性格的了解,他絕不會對我開這樣的生死玩笑,他老實,近乎迂腐,就像我村里人背地里說我的一樣:讀那么多書,都讀傻了,有什么用?對這樣的言論,我從來不屑,我天生話少,也不會跟他們辯解,但我有時竟覺得這樣的評論無比貼切于江學長。大多數時候他就是這樣一個人,癡癡的,木訥、沉默寡言,除了在導師辦公室、圖書館、食堂,就是關在寢室,有時我去找他,發現他一個人對著窗子低聲自言自語,因為久坐而長成一副臃腫的身體,遠遠看著就是一個傻子樣。我有些擔心他,透過火鍋的熱氣,我看到他那張因熬夜寫論文而蒼白、憔悴的臉,上面布滿了凄涼與絕望,他才三十一歲,但已經頭發稀疏,頭頂正中露出遠大于實際年齡的地中海。我暗自嘆息,似乎看到一顆未來的子彈,直指我壓抑的人生盡頭。
怎么,又遇到瓶頸,寫不了嗎?我試探著問。
他搖搖頭,苦澀地說道,是平時論文。我想起他曾經說過的平時論文達標發表情況,莊教授要求至少四篇sci以及兩篇核心,否則不能畢業。實際上,這只是莊教授的個人要求,按照雪宴大學的研究生畢業條件,達到他博導要求的一半原則上就沒問題,他早已過半,但離畢業仍遙遙無期。我安慰他,萬事不要想得太悲觀,放平心態總會看到曙光。
他艱難張口,想對我說什么又仿佛難以言狀,最后才重重嘆氣,畢業好難!
二
是的,都很難。時間在我們身上隨意踩下它野蠻的獸蹄,一臉戲謔地看我們垂死掙扎。
我看向十樓的窗外,想:如果跳下去會是什么樣子?會疼嗎,頭會破嗎,腦漿與腸子流一地,在別人看來過于凄慘?這多少有些尷尬。或者并不直接死去,撞上窗臺、樹枝、石頭等堅硬物體,眼睛被刺穿,余生在殘疾中度過,這更加讓人難以接受。我不禁退后幾步,陷入霎時的矛盾境地:不想繼續活著,但畏懼死;想要死的結果,但怕死H8GioA55qvoK3If8fb8WbN7o2Ff/B/6dGxubH4tICDc=的過程;或者只是一條通往死的殘缺之路,那比死不如。還有就是,這面窗子下是研究生公寓的后檐地帶,離外街道隔一堵厚墻,一般不會有人去,倒可以死得很安靜,但那里有一排因積雪停著的自行車,我并不想死在別人的臭屁股之下。我告訴自己,要盡量死得勇敢、壯烈一些,像雪一樣潔白地往下墜。
“蘇教授”帶著他那愁容問我站那干嘛,為什么還不睡覺?他是我室友,一個東北人,因為一臉絡腮胡酷似某教授,被我們戲稱“蘇教授”。他的愁容是因為要在緊張的時間里重寫并完成萬字以上的文獻綜述。我反問,教授不知?“蘇教授”低頭慘笑,說,我只是個狗屁教授。我倆都因這簡單的回答而稍有快意。他軟綿綿爬上床睡覺,我則拿洗漱品去公共盥洗室。女裝大佬也在,他仍然是以往那副扮相,長發披肩,格子短裙和白色長襪,只是那張臉稍顯滄桑,嘴唇上還有未剔除干凈的胡子。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私下聽別人叫他女裝大佬。實際上,這是他獨特的解壓方式。這些研究生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解壓方式,有人養烏龜倉鼠、有人抽煙喝酒、有人吃零食泡面,有人手淫等等,不一而足。我接著洗臉水,女裝大佬突然扭頭問我,兄弟,你剛才有看到什么東西掉下去嗎?
我看著他近乎慘白的臉色覺得奇怪,但還是搖搖頭。他看著我,支支吾吾說,似乎……是,一道人影。我被他的話電了一下,有些驚疑說,也許你看錯了,那么大的風雪。他顫抖著說,是,是的,可能錯了。說著端盆匆匆離開。
只剩我一個人,以及窗外呼呼的風聲,燈光散發著死豬一樣瘆人的冷氣。我回到寢室,但不再靠近窗子,也不敢再往下張望。我臨窗而睡,心里顫顫,女裝大佬的話一遍遍在我耳邊響起,恍惚中,似乎有一座墳墓似的黑影就緊貼在窗子上注視我,我閉眼強迫自己入睡,但并不能,我抱著自己狂跳的心臟輾轉反側了許久才睡著。
我睡到中午醒來,頭腦一片昏沉。并沒有做夢,也許做了,一些亂糟糟的影像,但醒來即忘。按照“蘇教授”說的,我們記憶力下降,反應變慢,對生活一片空白,從開始寫論文起就是這樣。“蘇教授”應該見他導師去了,空蕩蕩的寢室只有我一個人,每次我醒來,都仿佛是從一座死寂的墳墓里醒來,要多呼吸幾下,空氣才漸漸變得熟悉,慢慢引領著我回到熟悉的人世。我起來習慣性地打開電腦,只是茫然看著,并不想寫一個字。我忐忑等待“蘇教授”給我回復消息,看到他說,沒什么新消息啊,能有什么事,除了論文與工作還能有什么事?我突然長松了一口氣。我站起身,準備發消息叫江學長一起去吃飯,他太孤獨了,但想了想終究沒有。
我一個人冒雪去食堂,天地白茫茫一片,雪又堆厚了許多,風幾乎要把人刮走。
多點一條雞腿給自己額外加餐,這天最重要的儀式就算完成了。
我吃著總共不足六塊錢的飯菜,偶爾心酸地想:人命卑賤,有時連富人家的寵物都不如。我想起江學長來,江學長最怕吵鬧,因此他早在上個學期就搬到了十一樓的一間空寢室,一個人住下,反鎖上門,一頭扎在研究與論文的苦海里。我有幾次去找他,敲了好久的門他才慢吞吞打開,愣愣地看著我說,是你啊,學弟,有,有事嗎?我說周末一起吃個飯,他面無表情但并未拒絕。他坐我對面,一貫沉默,并不擅閑聊,但只要跟他說起在意的某個學術話題,他又往往能頭頭是道地說出許多獨到的見解來。他問我,你論文應該早就寫完了吧?我說沒有,七萬多字,大概差個一兩萬字才能交初稿。他顯得疑惑,碩士論文兩三萬就行,需要寫這么多?
我說,這其實和你們一樣,博士只要十五萬左右,你為什么寫到三十萬?
江學長一愣,是的。太卷了,像學術陰謀,你知道,但你不得不。只是沒想到碩士也這樣。
我說,現在大家都在湊字數,仿佛越多越好,越受重視。老師們雖然沒有明說,但正是他們的沉默助長了學生論文卷字數的亂象。
江學長說,論文不像論文,做研究的人也跟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總在想,這書讀著有什么意義?
我撇撇嘴,混個文憑,找個工作,繼續等死唄。
這句話說完,我看到江學長原本頹喪的臉色又挫了幾分。他端起面前的茶杯一口喝完,隨后才充滿迷茫地問我,學弟,我問你啊,你認真回答,如果你一早就知道你正在做一件毫無意義,最終也可能沒有結果的事情,你還會繼續做下去,或者有什么堅持的理由嗎?
他巴望著我,就像在巴望一個渴求已久的答案,讓他不至于枯竭而死。
我感到壓力,想了想,并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他,你知道人最終都會走向一個共同的,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終點嗎?他點點頭,說,都會死。
我嘆氣,是的,我們一早就知道我們最終都會死,一個毫無意義的結果,可為什么我們不直接去死?反而是更加努力地活著,難道你就可以說你正在毫無意義地活著嗎?
江學長沉默良久,最后才平靜地說,我想我懂了。
我則暗自長舒了一口氣。當時想的是,江學長懂了,或者說想通了,世間萬事萬物并不一定是要有明確因果和意義才得以存在的,一個事物有時僅僅只是一個事物本身,而不需要通過他者來關照才得以自證。就像我們活著,一步步走向死亡地活著,我們最終會走到那個毫無意義的終點,但我們并不是為了走到這個終點才活著;我們活著,毫無意義地活著,無奈地活著,不被需要地活著,我們以活著的過程來嘲笑必然的結果,就像一個出生就被指定為救世主的人最后成為惡魔,這個世界本不需要人來救,強加太多的主義反而讓我們終生被囚;就像在某一刻,真空說爆炸就爆炸,然后有了時間、空間、能量與物質,沒有因果、沒有定數、沒有意義,在毀滅的時候,宇宙無中生有。
我以為江學長懂的是這樣,后來我才后知后覺地意識到,或許江學長并沒有按照我的軌跡去想,而是走向了完全相反的另一端。而我的話就像蝴蝶效應的起源一樣,讓他直接看到了透明的結果。
三
我的擔驚受怕在第三天達到頂峰。中午,我又給江學長發去微信,依舊不見回復。我知道他基本不怎么登微信的,之前有一次聯系,他是隔了一個星期之后才回復的我。我也并不敢貿然直接敲門去打擾他的學術研究,雖然熟悉,但次數多了總歸不好,于是只能干等著,但這次不一樣,我總感覺冥冥之中有多個無形的征兆指向那個最壞的結果。
我連日來憂心忡忡,睡得并不好。實際上第二天下午時分我就聯系過他,并無結果。其間我又問“蘇教授”有沒有什么新消息,“蘇教授”照舊搖頭。在昏暗的走廊我再次碰見女裝大佬,他沒有作聲,瞥了我一眼之后就匆匆離開。我回到電腦前坐下,二十度恒溫的暖氣將我浸泡得身體發軟,頭腦昏脹,生活又回到一潭死水的樣子,三天的時間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腐爛并長滿蛆蟲的,我們活在一片窒息似的空氣里,有時,我竟無比渴望發生一場突然的意外或死亡,在巨大的爆炸中,肢體殘碎、規則破損,我們麻木的悲傷舉著我們,我們得以重生,眼睛長滿青草般水嫩的空氣,地球獲救般大口呼吸……
是的,存在毫無意義。但我不像暴君國王卡利古拉一樣擁有毀滅一切的權力和勇氣,我只能虛假地在近乎絕望的江學長面前說,活著本身就是意義,我們還能比《活著》里的福貴更悲慘?薩特告訴我們,存在無意義的意義在于空白的人生我們要自己去選擇,自己負責,將你的生命軌跡盡量生動地填滿這張空白的紙,這就是存在的意義。
自己選擇?生命軌跡?我那時清楚地看到從江學長嘴里發出嘲諷的嗤笑聲。
我們從出生開始,一切就已經被選擇好了,不是嗎?我們讀書,不停地讀,讀到某一天,茫然畢業,找工作,匆匆結婚生子,然后慢慢老死。一切不過都是提前預定好的而已,我們只是僵硬地配合著表演,這就是我們的生命軌跡,像透明膠帶,我們能一眼看透,但還是不得已被它粘住,纏死,我們又何曾真正有過選擇?江學長說著,臉上布滿落日般反復重演命運的悲壯,我想起推石頭的西西弗斯。
突然,江學長向前傾近,問我,你相信命運嗎?學弟。
我有些迷茫地說,也許吧,有時候……
有時候,就仿佛冥冥之中發生的事本應如此,是嗎?他看著我,我沒有回答,實際上我那時竟然愣神想起了被命運悲慘捉弄一生的俄狄浦斯王。江學長又喊了一聲,我驚醒,他自顧自說,或許你并不相信,我起初準備寫杜甫的論文的,但后來重新開題改寫了盧照鄰。
學長,你的《盧照鄰后期詩文研究》還在寫?最初是寫杜甫?
是啊。最初我以為杜甫是命運,包括我的名字來源,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無奈杜甫的研究太多了,已經沒有可挖掘的余地,我只能相對性選了盧照鄰,現在嘛,我似乎終于看清楚,盧照鄰才是真正的命運。江學長低聲冷笑。
我聽得糊涂,但江學長偶爾露出的神態讓我陌生且害怕,仿佛自從上次的談話后,他身上那股迂腐氣就變成某種偏執,幾乎瘋狂,待我再細看時,一切又仿佛不過是錯覺。
他沒再說起命運,連命運本身也像一種錯覺。
我們坐在食堂二樓靠邊的窗子,窗外大雪漫天,在肆意的寒風呼嘯下,雪花像無數被驅趕的細碎的夢,怎么也連綴不起來。我想,雪花也是一種花,只有在寒冬才遍地開放;春天也是一種死亡,以無數的腐爛堆積出來的生機;這樣的時節,說不清好壞,辨不清真假。
盧照鄰詩云:“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回。”
四
只是難以理解,為什么看起來人畜無害的導師、教授……
我接過話說,為什么他們有時幼稚、自私小氣,心胸狹窄?或者一個看上去過于清高、冷淡的教授最后往往成為最難以理解的反面,難以接受?
江學長支支吾吾,……也不全是,只是想知道他們是如何對待男女感情的,我看到的,很亂,特別是教授們,莊老師也——我不明白,他們,為什么——
江學長以手掩面,我能感受到他因他敬愛的老師而產生的極度失落、痛惜的心情。這就像一個圣人弟子有天看到圣人落魄的場景,或再貼切點,就像虔誠的和尚有一天看到佛祖奸了一個女人,他們那難以置信、失落、破碎的心境,一瞬間,信仰崩塌,好壞倒轉,真假錯亂。而作為信仰的他們的倒塌對外人的打擊與距離又是相關的,距離越近,受到的打擊越大,反之,則并沒有什么,在無關緊要的人眼中,頂多就是一個人對多年前虧欠的自己用化身野獸般的方式去惡補。
我只能用我所觀察和所想到的向江學長解釋,且同時悲哀地發現,我們正走在一個難以逆轉的惡性循環中。
我說,學長你看啊,從年齡上開始分析,那些與女學生或其他女人亂搞關系的老師、教授們基本都處在三十末近四五十歲的樣子,為什么?這么大的生理與心理年齡的反差?因為他們在年輕、在最合適的時候錯過了太多太多了啊。凡能走到教授這個高度的,誰不是讀書的能手?但,也正是因為他們讀了太多的書,在正當玩耍的時候他們只讀書;在該談戀愛,體驗情感的時候他們只讀書,后來又忙工作、做研究、評職稱,等終于都熬過來了,身心也放松了,巨大的落差與虧欠感也在對過往的回憶與思考中浮現出來了,這時他們會普遍產生一種對于人生的虛度與無意義感來,他們悲哀地發現,人過半百,他們的童真、歡樂、青春、愛情、性體驗一片空白,他們更不平衡,更空虛了。于是他們開始以惡補的方式,甚至是歇斯底里地去對當初那個失去太多的自己進行補償,哪怕毫無理性,哪怕罔顧人倫,他們也要填滿那片人生的空白,追求所謂的人生圓滿,所以,各種亂象就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
江學長問,真是這樣嗎?
我說,學長,問你個問題,你談過戀愛嗎?
江學長淡然搖搖頭說,沒有時間。
我說,你看,我們不也是這樣?我們活生生就是那些教授這個階段的樣子嘛,或許,未來某一天我們最終也不過就是他們現在的樣子。
江學長顯然被嚇了一跳,我看到他坐在椅子上的身體猛地向后一縮,臉色蒼白到毫無血色,我也會成為他們?不能避免?但我——不想成為他們!
我說,誰都不想,可我們不過是個俗人,固然我們堅持初心,但設身處地想一想,現在我們的所思所想是否還能鎮住那時的所思所想,我覺得,恐怕恰恰相反。
不,不會的,總有辦法避免,我可以不當老師的……
學長!不知道怎么的,我突然感到憤懣,這一刻,我似乎能理解村里面的人背地里說我讀書讀到迂腐的嘲諷表情了。我看江學長也同樣如此,我腦袋一發熱,開始冷語輸出,是對他,又仿佛是在針對某個我不愿承認的自己:誰不想當圣人,纖塵不染?但這個世界并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好與壞、美與丑、黑與白總是相生相伴,相互依存的。當你看到一件過于完美的事物時,你就要同時想到,在它的美破碎時所爆發出來的巨大的丑惡,丑是美的代價,美是丑的遮掩。你要去試著接受這個并不完美的世界,它那殘缺、骯臟、邪惡的一面,你不是也經常看到嗎?在美的旁邊,通常緊挨著丑,比如銀河緊挨著黑洞……
雪越下越大,在這一片晶瑩剔透的潔白之下,是黑乎乎的土地,土地下是無數交纏的污水、糞水的管道。或許,這大雪還隱藏了其他,等待被挖掘。
那個最壞的結果像夢魘一樣折磨著我。到中午十二點,我終于下定決心看看十樓窗下那座想象中的墳墓,深呼吸之后,我拉開窗簾,緩緩打開左邊的窗戶,水滴像血線,冷風灌入房間,我身后的寢室門在壓強下被嘭地關上,我渾身一震。我踮起腳尖俯身在窗邊,往十樓下的地面看去,地面白慘慘一片,一些樹與瘦弱的房屋在大雪覆蓋下不堪重負地強撐著,公寓后的地面冷清、蕭索,一排自行車停靠那里,有些被吹倒了,大雪淹沒了它們,使它們只露出部分來,遠遠看去,就像一些動物的斷肢。
我關上窗子,感到一陣輕松。至少,在我看來的情況是,那個懸空的結果并沒有落下去,此刻,對我來說,沒結果就是最好的結果。
我發消息給學長,仍舊沒有回復,連同上面的幾條也是,我的心又不安了,一個星期雖沒到,但我時刻感受到一種不能繼續等下去的焦躁。下午近傍晚的時分,我來到十一樓,江學長的房間關著,我叫了許久他都不曾開門,或許他在,也或許在導師辦公室,甚至和莊老師一起討論、研究學術并未歸來也是常見的事。
從最近一次交流的情況來看,他的論文似乎進入了某種難產期,甚至有回爐重造的可能,也是那時,我看到他臉上那徹底的絕望,帶著死亡的氣息。
五
十一月十二日的前一天,在購買圈有個俗稱,叫“雙十一”。
一個所有東西都被賤賣和被搶購的日子,半帶欺騙的性質,被那些躲在世界各個角落的便宜之人當神一樣供奉的日子。在下午江學長來找我之前,我也買了衣服、褲子和鞋,全身上下算起來不超過六十塊錢,便宜之人說的就是我自己。說起來,江學長還是第一次主動找我,這讓我感到很驚訝,我差不多以為我們不會再愉快相處了,特別是在上次我們有過不愉快的交談之后。他或許排斥我的俗氣,而我討厭他那無可挽救的迂腐,但我知道,我們本質上是同一種人,箍住我們屬于共同屬性的詞有很多,比如“窮酸”、“鄉野”、“內向”等等,我知道,我們這具廉價的身體能讀書一直讀到這里,都受過了太多難以言狀的屈辱,他只不過比我多受了幾年。
我問他不買點什么東西嗎?機會難得,他冷冷說,再也不需要了。我的話又被哽住了,于是不再問,而且我能看出來,他的狀態完全不對,平靜、淡漠,有一種魔鬼附體的死寂。我想起浮士德。突然他說,我請你。我有些生氣,還沒待我說話,他又說,你師門的那個什么珊請了全部男生沒有請你,你也不要總是放在心里,不要在乎他們,對我們來說,我們在精神上超越他們就夠了。我突然想哭,一種受盡屈辱后被看到的大哭。
他凝視著我說,學弟,好好完成論文,祝你如期畢業,找到一份好工作,去改變你一直想改變的根本性東西。
我說,學長你也一樣啊,而且你比我前途更好,機會更多。
他只是平靜地搖搖頭,不一樣的,我沒有可能了,我永遠畢不了業的。
我疑惑地問,怎么,是平時論文,還是盧照鄰的研究,你不是加班加點都快趕完了嗎?
他慘然一笑,是完成了,但是,他是不會放我走的,只要我還能出力,我就會永遠被困在這里,退不了,出不去。
他?莊老師?我問,江學長點點頭,其他老師都說沒問題,但他說推倒就推倒了,叫我重新開題,那是三十萬字啊!我也算是看清楚了,他是不會放我離開的。
可是,為什么啊,他憑什么這樣,他有什么權利這樣做?我的不滿與憤怒一下子就出來了,一想到三十萬字的鮮血被寥寥幾句就無情地推翻了,我的心就痛得難受,我對學長說,我們不能坐以待斃,我們上訴、舉報,去校長那里反應。
學長淡漠地搖搖頭,沒有用的,作為博導,他有一票否決博士論文的權利,校長也沒轍,我是真的走不了,像盧照鄰一樣,到最后了,進退無路。
我說,學長,你不要著急,一定還有辦法,我們找人,我們去告他!我們還可以網上公開他,讓他現出原形,身敗名裂。
不,不行的,我不能這樣做,他再怎么說也是我導師,在我心中等同于父親,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我……
又來了,又來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站起來大吼,學長!他算個什么狗屁導師,禽獸還差不多,你就是太順受,思想包袱太多,他才這樣為難你啊!
他嘆氣道,也許吧,我們不說他了,快坐下,別影響你吃飯的心情了。
我雖冒火,但也坐下來。他說,學弟,其實你比我更有前途,你的很多思想、見解,讀過的書,在我看來,很多博士都不如你,你一定要順利畢業,去實現你的精彩人生。
我點點頭,這一刻,我重新看到這個滿臉滄桑,憔悴堆積如霜的人,他像風中搖晃的微弱燭火,隨時有被撲滅的可能,我可憐起他來,但也是在那時,我終于下定了決心,我,不會想要繼續攻讀博士了。
以往“雙十一”。江學長坐在我面前自顧自說著,以往我買很多東西,都是些不值錢的玩意兒,都不需要了,感覺很沒意思呢,你說,我們這些便宜之人,是不是天生就和這些便宜之貨搭配在一起才最合適?為什么啊?因為我們生就如此啊,這是沒法改變的事實,甚至就算我們一步步忍受著走到了這里,也仍然毫無希望,我們什么也改變不了。沒法子呀,我爸媽希望我“江間波浪兼天涌”,一路飛上高空,逆襲人生,改變命運,帶他們享福,所以我叫江勇,勇敢的勇。可惜,我這一生都在辜負這個名字,辜負我爸,辜負我媽,是我對不起他們,我,我又怎么能空蕩蕩回去面對他們,他們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他們在等著我,我怎么可以讓他們這窮苦的一生,再次失望……
我看到他流下眼淚。我關心道,學長,不要太擔憂。
他平靜地搖搖頭說,我沒事,別擔心,既然生得便宜,這不可選擇,那我就與這便宜的人生抗爭到底,所以你看,我不買東西了,甚至也不會這么便宜地死。
我頓時放心下來。
但現在仔細想想,我覺得我可能理解錯了江學長所謂的對便宜之人的“抗爭”。或者說,他把這個“抗爭”的時段縮短成了特定的今天和明天,而不是現在和余生。巨大的不安在我心中像原子彈一樣爆炸。夜晚,我仿佛枕著冰冷的墳墓入睡。
第四天一早,我就跑到公寓樓窗子下方的地點查看,除了一排自行車,地上就只有一些腳印,雪有被翻動的痕跡,又新下了一層薄雪,從現場的痕跡來看,大概是有人來推走了自行車,不會再有什么新情況出現了。我這樣想。
我站在大雪中,幾朵雪花落在我的額頭,滑過臉頰,像親人安慰似的,溫柔、細膩,我感到無比安心,連日以來的猜想與緊張一下子就得到了松弛,疲倦也襲來了,我大步走回寢室,準備補個覺,然后靜待江學長看到消息之后回復我,或者來找我。
在夢中,我看到盧照鄰人生的最后一幕是這樣的:具茨山下,幽憂子再度咳血,他長嘆一聲,站起來推開窗子,看向田地外的穎水,一個早已在病痛與絕望的雙重折磨下蠢動的心思在此刻終于決然。他環顧四周,先拿起《釋疾文》掃了一眼,又捧起《五悲文》哽咽而讀,讀至“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手里的書落地,風灌門而入,快速翻動書頁,幽憂子得以快速回顧他短暫而又多難的一生。書合上,他回過頭,看向窗外不遠處的墳墓,曾經有多少無眠的日子他都在那墳墓的溫床里度過的,他的心再次安靜下來。他站起身,一步步走到環繞自己小屋的穎水河邊,像睡覺一樣,閉眼,然后躺下去。
六
尸體是后來被人發現的。
“蘇教授”搖醒睡夢中的我,我看到時間跳過12點,第四天的中午看起來像垂垂老矣的下午。我看到“蘇教授”震驚的臉色,聽到他急劇的喘息,顯然,他是著急跑回來的。他一把拉住我說,雪宴大學都在傳,有研究生跳樓自殺了。他一臉驚恐地看向窗外,聽說就是從十一樓的這面窗子跳下去的,是個博士,已經死了好幾天了,被埋在大雪下,今天才被人發現的。
我陷入巨大的沉默當中。“蘇教授”自顧自說著,聽說發現的人是去推自行車的,然后翻開大雪,發現了早已結冰、凍僵的尸體,頭碎成了幾瓣,身體破了一地,但并未腐臭。發現的那人隨后通知了學校,學校聯系警方,大概在早晨五六點的時候尸體就被運走了……喂,你怎么了,被嚇到了?說話啊!
我問,是誰發現的?“蘇教授”想了想,說是一個女生,但立即就搖了搖頭,又說是一個男生,有胡子,且嗓音渾厚。我和“蘇教授”對視一眼,我想,我大概知道是誰了。
學校公布有官方消息嗎?具體身份報道了嗎?為什么自殺?“蘇教授”像看傻子一樣盯著我,然后說,這種事,學校怎么可能會有官方公布?他們希望的是事情鬧得越小、影響越小最好,或者是能私下悄無聲息地解決就盡量私下解決,你也知道,自殺這種事,校方其實是沒多大責任的,就算要賠,也賠不了多少。
他拉著我的胳膊來到窗邊,問我,前幾天晚上,你聽到過什么動靜嗎?我看著他,發現自己說不出話,于是只好對他搖頭。他說,聽說是莊教授的博士生,具體自殺原因不知道,但我猜,大概率是論文不過關,壓力太大跳樓自殺的。莊教授歷來對學生就很嚴格。
又過了一個星期,學校和死者家屬私下解決了,由于是自殺,最終學校賠了十六萬。一條人命,曾經活生生的人,一個三十一歲的博士生,在他死后,被定性為一個冰冷且低廉的數字:十六萬。
我頹然坐在椅子上,翻看微信上我發出的信息,我知道,永遠不會再有回復了。手指一按一點,就像被系統刪除一樣,這個人,也徹底被這個世界刪除了,仿佛從來就沒有出現過。
下午我買了一束花來到宴湖邊,發現沿湖岸的一圈雪地上都擺放著鮮花,這是不相識的研究生們自發為他送行和祭奠。他們或三三兩兩,或一人單行,放下鮮花就走,因為學校禁止學生搞祭奠,周圍還有保安環伺,他們眼神冷冽,仿佛隨時都能逮住一個學生,給他定罪。來祭奠的人都沒有說話,他們的沉默是在為你吶喊,為你感到不值,悲憤。或許,他們也——羨慕你的勇敢。
你死得那么潔白、高貴,而我還在廉價地活著。
我才是那個躲在角落里的可憎的便宜之人,當然也包括他。實際上,當你熬過便宜之日,抵達新的凌晨時,你從十一樓像雪花一樣高貴地垂直墜落,“嘭”的一聲之后,你的死讓你完成了新生,卻讓另外兩個人陷入了掙不脫的死之迷瘴。我終日沉湎夢幻,不敢去揭開那個真相;而他,日夜被那死亡的陰影所籠罩,他臉色蒼白,胡子瘋長,我們承受的折磨和壓抑在第四日都達到了一個崩塌的臨界點。他比我去得更早,理由是推自行車,這顯然有悖于常理,大雪淹沒膝蓋的情況下,自行車沒有絲毫用處,他就這樣把沉睡的你當做真相一樣挖了出來,你破碎的樣子令我不忍細看,在他走后,我也走到了那里,除了腳印,那里只有一座真相的廢墟。像我們在人世低微的呼吸。而在我的記憶中,你一直停留在墜落的時刻——
好吧,現在讓我們三個人一起再重新數一遍,不許出差錯,從十默念到一,倒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