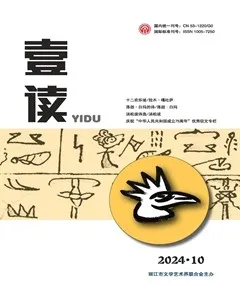寫在群山之上
一
大約初中畢業(yè)前后的某天晚上吃晚飯時,父親抱來一堆書,說是學(xué)校某某老師搬家時準(zhǔn)備當(dāng)垃圾扔了,碰巧遇著就全要來了。什么書都有,五花八門,很少看到過這么多的課外書,連飯都顧不上吃就讀了起來。有一本書名叫《你想成為一名詩人嗎》,當(dāng)時隨意翻了翻,一下就被深深吸引住了。之后如果說我與詩歌有緣的話,可能是從這本書開始的。
上師范學(xué)校時,學(xué)習(xí)壓力也沒那么大,有很多時間可以一整天地泡在圖書館里。圖書館里的詩集大都是世界名著,厚厚一大本。說實話,云里霧里的,看不懂。包括學(xué)校閱覽室里的那些詩歌雜志,也是云里霧里的,看得我昏昏欲睡。總是想不通,為什么詩歌就非得玄虛、不能說人話呢?當(dāng)時我自己認(rèn)為好的詩集,好像都是從路邊的舊書攤里淘來的。總感覺“名不見經(jīng)傳”的詩人的作品更好讀。
直到2001年來寧蒗工作,第一次接觸到時任寧蒗縣財政局局長的魯若迪基和其他小涼山詩人們的作品,我才發(fā)現(xiàn):哇,原來詩歌還可以這樣寫。簡單、易懂、口語化,而詩里的意境卻讓人回味無窮。這才是我一直追求的詩歌應(yīng)有之態(tài)。
當(dāng)時單單寧蒗縣財政局一個單位里就有好幾個詩人,有的是局長,有的是總會計師,有的是部門主管,都是管錢的專家,錢的味道和詩的味道、現(xiàn)實派和浪漫派就這樣互相交織著,彌漫在財政局院子的上空。那時縣里開“兩會”,財政局局長和發(fā)改局局長還要在會上念財政預(yù)算報告和計劃報告。時任縣長的沙萬祥跟時任財政局局長的魯若迪基調(diào)侃道:魯若,你干脆用詩歌來朗誦財政預(yù)算報告吧,標(biāo)題就叫:“赤字啊赤字!”當(dāng)時,寧蒗縣財政收入才幾百萬,財政支出卻超過幾千萬,真的是赤得一片通紅。后來聊到這事時,已經(jīng)成為我的上級領(lǐng)導(dǎo)的魯若迪基說,當(dāng)時就完全依靠“向上跑”,跟省里要錢。以普米大漢的酒量加上《小涼山很小》和《1958年》,整個縣的赤字才算“抹平”。
他的《小涼山很小》,在當(dāng)?shù)厥且粋€無法超越的高度。后來被一位大涼山的彝族歌手編成歌,在寧蒗傳唱至今。特別是在外求學(xué)、工作的寧蒗人,百唱百聽皆不厭。聽說這首詩曾被外地的某個詩人“抄襲”過,活生生把“小涼山”名稱換成另一個地名,就變成了一首“名作”。殊不知,《小涼山很小》因為有“小涼山”才出名,沒有“小涼山”了,換成什么山也都是沐猴而冠而已。
被稱為云南“小涼山”的寧蒗縣一直都是國家級貧困縣,直到我來寧蒗工作二十年后才摘掉這個帽子。小涼山雖貧困,但有兩樣最出名,一個是東西部教育合作的“寧海模式”,帶動了一大批貧困學(xué)子改變了命運,2020年還獲得國家脫貧攻堅獎;另一個就是“小涼山詩人群”。就這么一個小縣城,出了許多在全省全國都很有名的詩人。有3人獲得過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駿馬獎”,有多人獲“邊疆文學(xué)獎”、“云南日報文學(xué)獎”、“文學(xué)界詩歌評論金石獎”和云南省文藝創(chuàng)作基金獎、云南省文藝界“四個一批”人才“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新人獎”、“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之星”等等。小涼山詩人群與昭通作家群,被評論家認(rèn)為是云南上世紀(jì)80年代以來受到廣泛關(guān)注的以地域命名的兩個作家群。
“小涼山詩人群”正式命名也是近十來年的事。2006年,有人提議,這么多人了,是一個大家庭了,應(yīng)該有個名字才行。于是,這一群有著共同愛好的人聚在美麗的瀘沽湖畔一起開了個會,從此這個大家庭有了一個響亮的名字:“小涼山詩人群”。隨后,每隔一兩年,大家都會聚在一起,每人一兩首,合起來出一本合集,至今出了五六本。書名也從未改變,叫《小涼山詩人詩選》。有時候,在國內(nèi)有影響的刊物上開設(shè)專欄,大家一起以“小涼山詩人群”名義亮亮相。一個總?cè)丝谥挥惺畮兹f的小小縣城,能有這么多詩人,著實讓人料想不到。我很驚訝是什么東西給予了小涼山這片土地那么多靈性,“小涼山詩人群”里總是冒出幾個新人來,好像雨后的小涼山深山里從不缺少松茸和雞樅一般。這個群體數(shù)量大概在一百人左右,至今沒有誰正兒八經(jīng)統(tǒng)計過,也沒有什么門檻。只不過平時嘛各忙各的,上班的上班,上學(xué)的上學(xué),“戰(zhàn)”時誰登高一呼,嘩啦啦,從四面八方冒出來,滿山遍野,像古時的“寓兵于農(nóng)”。
十幾年前,麗江電視臺做了一期“小涼山詩人群”專欄采訪我時,我說“小涼山詩人群”是一個整體,而不是一個個的個體的簡單相加。整體大于個體的總和。就像一個家庭,有父母,有孩子,也有老人。“父母”(六零七零后)支撐著這個家庭的運轉(zhuǎn),是核心,是支柱;“老人”們(五零后之前的小涼山詩人們)不怎么露面,但他們是這個家庭的搖籃;孩子(八零九零后,也包括零零后)的性格不盡相同,成長得也各不一樣,但都得到家長們的呵護。難能可貴的是,這個家庭會源源不斷接納新人,而且新人也源源不斷地涌現(xiàn)。
這個群體像雪球一般越滾越大,一路生花,自帶一股強大的吸力,如木星一般,總是把大家吸引在“小涼山”這三個字的周圍。它是我們的身份,是頭銜,是割不斷的血脈。我們的生活和工作,好像都與“小涼山詩人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這里不連著就那里連著,割都割不斷。
二
2009年,我在寧蒗縣廣播電視臺工作時,在沒有一毫一厘經(jīng)費的情況下,創(chuàng)辦了一本新聞時評類的內(nèi)刊《新聞與評論》。先是每月一期,后來經(jīng)費緊張,改成雙月刊,再后來經(jīng)費又緊張,改成了季刊。在無經(jīng)費、無人員、無辦公地點的“三無”情況下,還是堅持了下來。一年后,在眾多讀者的建議下,改成了純文學(xué)內(nèi)刊,名字也改成了《寧蒗》。我從《縣志》里找到著名社會學(xué)家費孝通親筆寫的“寧蒗寶地”中“寧蒗”二字,作為這本刊物的“親筆題名”。從封面設(shè)計、內(nèi)容編排、文字編輯到審核、校對和發(fā)行,基本都是我們一群文學(xué)愛好者,一邊學(xué)習(xí)一邊摸索搞起來的。每期印好后,我們會抱著雜志給每個單位挨家挨戶送。后來,發(fā)行范圍也從最初的縣內(nèi)擴展到縣外,擴到市外。我們所有編輯,包括我這個自封的“主編”,都是沒有酬勞,作者也是沒有稿費,就寄一本樣刊代為稿費。而印刷用的經(jīng)費就只得想辦法籌集。為了找一家價格便宜的廠,我跑麗江、跑昆明,連續(xù)換了四五家,最后才固定了昆明的一家印刷廠,價格便宜質(zhì)量也可以,每個月兩千元左右。經(jīng)費主要來自“化緣”所得,每次我們會帶著一堆雜志,利用我的電視臺臺長的身份,跟縣直單位的一把手們要個幾百上千的小錢。給多少不計較,只要給就行,是當(dāng)時我們經(jīng)常“磨”他們的招數(shù)。兩百三百,那是常態(tài),遇上給兩三千的,那個興奮,從他們辦公室門口出來時感覺輕飄飄的。當(dāng)然,當(dāng)“叫花子”的事是叫上我的幾個電視臺的同事一起去的,叫上“清高”的文人們肯定不會干的。每每看到通過自己努力而誕生的嶄新的一期《寧蒗》雜志擺在眼前,聞著那些剛出爐的新書散發(fā)出來的淡淡的書香味,好像再多的委屈和誤解都值得。
我在編《寧蒗》內(nèi)刊之初,定位就是辦寧蒗人自己的雜志,重點刊發(fā)的對象是“小涼山詩人群”。后來許多人提出改版意見,但這個初心始終未變——不遺余力致力于推介“小涼山詩人群”這個品牌。每期推一位小涼山詩人群詩人,封面刊登這位詩人一張大大的近身照——我們戲稱為“封面詩人”,然后正文里開設(shè)了一個專欄,專門介紹這個詩人的創(chuàng)作情況,刊登代表詩作以及評論家對這位詩人的評論。另外,作為補充,還開設(shè)了一個欄目,專門介紹年輕的詩人或新發(fā)現(xiàn)的詩人,或者單純是為了激勵新人而刊發(fā)——自家人寫得再不好畢竟都是自家人,別人寫得再好終究是別人。
當(dāng)時,還專門為寧蒗在外讀書的大學(xué)生出了一期專刊,封面是所有作者的照片,大小不一、密密麻麻,像夜空中璀璨的群星。當(dāng)然,這群大學(xué)生的作品,詩歌類占了一半以上篇幅。如今許多活躍在云南詩壇的“小涼山詩人群”中九零后詩人,當(dāng)時都曾在這本專刊里閃爍過。
如今,小涼山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總是在國內(nèi)大報大刊上驚現(xiàn)我們并不熟悉的詩歌創(chuàng)作者名字,我們就像在茫茫森林中發(fā)現(xiàn)了一朵松茸一樣,自然而然地把他們拉入“小涼山詩人群”。也沒什么“入群”儀式,只要一“出現(xiàn)”就被“變”成我們的人。我說,“小涼山詩人群”,從不會斷代,他們會一代接著一代傳承下去。
2015年,我在寧蒗縣文廣局任副局長時,以《寧蒗》內(nèi)刊編輯的身份獲得了云南省優(yōu)秀編輯獎。第二年,調(diào)到麗江市文聯(lián)工作。從縣里調(diào)到市里來并不容易,我想與我創(chuàng)辦的《寧蒗》有一些關(guān)系,也與我默默地一直堅持做“小涼山詩人群”幕后工作也有關(guān)系。每個群體都需要沖鋒在前的勇士,也需要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
三
2016年是我詩歌創(chuàng)作的“爆發(fā)”年。一年里大大小小詩歌創(chuàng)作了兩百多首,基本每天一首。靈感忽現(xiàn),一首詩立馬就出來了。當(dāng)時感覺寫得很順手,一點也不卡殼,等靈感在腦子里一閃現(xiàn),后面的句子隨之而來,水到渠成。那一年的感覺就好像我腦子里的水龍頭突然被誰打開了一樣。有可能每個詩人都是一座“活火山”,也有那么一兩年是“爆發(fā)”期吧。挑一些自己覺得好一點的,投給《民族文學(xué)》《星星》《詩選刊》《邊疆文學(xué)》《滇池》,發(fā)了一些。當(dāng)然,絕大部分石沉大海。幸運的是有的還選入《中國詩歌年度精選》《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品選》《中國青年詩人詩選》,入選國字頭的選集,感覺蠻好。至于剩下的作品,一直到七八年后的今天,我還在固執(zhí)地、不斷地投。好像一只在空樹干里藏了許多板栗的松鼠,每天偷偷拿出一顆,直到另一個豐收季節(jié)的來臨。
而有靈感的僅僅這一年,后來偶爾來一首,自己感覺也沒有那么好。可見靈感對寫詩是如此的重要,至少對于我是這樣的,沒有靈感寫出來的詩,像是沒到秋天就被風(fēng)打落的果子。再加上后來被下派到村里當(dāng)駐村扶貧工作隊隊長,壓力更重,每天睜眼閉眼都是貧困戶,天天都感覺身心疲憊,好像一個沒氣的籃球一樣。
駐村四年多,沒有寫出像樣的作品,感覺很是對不起“小涼山詩人”這個身份。有一次,我在朋友圈發(fā)感慨時,一位多年的朋友、也是“小涼山詩人群”的重要成員之一、寧蒗縣作協(xié)主席李永天在我的朋友圈寫了這么一條評論:
“你不是沒有作品,你是把詩寫在了小涼山的群山之上。”
我為之一震,好像確實如此——也貌似為自己的“失職”推脫“責(zé)任”——但不管怎么說,如果說脫貧攻堅是一首寫在群山之上的詩,一點都不為過。
這確實是一首深深寫進大山骨頭里的詩。
每行詩句,都表達出外人無法理解的艱辛。那些深深地留在每一條進村路上的腳印,甚至用生命和鮮血,使這首詩變得驚天動地。跑馬坪村第一書記、駐村工作隊長沙天文,沙力村總支書楊大林,以及全國犧牲在扶貧一線的第一書記和工作隊員們,他們是用自己的生命歌頌了這個時代的光榮,他們是用那金黃色的鐵錘一句一句地把詩鐫刻在共和國的群山之巔。
2017年3月,我剛被派往寧蒗縣翠玉鄉(xiāng)春東村駐村時我就想,如不為老百姓做點實事,哪怕很小的實事,以后回去了人家問我駐村這幾年做了哪些事該如何回答。第二年,我成了第一書記、工作隊長,還掛職鄉(xiāng)黨委副書記。有了這些頭銜,我為老百姓辦實事就有了更多的話語權(quán)。盡心盡力為群眾辦事的初心和堅持,一年后得到了回報,大家都覺得這個戴眼鏡的隊長是個實在的人,對我的稱呼也不知什么時候開始從“隊長”變成了“干兒子”“親家”“兄弟”。
扶貧工作是艱辛的。有一次,有個喝了點酒的村民,站在路邊往我們正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顛簸的車子吐口水罵道:人嘛天天來下鄉(xiāng),路嘛不給修一下。這個吐口水的,后來有一次我們?nèi)ニ易咴L,完了拉著我們不讓走,說現(xiàn)在路也修好了,水泥路都打到家門口,產(chǎn)業(yè)也發(fā)展了,這幾年你們?yōu)榱宋覀兝习傩盏氖率鼙M委屈,必須在他家吃一頓飯再走。那天晚上,我們喝干了他家的一大壇自烤酒。
2019年,麗江廣播電臺記者胡世芳的一篇叫《老百姓的“干兒子”》的報道,使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的許多朋友都戲稱我為“春東的干兒子”。這篇報道我的文章不長,寫的事也不多,卻被春東村的許多老百姓在微信里不斷轉(zhuǎn)發(fā),也獲得了許多點贊和好評。從那次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堅守沒有白費。2020年,市里安排采訪團到寧蒗縣采訪脫貧攻堅,縣里推薦我作為第一書記代表接受采訪。幾天后,麗江電視臺記者閔志龍打電話給我,說我的事跡素材被央視的一位編導(dǎo)看中,要重新采訪,而且要在“五四”青年節(jié)那天作為青年代表播出。當(dāng)時都快五月份了,卻突降大雪,使我的工作看起來似乎平添了幾分艱辛。幾天后,節(jié)目在央視《新聞聯(lián)播》《新聞30分》《午夜新聞》以及云南臺《晚間新聞》、麗江臺《麗江新聞》播出。節(jié)目播出那天,有好幾個村民激動地打電話給我,好像看到自己的某個親戚上了電視一樣。
2020年10月,經(jīng)過半年多的倒計時,寧蒗縣終于迎來脫貧攻堅第三方評估。驗收結(jié)束那天,我們躺在村子邊的林子里,安心地睡了一個下午。我反復(fù)念道:沒想到轟轟烈烈的脫貧攻堅就這樣在一個安靜的午后結(jié)束了。始終無法相信,辛辛苦苦了五年的工作,突然間結(jié)束了,像做夢一樣。感覺從那分鐘起,看見路人的腳步似乎放慢了許多,吹到臉上的風(fēng)似乎也輕了許多,連天上的白云也暫停不動了,好像這個地球突然停止了轉(zhuǎn)動似的。
驗收完第二天一早,村子里有一位老鄉(xiāng)打電話給我,問我是不是要回去了,回去之前務(wù)必去他家坐坐。我說不會馬上走,還要等北京的習(xí)總書記向全世界莊嚴(yán)宣布中國脫貧了,我們才能走。之后一兩個月了,我也沒去赴約。喊了我?guī)状危叶家愿鞣N理由推掉后,他干脆“先斬后奏”,跑到街上的飯館訂了一桌飯,然后打電話給我說:“現(xiàn)在脫貧了,我代表全家請你喝一杯酒,這是我一家人的共同心愿,飯已經(jīng)上桌了,退是肯定退不掉了,這次務(wù)必賞臉。”他的名字叫熊文,是一家七口人的“頂梁柱”。曾經(jīng)因母親患病去世,兄弟又得大病,差點拖垮了整個家庭。經(jīng)過國家的幫扶和他自己的努力,現(xiàn)在家里每年收入達十多萬——他的事跡曾被新華社云南網(wǎng)報道過。2020年,他向組織提交了入黨申請書,鄉(xiāng)里高度重視,單獨給了他們村一個指標(biāo)。他家脫貧到致富這一過程,我一直是見證人和參與者。
我的同事們寫了許多關(guān)于我駐村的文章,黃立康的一篇散文《木呷的身份》,寫得入木三分,把我媳婦都看哭了。我媳婦問我黃立康是你的什么人,怎么對你了解得那么透徹?兒子說他寫得不對,做那些造句題時我沒有想這么多,也沒“靠在椅子上,看向窗外……”隨后,我們都哈哈大笑。那是一種放開心思的大笑。大笑間,我突然想起與我們一起并肩作戰(zhàn)過、已犧牲在扶貧一線,永遠留在那兒的戰(zhàn)友。他們,沒有寫完自己的這首詩,卻把自己永遠鑄成了中國脫貧史詩上最明亮的詩句。
但是,這首詩,至今誰也沒有寫完它。
你看,那滿山遍野的索瑪花之綻放,白雪之皚皚,是不是像一頁頁潔白的稿紙,在小涼山群山之巔緩緩鋪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