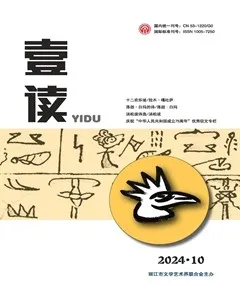談凌叔華《酒后》女性心理的復雜變化過程
凌叔華作為新文化運動后受過現代教育的新式知識女性,在成名作《酒后》中寫了女主人公采苕想要征得丈夫的同意去親吻男性朋友子儀的一系列心理變化活動,以主人公的情緒和心理活動貫穿全文,展示出采苕復雜的心理活動和變化:本我、超我、欲望的產生、爭取親吻行為的合理化以及封建殘留的意識和女性的自虐等心理。
作品一開篇,就有場景描寫:“客廳中大椅上醉倒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酣然沉睡;火爐旁坐著一對青年夫婦,面上都掛著酒暈,在那兒竊竊細語;室中充滿了沉寂甜美的空氣。”營造出一個香甜迷醉的氣氛。“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是醉的:子儀是因為飲了過量的酒而真醉,永璋則是因為人而醉,采苕之醉非關乎酒而系于人。”在人人皆醉的情況下,采苕對子儀的關心已然超越了對丈夫的關心:“等我拿塊毛氈來,你和他蓋上罷。把那邊電燈都滅了罷,免得照住他的眼,睡的不舒服。”“輕輕的給他脫了鞋了罷。把氈子打開,蓋著他的肩膀和腳,讓他舒舒服服的睡覺。”而丈夫都一一照做,只是丈夫也流露出對妻子忽視自己的些許不滿,他提醒到:“采苕,我也醉了。”這句話大可以挖掘出深層含義:我是你的丈夫,我也醉了,你也該如此照顧我。而采苕卻反駁說“你沒醉”,可以體會出她并不想像關心子儀一樣關心丈夫。此時丈夫在察覺出妻子的冷淡時,開始故意找話,先是說采苕臉上的紅暈不像桃花、牡丹、菊花、梅花,又說采苕的眉不能形容為遠山、蛾眉、柳葉、新月,再說采苕是仙子下凡他千金不換。他的滔滔不絕,并不能博得妻子的好感,甚至被妻子認為是“吵醒子儀”的存在。永璋的聒噪與子儀的安靜“他的容儀平時都是非常恭謹斯文,永沒有過像酒后這樣溫潤優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使得“采苕內心對于子儀的傾慕,由前面的關注上升了高度,感情愈加濃烈。”
采苕在醉的狀態下,“醉的狀態會引領人進入‘本我’超越‘自我’之中。同時,這種‘本我’在外界壓力下或內心的壓抑中只有醉后才能得以顯現。”關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解釋,百度百科收錄大致如下:本我:“簡單定義:依據理論,本我代表所有驅力能量的來源。本我是在潛意識形態下的思想,代表思緒的原始程序——人最為原始的、屬滿足本能沖動的欲望,如饑餓、生氣、性欲等”;自我:“簡單定義:是自己意識的存在和覺醒。其作用主要是調節本我與超我之間的矛盾,它一方面調節著本我,一方面又受制于超我。它遵循現實原則,以合理的方式來滿足本我的要求。”;超我:“簡單定義:本我的對立面是超我,也就是人類心理功能的道德分支,它包含了我們為之努力的那些觀念,以及在我們違背了自己的道德準則時所預期的懲罰(罪惡感)。”采苕的內心充滿對子儀的強大感情,在她眼中的子儀是“恭謹斯文”“溫潤優美”,并且擁有她所青睞的舞文弄墨的豐姿。在醉態下,采苕的超我對于本我的克制和約束顯得力度不足,于是采苕也敢于向丈夫吐露自己對于子儀的傾慕:“我自從認識子儀就非常欽佩他;他的舉止容儀,他的言談筆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時時使我傾心的。”“他哪一樣都好!”等等。不僅敢于向丈夫傾訴對另一名男子的愛慕,也敢于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聞一聞他。沒有肢體接觸,只有兩人距離的拉近,這個行為雖是采苕本我的展露,但這個行為并沒有非常失禮,還算是在采苕自己作為一個從封建社會女性過渡到新式知識女性能夠允許的道德范圍內。但丈夫錯聽為“親吻”,而采苕也沒有糾正錯誤甚至采取了默認態度,可以體味出采苕并不拒絕從不失禮的朋友行為(聞一聞)到略顯親密的男女行為(親吻),這是采苕本我的進一步表露——對子儀存在欲望。
王亮在《“醉”與“欲望”——從精神分析視角解讀凌叔華的<酒后>》中提到:“用拉康的話來說,欲望是‘從說出來的需求與需要的差異中產生的,它無疑是主體在其要求中說出來的需要得到滿足后仍然缺乏的東西’……對于采苕來說,丈夫或許可以滿足她的物質上的生活需要,但不可能無條件地滿足她對于愛的要求。這兩者之差讓她產生了一種欲望,而沉睡中的子儀就成為了這個欲望投射的對象。”丈夫能滿足她的物質需求(“給你想要的東西,花錢我是最高興的”)卻滿足不了她對于愛的全部需求,比如說采苕的“天生有一種愛好文墨的奇怪脾氣”,丈夫是沒法滿足的,而能滿足采苕這一奇怪脾氣的只有“有著豐采言語”的子儀。無疑,丈夫給了采苕很多愛:甜言蜜語,金錢,甚至允許她去親吻男性友人,但是恰恰是無法滿足采苕那“愛好文墨的奇怪脾氣”,欲望就在此發芽。
但采苕卻把這欲望掩飾得很好,亦或者是把這欲望包裝成其他的情感。張君在《凌叔華小說<酒后>中的女性意識》中提到:“采苕試圖用更符合社會道德標準的‘溫柔情感’來遮蔽內心‘感官肉欲'的成分。也正因為這種辯護,采苕的越軌之舉得到了丈夫的體諒和允許。”而實際上,采苕對子儀確實存在感官肉欲,除卻上文分析的欲望之外,原文中還有更直接的視覺描寫:“此時子儀正睡的沉酣,兩頰紅的像浸了胭脂一般,那雙充滿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適的微微閉著;兩道烏黑的眉,很清楚的直向鬢角分列;他的嘴,平常充滿了詼諧和議論的,此時正彎彎的輕輕的合著,腮邊盈盈帶著淺笑……”而子儀也出現了非常明顯的生理反應:“采苕怔怔的望了一回,臉上忽然熱起來。”很明顯,采苕要么是害羞要么是動情。而無論是害羞還是動情都是由于子儀此時的溫潤優美的形象對采苕的感官(視覺)造成了刺激,從而在超我放松對本我的克制與管束下,欲望透露出來:聞他或吻他。雖然因為“醉”的狀態,本我更多地被釋放,但超我并未完全喪失管束本我的能力,采苕還是想要為自己的欲望尋找一個較為合理妥當的借口,那就是:“他處在一個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憐他”,“一個毫沒有情感的女人,一些只知道伸手要錢的不相干的嬸娘叔父,又不由得動了深切的憐惜。……他真可憐!”,“愈動了我深切的不可制止的憐惜情感”,總歸起來就是對子儀這樣一個風姿卓絕的人卻有這樣一個不如意的家庭的悲憫和憐惜。在張君的觀點中,在采苕的辯解中,這種憐惜近似于母親對孩子的溫柔情感,是一種近似于母性的表達。我并不是很贊同這個觀點,因為在原文中有“……就是子儀,你也非常愛他,……”以及“夫妻的愛和朋友的愛是不同的呀!”,可以看出采苕的辯解實際上更多地是把這種憐惜歸結于對朋友的憐惜,或者是對一個有著絕妙文采卻有不幸家庭,甚至還在新年時分醉倒在自家的這么一個個體的疼惜。那么這個親吻,就可以更多地包裝成是一種安慰對方和表達自己疼惜的方式,就像朋友之間的親吻,傳遞友好和善意的情緒一樣,而自己真正的欲望就被刻意地隱藏和掩飾起來了。
而在去想要親吻子儀的過程中,采苕一直都在請求丈夫同行。李一媛在《本我·詩意·和諧——凌叔華<酒后>女性意識解讀》中指出:“采苕其實清醒地認識到對子儀的這種情感體驗和行為在現實世界中是非倫理和非合法性的,在人們的倫理觀念中是不會得到認可與同情的。但是采苕還是希望在正常的秩序下使這種‘本我’意識合理化,于是她把問題直接拋向有人倫關系的丈夫的身上,她要求丈夫尊重她的情感體驗,尊重她來自生命本能的欲望,以獲得人格的平等。”即采苕想要這不被倫理觀念認可的情感體驗和行為得到自己有人倫關系的丈夫的認可,也就是所謂的外界的肯定和安全感的給予,讓她能夠減少去親吻子儀的罪惡感,并且要求丈夫尊重自己的情感體驗、本能欲望和人格平等。另外,張君的論文中也有類似的觀點:“在潛意識中,她認定自己的行為是越軌的,是不合道德,不合秩序的。所以,她需要得到象征秩序與法律的丈夫的允許,……丈夫就象征著秩序與法律中的‘抽象的父親’”,“父親”在孩子們眼中意味著權威和規則,是不可違逆和抵抗的存在,若是與之相悖就是大逆不道。張君在此處用了“抽象的父親”一詞,意味著丈夫是采苕心中的道德、秩序和規范的底線,而采苕親吻子儀的行為本身已經是越軌的,她惶惶不安,需要得到這條“底線”的承認——你并沒有做錯什么。可見,張君的觀點是采苕親吻子儀的行為需要得到丈夫這一“抽象的父親”的允許,而李一媛的觀點則是使“本我”意識合理化并且追求人格平等。雖然二者的觀點都根植于采苕需要得到丈夫這一外界存在的認可,但我還是更傾向于贊同張君的觀點。因為若是李一媛的觀點成立,采苕“要求丈夫尊重她的情感體驗,尊重她來自生命本能的欲望,以獲得人格的平等”就不會在征得親吻請求后還一直祈求丈夫陪自己過去并且要求丈夫“我心跳的厲害,你不要走開。”她應會顯得更加自信和更加獨立,因為她要做的是一場在男權社會中呼吁女性的尊重和平等的反叛運動,絕不會畏畏縮縮地要求丈夫陪著自己不要離開。所以我認同張君的觀點,采苕在前去親吻子儀的路上要求丈夫的陪伴是因為這個行為需要得到象征法律和秩序的“抽象的父親”的認可。
而在小說結尾,采苕從“心跳的速度愈增”“臉上奇熱,內心奇跳”的狀態變為“一會兒她臉上熱退了,心內亦猛然停止了強密的跳”到最終放棄能夠親吻子儀的機會,反映出來的是由于新式女性思想的不徹底性、封建思想的殘余和女性自己的受虐傾向,導致女性本我超越自我的時間非常短,最終還是在封建思想藩籬的禁錮下無法做出親吻自己傾慕的男性的行為。張君的觀點為:“不僅反映了男權社會所規定的社會秩序以及所形成的女性角色定位對于女性的壓抑,也反映了女性受壓抑的地位不僅僅是男權制社會所強加給女性的,更是女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所自主選擇的,而這也就形成了女性主動的‘受虐'地位。”即這種女性被壓抑本我的地位不僅是由于男權社會更是女性自己主動的;馮娣在《凌叔華小說的怨恨心理》中提到:“采苕身上傳統社會教化的道德規范,最終還是‘戰勝’了女性本初的生命感。……采苕是一個具有現代思想的女性,……但她還是一個帶有封建禮教殘留的女性,當情感即qDqNzLDcLZ9hIQgD3Gt2S57Y2W6pgFPTLgtwk+I+GIU=將掙脫捆綁時,來自傳統的主導價值觀又將它粉碎。”即現代思想還是超越不了封建禮教殘余的思想;馮曉青在《凌叔華小說對女性心理的藝術觀照》中采苕想去親吻子儀最終卻卻步的解釋是:“小說刻畫了特定的歷史時代半新半舊、亦新亦舊的女性的特征。”;洪蓮在《淺析凌叔華短篇小說中的女性心理特征》中提出:“五四時期受過新文化影響的知識女性,大膽袒露自己的想法,體現了五四后新女性正視人格獨立、自由生活的新追求。……體現了即使是新女性還是無法沖破自我禁錮,這個自我禁錮來自傳統意識里封建社會的外部規則,作為女人要‘恪守婦道’”;而張寧的觀點則是從自我和本我的角度出發:“她應該感謝于酒后的醉,使她吐出了真言,使她長期壓抑的本我暫時超越了自我。可是‘本我’本身的不徹底性導致了這種‘超越’是如此短暫……當‘本我’要對自我進行超越之時也要刻意看一眼周圍的社會環境了,并且要仔細認真地看。”這些學者的觀點都基本一致,即采苕這個還帶著封建禮教觀念殘余的不完全的新式女性無法翻越內心的禁錮和藩籬去親吻子儀,所以最終卻步。
總之,即使采苕在“醉”的狀態下超我放松了對本我的審查,對子儀的傾慕表現為欲望并想把這種欲望包裝為更為合理的朋友之間憐惜的“溫柔感情”,并爭取外界象征法律和秩序的“抽象的父親”的準許,采苕最終仍然無法跨越她作為有封建禮教觀念殘余的新式知識女性心中的那一道屏障,最終放棄親吻的機會。這一心理變化過程復雜且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