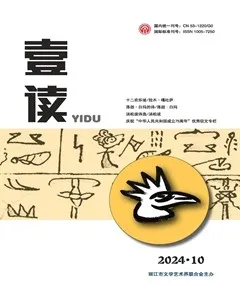返鄉記
亂世藏金,盛世修譜。如今,我們躬逢盛世,大伯要組織大家制作一本家譜,召集大家到空宗伊德村阿普福光家里聚會。我們家族的譜系分支情況沒能用文字記錄下來,這次要制定家譜,很多細節都得靠年長的老人口述補充。祖父輩的老人如今只剩阿普福光一人了,要制作家譜,少不了他。
那天早晨,下了一場小雨,地面濕漉漉的。我們從新營盤鄉鎮中心搭了車,帶著清爽的涼氣往空宗伊德村駛去。
汽車疾馳在盤曲回環的山路上。時值仲夏,沿途盡是鱗次櫛比的村落和麥苗青青的田野。從車窗內往遠處眺望,牦牛坪風力電站銀白色的大風車在山頂輕輕地旋轉著。我的思想也隨之旋轉到二十年前的空宗伊德村去了。
在我的記憶中,空宗伊德村是個蕭索的小村莊,整個村子都是簡陋的土坯房。一條坑洼不平的土路縱貫其間,起風時,大風揚起滿地的黃土,席卷著路邊家畜的糞便漫天狂舞。那樣的時節,總得把門窗關得死死的。盡管如此,灰土還是會鉆過土墻與梁木的間隙,呼呼地狂嘯著往屋里鉆。雨季來臨后,整個村子仿佛陷入了沼澤一般,地面的泥濘沒過了腳脖子,一腳踩下去,卻邁不開步子。沒走幾步,鞋子已深陷泥濘中不知所蹤。由于地處偏遠的高寒山區,這兒土地DWIDmA6R1B4p0DtaU4j32A7u4FHewnTdAmvMihImdUY=貧脊,僅能種植洋芋和苦蕎,加上交通閉塞,因此經濟很落后。村民狠命地勞作,卻常常填不飽肚子。那時,播種,收種都得靠肩扛馬馱。我二叔有一輛三轅馬車,可算是我們村為數不多的先進設備。每回駕車運送農家肥和洋芋時,二叔總是吆喝一聲,甩著馬鞭,高昂著頭,一副神氣十足的派頭。我們那時還年幼,總偷爬馬車。倘若能夠堂堂正正地坐一回馬車,夢里都會偷著樂。
空宗伊德村缺水,那時沒有水窖,人畜飲水都要到兩公里外的大水溝中去背。每天下午,忙完農活后,村民們背上水桶,成群結隊地去背水。小孩也不能閑著,我記得我十歲以前有個能裝二十五斤水的塑料膠桶,母親總要帶上我們哥倆去背水。我家修建全村第一個蓄水池時,村民們都很羨慕。但直到我家搬離空宗伊德村時,全村仍然只有我家那個蓄水池——大家沒有經濟能力修建私人畜水池。那時,村里還沒有通電,照明全靠松脂。落霞滿天的傍晚,老老少少都披上羊毛披氈,集中在村口的院壩內嘮嗑,孩子們嬉鬧著,追逐著,歡呼著。直待暮色蒼茫的時候才陸續回到昏暗的屋內。我的母親頂不愛湊熱鬧,每晚天一黑,她總是立在院外的柴禾堆上拖著長長的音調招呼我們回屋。那時,我父親還在外地工作,家中只有母親和我們兄妹仨。多少個寂靜黑暗的夜晚,母親點上松脂,坐在溫暖的火塘邊,給我們講述那些古老卻五彩斑斕的民間故事。影視自然是新奇的玩意兒,有一段時間,鄰村放映電影,我們偶爾點著火把走幾公里的山路,花上兩毛錢去看一場電影,心里總是甜滋滋的。
阿普福光的長孫布都與我最要好。他是個機靈乖巧的家伙,但家里光景不好,七八歲的時候還常常光著屁股到處竄。那時,吃上一頓肉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兒,每逢村里辦喪喜事時,就是人們最高興的時候——能吃上肉。國慶節的時候,村里總要殺一頭肥壯的豬,有一回,布都光著屁股擠在殺豬現場,讓豬血濺了一身,還嘿嘿地樂個不停。
這么多年過去了,空宗伊德村可曾變樣了呢?如今,人們的生活蒸蒸日上,空宗伊德村大概不會再是我幼年記憶中的模樣了吧。
“要進村了。”只聽大伯說道。
我一回神,汽車已緩緩駛進了村子。雨已經停了,大片大片的秧苗在雨后的山地上泛著綠油油的光芒。葉片上凝結著一點點透明的小水珠,偶爾有涼風輕輕地拂過山崗,那片綠苗隨之微微地顫動著,仿佛綠海中掀起一陣陣波瀾。
“呵,附子。”大伯隨手指著窗外那一片綠秧苗驚呼了一聲。
噢,原來這就是附子。我在心里默念道。
早就聽說脫貧攻堅戰打響之后,空宗伊德村在寧蒗縣委、縣政府的指引下開始種植重樓、附子等中藥材。這幾年,在縣委、縣政府的幫助下,萬格練托的羊肉和苦蕎、洋芋等農產品也打開了市場。不少村民借此脫貧了。只是不知空宗伊德村的父老鄉親們,他們的生活如今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了呢?
汽車緩緩駛進了阿普福光家。我記憶中那條“晴日灰土三尺,雨天泥濘滿地”的土路已鋪成了水泥路。道路兩旁的農舍已不是我幼年記憶中那些簡陋的土坯房。多半是刷了白漆的磚房和玲瓏有致的松木屋。村子顯得干凈而整潔。路旁偶爾遇到幾個衣著時髦的年輕人,他們大概已知道了我們此行的目的,朝我們頻頻招手。我突然記起光屁股的布都。他如今的日子過得不再像兒時那么艱難了吧?
阿普福光身體很硬朗,他精神矍鑠,完全不像一個已年過七十的老人。他端出一盤盤砣砣肉招待大家。他說如今生活好了,頓頓都離不開肉。去年洋芋大豐收,每家都宰了一只肥壯的綿羊慶賀,今年的形勢也挺樂觀。老伴去世后,布都給他買了一臺電視機,他說他最愛看新聞聯播,不用出門就可以知道許多國家大事。如今,扶貧辦為村民挖了水窖,雨季蓄滿水,整年都夠用。再不用大老遠地跑到幾公里外去背水了。布都前幾年外出務工,已修好房屋,準備年末回村娶媳婦兒。他用手指了指附近一座松木壘成的木屋。那座木屋真漂亮,壘木外部漆得火紅,屋頂用彩瓦鋪得瓦藍瓦藍的。我到村口轉了轉,那個集體院壩已改建成了籃球場。球場周邊停放著一輛輛農用拖拉機與面包車。馬車時代如今已一去不返了。
啊,新時代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使空宗伊德村煥然一新,完全變了樣!
立在村口朝四下張望,只覺得整個村子都被籠罩在一股氤氳清爽的涼氣當中。村子外圍的松林中傳來一陣陣鳥兒的啁啾聲。清風駘蕩,草木的微香中混雜著泥土特有的氣息迎面撲來,讓人心曠神怡。
傍晚,我們離村時,天已一片霽朗。遠處光兼阿別山和村后的山坡間正憑空架起一座燦爛的彩虹橋。這座彩虹橋橫貫在空宗伊德村的上空,顯得空幻而迷離。哦,那是一座通往幸福的橋梁,它連接了空宗伊德村貧窮落后的昨天與幸福安樂的明天。故鄉的親人們正踏上這座美麗的橋梁,滿懷希望地走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