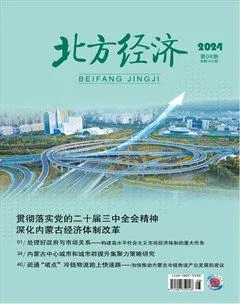游牧業向建設型草原畜牧業轉變的歷程及原因分析
摘 要:本文依據《蒙古秘史》記載的相關信息,解析了在依賴河湖水源、牧草季節性枯榮、氣侯多變易災等自然條件下,古代游牧業的畜種結構、繁殖育成、產出能力及食物特點等基本狀況,進而揭示注入建設要素是游牧生產適應社會需求的必然途徑。
關鍵詞:蒙古秘史 游牧生產 建設養畜
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后始終貫徹建設養畜的方針政策,經過幾十年的建設與發展,以往依附自然的草原游牧業已轉變為生產穩定、生活安定的建沒型草原畜牧業,并已進入現代化的發展軌道。然而,近年來有些學者從一些空泛的概念出發,無視完全依附自然對游牧業造成的草原利用失衡、生產豐欠懸殊、人畜安全面臨威脅等危害性,要求重新恢復游牧生產方式。本文依據《蒙古秘史》①這一被譽為游牧民族自主實錄巨著中的有關信息,還原歷史上存在過的原始游牧及注入建設要素的開啟,以便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認知誤區,持續推進草原畜牧業的轉型升級及現代化建設進程②。
一、《蒙古秘史》中的相關信息解析
(一)河湖水源是原始游牧生產的依存條件
《蒙古秘史》記述的歷史事件大部分以河湖泉的名稱指明發生方位。據粗略計數,全書共出現與水相關的地名73個、116次。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鄂嫩河(斡難河)8次、克魯倫河(客魯漣河)6次。出現3次的有貝爾湖(捕魚兒海子)、呼倫湖(闊連海子)等8個水名。出現2次的有烏拉蓋河(兀勒灰河)等12個水名。
經考察,出現2次以上的22個水域,全部分布在大興安嶺北段到肯特山脈之間。“肯特——興安” 矩形地帶是《蒙古秘史》記述政治、軍事、生產生活歷史事件的中心區域。充分印證了河湖水源對游牧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例如,帖木真與札木合從結義兄弟走向敵對的時點,就是以距離河水遠近而隱喻表達的。在一起合營住了1年半后遷移時,札木合說:“靠近山丘下營,方便牧馬人到帳房里歇息;靠近河水下營,牧羊人、牧羊羔人飲食方便”,以此暗示兩人分離的含義。因為馬群在暖季可以到距離水源遠至二三十公里的草場放牧,而羊只適宜在水源兩三公里范圍內放牧,由此產生了靠山和靠水之別。
(二)抗災能力和繁育特性決定草原五畜的構成
《蒙古秘史》中提及的畜種,馬最早最多,綿羊和山羊次之,駱駝較少,牛最少。這是當時草原五畜結構的反映,是由抗災能力、育成周期、繁殖性能和騎乘機動性四大因素所決定的。馬因四者兼優而成為古代游牧最主要的畜種。羊因繁殖性能最高、抗災能力較強而成為普遍適應各類草原的畜種。駱駝的抗災和遠牧能力最強,但因繁殖性能最低,所以除荒漠地區外只能居于更次要的地位。牛則因為采食方式特殊和抗災能力最差,在純粹依附自然的游牧條件下繁育水平比羊和馬要低得多。
《蒙古秘史》記述的成吉思汗以“春天馬瘦需要喂養”①為由躲過以許婚宴為名的誘殺事件表明,即便是適應自然能力很強的草原馬,經歷漫長的冷季枯草期后馬瘦體弱是人所共知的。在剿滅不可一世的乃蠻部時,成吉思汗甚而反其道用之以出奇制勝。他刻意在春季馬瘦季節出征,長途行軍后又以一匹帶著破鞍的瘦馬麻痺敵方,作戰時卻指定專人負責輪換戰馬(闊脫惕 札撒兀勒)以消除己方弱點,從而一舉消滅了蒙古高原上最后一個強敵,完成了統一大業。
(三)古代游牧時期牲畜的繁育狀況
書中數次出現的“雙母乳喂肥的羊羔(帖勒忽里罕)”,則是牲畜在游牧狀態下繁育水平低的例證。本來綿羊和山羊都屬于多胎性動物,正常營養條件下1只產仔母羊的泌乳量能夠哺育兩三只羊羔。文中說羊羔需要“雙母乳喂肥”,說明當時普遍存在母羊泌乳量不足。另一方面,1只羊羔由兩只母羊喂奶能夠成為一種通行的育肥措施,說明產仔后羊羔早亡的泌乳母羊不在少數。游牧時牲畜產仔保育季節正值牧草青黃不接和自然災害頻發之時,因缺奶、受凍而損失的比率很高,直到當代有了接羔暖棚和儲草補飼條件之后,繁殖成活率才得以穩定提高。
(四)古代食物特點與功能
以鐵騎統一蒙古高原的戰爭難以計數,卻沒有通常所言的“糧草先行”。這是因為游牧人群的基本食物肉和乳可以在遷移過程中生產。書中還記錄了幾種功能各異的食物。
一是營養健身珍品發酵馬奶。出現在《蒙古秘史》中的乳類主要有鮮奶(循)、發酵牛羊奶(塔剌黑)、發酵馬奶(額速格)。其中有關馬奶的擠取采集、發酵加工、日常飲用和宮廷宴飲等內容出現在全書各卷。以馬為主的畜種結構、在遷移過程中母馬便于擠奶和管理的特點,適應了當時游牧和征戰的需要。現在所研究的馬奶具有的補充人體維生素、微量元素和運動能量等特殊作用古人即有感知。《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受傷后,在未找到發酵馬奶的情況下,只能飲用發酵牛羊奶,喝了3次后即感到“心暢眼明”②。可見,退而求其次的發酵牛羊奶仍然取得了很好的營養健身效果。
二是羊肉珍品湯羊(暑洌捏)。《蒙古秘史》將宮廷食用的2歲羯羊稱為湯羊。這與當代牧民以“喝肉湯”代指為待客或保健,食用新鮮手把肉和肉湯(包括肉湯面條或米粥)是一致的。“2歲羊肉”是公認的嫩度、肥度、營養、肉味、湯味都最佳的羊肉。選擇“羯羊”,則因為其沒有繁殖功能,從草原上攝取的營養物質可以最大限度地轉化為優質肉類成分。
三是快速食品羔羊肉。羔羊憑借宰、煮、食用都很快捷的特點,多次作為應急行糧出現在《蒙古秘史》中,有的還寫明“雙母乳喂肥的羊羔”以示肥美。
四是儲備食品風干肉。游牧牲畜的膘情在冷季枯草期消耗殆盡,每年都有很長時間不適宜屠宰食用,因而適宜制成風干肉以供食用。例如阿闌豁阿五箭訓子的場景,展現的就是春天煮干羊肉。
五是獨特的野外生存食品。《蒙古秘史》記載,王罕從哈剌契丹經過幾大沙漠投奔成吉思汗時,趕著5只山羊以擠奶食用并刺取活駱駝血為食物①。合撒兒在尋找成吉思汗的長途跋涉中,吃干皮條充饑②。
(五)作物種植與定居的信息
《蒙古秘史》中反映蒙古高原存在種植業的信息,一是王罕在7歲時被薛涼格河處的篾兒乞惕部人擄去舂碓搗米,二是成吉思汗打敗篾兒乞惕部繳獲有谷物(塔里牙惕)。
成吉思汗給母親收養的義弟分配百姓時說:“依照從全國百姓中分封母親、諸弟、諸子之例,可將住氈帳的游牧百姓、住門板房的定居百姓分一些給你”③。這表明并沒有排斥所征服地方的農耕居民或定居牧民。例如,在原西夏境內的阿拉善(阿拉篩)以“背不走的營盤”即定居不定牧的方式放牧駱駝。這些先例可以對其他地方改進游牧生產條件產生積極影響。
(六)生活物資短缺的信息
成吉思汗的11世祖用1條野鹿后腿肉換了一個孩童回家役使的事例,反映了在狩獵為主時期物質生活極端貧乏的狀況。游牧的興盛壯大支撐了蒙古部落的崛起和蒙古高原的統一,但是仍不乏物資短缺的事例。部族遺棄帖木真一家人時,不顧近親和首領遺屬的情義,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可以繁衍增殖的牲畜。青年帖木真追尋被盜的8匹騸馬,6天6夜的路程只出現過兩群馬,說明當時曠野中十分稀疏的人畜分布狀況。別勒古臺的母親被篾兒乞人擄去后在一個有東西兩個門的營帳被解救,說明占有者是部落的一個貴族。但是在暖季穿著襤褸的羊皮衣的記述,說明即便是貴族上層也存在應季生活物資匱乏的現象。另外,一度是蒙古高原強人的扎木合,因其弟盜掠成吉思汗部屬馬群后被殺而發動了著名的十三翼大戰,可見,號稱強大的部落當時也處于牲畜短缺狀態。
二、討論與結論
《蒙古秘史》中的相關信息表明,古代原始游牧由于沒有建設基礎設施的條件,只能完全依附自然環境進行生產,牲畜的繁衍及提供產品的多少基本由水源分布、遭災幾率、牧草枯榮等自然條件所決定。
(一)單純依賴河湖水源造成大部分草場閑置、半閑置
牧養牲畜與其他生產活動根本不同在于必須有大量水源供牲畜按時飲用。《蒙古秘史》中河湖水源最為密集的“肯特——興安”矩形地帶在當代分屬中國內蒙古東北部、蒙古國東部、俄羅斯阿加布里亞特地區,自古以來一直是蒙古高原上水草最為豐美的天然牧場。然而,馬、牛、羊能夠利用河湖水源放牧的草場即通常所說的有水草場,也只能占其一半左右,另一半無地表水源的草場也稱為無水草場,在青草期營養豐富時卻因沒有飲水條件而無法放牧。無水牧場只冷季積雪且達到“人可以化雪用水、牲畜可以吃雪代水”的條件后才能放牧,即大半年閑置。如果遇到冰凍期無雪可吃或積雪過厚無法放牧的年景,就只能全年閑置。地表水源越少的草原,無水草場的比例也越大。無水草場閑置、半閑置與有水草場集中過度利用的失衡,對游牧社會的生產、生活以及自然生態都有多方面的不利影響。
(二)氣候多變形成的自然災害成為游牧牲畜的繁育障礙乃至致命威脅
《蒙古秘史》載有成吉思汗對常見不良氣候的一句概括:“強勁飄蕩的風雪、令人顫抖的嚴寒、傾瀉的大雨”。現代研究資料表明,這是由特定的地理位置所決定。蒙古高原的降水量年變率懸殊是氣候常態,也是最主要的致災因素,可以造成旱災、澇災、致命的冷雨以及冰凍季節積雪過厚無法放牧的“白災”和沒有積雪用以代水的“黑災”。加之大陸性氣候伴有的嚴寒、酷暑、暴風、強對流等現象與降水變率交織,更會加重自然災害的危害程度。另據清朝時期的資料,蒙古高原平均每1.31年即有一次嚴重的自然災害。古代游牧時期,無力建設基礎設施進行防災抗災,每遇自然災害牲畜只能依靠消耗暖季青草期抓膘儲存的體內脂肪,由自身能量維持繁育以及決定生死。
(三)營養攝取單純依賴自然環境決定了游牧業的產出能力低下
游牧牲畜的繁殖育成周期長達2—5年,持續增加的營養需要無法由季節性枯榮的牧草自然生長滿足。正常年景中可供牲畜攝取各種營養物質的青草生長期僅有4個月左右,冷季的枯黃草僅保留一小部分營養物質,牲畜即便飽食也無法滿足機體生長和保膘御寒所需。暖季的青草與冷季的枯黃草中營養含量多寡的交替,決定了游牧牲畜每年都要經歷一次“夏壯、秋肥、冬瘦、春乏”的生存體況循環,有很大一部分潛在生產性能被無謂消耗損失。加之自然災害頻繁,年度性與季節性的營養來源不足相互疊加,制約著游牧生產的畜種結構、繁育能力、育成出欄,無法滿足不斷增長的社會需求。
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人為調節游牧生產的能力逐漸增強,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減少對自然的依附性成為增加產出能力的必然選擇。蒙古高原統一時即留存著種植谷物和定居民的信息,就是這種變化的印跡。斡哥歹罕指令各千戶由營地草場官統領打井,使更多的無水草場變為可四季放牧的有水草場,則是最早的主動減少對自然依附牲的草原基本建設。當代中國牧區致力于將依附自然的傳統游牧轉變為可均衡供水放牧、冷季有暖舍防寒、枯草季節和受災年景具備補飼舍飼條件的建設型草原畜牧業,是順應歷史規律,兼顧生產生活和自然生態的良性變遷,為中國式現代化積累物質基礎的有力舉措,可謂和諧共贏。
(作者1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作者2系原國家農業部總經濟師、國家首席獸醫官)
責任編輯:康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