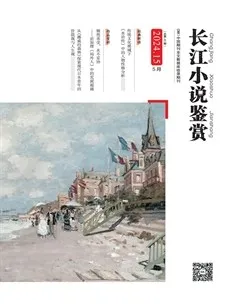黑暗與光明的對話,夜行者與黑色的眼睛
[摘 要] 《1984》是英國作家奧威爾的傳世名作。后世評論家多聚焦其政治諷喻及反極權立場,但其人性封閉與抗爭主題也應給予更多關注。本文基于這一新的主題,對其中的人性覺醒與生命重生意義進行探索,認為只有在黑暗中存蓄力量,積攢希望、懷疑、探尋、求索、抗爭,人性才能進入覺醒和重生。
[關鍵詞] 《1984》 人性 覺醒 重生
[中圖分類號] I106.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15-0043-04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本名埃里克·亞瑟·布萊爾。1903年出生于英屬印度,1907年舉家遷回英國。經濟的拮據和流亡,以及二戰參軍的經歷,讓他對戰爭、和平,社會與人類等主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考。
在文學的璀璨星海里,《1984》這部由喬治·奧威爾精心雕琢的作品,猶如一顆獨特的寶石,閃耀著引人深思的光芒。它不僅僅是一幅描繪極權社會陰暗面的畫卷,更是深入探索人性深淵與生命力量的壯麗史詩。作為與赫胥黎并稱的英國著名作家,奧威爾在其作品中,將自我的生命體驗和社會感知深深刻畫進人類和歷史的宏大圖景之中[1]。世人多討論其反極權的初衷和反烏托邦的立場,而如果認真審視,會發覺其對人性深處最脆弱和隱秘的角落,也進行了深刻的探索與張揚,進而生發出嶄新的意義。它勇敢地揭示了極權統治的可能現實,同時,也細膩地刻畫了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復雜多變與不屈抗爭。
一、文獻綜述
自《1984》出版至今,國內外的研究已產生眾多成果。如約翰·W·揚研究極權主義語言在小說主題彰顯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羅納德·伯曼將奧威爾作品所體現的思想與杰茨弗拉德和海明威的思想進行對比;有的則從其他的視角解讀作品,例如杰姆斯A·泰那借用福柯的相關理論對于極權社會如何控制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行分析等等。國內學者如鄭鈺的《烏托邦的顛覆與重構》則從反烏托邦的視角進行研究;有的如聶素民的《就〈動物農莊〉和〈1984〉看奧威爾政治小說的藝術性》探析小說的寫作特色;何輝彬的《在非人性社會追尋人生的真諦》則從心理分析視角對《1984》進行解讀;有的通過比較研究,探究人性的主體性問題,如周佩鑫的《從〈1984〉到〈1Q84〉:論人的主體性喪失與重建》。雖然研究成果多元呈現,但較多還是圍繞極權主義和反烏托邦文學展開,缺乏更廣闊的批評視野,因此還需繼續開拓和深化。
二、重塑人性光輝的嶄新期望
在奧威爾的預言性小說《1984》中,作家通過溫斯頓這個大洋國的工作人員,以一種夸張甚至對于未來社會深刻期待的反諷的方式,對于人類理想進行了深刻的書寫與描述。通過研讀,不難發現,奧威爾所要創造出的大洋國,其實本不該如此蕭瑟而壓抑,而應該展現出與其相反的“鏡像”模樣,在社會的治理結構和人性自我完善與升華上,更加出色。奧威爾通過一種“擔憂”似的告誡,做出基于對于人類未來美好社會和發展的深刻期冀與展望。
1.權力結構的健康展望
理想的社會,不再是如奧威爾般對于未來的“預測”,而是在治理體系和民眾幸福指數體驗上更加完善。奧威爾所期待的社會,應該是向未來發展的過程中變得更加美好和祥和的時代。各種日常科技不僅應該服務于公共空間,也應溫馨融入家庭角落。《1984》對于“電幕”的描述,讓很多人對于奧威爾的創造性手法印象深刻,但若仔細研讀,卻發現處處透著對于真正的科技運用的期待。科技應旨在促進人類間的開放溝通,而非疏離。應該讓人們的每次發自內心的微笑都能成為連接彼此的橋梁。人們感受到的是溫暖與安心,而非緊張。這種透明的交流環境才可以真正地鼓勵真誠與理解,展現出一個人性化的政府同民眾間的新型信任關系。
2.人性的升華與共鳴
2.1信任與啟迪
奧威爾所處的時代,有其局限性。但奧威爾對于人類美好未來的期待,卻在小說的反諷手法下,愈加清晰。在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上,民眾可以沐浴信任與知識的陽光,他們可以通過多元的學習,得以從不同角度審視世界,享受探索未知的樂趣。這種環境讓每個人的心靈都充滿陽光,他們可以勇敢地表達自己,無懼誤解與偏見,共同構建一個充滿智慧與愛的社會[3]。
2.2希望與成長
在自由與尊重的土壤上,個體的創造力與潛能得以充分釋放。他們勇于追求夢想,敢于挑戰未知,每一次嘗試都是對自我的超越。在這片天空下,每個人的價值都得到充分認可與尊重,他們相互支持、共同成長,共同書寫著人性升華的輝煌篇章。而達到這樣的世界和未來,并不是奢望,也并非遙不可及的理想。以主人公溫斯頓構成的人物群體致力于構建未來更加理想的美好社會,從人類自身內心潛藏著的對于當下局面的突破,對困境和不完美現狀的思考與改變,從人性深處對于完善自我、創造精彩的不斷探索和革新,對于追求卓越的更大勇氣和嘗試,推動著人類,在發現自身渺小和弱點的過程中,在重新認識自我與創造更加精彩生活的進程中,一步步、不斷激發潛能,同不完美、不優秀博弈。進而在人性的層面,在看似懵懂的荒蕪中,開始覺醒,用自己的每一次探尋,去推動人類不斷地追求美好,走向更好的未來。
三、黑色的眼睛與夜行者的覺醒:人性光明的初現
在《1984》中,溫斯頓可以被視為一個“夜行者”,這也應該是學術界第一次將其定義為“夜行者”。筆者認為,所謂夜行者,是黑暗中的探索者、孤獨的潛行者。不只是物理世界現實生活中的探索者,更是人性深處,對于自我的探尋。他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尋找著通往光明之路,雖然黑夜漆黑一片,但是他卻有一雙“黑色的眼睛”。他的黑色眼睛象征著他對現實的深刻洞察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念。通過自己的觀察和思考,溫斯頓發現了他所處社會的虛偽和殘酷,從而堅定了反抗的決心。
顧城曾說,“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用在溫斯頓的身上是同樣的振聾發聵。黑暗往往不是一種消極和否定,不是寂靜與無助。反而,是一種心靈與靈魂的重建與重生。這看似冷漠、黑暗與安靜的時刻,卻是那“光明”之時飽受著壓迫與封閉的人性可以肆意馳騁的天堂。黑色、黑暗,不是如“白天”般,繼續著的混沌與無知,而是重新燃起的希望,是激活的靈魂重新覺醒與人性徹底回歸的地方。
“在黑暗中才能連貫地思考問題”[2],這正是奧威爾對人性的黑與白、光與暗問題的辯證思考。在黑暗中積聚力量,重返本心,勇于懷疑,才可沖破封閉與藩籬。
盡管溫斯頓所處的社會試圖誤導人們的思想,但總有一些人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追求真理。溫斯頓作為夜行者,在黑暗中開始了對自由與真理的孤獨探索。溫斯頓說:“在黑暗中,只要你保持靜默,你是能夠躲開電幕的監視而安然無恙的”,他通過寫秘密日記的方式,記錄自己的思考與感受,逐漸開始對大洋國的歷史產生好奇進而開始質疑,試圖通過閱讀禁書等方式了解過去的歷史真相,并逐漸覺醒并質疑現有的權力體系。溫斯頓的覺醒和對真相的追求標志著人性中光明面的初現,為后續的抗爭與重建奠定了基礎。
同時,他還通過與一些反對者的交流,獲取了對極權主義社會更深層次的理解,了解到不為人知的一面。這些反對者雖然身處黑暗之中,但他們的存在和行動為溫斯頓提供了希望和勇氣,為溫斯頓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引與啟示。溫斯頓通過黑色的眼睛逐漸洞察真相,逐步實現心靈的覺醒。
四、黑暗與光明的對話:人性的重建與生命的重生
1.人性的重建:從覺醒到抗爭
主人公溫斯頓是大洋國的一名政府外圍工作人員,始終保持獨立的思考,他在探索過程中,不斷追求真相,試圖揭露謊言和欺騙。
1.1人性光明的覺醒過程
他通過閱讀“禁書”、與反對者交流等方式獲取真相,盡管這些行為都帶來了極大的風險。溫斯頓的覺醒過程充滿了痛苦與掙扎。他不僅要面對來自外部的監視與鎮壓,還要克服內心的恐懼與矛盾。他會時常回憶起過去的美好時光,如童年時的輕松和快樂。這些不斷激發和促使他更加堅定地追求自由與真理,從而推動了人性光明的覺醒與升華。
在戀情中,溫斯頓和朱莉婭互相安慰和支持彼此,他們試圖在黑暗中尋找一線光明,對美好未來的憧憬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溫斯頓通過寫日記的方式,記錄對現實的質疑與不滿、懷疑和否定,記錄自己對所處社會的反抗和對自由的渴望。他逐漸覺醒并意識到某些規定的荒謬與殘酷,他的覺醒標志著其人性中光明面的初現。
1.2人性抗爭與重建的過程
人性的抗爭并非一時即可完成,它需要個體在覺醒的基礎上付出巨大的努力與犧牲方可達到。溫斯頓等人在抗爭過程中不僅要面對來自外部的監視與鎮壓,還要克服內心的恐懼與矛盾。然而,正是這些挑戰促使他們更加堅定地追求自由與真理,從而推動人性重建的進程。人性的重建又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它需要個體在覺醒的基礎上,勇敢地挺身而出與壓迫勢力進行抗爭,同時還需要社會的共同努力與支持。在《1984》中,溫斯頓等人的抗爭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他們的精神卻激勵著更多人去追求自由與真理,去不停地奮斗,雖然微光閃爍,但是卻為更大范圍人性的重建鋪平了道路[4]。
2.生命的重生:從毀滅到希望
重拾希望需要勇氣和信仰,這在溫斯頓的身上得到清晰的顯現。
2.1生命的重生象征
在《1984》的結尾部分,溫斯頓雖然被思想警察逮捕并接受“改造”,但其人性中的光明面也并未完全熄滅,它通過啟迪定會在某個時刻重新煥發出生命的光芒。
2.1.1思想和精神的重生
溫斯頓的生命在反抗和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得到了重生。他從一個盲目服從的外圍成員轉變為一個具有獨立思考和反抗精神的個體。他的經歷充滿了驚險和挑戰,他的成長和變化讓人感到振奮和鼓舞。盡管溫斯頓在身體上的反抗最終失敗了,但他的精神卻得到了重生。他不再盲目服從,而是一個擁有獨立思考和判斷力的生命。盡管其所處社會試圖控制和壓制人性,但人性中的反抗精神卻從未消失。他的經歷充分證明,只要擁有堅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在逆境中就存在尋求生命重生的巨大可能。
2.1.2嶄新認知的來臨
在經歷了痛苦與掙扎后,溫斯頓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他意識到在其處處社會中,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也許并不可能。個人的價值和尊嚴被極度貶低,人們被剝奪了自由、思考和愛的權利,生命變得毫無意義,都成為被控制和操縱的對象。他開始認識到自己作為一個個體的價值。他通過寫日記、與朱利亞的秘密戀情等方式,試圖保留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和思考,這是他對個體價值的肯定。
他開始勇敢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希望能夠在有生之年實現這些目標,開始了對言論自由的渴望,對思想自由的追求,對行動自由的向往和對精神自由的堅守。這些推動了他嶄新的認知的突現,最終變為其認知中嶄新篇章的開始,得以完成其生命精神意義上的重生。
2.2對人性自身重塑與未來社會的啟示
無數次親身的經歷可以更好地佐證黑暗孕育光明的法則。過往與當下,只有在一切歸于寂靜和平和之后的夜晚,才可以讓思維與靈魂進行徹底的釋放和自由的馳騁。思想,就在這個時空中,進行清晰的自我書寫。
凡是有人的地方,社會中各種規則或條律就像一條條無形的鎖鏈將人類封閉,將彼此牢牢地“拴住”。每天的匆忙和繁雜的瑣事、提心吊膽的擔憂和抉擇,怕語言不恰當,怕行為不得體,人類不停地“被”自我創設的情境所限制。現代社會中的人類更是被種種華麗外衣披裹著的“便捷”工具認真地“監督”著,移動電話和其他科技的運用更加強了這一“監督”行為。
《1984》在成書之時,也許人們看到的,是其將矛頭指向了人類社會中可能或已經顯現的極端。但在人類的思想深處,已經是在投射人類人性中那最初的天然的無法超越的自我封閉。人類總是先拴住自己,再拴牢他人。以為規則越多,才可以通向一個勝利的彼岸。卻不曾想到,這艘承載人類的航船,在通往真理與成功的大海上有時卻做著無休止的循環,最后又回到原點。人類的科技、文化和文明史,一再展示出歷史的這種有趣的演進。
但也許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雖然,人類在用自己創設的“囚籠”封閉著自己,但是在“囚籠”中,卻并未停下“懷疑航路”和“勇敢出走”的沖動。在這種繞著永恒航線,循環往復地對前途未知航路不斷開拓與探尋的過程中,巨輪一次次靠岸、離岸、遠行。人類在一片蒼茫與浩瀚中,在絕望與困境中,不斷地尋找與突破,在驚濤駭浪中維持內心的安靜與沉穩。在這動與靜的牽制中,完成自我反省和追尋。也許正是在突破自己的每一次實踐中,人類才完成了對自我存在意義的審視。也許是在暗淡希望和對人性的壓抑中,人類才最應該淡然處之并蘊藏能量。在《1984》中,溫斯頓的自我懷疑和覺醒,對曾經大洋國的社會真實的探知,對自我和他人存在意義的思考,最后雖被同化,但他卻不停地勇敢實踐,在“黑暗”中勇敢積蓄和蘊藏改變與突破的能量。自我封閉也是人性自己創設的牢籠,也只有人類自己,在每次對這個牢籠的摧毀之中,在每次對當前限制階段的抗爭和躍進中,才能夠再一次地戰勝自己,去往未來。
不要懼怕暫時的停頓與壓抑,只要你的心中還存著思考,還存著不會停止的自我懷疑與否定,人類的思維和自身發展終將可以迎來一個更大的突破。
在《1984》中,溫斯頓的自我懷疑和覺醒,對曾經大洋國的社會真實的探知,對自我和他人意義的思考,最后雖被消解,但仍舊不停地勇敢實踐,在“黑暗”中積蓄不斷改變與突破的能量!只要你的心中還存著靈魂與思考,還存著止不住的懷疑和對自我的否定與探尋,那終將可以迎來一個更加燦爛的明天。
《1984》不僅是對虛構的大洋國社會的批判與警示,更是對未來社會警惕性的深刻思考。它告訴我們,只有珍惜自由與真理、警惕權力的濫用、積極推動人類自我人性的重建與生命的重生,才能避免極端情況的發生,并創造出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五、結語
小說最后,溫斯頓“走在了陽光中”,這帶有反諷和期冀意義的“光明”其實也在彰顯和照耀人性深處的那點不舍、不甘,和在最絕望的環境中,等待重生的理想!溫斯頓的前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昭示和宣揚。人性深處的重建和生命的重生并不是奢望,而是人類必須完成的自我超越和對存在意義的追尋。
《1984》通過黑暗與光明的對話以及夜行者溫斯頓·史密斯的形象,深刻揭示了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崩潰、重建與生命的重生過程。小說以其獨特的敘事手法和深刻的主題思想,為人類提供了一面反思歷史、審視現實、展望未來的鏡子。在未來的日子里,讓我們銘記《1984》的警示與啟迪,共同努力去守護自由與真理、推動人性的重建與生命的重生。
參考文獻
[1] 章安祺,黃克劍,楊慧林.西方文藝理論史:從柏拉圖到尼采[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2]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M].董樂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3] 周軍麗.喬治·奧威爾小說《1984》的文學倫理學批評[J].海外英語,2021(7).
[4] 李娟.《1984》中的權力問題研究[D].伊寧:伊犁師范大學,2022.
(特約編輯 楊 艷)
作者簡介:孫泰,山西通用航空職業技術學院公共基礎教學部,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美國文學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