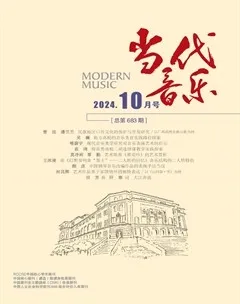音樂表演姿態理論在古典吉他舞臺表演分析中的應用
[摘要]在音樂表演理論研究當中,“姿態”為近些年的熱點話題,本文通過對音樂姿態理論的記譜、音響與身體三個層面,以及音樂姿態理論中的四種表演姿態在古典吉他演奏中的具體體現進行闡述,并重點對兩位演奏家所演奏的《紳士幻想曲》錄制文本中的表演姿態進行對比分析,期望通過分析研究,幫助音樂表演者了解自身表演姿態,在分析中找到自身個性,從而更自如地進行舞臺表演,使音樂作品更好地呈現。
[關鍵字]音樂表演理論;音樂姿態;表演姿態;古典吉他
- 音樂姿態理論框架的三個層面
世間萬物之所以能發出一定的聲響,在本質歸結于物體的運動,根本上是物理學的范疇,而物體只要產生了運動,就會形成一系列的“姿態”。近年來眾多學科關注到“姿態”的重要性,并進行了綜合性的跨學科研究,有關“音樂姿態”的研究便是如此。“音樂姿態”研究是“姿態”研究趨勢下的必然產物。并且音樂姿態的研究在音樂表演研究中占據重要的地位。
在音樂表演中會涉及到三個層面的姿態,第一個層面為作曲家所寫作出的記譜姿態。所有非即興而出的音樂音響都是基于樂譜而存在的,這種姿態是作曲家腦海中意向性活動的具體體現,在譜面上表現為不同的旋律、和聲、調式調性等。而對每一位表演者來說,先是認識到這種記譜姿態才會產生接下來的一系列音響姿態或身體姿態,這種姿態間接地將表演者與作曲家雙方通過譜面文本進行跨時空的連接。因此,表演者對此種姿態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能夠進入作曲家的“視界”,清晰作曲家的創作意圖,更好地與表演者自己的“視界”進行融合,從而更加準確且創造性地進行音樂表演。
第二個層面為表演者個人表演時的相關控制,如速度、強弱、節奏、音色等,即音響姿態。音響姿態是記譜姿態的最直接表達,而記譜姿態是音響姿態的最直觀體現,即音響姿態為記譜姿態的輸出媒介。音響姿態是由表演者直接完成的,其將作曲家意圖通過表演者的表演展現而出。它與表演者的技術技巧、以及表演者個人對所表演曲目的記譜姿態的理解程度密切相關。表演者的技術越高,在演奏時所產生的音響姿態的清晰度與準確性越高,而清晰與準確都是基于作曲家的記譜姿態而言的,因此表演者個人對于記譜姿態的理解程度也會影響音響姿態的產生。
第三個層面為表演者在表演時或審美者在欣賞時所產生的肢體動作與面部表情等變化,即身體姿態。在構成音樂表演的必要條件當中,表演者與聆聽者的姿態都構成了音樂表演姿態理論中“身體姿態”的研究對象。按此分類,可將身體姿態分為“表演姿態”與“聆聽姿態”兩部分。表演者在表演過程中,如器樂演奏者為使樂器發出音響所產生的動作或聲樂演唱者為控制聲音音色與嗓部發聲位置所做出的面部表情——可概括為“肢體姿態”與“表情姿態”。觀眾通過聆聽音樂所做出的相關肢體反應與表情反應也可歸類到身體姿態的研究當中,觀眾的聆聽姿態會在現場直接地反應給表演者,在一定程度上會對表演者音響姿態與身體姿態的生成產生影響。在我國目前的研究當中,主要以“身體姿態”為重點,而在“身體姿態”研究中主要以“表演姿態”為中心進行研究,同時在研究中涉及小部分“聆聽姿態”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對案例進行分析時,也將著重對“表演姿態”進行分析研究。
- 表演姿態的分類
在音樂表演當中,不同的表演姿態會起到不同的功能作用,按照其功用可大致分為四類:音響生成姿態、音響輔助姿態、交流性姿態、音響伴隨姿態。
音響生成姿態指對音響的生成有直接關聯、能夠產生直接作用的姿態。其可被進一步劃分為激勵姿態與修飾姿態。如使用古典吉他演奏一條普通的音階并不加任何技巧性的演奏時,左手的按弦與右手的撥弦同時進行的這個動作能使樂器直接產生聲音,這時的音響生成姿態則屬于激勵型;而在古典吉他的技巧當中通過揉弦可以使所演奏的音響發生變化,左手的揉弦動作則屬于修飾型的音響生成姿態;此外滑弦、擊弦、勾弦演奏技巧既屬于激勵型也屬于修飾型。
音響輔助姿態指能夠促進音響生成的發揮輔助性作用的姿態。這種姿態還可被細分為支持型姿態、分句型姿態以及夾帶型姿態。在古典吉他演奏時其最直接與琴產生聯系的是左右手,在左手觸弦時要求“指尖觸弦”,直觀的來看指尖的力作用于琴弦之上,但從生理結構上來說,手指的力是從肩膀到手臂再到手掌,最終才將力量集于手指進行發力按弦。那么肩膀與手臂在暗自發力時,其動作不與古典吉他這件樂器的發聲產生直接聯系,這時的動作便屬于支持型的音響輔助姿態;在許多節奏規整的古典吉他曲目當中,許些演奏者會通過連續的肢體動作如身體前傾、頭部的扭動來表現音樂的句法結構,有時也會通過呼吸來對樂句進行連接,這些便屬于分句型的音響輔助姿態;此外還有演奏者會通過一些細碎的動作如快速用力地向下點頭、踮腳打拍子等來強調音樂中的重音或節奏,這種具有輔助性質的動作可理解為夾帶型的音響輔助姿態。
交流性姿態。交流存在于兩個對象之間,而音樂表演中的交流性姿態也主要產生于兩個對象之間,主要表現為表演者與表演者(指揮者)、表演者與聆聽者(欣賞者)之間。二者之間的交流性姿態主要表現為細微的面部表情與自由的肢體動作。在古典吉他重奏、合奏表演開始時,有時會根據呼吸的動作形成交流從而約定起奏的時間與速度,有時還伴以點頭的動作。在表演過程中會根據曲目中不同的節奏、節拍變化、強弱變化用以不同的面部或肢體動作進行演奏者間的交流,從而提高配合度促進曲目的流暢進行;其次,在古典吉他協奏曲表演當中,此時的古典吉他往往作為主要旋律樂器出現在樂團當中,如著名的《阿蘭胡埃斯協奏曲》、《紳士幻想曲》。演奏此類型的曲目時,古典吉他表演者與指揮之間的眼神交流與身體動作則屬于交流性姿態。此外,這種交流性姿態不僅只存在于表演者之間,還存在于表演者與聆聽者之間。上文中所提及的音響輔助姿態當中的分句型與夾帶型姿態雖為表演者所產生的姿態,但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會促進聆聽者對樂曲的感知,從而能夠通過這種交流性的姿態加強與表演者的交流互動。因此,分句型與夾帶型姿態也可以被歸屬于交流性姿態。
伴隨性姿態指常伴隨于音樂的姿態,與音響的生成沒有直接關聯。這種姿態在古典吉他獨奏演奏時很少出現,但會出現于協奏曲的演奏當中,如在協奏曲的前奏或間奏段落中,古典吉他演奏者可能會根據樂團的演奏作出一些面部的表情或身體的律動,這是一種個性化的體現,僅具有視覺效果。但從音樂的本質來看,音樂是一門聽覺的藝術,這種伴隨性姿態往往不被看做是產出音響的音樂演奏者所發出的,其更多的是體現于為伴隨音樂表演的舞蹈者之上。如古典吉他與弗拉門戈舞蹈的跨界融合表演曲目《阿斯圖里亞斯的傳奇》。此時的弗拉門戈舞蹈被看作為伴隨性姿態,通過舞蹈伴隨的方式深化了對此首音樂作品的詮釋,同時給予欣賞者更沉浸式的視聽體驗。
- 《紳士幻想曲》第四樂章兩個演出版本的表演姿態對比分析
本文選擇對中國古典吉他演奏家匡俊宏與廈門愛樂樂團合作的版本及西班牙演奏家PabloSainzVillegas(下文稱其為維萊加斯)與delaMineria管弦樂團的合作版本的《紳士幻想曲》第四樂章的演奏作為研究樣本。此曲目為古典吉他著名協奏曲之一,表演主體由古典吉他演奏者、樂團、指揮組成,表演過程中會交織出多元化的表演姿態,下文以二位古典吉他演奏者為主體,對其在表演時產生的一系列表演姿態進行分析,探討二者在音樂表演上的差異性與共性。
(一)兩版本的表演姿態差異性比較
首先從音響生成姿態來說,在以上提到古典吉他演奏中,左手的揉弦動作屬于修飾型的音響生成姿態,這種姿態可以使古典吉他的音色得以變化,從而加強演奏的韻味。筆者對比了二者在演奏時所發出的揉弦動作的次數與此動作在樂曲中所發生的小節位置,發現二者揉弦的次數與出現的位置稍有不同,匡俊宏在整個第四樂章演奏中可觀測到的揉弦次數為10次,共分布在10個小節;而維萊加斯揉弦次數為16次,共分布在14個小節(表格一)。
可以發現二者對于音響的處理存在些許差異,維萊加斯對于音響的修飾更為頻繁。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差異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表演者理解的差異性以及個體的創造性兩方面。理解的差異性主要為表演者個人對于記譜姿態的理解不同,不同的理解將促使表演者產生不同的修飾型的音響生成姿態;個體的創造性首先基于表演者對記譜姿態的理解,忠實性是創造性的前提,只有清晰了解作曲家的創作意圖以及在譜面上隱喻的“召喚結構”后,才能更加自如地加以創造性的發揮,創造性同時也體現著表演者的個性。
其次在音響輔助性姿態當中,主要對演奏時出現的分句型姿態與夾帶型姿態進行分析。這首協奏曲的古典吉他樂譜當中出現了多次長時間的休止空拍。在第四樂章中,共出現9處超過兩小節以上的休止,而兩位演奏家對于休止前的分句處理也表現出不同的姿態,主要體現在休止處前一小節的最后一個音符奏響后的右手姿態上。從視頻文本中觀察到,匡俊宏在這9處的分句型姿態體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其右手的運動軌跡皆為向上方抬起,但在其抬起的幅度上稍有不同,第7處的運動幅度稍小(譜例一)。但從整體來看其運動幅度都不是很大,其右臂肘部始終未離開琴身,僅有小臂出現明顯的運動;相比來說,維萊加斯在此9處的右手分句型姿態與匡俊宏呈現出完全相反的狀態,其右手的運動軌跡均為大幅度的向右下垂,并伴隨右臂的張開,同時帶動了整個身體呈現出向后仰的姿態,表現出演奏的自由,也體現出了其自身演奏姿態的一致性。
在二者演奏時出現最多的為夾帶型的音響輔助性姿態。匡俊宏在演奏時的夾帶型姿態主要體現為小幅度且有力地向正下方點頭、向右下方點頭,微抬左前腳掌、右后腳跟,身體隨旋律微微擺動,掃弦時微抬小臂;維萊加斯在演奏時體現的夾帶型姿態主要體現為向右有力地歪頭、向下有力地點頭、向右轉頭、向右轉頭同時點頭,頭部向上彈起,微抬右后腳跟,身體隨旋律擺動,掃弦時大幅度抬臂。這些動作大量分布在在曲目中的兩個連續跳音片段、兩個連續快速音階片段、兩個連續掃弦片段。
在第一個跳音片段中,匡俊宏與維萊加斯都隨強拍音符的彈奏而點頭,其不同的是匡俊宏在此時伴有右前腳掌離地的姿態;維萊加斯跟隨旋律伴隨有較大幅度的身體律動。第二個跳音片段當中,其二者也都有強拍點頭的表現,而匡俊宏在此處右后腳跟與左前腳掌離地,相較第一個跳音片段表現出更加放松自如的狀態;維萊加斯在此處的身體律動則相較第一次幅度變小。其次,二者在快速音階片段演奏時呈現出較大的差別。匡俊宏在演奏時無過多的姿態,僅在第一個快速音階片段即將結束時微抬右后腳跟;而維萊加斯在兩段快速音階的演奏時均有伴隨強拍音符點頭的姿態。最后,在兩個掃弦片段當中二者呈現出來的頭部姿態均為向右轉頭并隨強拍點頭,但二者在點頭的力度上稍有區別,維萊加斯較匡俊宏的點頭力度要強。同時在第一個掃弦片段當中匡俊宏呈現出左前腳掌與右后腳跟離地的姿態。總的來說,從夾帶型姿態的呈現來看,匡俊宏在點頭的同時會伴以適當的腳部抬起,而維萊加斯則伴有相應的身體律動;從二者的姿態幅度來說,維萊加斯的幅度較大,這也隱喻地體現出二者個性的不同。
再次,在交流性姿態方面,主要產生在古典吉他演奏者與曲目指揮者之間。在匡俊宏的演奏中與指揮者共有一處平淡的眼神交流;而維萊加斯與指揮有兩處密切的交流姿態,體現為直視的眼神、微笑的面部表情與隨音樂律動的身體與,且這兩次的交流都位于快速音階演奏后的休止小節處。
最后,二者在演奏過程中的伴隨性姿態較為多樣,出現次數頻繁,且體現出不同的個性。由于伴隨性姿態與音響的生成無直接關聯,因此在此首作品中主要體現在連續的休止小節處。匡俊宏在休止小節處所產生的伴隨性姿態多為小幅度的、小力度的手部動作與微小的身體律動;維萊加斯則表現為自然下垂的右臂與大幅度的身體律動。
(二)兩版本的表演姿態共性
雖然在以上分析中發現兩位演奏家在許多姿態上呈現出不同的表現,但其也存在著一定的共性。主要體現為二者對于樂譜理解的一致性。例如在上文音響生成姿態的分析當中,二者共有六處在相同小節的相同音符上進行揉弦的修飾型音響生成姿態。在譜面上可發現,73小節處標記了兩個音樂術語(稍轉慢、如歌的),二者都對此做出了相同的修飾型姿態,在音樂的處理上體現出一致性。同樣在第183小節的附點四分音符上出現了自由延長符號,二者也對其做了相同的揉弦處理;其次在音響輔助性姿態方面,如上方提到的連續跳音、快速音階與掃弦片段,二者都同樣在相同的位置做出反應;又如在空拍時,二者都能夠隨著其他聲部的旋律進行身體律動。
結語
分散于不同學科的記譜姿態、音響姿態于身體姿態通過跨模態映射從而形成了現如今的姿態理論框架。音樂表演姿態理論不僅為音樂表演理論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同時對于表演者來說,對于音樂姿態理論的學習也是不可或缺的,從以上分析中可發現不同表演者對于同一首曲目的演奏展現出不同的風格,其在演奏中的姿態表現也不同。表演者通過姿態理論的學習與分析研究,可對同首作品的不同演奏版本與同位演奏家所演奏的不同作品進行分析,在不同中找到共性、在共性中挖掘個性以幫助找到自身演奏個性,同時通過理論學習+日常練習+舞臺實踐的三個維度,使舞臺表演者不斷提升自身表演水平與表現力,使舞臺表演更加穩定化、精細化,為觀眾帶來更加精彩的音樂舞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