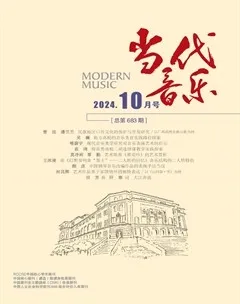斷裂與反叛:“國潮”舞蹈現象中“刺點”的生態學釋義
摘要:近年來,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感和文化自信不斷增強,“國潮”舞蹈熱作為一種新的現象,漸漸成為國人表達民族情懷和文化態度的新方式,人們對于“國潮”舞蹈的追尋成為一種時尚。而“國潮”舞蹈現象中“刺點”的出現,使中華民族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元素進行“破圈、融合、發展、再創”,以突破常規的解讀方式講述中國故事,同時也在“國潮”文化發展的趨勢下為中國本土舞蹈的創作與傳播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文章聚焦于“國潮”舞蹈現象,以生態學為理論視角,構筑“國潮”舞蹈現象中“刺點”的生態模型,探討本體與客體生態位的多元構建。“刺點”與舞蹈創作內涵是否深刻息息相關,故詳細梳理“國潮”舞蹈現象中“刺點”的生態學釋義,對于中國本土舞蹈創作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國潮”舞蹈現象;“刺點”;生態學
引言
隨著新媒體的應用日益廣泛,傳統文化通過新媒體這一窗口迅速吸引著大眾的目光,以獨具一格的形式重新展現著自身的獨特魅力。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關注中國元素,“國潮”舞蹈現象也儼然成為年輕人眼中的時尚,日益成為新媒體時代潮流文化的新寵。“刺點”的出現則為舞蹈創作打開了全新的創作體驗空間,也以強烈的斷裂點迅速刺中觀者內心深處,引發觀賞者的共鳴,舞蹈作品的深刻內涵也在“刺點”的特定位置下猶如裂縫中的陽光般折射出絢爛的光芒。“‘刺點’的存在迫使接收者放棄原有秩序直接體驗,以得到新的經驗,從而獲得新的意義”,同時也賦予舞蹈創作以新的藝術表達方式和更深刻的主旨意義。
一、何為刺點
“刺點”一詞源于拉丁語,其含義為“刺”、“小洞”、“小切口”。“刺點”一詞被廣泛應用于攝影領域,是符號學家和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特在最后的著作《明室:攝影縱橫談》(LaChamberClaire)一書中使用的術語,指照片內影響觀看者、使其被觸動的細節。羅蘭·巴特在探討攝影作品時用“刺點”這一術語的概念來描述作品中那些看似格格不入卻又意味深長的局部畫面。“這個要素從照片上的場景里像箭一樣/GY2pVZMl8xlj2mz13RQ7Q==射出來,射中了我。”巴特被照片中的“刺點”引起注意,吸引著他繼續了解照片背后所帶來的深層含義。與常規畫面元素不同的是,“刺點”“足以讓我整個閱讀出神入化,使我的興趣變得活潑,心花怒放”,它讓照片不止停留在常規秩序按部就班地陳述,而是在照片畫面的某一細小斷裂處迅速沖出畫面本身,以看似與之不相協調的姿態刺中觀者的內心,“這某個東西扎了一下,激起我心中小小的震蕩”。與此同時,它“像一種天賦,賜予我一種新的觀察角度”,帶給觀者常規秩序所不能產生的思考視角。由此可見,帶有“刺點”的照片使觀者更具有新奇、刺激的感受,以突破常規的因素賦予照片更深刻的主旨意義。
而在“國潮”舞蹈現象中,同樣存在著“刺點”。它們的出現看似突兀、不合常理,但當它們與舞蹈作品中的舞蹈動作、音樂、道具等構成要素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不僅使觀者在感官體驗上增加了新奇感受,更將隱喻意義引向畫面之外,引發觀者對于舞蹈作品更深層次的認知與思考。同時“刺點”也為“國潮”舞蹈以嶄新的姿態重回大眾視野注入了不竭動力,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融入新時代舞蹈提供了獨特價值與意義。
二、“刺點”在“國潮”舞蹈現象中的特征表現
(一)“刺點”中的“陌生化”
“陌生化”是俄國形式主義文論的核心概念之一,由俄國形式主義評論家維克托·鮑里索維奇·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他指出文藝的美感特征首先是驚奇陌生的新鮮感。他認為文學創作不能對于所描寫的對象完全照搬,而是要對描寫對象進行藝術化的加工和處理,而“陌生化”便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陌生化”就是要將我們所熟知的對象通過藝術加工變得陌生,從而使觀者從中獲得新穎奇特的感受,以此來完成獨特的審美體驗活動。
對于“國潮”舞蹈來說,“刺點”中的“陌生化”便是其重要特征。當舞蹈作品以常規秩序講述一段故事,毫無變化的故事節奏和完全在預料之內的故事走向便會讓觀者覺得索然無味。而當“刺點”出現,故事的平整性則被打亂,觀者接收到看似陌生的碎片化信息,在某一舞蹈動作、音樂、道具的催化作用下,它們便在觀者腦海里拼湊出完整的邏輯脈絡。此刻,這些陌生的碎片化信息擁有了意義,對于觀者而言,他們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體驗感和成就感。“刺點”中的“陌生化”顛覆了傳統舞蹈創作模式,也使觀眾摒棄了常規的習慣性思維,根據所接收的陌生碎片化信息主動參與其中,思考其背后的聯系與價值意義。榮獲第十三屆中國舞蹈“荷花獎”民族民間舞最高獎的《陽光下的麥蓋提》以黨的溫暖光輝帶給觀者陣陣暖意。其中多次出現的鼓子秧歌元素讓觀者感到陌生且困惑,為何不使用獨具地域特色的維族舞蹈而是使用山東地區特有的鼓子秧歌?也正是因為這陌生化的“刺點”的出現,讓觀者了解到麥蓋提作為山東日照的對口扶貧縣,受到了山東日照的幫助與扶持。舞蹈作品的意義得到了全新的詮釋,準確地將舞蹈主題引向“脫貧、扶貧”的更高維度。
(二)“刺點”中的“割裂化”
從舞蹈作品訴諸于鑒賞者的感覺特點來看,它是一種綜合了聽覺和視覺的表演藝術。因此不管“刺點”在“國潮”舞蹈中以動作、音樂亦或是道具的形式出現,它們都或多或少地在視覺或聽覺體驗上給予觀者一定的割裂感。這種割裂感源于觀者對于常規符號的認知,觀者以常規符號為認知基礎,以此獲得常規符號性表達以外的新的感官刺激,從而產生割裂感,出現畫面斷裂點,“刺點”便在此處誕生。“刺點”的割裂感起始帶給觀者一種殘敗、缺失的感受,但舞蹈深層意義也在斷裂處萌發出嫩芽,不僅填補了畫面的殘缺,更給予觀者多維度的畫面解讀方式。舞蹈詩劇《只此青綠》中對于《千里江山圖》的渲染和描繪為觀者帶來了宋代藝術之美。而《千里江山圖》的作者王希孟的出現,打破了作品對于時空的限制,使作品不僅僅停留在對于畫作畫面的單一描繪。“刺點”王希孟的出現對于觀眾來說或許畫面是割裂的,但也正是因為他的闖入,在舞臺上酣暢淋漓地揮灑著筆墨,我們看到的不止是《千里江山圖》帶來的色彩盛宴,更是其背后默默付出的無名匠人對于作品精雕細鏤、日臻完善的專注堅持。
三、“國潮”舞蹈現象中“刺點”的多元生態構建
(一)本體生態位的多元化構建
(1)舞蹈動作
舞蹈動作作為“刺點”在“國潮”舞蹈現象中本體生態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編導設置“刺點”標識的位置之一。當某一舞蹈動作作為“刺點”,它首先刺激著觀者的視覺感官。或許是這一舞蹈動作的出現與故事內容不相協調,又或許是與舞臺氛圍產生沖突,它都在以自身獨特的方式吸引著觀者的視線。
《唐印》作為第十二屆全國桃李杯展演中國古典舞作品,以濃郁的唐風華韻將觀眾帶入那個豐腴自信、奔放瑰麗的時代。舞蹈起始,舞者以靜態造型映入眼簾。伴隨著舞蹈開頭細碎的鈴聲,舞者們好似八音盒中旋轉起舞的小人。她們的肢體為什么看起來是僵硬的?為什么就像是提線木偶一般的存在?此時觀者帶著舞蹈第一段的這些疑問主動融入其中尋求答案。待到舞蹈的第三段,仕女們再次出現了類似的動作。此刻觀者的記憶被喚醒,當下的畫面也瞬間將觀者拉回舞蹈的第一段。原來《唐印》中看似違和的動作,實則展現的不僅僅是仕女的形象,更是博物館中的仕女俑雕塑。她們在逐漸密集的鼓聲中漸漸蘇醒,回到了屬于自己的時代,再到活潑奔放地展現著唐代的興盛,最后回歸沉睡,動作變得緩慢、卡頓,逐漸失去了鮮活的生命力,整個過程也映射著唐代的繁榮與落沒。這看似不合理的畫面斷裂點,將舞蹈主題從單一唐代仕女的形象描繪升華至對于唐朝時代風貌的再度游歷。由此,作品意義實現了全新維度的跨越。
(2)演員本身
如果說一度創作是編導對于舞蹈整體框架的建構與把控,那么舞蹈演員的二度創作則是在一度創作的基礎上將其書面符號轉化為可視的藝術形象的再創造活動。在表演的過程中,舞蹈演員需要細心揣摩人物角色,同時在編導規定的舞蹈語言框架內提出自己的體會與見解。“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舞蹈演員對于劇本的理解亦是如此。因此,不同舞蹈演員對于同一部舞蹈作品的詮釋也不盡相同,舞蹈演員自身對于作品二度創作的細節處理,也作為“刺點”給予觀眾除劇本之外的新的畫外意義。
17歲時的王亞彬憑借《扇舞丹青》獲得第五屆全國舞蹈比賽表演金獎。在排演過程中,王亞彬細心體會多種傳統藝術的表達方式以及自然景物。例如觀看書畫大師如何潑墨作畫,觀察隨風舞動的草坪、飄搖的柳枝以及天空中的云層如何舒卷自如、變化萬端。王亞彬認為《扇舞丹青》應該以一種輕盈靈動、行云流水的狀態呈現,因此她不斷地根據看到、感受到的事物的動勢、走向,轉化為自身的舞蹈藝術形象,并將其精準地融入到作品之中。此外,王亞彬有學習書法的經歷。中國書法的藝術特點在于剛柔并濟,王亞彬吸收中國書法的精華所在,將其轉化為舞臺上描繪丹青的一招一式,營造出端莊、典雅,卻又不失剛勁、灑脫的藝術文化景象。在《扇舞丹青》中,王亞彬自身對于作品的再體會、再創造作為“刺點”,突破了大眾對于扇舞既有的認知與創作思路,將古典舞與中國書法文化、扇文化、劍文化相結合,尋覓著書舞共存的藝術精神,訴說著“書中有舞,舞中有書”的畫外意義。
(二)客體生態位的多元化構建
(1)情節內容
舞蹈《小城雨巷》在全國第五屆“荷花杯”舞蹈大賽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得了創作、音樂、舞美三個金獎和表演銀獎。《小城雨巷》通過景、人、情的高度結合,將江南之美用藝術筆墨呈現了出來。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女孩跑向屋檐處躲雨。當女孩佇立在屋檐下,屋里伸出一把雨傘為女孩擋雨。舞蹈將江南之美貫穿始終,但結尾小女孩的出現卻好似將沉穩靜謐的氛圍打破,變得活潑生動起來。也正因如此,雨傘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撐起了人與人之間一片溫馨的天空。在情節的處理上,女孩的出現將舞蹈意義轉向和平安寧的美好愿景。《只此青綠》中展卷人角色的出現亦是如此。當展卷人“隔空”為疲憊的王希孟披上一件寒衣,這種情感與力量仿佛超脫時空傳遞給了千年之前作畫的少年,此刻便像是在進行一場絕美的“時空對話”。他們分明是不同時空的存在,卻又彼此產生交集。由跨越時空產生聯系的二人組成“刺點”,通過現實與過去的時空碰撞以及極具張力的對立畫面,實現畫面意義與舞蹈意義的跨越與提升。那一刻,王希孟并未真正看到展卷人,但他一定感知到了千年后無數注視著他的目光。而穿越過去的展卷人也被王希孟的匠人精神深深打動著,身上更肩負著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
(2)服飾
《陽光下的麥蓋提》起始,22位舞者整齊劃一地展現于舞臺之上。他們每個人的服裝都不同,其中一位身穿白襯衫的舞者引起了很多觀者的注意,這位演員的穿著打扮與舞臺上其他演員完全不同。其實,白襯衫的出現來自于編導的精巧構思。編導在采風活動中,注意到援疆干部們和大家交談時的親切,他們記得全村人的名字,生活樸實簡單,并且一心為民。他們無私奉獻的精神給編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襯衫的出現或許剛開始是突兀的,但當觀眾真正了解到援疆干部的暖心舉動,其又以“刺點”的特殊符號將作品推向新的高度。
(3)舞臺布置、道具
舞劇《朱鹮》以瀕危保護動物朱鹮為題材,將生靈的優雅恬靜展現得淋漓盡致。由于環境惡化等因素導致種群數量急劇下降,20世紀中葉,野生朱鹮宣告瀕臨絕跡。場景一轉,舞臺上出現的透明罩將朱鹮完全罩住,朱鹮卻一動不動,供人欣賞。這時舞臺完成了場景的轉換,昔日靈動的朱鹮如今成為了博物館玻璃罩中的標本,它依舊優雅卻無法再次展開翅膀。舞劇中將舞臺布景玻璃罩作為“刺點”,增加了畫面沖突,也借此將舞蹈意義再次升華,以此傳達出“為了曾經的失去,呼喚永久的珍惜”的主旨。舞蹈作品《覺》榮獲第十三屆中國舞蹈“荷花獎”古典舞獎。舞蹈將演員放置于圓盤裝置中,看似具有空間限制性的舞臺裝置,卻也是對于舞蹈主題的合理解讀。習武之人在一招一式中叩問消沉徘徊的內心,在方寸之間探尋人間正道的真諦。圓盤裝置以限制性的表演空間展現了舞蹈始終遵循圓的定律,以盤手、平轉、云間轉腰、端腿轉等動作,在不同維度完成對圓的繪制。舞蹈也以此在意象表達上實現了對立統一,通過太極八卦的具象畫面完成對于修煉心境的精神之旅。
結語
隨著更多“國潮”舞蹈現象中優秀作品的不斷涌現,觀眾對于舞蹈的藝術表達也不僅僅滿足于過于簡單的流水敘事和形式主義的精神表達。如果我們依舊借用千篇一律的編導技法進行舞蹈創作,那么創作思路便會受到一定的束縛,舞蹈作品也并不能真正做到打動人心。《只此青綠》《朱鹮》《唐印》等一部部舞蹈作品的出圈,也不斷印證著“刺點”對于“國潮”舞蹈現象所帶來的特殊意義,即使是一件簡單的服飾,一個細微的動作,“刺點”總以不同尋常的面貌展現在觀者面前,試圖將舞蹈意義引向畫面之外更寬闊的領域。在“國潮”舞蹈現象中,畫面中的每一次斷裂,創作中的每一次反叛,都為舞蹈內容、題材、思路帶來了全新的視角,也為舞蹈未來的多元創作方式提供了探索路徑。或許,反叛精神不是一意孤行,而是對于藝術表達邊界的一次次拓寬,對于時代精神的不斷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