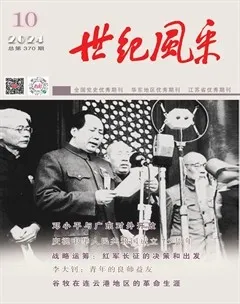白駒會(huì)師:華中抗日斗爭(zhēng)的關(guān)鍵落子


1940年10月10日,陳毅、粟裕領(lǐng)導(dǎo)的新四軍和黃克誠(chéng)率領(lǐng)的八路軍在江蘇省鹽城市大豐區(qū)西南部的白駒鎮(zhèn)獅子口勝利會(huì)師。作為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人民軍隊(duì)的重大會(huì)師之一,白駒會(huì)師不僅粉碎了國(guó)民黨頑固派企圖把八路軍封鎖在華北、新四軍封鎖在江南,最終分化消滅的陰謀,而且為壯大華中抗日力量,開辟蘇北抗日根據(jù)地,打開華中敵后抗戰(zhàn)新局面奠定了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為全民族抗戰(zhàn)事業(yè)和反法西斯斗爭(zhēng)作出杰出貢獻(xiàn)。
黨中央運(yùn)籌帷幄:開辟蘇北,發(fā)展華中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發(fā)動(dòng)盧溝橋事變,抗日戰(zhàn)爭(zhēng)全面爆發(fā)。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國(guó)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根據(jù)國(guó)共兩黨達(dá)成的協(xié)議,陜北的紅軍改編成國(guó)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長(zhǎng)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duì)改編成國(guó)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分別開赴華北、華中抗日前線。1937年至1938年5月間,隨著上海、南京、徐州等大城市的相繼陷落,日本侵略軍又把目光瞄準(zhǔn)了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軍事、政治、經(jīng)濟(jì)的中心武漢。1938年6月,日軍調(diào)集兩個(gè)軍,共9個(gè)師團(tuán),在航空兵團(tuán)和第三艦隊(duì)的掩護(hù)下突襲武漢。為了避免多線作戰(zhàn)兵力不足的窘境,日軍不得不將蘇北阜寧、東臺(tái)等地的軍隊(duì)撤走,蘇北中北部地區(qū)暫時(shí)成為“真空”地帶。
華中地區(qū)濱江臨海,津浦、隴海鐵路大動(dòng)脈貫穿其間,是堅(jiān)持持久抗戰(zhàn)的縱深后方,也是發(fā)展壯大我軍力量的重要區(qū)域。早在1937年8月下旬,八路軍便開始向華北挺進(jìn)。1938年2月15日,關(guān)于新四軍的行動(dòng)原則問題的電報(bào)中,中共中央復(fù)電項(xiàng)英、陳毅,指出:“目前最有利于發(fā)展地區(qū)還在江蘇境內(nèi)的茅山山脈……必能建立根據(jù)地,擴(kuò)大四軍基地。”這也成為中共中央最早關(guān)于新四軍行動(dòng)方向的戰(zhàn)略部署。5月4日,中共中央給時(shí)任新四軍副軍長(zhǎng)項(xiàng)英發(fā)出《發(fā)展華中敵后游擊戰(zhàn)爭(zhēng)》的指示中再次強(qiáng)調(diào):“在茅山根據(jù)地大體建立起來之后,還應(yīng)準(zhǔn)備分兵一部進(jìn)入蘇州、鎮(zhèn)江、吳淞三角地區(qū)去,再分一部渡江進(jìn)入江北地區(qū)。”這也標(biāo)志著中共中央正式選取蘇北作為發(fā)展華中的重要突破口。
隨著抗日戰(zhàn)爭(zhēng)進(jìn)入相持階段,國(guó)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反共摩擦日益加劇。為了凝聚最廣泛的抗戰(zhàn)力量,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擴(kuò)大的六屆六中全會(huì),針對(duì)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新形勢(shì),進(jìn)一步明確了“鞏固華北和發(fā)展華中、華南的戰(zhàn)略與方針”。1939年2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來到皖南云嶺新四軍軍部視察,闡明中央關(guān)于“新四軍向北發(fā)展”的方針,并與新四軍領(lǐng)導(dǎo)商定了“向北發(fā)展,向東作戰(zhàn),向南鞏固”的具體方針。1939年4月至5月間,中共中央書記處再次發(fā)出關(guān)于發(fā)展華中武裝力量的指示,指出“華中是我黨發(fā)展武裝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戰(zhàn)略上華中亦為聯(lián)系華北華南之樞紐,關(guān)系整個(gè)抗戰(zhàn)前途甚大”。1940年以后,國(guó)民黨頑固派企圖把八路軍、新四軍納入黃河以北,劃定黃河以北為我兩軍防區(qū)。毛澤東給八路軍、新四軍指戰(zhàn)員發(fā)出《發(fā)展華中根據(jù)地的部署》,明確指示:“華北敵占領(lǐng)區(qū)日益擴(kuò)大,我之斗爭(zhēng)日益艱苦,不入華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國(guó)性突變時(shí),我軍決不能限死黃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為打破封鎖,求得最基本的生存空間,進(jìn)而在復(fù)雜戰(zhàn)局中占據(jù)主動(dòng)地位,中共中央于1940年5月4日向東南局發(fā)出《放手發(fā)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jìn)攻》的指示,要求在“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驟有計(jì)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qū)域控制在我們手中”。6月1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發(fā)出《對(duì)華北華中的戰(zhàn)略部署》,要求“彭朱支隊(duì)即八路軍第一一五師蘇魯豫支隊(duì)及黃克誠(chéng)縱隊(duì)?wèi)?yīng)立即出發(fā)。黃應(yīng)親率全部或至少兩個(gè)旅南下”。
中共中央對(duì)于華中地區(qū)的戰(zhàn)略地位有著清醒的認(rèn)知,從最開始“挺進(jìn)華北”堅(jiān)決抗日,到為應(yīng)對(duì)摩擦決定“鞏固華北、發(fā)展華中”,再到“發(fā)展華中”戰(zhàn)略中的“向北發(fā)展”,將蘇北確定為發(fā)展華中敵后抗戰(zhàn)最有利的地區(qū),最終促成新四軍北上和八路軍南下,挺進(jìn)蘇北,填補(bǔ)華中的真空。在瞬息萬變的斗爭(zhēng)形勢(shì)中不斷調(diào)整華中的戰(zhàn)略部署,顯示出中共中央運(yùn)籌帷幄的戰(zhàn)略思維和果敢決斷的應(yīng)對(duì)策略。
指戰(zhàn)員堅(jiān)決執(zhí)行:挺進(jìn)蘇北,創(chuàng)建華中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新四軍軍部部署,1938年4月起,陳毅、張鼎丞率領(lǐng)新四軍第1、2支隊(duì)向蘇南敵后進(jìn)軍,開辟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jù)地。9月,江南人民抗日義勇軍挺進(jìn)縱隊(duì)率先渡江,控制了江都縣境內(nèi)的嘶馬、大橋地區(qū),為后期迎接主力部隊(duì)渡江建立了橋頭陣地。中共六屆六中全會(huì)之后,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來到華中,并于1939年12月19日向中共中央提出我黨在華中領(lǐng)導(dǎo)抗日游擊戰(zhàn)爭(zhēng)的意見,即“江蘇北部我們都沒有正規(guī)部隊(duì)及黨的機(jī)關(guān)去活動(dòng),亦無地方黨,而這又是有最大發(fā)展希望的地區(qū),因此,這是我們突擊方向,應(yīng)集中最大力量向這方面發(fā)展”。1939年12月至翌年2月,劉少奇在皖東北地區(qū)連續(xù)主持召開三次中原局?jǐn)U大會(huì)議,進(jìn)一步明確了以開辟蘇北抗日根據(jù)地為突圍方向,逐步發(fā)展華中的方針,即將蘇北作為華中的突圍方向,調(diào)江南新四軍主力渡江北上,同時(shí)派八路軍一部迅速南下,共同完成開辟華中敵后根據(jù)地的重任。
1940年7月8日,陳毅、粟裕率領(lǐng)江南指揮部機(jī)關(guān)及老2團(tuán)、新6團(tuán)等主力經(jīng)揚(yáng)中縣北渡長(zhǎng)江,到達(dá)江都縣吳家橋,與挺進(jìn)縱隊(duì)、蘇皖支隊(duì)等部會(huì)合。隨后部隊(duì)在塘頭整編,部隊(duì)整編為3個(gè)縱隊(duì)9個(gè)團(tuán),共7000余人。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zhǔn),7月下旬將江南指揮部改稱江北指揮部。7月25日,陳毅率部東進(jìn),建立了以黃橋?yàn)橹行牡奶K北抗日根據(jù)地。
為配合新四軍開辟蘇北抗日根據(jù)地,194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黃克誠(chéng)率八路軍主力一部南下,開赴華中,與彭雪楓部會(huì)合,組建八路軍第4縱隊(duì)。1940年8月7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蘇皖豫支隊(duì)、新2旅隴海南進(jìn)支隊(duì)和新四軍第6支隊(duì)第4總隊(duì),統(tǒng)一編為八路軍第5縱隊(duì),任命黃克誠(chéng)為司令員兼政委,全縱隊(duì)轄3個(gè)支隊(duì)9個(gè)團(tuán),2萬余人。部隊(duì)整編結(jié)束后即刻擎旗南下,東進(jìn)至淮(陰)海(州)地區(qū),配合已經(jīng)渡江北上的陳毅、粟裕等部東進(jìn),進(jìn)行“堅(jiān)決爭(zhēng)取控制全蘇北”的斗爭(zhēng)。
當(dāng)時(shí)蘇北各方勢(shì)力錯(cuò)綜復(fù)雜,不僅日、偽軍長(zhǎng)期盤踞,還有韓德勤為代表的國(guó)民黨頑固派,李明揚(yáng)、李長(zhǎng)江為代表的地方實(shí)力派,斗爭(zhēng)形勢(shì)異常復(fù)雜嚴(yán)峻。陳毅冷靜分析蘇北地區(qū)軍事態(tài)勢(shì),提出“擊敵、聯(lián)李、孤韓”的戰(zhàn)略方針,并三次冒險(xiǎn),親赴泰州與李明揚(yáng)、李長(zhǎng)江談判,達(dá)成共同抗日的協(xié)議。但是國(guó)民黨頑固派韓德勤自恃軍事占優(yōu),狂妄叫囂要先消滅北上的新四軍,再消滅南下的八路軍。1940年10月4日,韓德勤調(diào)集3.5萬人,兵分三路悍然向我新四軍駐地黃橋大舉進(jìn)攻,新四軍奮起反擊。為了支援黃橋決戰(zhàn),中共中央發(fā)出指示,韓德勤又大舉壓迫我軍,八路軍不能坐視。并提出:“我們的方針是,韓不攻陳,黃不攻韓;韓若攻陳,黃必攻韓。”黃克誠(chéng)命令八路軍第5縱隊(duì)1支隊(duì)和2支隊(duì)一部奮力南下支援新四軍,分路向鹽城、阜寧進(jìn)發(fā),先后突破鹽河、廢黃河防線,連克東溝、阜寧等城鎮(zhèn),直逼蘇北重鎮(zhèn)鹽城。在八路軍的戰(zhàn)略配合下,10月6日,陳毅、粟裕指揮新四軍約7000人在黃橋迎戰(zhàn)來犯頑軍,共殲滅韓德勤部1.1萬余人,俘獲3800余人。黃橋戰(zhàn)役的勝利,成為開辟蘇北的奠基禮,為發(fā)展和堅(jiān)持華中敵后抗日根據(jù)地掃除了障礙。
黃橋決戰(zhàn)取得決定性勝利后,新四軍乘勝向北追擊潰逃的韓軍殘部,勢(shì)如破竹。10月10日,新四軍1支隊(duì)2縱隊(duì)6團(tuán)的先頭部隊(duì)與八路軍5縱隊(duì)1支隊(duì)的先頭部隊(duì)在鹽城大豐白駒鎮(zhèn)獅子口勝利會(huì)師。
根據(jù)地抗日反頑:經(jīng)略蘇北,問鼎華中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勝利會(huì)師奠定了蘇北抗日根據(jù)地的基礎(chǔ)。兩軍勝利會(huì)師從根本上扭轉(zhuǎn)了蘇北地區(qū)敵我斗爭(zhēng)形勢(shì)。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lǐng)導(dǎo)下,新四軍開始獨(dú)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quán),各項(xiàng)事業(yè)蓬勃發(fā)展,先后開辟形成江南、蘇中、鹽阜、淮海、皖東、豫皖蘇邊等總面積達(dá)18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1500萬的敵后抗日根據(jù)地。中共中央華中局、華中黨校、魯藝華中分院、抗大五分校、江淮日?qǐng)?bào)社、華中銀行等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機(jī)構(gòu)陸續(xù)建立,著名人士、社會(huì)賢達(dá)紛紛來到蘇北抗日根據(jù)地,蘇北迅速成為華中抗戰(zhàn)的軍事、政治和文化中心,“陜北有個(gè)延安,蘇北有個(gè)鹽城”的美譽(yù)傳遍大江南北。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勝利會(huì)師打開了華中抗戰(zhàn)的新局面。兩軍勝利會(huì)師,標(biāo)志著中共中央“發(fā)展華中”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基本實(shí)現(xiàn),其中華南、山東、中原、華北等地多個(gè)抗日根據(jù)地連成一片,使得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下的抗日武裝形成了一個(gè)整體,便于從戰(zhàn)略上統(tǒng)一指揮、統(tǒng)一意志、統(tǒng)一行動(dòng)。1940年11月17日,經(jīng)中共中央批準(zhǔn),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在海安成立,葉挺任總指揮,陳毅任副總指揮,劉少奇任政治委員。1941年1月,皖南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duì)遭受嚴(yán)重?fù)p失,正是此前的兩軍會(huì)師,為保存和發(fā)展新四軍做好了組織上的準(zhǔn)備,成為新四軍浴火重生的轉(zhuǎn)折點(diǎn)。1941年1月20日,中央軍委發(fā)布在蘇北鹽城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zhǎng),劉少奇為政治委員。新軍部成立后,根據(jù)中央軍委的命令,隴海路以南的新四軍、八路軍部隊(duì)統(tǒng)一整編為新四軍,全軍擴(kuò)軍為7個(gè)師、1個(gè)獨(dú)立旅,總兵力9萬余人。完成整編的新四軍立刻投入挽救民族危亡滾滾洪流之中。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勝利會(huì)師鑄就了偉大的“鐵軍”革命精神。會(huì)師過程中,八路軍、新四軍生動(dòng)詮釋了堅(jiān)決聽黨指揮、加強(qiáng)團(tuán)結(jié)協(xié)作、連續(xù)英勇作戰(zhàn)、堅(jiān)定必勝信念的革命精神和頑強(qiáng)作風(fēng),形成了鐵一般的理想信念、鐵一般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鐵一般的過硬本領(lǐng)、鐵一般的紀(jì)律作風(fēng)的精神內(nèi)核。跨越歷史時(shí)空,新四軍“鐵軍”革命精神在新時(shí)代依然熠熠生輝,成為引領(lǐng)我們不斷前行的強(qiáng)大動(dòng)力。
責(zé)任編輯:侍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