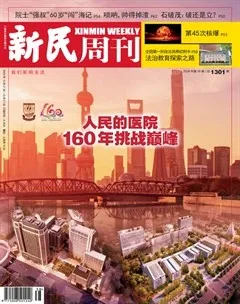舶來品如何吹響搖滾國潮

好神奇一樂器。
你以為它俗,它偏偏是挺洋氣的舶來品——據傳由波斯、阿拉伯流入中國。
你以為它low,無非村口非主流黃毛看熱鬧時幫著烘托氣氛的“套路”背景音樂,它偏偏用《男兒當自強》《好漢歌》《囍》《艷》《鴛鴦債》《九州同》……一長串亦老亦新的歌單告訴你,偏見源于無知,它可豪放可凄艷,可傳統可時尚,是不可抵擋的搖滾國潮。
嗩吶一響,制霸全場。這種神奇的樂器,可以在“恨血千年土中碧”與“雄雞一唱天下白”之間無縫切換,催汝心肝,食汝魂魄,囫圇吐出,開天辟地。
這樣想想,嗩吶的重新走紅根本毫不意外。事實上,近十年來的民樂復興與革新求變,只能更加證明一個觀點:從來都不是“器”的問題,是“道”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來自波斯、阿拉伯的“吶”喊
劉勇的《中國嗩吶歷史考索》一文,列舉了三種引起關注的、關于嗩吶起源的討論——
日本學者林謙三在著作《東亞樂器考》中曾論述:“中國的嗩吶, 出自波斯、阿拉伯的打合簧 (復簧) 樂器蘇爾奈。”林氏提出此說, 主要是從語言方面考慮, 他認為嗩吶這個名字是波斯語zourn?的音譯。“嗩吶這名字的音韻, 就表示著是個外來的樂器。”“其原語出于波斯語zourn? (zurnā)。”
另一位日本學者岸邊成雄亦于20世紀60年代赴西亞考察,解釋surnay(sourna)一詞時,岸邊表示:“波斯語的斯魯奈伊或斯魯納比阿拉伯語的‘扎姆爾’更通用些,這是把‘奈伊’(葦子之類)與斯魯(祭之意)合起來的一個用語。也稱作嗩吶,很明顯這是surnay的音譯。”
以上暫稱為“波斯、阿拉伯說”。

周菁葆1984年所撰《嗩吶考》介紹了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第38窟壁畫中的嗩吶,爾后提出新的嗩吶起源說,認為嗩吶最早產生于新疆,傳入阿拉伯、印度后,又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此說暫稱為“龜茲說”。
山東省嘉祥縣文化館賈衍法則在1996年撰寫的《樂聲如潮的嗩吶之鄉》一文中, 談及了嘉祥武氏祠的漢畫像石, 上“刻有一幅完整的鼓吹樂隊……而中間一人所吹奏的樂器,上尖下圓呈喇叭口狀,既不是篳篥,又不是角,正是嗩吶”。賈衍法認為, 嗩吶在東漢時期已在當地流行, 只不過那時不叫嗩吶而叫“大笛”, 到了明代,“才吸收采用了波斯語的音譯surna”。據此說, 嗩吶在內地流行的年代又比龜茲早了200年左右。由于此說認為除當地有嗩吶外, 波斯也有嗩吶, 故暫稱為“二元說”。
“龜茲說”和“二元說”均有圖像為證,但圖像一定可靠么?
霍旭初就對克孜爾的嗩吶持懷疑態度。“篳篥,是龜茲創造的一種管樂器。38窟‘天宮伎樂’圖中有二支, 該樂器的口部呈喇叭形, 故有的學者認為是‘嗩吶'。但在龜茲石窟壁畫里, 除此之外沒有第二例。……關于此樂器的喇叭口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研究。”霍旭初表示,畫中的喇叭口與管身顏色有異, 疑為后人所加。

事實證明霍旭初的判斷是正確的。1998年10月, 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館長瑪麗安娜·雅爾狄茨 (Marianne Yaldiz)和助手訪問了克孜爾石窟, 帶來了她們的前輩本世紀初拍攝的照片, 其中有一件就是第38窟的“嗩吶”。照片顯示, 當時這件樂器沒有喇叭口(估計后來臨摹壁畫者整了活)。至此,“龜茲說”徹底退出討論。
劉勇親往調查了嘉祥武氏祠的刻石,僅憑觀察,實在無法確定樂器就是嗩吶。而多年研究武氏祠石刻的朱錫祿在專著《嘉祥漢畫像石》里指出,這件樂器是塤。
根據排除法,“波斯、阿拉伯說”的可能性最大。綜合各國專家學者的研究考證,波斯、阿拉伯的嗩吶出現早于中國,有線索能夠表明二者之間存在傳播關系,劉勇推測,嗩吶在北朝,至遲于唐代傳入中國。
自古至今,絲綢之路讓東西文明的精神世界得以相通。玄奘、鄂本篤以及蘇菲派傳教士從這里將三大宗教原典帶入中原,無數不知名的樂師,則帶來諸多漢族眼中“奇形怪狀”的樂器,它們在神州大地播下種子,終于開出了“華樂”的花朵。除了嗩吶,還有揚琴、琵琶等等,例子不勝枚舉。
唐宋兩代,嗩吶的信息不多。到了明朝,不僅有了精確的文字記載,且其身影于廟宇壁畫、藩王和官員墓中不時閃現(嗩吶俑)。此外,嗩吶還頻頻在小說、唱本的插圖內“友情客串”一把,特點突出,無可錯認。然而,因為發聲夠響,適宜預警通報、鼓舞士氣、提振精神,彼時嗩吶最正確的使用方式仍是軍樂和儀仗樂器,戚繼光《紀效新書》和王圻《三才圖會》即強調了嗩吶的軍樂/撐場面功能。清中葉后是嗩吶藝術的一個繁榮時期,這個繁榮時期的到來或與大量地方戲曲的草根爭鳴相關。在民間尤其是離游牧文明更近的黃河流域,代表“朕要飆歌”的舶來樂器總算咸魚翻身,搶占了不少演奏難度較高卻聲勢較弱的傳統樂器的地盤——古代小資文青大多覺得嗩吶粗鄙,偏老百姓愣頭愣腦直來直往,就中意一份“要聞播送—快上嗩吶—C位出行—路人側目”的痛快。
因為無敵,成了寂寞“流氓”
嗩吶一響,黃金萬兩。
其聲之亢,八個單簧管估計都壓不住;其聲之烈,整個樂團大概也控不了。因為存在感忒強,嗩吶也被戲謔地稱為樂器界的“流氓”。
流氓無敵,流氓寂寞。嗩吶的音色,天生不適合與任何樂器進行合奏——打擊節奏的鼓可以與嗩吶組CP,但漢族傳統雅樂里留給鼓的發揮空間似乎同樣不多。于是,說起其它民族樂器,有“高山流水”,有“朱弦玉磬”,有“伯塤仲篪”,不乏矜貴氣度,但畫面一切換到嗩吶,不和諧的評價比比皆是:
“中原自金、元二虜猾亂之后,胡曲盛行,今惟琴譜僅存古曲。余若琵琶、箏、笛、阮咸、響〔角戔〕之屬,其曲但有《迎仙客》《朝天子》之類,無一器能存其舊者。至于喇叭、嗩吶之流,并其器皆金、元遺物矣。樂之不講至是哉!”(徐渭《南詞敘錄》)
“喇叭,嗩吶,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抬身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見得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得水盡鵝飛罷!”(王磐《朝天子·詠喇叭》)

“近今且變[弋陽腔]為[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為[梆子腔]、[亂彈腔]、[瑣哪腔]、[啰啰腔]矣。”(劉廷璣《在園曲志》;瑣哪,通嗩吶)
白眼也好,青眼也罷,嗩吶但管徑自殺出生天。而20世紀初至新中國成立這段時期,我國嗩吶流派的發展極具地區特色,其中,以山東嗩吶、河南嗩吶、河北嗩吶、安徽嗩吶及東北嗩吶這“五大派”影響較大。1952年國慶三周年,由楊繼武指揮、胡海泉獨奏的嗩吶協奏曲《歡慶勝利》在沈陽首次公演,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以獨奏的形式將嗩吶音樂搬上舞臺。同時,任同祥、劉鳳鳴等為代表的嗩吶藝人從民間藝術的土壤中茁壯成長,走進了音樂廳、歌劇院。
任同祥的演奏集魯西南民間音樂之長,從容自如、干凈利落、剛柔相濟,聲情并茂;運氣輕松飄逸、技巧高超靈活。他把傳統的演奏技法同現代吹奏樂器的演奏方法融為一體,獨創了許多新的哨響演奏技巧。經他創編的《百鳥朝鳳》,已成為嗩吶經久不衰的名曲,系演出時最受歡迎的曲目之一。20世紀50年代以來,他多次參加國內重大慶祝活動及藝術節,出訪過20余個國家和地區,堪稱把中國嗩吶吹向世界的第一人。
不錯,嗩吶曾經迎來一輪心花怒放、艷陽高照的盛夏。可惜,喧囂躁動的夏天過去,清冷蕭瑟的秋天便降臨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商品經濟一并席卷村莊的,還有來勢洶洶的西洋樂器,以及插上電就能“感天動地”的麥克風和大音響。面對新時代的機械降神黑科技,樂器界的流氓大抵是脫節了、心態老了、懶得繼續“橫”下去了,聲音漸漸嘶啞,神情漸漸落寞。
網上有個樂器評論的段子總結出了嗩吶的風光與無奈:不是拜堂,就是升天,一把嗩吶吹一生。婚曲響,紅布蓋,全村老小等上菜。走的走,抬的抬,滿目愴涼雪雪白。調一悲,土一埋,親朋好友哭起來。初聞難解嗩吶意,再聞身已入黃泉,兩耳不聞棺外事,此心斬斷塵世緣。
一個人出生了,一個人成親了,一個人離開了,都是在這片土地上,都能聽見嗩吶的呼喚。所以,紅白喜事、來來往往很可笑么?田埂邊的雜草、荒原上的野風很可笑么?
與紅白喜事深度捆綁,與鄉土中國深度捆綁,難道反成了困住嗩吶的魔咒?

一把嗩吶,吹完一生鄉戀
其實不是。我們只是不懂。
朱天心說過,“原來,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作家鄉的”。一個人出生了,一個人成親了,一個人離開了,都是在這片土地上,都能聽見嗩吶的呼喚。所以,紅白喜事、來來往往很可笑么?田埂邊的雜草、荒原上的野風很可笑么?
對嗩吶的刻板印象與不理解,實際亦反映了鄉土傳統在現代化沖擊下所面臨的困境。吳天明電影《百鳥朝鳳》里的焦三爺道出他作為匠人的堅守,“嗩吶不是吹給別人聽的,是吹給自己聽的”。焦三爺又道,黃河岸上不能沒有嗩吶,不光是婚喪嫁娶的時候要弄幾管嗩吶鬧鬧,鄉親們平常干活累了,吹一段嗩吶,也能幫他們解乏——嗩吶的價值,從一開始就是跟土地密切聯系的,有豐厚的文化內核。影片中那再熟悉不過的黃土山茆、自帶牧歌氛圍的蘆葦蕩、麥田、夜晚的螢火蟲、送干糧的小狗,雖飽含無從克制的浪漫化表達的成分,卻的確吹出了鄉村江湖的一闋絕唱。
我們還會想起儺班的吹火節目,對著火吹嗩吶,象征來年大家日子都過得風風火火。還會想起狂歡意義的“社火”,大都在正月祭社、廟會迎神、祈雨時表演,社火隊伍沿著鄉間小路九曲十八彎,鑼聲鼓聲嗩吶聲送出最隆重的祝福,大地為之沸騰……當然了,所有民間藝術以“無濾鏡”樸素面目呈現在陌生的看客面前時,難免會承擔被獵奇、被誤讀甚至不被接受的風險。更嚴重的問題是,為了迎合都市受眾突然心血來潮的怪誕胃口,這些業已牢牢扎根泥土的民間藝術可能被迫更改原本的模樣,喪失尊嚴與地基,譬如表演用鼻孔吹嗩吶,一個人同時吹九個嗩吶之類。
自怨自艾終歸是無用的。嗩吶一度看不清前景,不是因為“土味”,而是創作的步伐、激情的靈光沒跟上。音樂沒有“對”和“錯”,只有“好”和“沒那么好”。國際著名管風琴演奏家沈媛就舉過一個例子:什么是“沒那么好”呢?比如在巴洛克音樂中,如果你運用了浪漫主義思維,做了一個宏偉延綿的漸慢,就會聽起來很油膩。但即便油膩,也不是錯的,只是你多了一份解釋成本,要給觀眾講你為什么這樣演奏。
依照這樣的概念,聽眾適宜用“精致復雜”或者“粗糙簡陋”這樣的形容詞,而不適宜用非黑即白的“高低雅俗”來形容旋律及樂器。聽眾反感的實質上絕非一首曲子的民歌性、一種樂器的音色音量,而是情感態度和演繹技巧的毫不走心、毫不過腦,包括過于簡單的和聲、從素材庫里直接復制粘貼的鼓點和自動伴奏,以及全無設計感甚至不搭調的編曲和配器等等。
嗩吶需要從鄉村小鎮來到更廣闊的天地,需要軟件、硬件的升級,思路的革新。在當代的舞臺上,傳統嗩吶主要有這么些“槽點”:一、演奏半音把握性差、音準不穩定、音色不統一、速度慢等,甚至有些音階很難連續進行。二、在音樂進行中,遠關系轉調,短時間內無法換樂器。三、各種調的嗩吶太多了,修理哨片及保養方面較煩瑣。“傳統樂器也要適應時代,與音樂藝術的發展一樣與時俱進。”1992年,管樂演奏家郭雅志發明嗩吶“活芯”裝置,令傳統嗩吶奏出半音階、十二音體系,大大豐富了嗩吶的表現力。此后,嗩吶活芯技術在實踐應用中不斷改進,愈受垂愛。在民族樂隊合奏及現代音樂、流行及爵士音樂的應用中,嗩吶活芯積極發揮,表現搶眼。
2002年,郭雅志推出第二代嗩吶活芯。2016年初,他綜合廣大嗩吶演奏家對活芯應用的反饋,重新設計嗩吶活芯。2017年3月,精制而成的第三代嗩吶活芯成功面世。
華麗變身,嗩吶王者歸來。
具有搖滾精神的老伙計
如今,我國嗩吶藝術在樂器本體、音樂作品、傳承體系等方面均發展迅速,更令人欣喜的是,它融入了互聯網文化,創作團隊與受眾群體正不斷增加,呈現年輕化、多元化的趨勢。
第三代嗩吶活芯“開始浪起來”的2017年,還上映了一部“2.5次元樂隊征伐四方”的《閃光少女》,而這部電影最中二、最經典的名場面,是陳奕迅飾演的領導來校視察時,同學們一段火花潑溢的中西樂器大battle。揚琴、二胡、琵琶集合己方一票死黨,抗擊鋼琴、小提琴、豎琴等敵方選手,針尖對麥芒短兵相接,見招拆招燃到炸裂。我用《廣陵散》下戰書,你以德彪西《第一號阿拉伯風華麗曲》化解殺氣;你有《野蜂飛舞》,我出《百鳥朝鳳》的“嘲諷”版,嗩吶吹響鳳首昂起,驕傲地將野蜂驅除殆盡。主提琴手潰敗停音,嗩吶又引領各民族樂器重奏《野蜂飛舞》肆意炫技,不啻“在你擅長裝腔的領域勝利反攻”。
《閃光少女》的編劇是以《失戀33天》成名的鮑鯨鯨。她學了十年民樂,但屢次發覺學西洋樂的會把學民樂的置于鄙視鏈末端,遂決定在片子里展開一場酣暢淋漓的復仇。細細咂摸個中滋味,卻也品出幾分搖滾精神——不管年紀老小,不管有錢沒錢,不管生活困頓抑或富足,還是不甘心,還是忍不住跟這個世界過不去,所以要用音樂宣泄滿腔情愫,盼平凡庸碌的軀殼,也能被一道道勇猛的光芒照耀。這樣的無畏、叛逆,恰與嗩吶的渲染力、穿透力相得益彰,年輕人特別有共鳴。因此,近些年來,嗩吶既可以是視頻網站“鬼畜區”的哏王,也可以是一首千萬級播放量熱門原創歌曲的靈魂。

嗩吶重新成為流行文化的弄潮兒。
而黃霑、鮑比達、羅大佑、崔健、劉元……滄海一聲笑:當年,我們早就玩過一遍了。
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里有嗩吶,發行日期1983年。“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崔健的《一無所有》無須過多介紹,吹嗩吶的劉元還會吹笛吹簫,典型的“六邊形戰士”。1991年,徐克導演的首部黃飛鴻系列電影《黃飛鴻之壯志凌云》在港上映,次年的金像獎上一舉斬獲導演、配樂、剪輯、動作指導四個最佳。黃霑、鮑比達攜手、改編自古曲《將軍令》的那首《男兒當自強》,聲威震天的嗩吶搭配林子祥蒼勁有力的詮釋,簡直神仙陣容。至于商易為民族舞劇《小刀會》(1959)創作、開頭就用嗩吶鋪墊氣場的《小刀會序曲》,更在《新龍門客棧》《龍門飛甲》《大話西游》《西游·降魔篇》《大圣歸來》等多部電影里強勢發聲。

電視劇方面,卞留念演唱、吳京主演的《太極宗師》(1997)片頭曲《英雄誰屬》,趙季平譜曲編曲、劉歡演唱的《水滸傳》(1998)主題曲《好漢歌》,也都是“嗩吶一出,誰與爭鋒,豪杰飛渡江川闖九州”的范兒。20年后,譚晶在《我是歌手》的舞臺上翻唱了《紅高粱》的片尾曲《九兒》,嗩吶貫穿始終,女子從芳心暗許到慷慨赴死的一往無前,盡付樂章。
葛東琪的《囍》、關大洲的《九州同》,乃至手游《紙嫁衣》系列的歌曲《鴛鴦債》《癡情客》,每每是嗩吶還沒出,瘋狂彈幕早已忙不迭地提早劇透:前方核能,前方核能,前方核能!忽而凄婉忽而勇猛,一邊傳統一邊搖滾,音符扎在胸口上,刀刀正中靶心。新時代優秀的“吹手”們各有站位、各逞其才,好就好在把握住了嗩吶的精髓,為其量身打造王者榮耀的登場方式,花樣翻新不拘泥,中西合璧無顧忌。
在國潮洶涌、情潮洶涌的當下與未來,嗩吶不再僅僅是“死去活來”“夫妻對拜”的標志,而是人們詠物抒懷、表達內心感受的重要音樂渠道之一。因為熱愛,無論是村落的小徑還是城市的大劇院,都該有投入吹奏的朋友;因為熱愛,哪怕隔著網線,我們都被同一個老伙計所征服。
嗩吶值得被認真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