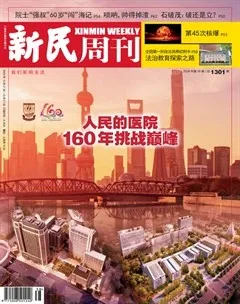極簡和繁復
1990年,一位名叫津月(Kyoichi Tsuzuki)的年輕攝影師開始拍攝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東京,他的鏡頭對準東京的數百套公寓,拍攝了許多人的生活空間。這些照片結集為《東京風格》,要說這些圖像有什么“風格”,那就是擁擠和雜亂。在這本畫冊的英譯本序言中,津月說,外人癡迷于日本的極簡主義,但那是“日本愛好者的幻想”。外人喜歡無印良品、喜歡安藤忠雄的清水混凝土,而后以為日本美學就是簡單、極簡主義和克制,但實際情況并不如此。東京有許多住宅和小店鋪,都擁擠雜亂。
且慢,我們喜歡日本的枯山水,極簡風格的寺廟,還有他們的俳句,連詩歌都這么簡單、克制,但津月說,極簡風格的寺廟和枯山水,都是排斥游客排斥他人的,“極簡主義是一種建立隱私的方式。你無法分辨那個人穿什么或吃什么”。他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富人都可以奢侈地生活在干凈的空間里,而窮人不得不在狹小的空間里生活,沒有辦法隱藏他們的物品。當你有錢建造一個空間時,你才可能使它的功能單一,“極簡主義是那些有空間和金錢的人才能創造的東西”。
文化評論家松岡寫過一本書叫《The Method Called Japan》,他說日本文化向來有加法和減法兩個維度,茶舍或禪宗花園、能戲和日本舞踴、和歌和俳句,這是減法的符號,祭節花車、歌舞伎舞臺、日光東照宮神社的華麗炫耀造型,則是加法的符號。

專欄作家
讀書,寫字,旅游,鍛煉
“極簡主義是那些有空間和金錢的人才能創造的東西。”
我們去日本旅行的時候,會為這兩個維度的美學所吸引。但是居家過日子的時候,就需要減法了。有好幾本暢銷書,比如Marie Kondo的《改變生活的整理魔法:日本整理和組織藝術》(2011年)和Fumio Sasaki的《再見,事物:新日本極簡主義》(2015年)都將雜亂定義為對心理健康和精神成長的嚴重威脅。這些書在中國很受歡迎,但是,這些書起初都是為雜亂的日本人寫的。其中,最為著名的概念就是“斷舍離”,新詞danshari,來自瑜伽術語,指放棄世俗的依戀,如果你不能重組社會,你可以重組你的衣柜。
早期的西方人也喜歡日本的極簡,他們把“普遍缺乏奢侈品”視為一種超越,這樣可以擺脫消費主義的影響,但有一位叫Morse的西方人說,缺乏東西與其說是美學的產物,不如說是經濟學的產物,日本早期的極簡,就是匱乏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里,日本是一個遠不如現在受歡迎的旅游目的地。在那個時段里,日本家庭充滿了各種電子產品和娛樂設施,隨身聽、卡拉OK機、錄像帶播放器、電視、立體聲、無數的玩具、視頻游戲、卡通、漫畫等等。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后,人們開始重新審視他們與消費的關系。到2000年,才有人把整理術這樣的自助圖書和日本國內的清潔傳統相聯系起來,這些圖書號召人們丟棄不需要的東西。
馬特·阿爾特,是一位居住在東京的自由撰稿人,他提醒我們注意,當日本提供了減法的路線圖時,它也給了我們一個雜亂的愿景。不整潔的空間也有魔力。阿爾特造訪吉卜力工作室,他說,那里是一個光榮的爛攤子,滿是木架和厚厚的書,空間的焦點是一張堅固的古董桌子,上面堆滿了參考資料,上面還堆滿了便條、一罐鋼筆、畫筆和油漆,準備捕捉一些新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