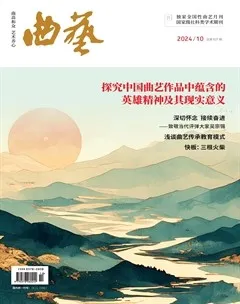黃俊英廣州相聲文本創作特色芻論
作為羊城家喻戶曉的相聲表演藝術家,黃俊英在60年的藝術實踐中,不僅身體力行地推動著廣州相聲(即使用廣州方言說演的相聲曲種)的行業發展、域外傳播及傳人培養,而且還創作表演了一大批獨具特色的作品。這些作品的文本特點鮮明,在形式上側重于“子母哏”,第一人稱運用十分常見;在內容上將趣味性包袱和演員的個人綜合修養相結合,為舞臺表演留下了充分的空間。
一、形式:“子母哏”與第一人稱的常見及假定性運用
作為廣州相聲的代表性人物,黃俊英創演的廣州相聲作品不勝枚舉,其中就包括《廣州話趣》《一對一》《省港澳大比拼》等代表性作品。這些作品最鮮明的特點就是甲、乙二人的論辯式說演,是“子母哏”式相聲作品。黃俊英的相聲往往在闡明語言趣味意理、揭示語言幽默特色的同時,還恰如其分地展示甲、乙二人的本色面貌,充分展示了演員的智趣、風度和風范。

眾所周知,相聲的表現形式可以根據表演的人數分為一個人表演的“單口相聲”,兩個人搭檔演出的“對口相聲”,以及三人及更多人共同表演的“群口相聲”。其中,“對口相聲”的表演往往由被稱作“逗哏”的甲方和被稱作“捧哏”的乙方共同完成,甲乙二人在一捧一逗間共同完成喜劇性的審美創造。“由于節目內容及兩個人說演配合的方法不同,又有一人主說,一人幫腔附和的所謂‘一頭沉’和兩個人互相詰辯,說演分量旗鼓相當的所謂‘子母哏’”①。黃俊英創演的廣州相聲多為“子母哏”的對口相聲,常常將包袱構建于甲乙二人語言機鋒的論辯、詰問之間。在這樣對等的語言論辯和交鋒之中,甲乙二人又以第一人稱的“我”進行藝術創造。而隨著辯論的推進,說演的節奏必然趨快,情節張力隨之產生,“包袱”產生也就有了必然性。可以說,黃俊英的相聲文本中,“子母哏”“第一人稱”這些看似限制的形式,實際上蘊藉著“方塊字”模式的“整齊”笑料,富有形式的美感。這些笑料并不止是對bKgVch591BFBH6IOYfj/lzSqjlIwg31Bg6EDfvn/KV4=說演內容的精彩演繹,更可以將內容和表演者的個人風采相互統一,展示演員的風采、智趣和幽默。
在《一對一》中,我們便不難發現黃俊英在文本創作中對形式美的特殊追求。甲乙二人說演帶有數字“一”的日常用語,隨著說演節奏的加快,兩人在原有說演帶“一”的基礎性規則上,再附帶新的限定性規則——說演的日常用語不僅帶有數字“一”,而且還要帶有否定性的內容(即“無”“不”等字眼)。
甲:再來。
乙:再來就再來。
甲:我一無所獲。
乙:我一無是處。
甲:我一成不變。
乙:我一塵不染。
甲:我一錢不值。
乙:我一竅不通。
甲:我一絲不茍。
乙:我一絲不掛,嗐!②
這樣的語言游戲本身趣味性就極強,增加的限定性條件看似不利于語言論辯的交鋒,但實際上收束了語言的流量,對演員的應變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觀上增加了作品的緊張感,進而讓“包袱”的產生更為迅捷干脆,畢竟,日常用語中同時滿足以上條件的詞匯相對有限。而在上述作品中,甲乙二人使用“我”的第一人稱進行詰辯,在客觀上強化了以上特點的同時,更讓“一絲不掛”在被“抖”出時有了更強的喜劇色彩。毫無疑問,這里的第一人稱作為一種特殊的敘述角度,同“子母哏”一樣,成為了一種形式上的特殊組成。有學者曾指出,“傳統相聲……更多的是采用第三人稱的口吻進行說表敘述。而采用第三人稱的口吻說表較之用第一人稱,要來得自由靈活,更便于天馬行空、信手拈來,有較大的創造和表現時空”③。如侯寶林說演《關公戰秦瓊》時,以敘述者的口吻向觀眾講述故事、加以點評的同時,亦有著跳入說演人物的時空,“學唱”關公、秦瓊唱腔進行代言敘述的特殊處理。作為傳統的“一頭沉”作品,《關公戰秦瓊》在人稱上充分表現了傳統相聲表演中“演員可以靈活地進入劇情和退出劇情作客觀的敘述”④。
黃俊英以第一人稱為主要表演角度之一,與其說是黃俊英大膽的藝術創造,不如說是為“子母哏”的文本結構所限定而產生的“無心插柳柳成蔭”。“一絲不掛”的滑稽就在于黃俊英作為演員在不知不覺之間,落入陷阱,出于想要反駁對方的意圖但最終卻使自己落入滑稽的境地。“包袱”的合理性與喜劇性天然地統一在一起。正如相聲大師侯寶林曾總結的:“‘子母哏’這種形式卻恰恰相反,盡管在爭辯過程里有許多滑稽可笑的事情,演員(即劇中人物)自己可是不知不覺。因為演員已經進入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境界中去了。”⑤
好的“子母哏”作品應該從文學上自覺追求“通情達理”的境界,充分展示出文本作者的智慧和情趣,開掘或拓寬相聲主題的深度或廣度,成為演員進行二度創作時展示風采、風范的堅實依托,就如相聲表演藝術家馬季所歸納總結的那樣,子母哏的相聲在文本意義上講究“貴在通情達理,切忌強詞奪理、故意狡辯”⑥。由此可見,“子母哏”作品應該具有鮮明的“樓上樓”特點,有著“更進一步”的表現力。而《一對一》在這方面也有鮮明的表現。
甲:我一刀兩斷。
乙:我一盅兩件。
甲:有一盅兩件嘅咩?
乙:乜冇呀,朝早飲茶,多數都一盅兩件嘅啦。
甲:一盅兩件唔算成語。
乙:唔算?我……你咩話?
甲:我一刀兩斷。
乙:我一拍兩散。
甲:我一箭雙雕。
乙:我一胎雙胞。
甲:又嚟啰?
乙:乜又嚟啰?
甲:一胎雙胞都得?
乙:得,系咁意思就得啦。
甲:又算你,繼續。
乙:好呀。
甲:我一舉兩得。
乙:我……
甲:我乜呀,冇嘢嚟嘅嘞,一胎雙胞都嚟埋。
乙:我……一國兩制。
甲:咁都得?
乙:好嘢系呀,唔得!一國兩制系鄧伯伯嘅偉大創舉,一國兩制!
甲:算你好嘢。
乙:梗好嘢格。⑦
在這塊活中,說帶“一”的日常用語難度系數有了變化,除了有“一”還要有“二”。這無疑又從另一個角度收束了語言的流量,隨著甲乙的語言交鋒,相關詞匯很快就會用完,所以讓節奏緩下來就成為必然。而黃俊英作為《一對一》的文本作者,深知把握節奏的重要性,如果讓“一盅兩件”和“一胎雙胞”并列出現,不僅會讓作品的“弦”繃得過緊,更會使表演太過油膩,讓人物喪失原本的藝術魅力,最終使作品陷入馬季先生歸納的“強詞奪理、故意狡辯”的尷尬境地。因此,他將正確的“一刀兩斷”“一拍兩散”和“一箭雙雕”穿插在“一盅兩件”和“一胎雙胞”兩個“詭辯”之間,既留出節奏處理的空間,又合乎了傳統相聲中“三番四抖”的藝術規律,還讓人物不會顯得太過偏執、油膩,一舉三得。
人物形象在詞窮時難免“詭辯”的“窘迫”式可愛和之后的機智共同成為《一對一》中乙的人物特點。“一盅兩件”和“一胎雙胞”的前后出現,難免會使觀眾認定乙會在“一”“二”的限定下敗下陣來。這時,乙講出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國兩制”基本國策,既宣傳了我國偉大的政治創舉,又符合了文字游戲中先前制定的規則。“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日常用語與前面“頹勢”相悖反,在強烈的反差中彰顯出了乙的智慧與幽默,充分表現出人物的風范、智趣。可以說,“一國兩制”這個精彩的包袱,將個人風范和作品說演內容、喜劇性包袱有機地統一起來,成為了整個作品最“吸睛”的部分。
“子母哏”是相聲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黃俊英選擇“子母哏”為框架進行相聲創作,自覺或不自覺地觸及到了相聲表演中特殊的“我”—第一人稱,使得形式美更為立體,大大豐富了作品的美感。在闡釋語趣意理的同時,個人的風度得到了充分表現,人物形象更加生動,不失為一種相聲創作意義上的“有意味的形式”。
二、內容:語趣的追求和風采的展示
縱覽黃俊英相聲藝術的創演實踐,在內容的角度來說,筆者認為,外在方面,黃俊英的創作表現出對語趣“包袱”的追求;內在方面,黃俊英極善于發揮自己的各項才能,以充分表現自己的素養、風度,從文本創作的角度為舞臺表演的“二度創作”留出空間。
(一)外在表現:語趣“包袱”的追求
相關研究表明,黃俊英自1978年的《老張師傅》起,基本告別了對已有相聲的“移植”與改編,正式開始了廣州相聲的獨立創演。在40余年的獨立創作中,一以貫之的線索當屬黃俊英在創作時對語趣“包袱”的追求。
“實際上‘包袱’就是相聲里的笑料、噱頭、引人發笑的地方”⑧。從曲藝學意義上說,作為喜劇性笑料而存在的“包袱”并不為相聲所獨有,同樣廣泛存在于數來寶、北京評書、蘇州評彈等曲藝藝術之中,也因此引起了各曲種專家和從業者的積極研究。筆者認為,劉學智、劉學濱二人圍繞韻誦表演的數來寶開展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囊括了曲藝表演中形成“包袱”的四種方式。
①表意的深刻、新穎、突破了一般聽眾對這一事物理解的程度;
②表達內容的順序曲折、巧妙、超出了一般聽眾理解這一事物的思路;
③語言生動、形象、說出了一般聽眾所想象不到的話;
④唱詞格律嚴整,使聽眾感受到節奏的明快和韻味的美,而為之稱快。⑨
在此基礎上,相關曲藝學者曾指出,對許多“包袱”而言,其組成使用的方式方法并不唯一,往往是四種方式的綜合運用。“……其他大部分的‘包袱’,可以說是內容與形式、構思與表達、語言與修辭、句式與韻律等不同的方式與方法共同作用的結果”⑩。就黃俊英廣州相聲的藝術實踐來說,其“包袱”組織的基礎往往是語言的精巧所展現出來的幽默,“語言”與“表意”“表達內容”存在著高度的統一性。在此基礎之上,因為使用廣州方言進行說演,語言的韻律、腔調更為豐富,往往也能表現出“節奏的明快和韻味的美”。可以說,黃俊英組織“包袱”的方式方法十分綜合,表現出強烈的語趣智慧。
黃俊英與楊達這對“夢幻拍檔”為廣州觀眾熟知,他們合作的作品也在當地長久傳播。除了兩人的舞臺風采,筆者認為,“夢幻拍檔”廣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就是兩人創演了相當數量的以廣州方言為主題,將對方言文化的論議融入甲乙二人的語言論辯之中,充分體現廣州方言豐富內容和音韻之美的作品。在表演中,黃俊英的機巧、幽默和楊達的外冷內熱等人物特點在說演中逐步顯現,并因說演的內容和“二度創作”而逐步強化,廣州相聲《廣州話趣》堪稱典型,其中的“趣”既是廣州話作為一種藝術質料的意趣,也是甲乙二人的論辯之趣。
甲:我高洞洞。
乙:我矮D突。
甲:我肥騰騰。
乙:我瘦蜢蜢。
甲:我滑LuLu。
乙:我鞋霎霎。
甲:我嫩蚊蚊。
乙:我老兀兀。
甲:我咸爽爽。
乙:我淡貿貿。
甲:我甜椰椰。
乙:我酸敦敦。
……
甲:我緊擘擘。
乙:我松匹匹。
甲:我生勾勾。
乙:我死咕咕,嗐,揾老襯呀,你先死咕咕。11
《廣州話趣》因為要對廣州方言的文化進行論議,人稱上選擇本色面貌進行論辯,較一般的代言敘述更為生動形象。楊達作為“甲”在此處說演的粵語“ABB”式疊詞時,隨著說演節奏的緊湊,將與“生勾勾”相對應的“死咕咕”留給了作為“乙”的黃俊英,一個簡單的“包袱”就將楊達不動聲色的“蔫壞”表現得淋漓盡致。而得以塑造人物的,卻是廣州方言文化中極為常見但卻缺少舞臺集中呈現的日常生活詞匯。可以說,《廣州話趣》中,人物的趣味性和語言的趣味性有機融合,相輔相成。

除了在《廣州話趣》《省港澳大比拼》《一對一》等“子母哏”作品中追求語趣,黃俊英在創作一些“一頭沉”的作品時也表現出對語趣“包袱”的青睞。以其獨立創作的首部廣州相聲作品《老張師傅》為例,作品在敘述張坤服務人民群眾等事跡的同時,還以第三人稱的視角“跳入跳出”地創作了一些打油詩對這些事跡進行評析,如“條條毛巾送親人,杯杯熱茶暖人心,飯熱菜香情誼厚,工農團結親又親”12“熱情和藹又細致,端菜送茶抹臺椅,洗碗洗碟掃客廳,一掃掃出疊十文紙”13“中國革命捷報頻,遠道重洋留腳印,香肴美點情誼重,世界人民心連心”14。這些打油詩短小精悍,趣味性極強,在評點故事中人物的同時,因為使用廣州方言說演,又表現出極強的韻律感。這些打油詩盡管在今天看來似乎十分粗糙,但《老張師傅》作為黃俊英“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個相聲作品,同時也是黃俊英第一次嘗試進行廣州相聲的獨立創作,已然表現出語趣“包袱”的特殊魅力,具有相當的藝術價值。
(二)內在本質:個人修養的展示
有曲藝學者曾指出,“相聲是一門極具個性化的藝術形式,相聲表演強調的便是演員的個體差異性,是一種絕對彰顯個性化的表演”15。相聲演員在表演中自覺或不自覺所表現的風度、風范往往是相聲作品藝術意蘊的集中體現。作為相聲演員的黃俊英有著極為豐富的藝術經歷,磨練出了綜合多樣的藝術才能。對音樂、戲曲等藝術和對廣州方言的熟稔掌握,使得黃俊英創作的相聲文本,或側重表現相關藝術優長,或充分彰顯他對語言文化的成竹于胸。而相聲演員身份和相聲作者身份的重合,更使得黃俊英在“一度創作”時往往就將舞臺呈現的“二度創作”納入了考慮范疇之內。
考慮到舞臺表演而對文本進行選擇和取舍,以便充分表現演員的個人風范,對黃俊英而言,是一種創作的路徑和策略。早在改編、“移植”已有相聲時,黃俊英就已經具備了這種意識,表現了這種創作傾向。初期選擇對已有相聲進行改編時,黃俊英就在一眾作品中遴選出了《關公戰秦瓊》這一有大量“柳活”的作品。黃俊英早年學習粵劇時專攻武生,對粵劇武生的表演程式爛熟于心,從手眼和身法都可以精準而傳神地表現出戲曲演員的神態精髓。《黃俊英笑話人生》中描述到:“演關公,雖然沒有掛須,但他運用準確的‘造手’,惟妙惟肖地表現出‘開臉關公’那理髯、捋須、撚須等一系列人的神態,功架老到‘大邁’一派大將風范;演方世玉,身手矯健、拳腳利索、風趣滑稽、玩世不恭……”16可以說,這一文本為黃俊英展示其扎實的戲曲功底和摹學自如的神態提供了優質的底本。對該作品進行移植時,或有意或無意以展示自我風范為重心進行文本創作的追求已經在黃俊英心中萌芽。
在黃俊英創作的廣州相聲中,不少作品都有著一兩句的展示“唱”,借以“充分展示演員的演唱技巧”17。借由此,黃俊英的藝術風范得到了進一步彰顯。其中,最能集中表現這點的就是作品《歌迷與迷歌》。作品開篇即是甲乙二人對唱流行歌曲和戲曲選段,集中表現黃俊英在粵劇學習中,因為癡迷于伴奏而自學的音樂知識。
甲:(唱)一葉輕舟去,人隔萬重山。
乙:(唱)烏南飛,烏南返。
甲:(唱)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無需為我假意挽留。
乙:(唱)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會分手。
甲:(唱)難燃死灰,只因雙方都錯,你要怨佢卻是為何?
乙:(唱)你雖不甘心,卻是為何?
甲:(唱)相對凄涼。
乙:(唱)相看神愴。
甲:(唱)樹上的鳥兒成雙對,
乙:(唱)綠水青山帶笑顏。
甲:(唱)新娘蘭花樣,
乙:(唱)花容缺系靚。18
在甲乙二人的集中對唱中,展現出了黃俊英對音樂的準確把握,其內里則是黃俊英作為相聲演員提煉生活碎片,再現各個音樂作品、戲曲選段的音樂才能。換言之,《歌迷與迷歌》的藝術魅力就在于黃俊英與搭檔林運洪通過音樂作品所展示出來的演員風范。
在黃俊英的作品中,多數是前文反復討論的論辯型“子母哏”作品,這類作品往往語趣意味極強,從簡單的游戲規則入手,語言語匯的交鋒展現的則是演員的個人風度。前文所引的廣州相聲《一對一》中就表現出黃俊英的機智,廣州相聲《廣州話趣》的片段則表現出楊達不動聲色的“蔫壞”。這種舞臺形象和本色面目在作品中的高度重合,所表現的既是舞臺形象,又是演員的個人風范。在語言游戲當中,不論是機智,還是“蔫壞”,其背后的共同點,則是智慧。而智慧如何呈現,既是演員在舞臺表演時所需考慮的,同時文本作者也應該考慮,同樣的個人品質如何以不同的面貌進行呈現,關鍵就在于創作時對個人風范的考慮。
從曲藝學的學理意義考察,表現個人風范似乎應該被歸結為曲藝表演的范疇而非文本創作。但是,《關公大戰方世玉》中揮灑自如的武生展示,《歌迷與迷歌》中的“學唱”,《廣州話趣》中對廣州方言的深刻理解……黃俊英用自己的創演成果證明了,從演員自身才能和修養出發進行創作,完全是文本創作的可行方式。可以說,作為文本作者的黃俊英以其創作實踐再次印證了有關學者對曲藝的定義—“曲藝是演員以本色身份采用口頭語言‘說唱’敘述的表演藝術”19。今天的相聲隊伍中,個別相聲演員簡單而又片面地認為好的相聲就一定要“講故事”,將作品的藝術品格完全地交予文本作者的故事構建。殊不知,曲藝的創作表演之中,演員始終以本色身份進行演出,其使用的語言亦不僅有代言敘述和跳出評點,語體上還存在著議論、雜談、抒情。如侯寶林大師創作的《婚姻與迷信》《戲劇與方言》,作為藝術品的審美意蘊無不建立于侯寶林個人風范、風度的展示。可以說,這樣的創作策略在今天仍有著啟示意義。
作為一位相聲藝術家,黃俊英的文本創作獨具風格。他選擇“子母哏”進行第一人稱的論辯,賦予作品獨特的形式美感;他深入了解廣州方言文化,充分利用方言在語言趣味表現上的感染力;他還從自身修養出發進行創作,使得作品更容易表現演員的舞臺風范。筆者以為,這些文本創作上的特色對當代相聲演員最為深刻的啟示應該是:美是多元,作為藝術的相聲也不例外。《古今賢文》中說:“一花獨放不是春,萬紫千紅春滿園”;中國古人亦講究“君子不器”。相聲藝術有著“子母哏”和“一頭沉”兩種不同結構,相聲演員也因不同的籍貫、特點、經歷,賦予相聲不同的藝術美感。而想要更好地傳承包括廣州相聲在內的相聲藝術,離不開廣大相聲工作者們在扎根生活的基礎上,積極繼承相聲的藝術傳統,才能真正做到“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的境界。
注釋:
①吳文科:《中國曲藝通論》,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7頁。
②蔡衍棻:《黃俊英笑話人生》,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9頁。
③吳文科:《姜昆、梁左與“我”》,《曲藝綜論》,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5年,第245-246頁。
④侯寶林口述、劉祖法執筆:《侯寶林談相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頁。
⑤侯寶林口述、劉祖法執筆:《侯寶林談相聲》,第23頁。
⑥馬季:《相聲藝術漫談》,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頁。
⑦蔡衍棻:《黃俊英笑話人生》,第249-250頁。
⑧馬季:《相聲藝術漫談》,第57頁。
⑨劉學智、劉洪濱:《數來寶的藝術技巧》,中國曲藝出版社,1981年,第61頁。
⑩吳文科:《中國曲藝通論》,第252頁。
11蔡衍棻:《黃俊英笑話人生》,第179頁。
12蔡衍棻:《黃俊英笑話人生》,第217頁。
13蔡衍棻:《黃俊英笑話人生》,第218頁。
14蔡衍棻:《黃俊英笑話人生》,第219頁。
15蔣慧明:《相聲表演的藝術風格與流派辯說》,《曲藝學》第1輯,文化藝術出版社,2020年,第259頁。
16蔡衍棻:《黃俊英笑話人生》,第90頁。
17薛寶琨主編:《相聲大詞典》,百花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47頁。
18蔡衍棻著:《黃俊英笑話人生》,第152頁。
19吳文科:《中華曲藝的文化形象:定義·特征·種類·價值》,《中國藝術報》,2017年4月10日,S05版。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