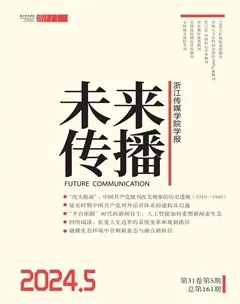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話語體系的建構及啟迪
摘 要:延安時期,為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信息“封鎖”和“污化”傳播,準確闡明黨的方針和政策,展現真實的黨的形象,積極爭取更多的外援,中國共產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對外話語傳播策略。黨對外話語體系的傳播內容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中共不僅通過各種出版物和廣播向國內外宣傳自身的政策和成就,還積極邀請外國記者和學者訪問延安,以其親身經歷,客觀報道延安的真實情況。通過這些對外傳播手段,中共成功地打破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信息戰,贏得了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探究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話語體系,對當下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關鍵詞:延安時期;對外宣傳;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個結合
中圖分類號:G2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6-8418(2024)05-0016-08
加強對外話語體系的建設,有助于提升國際話語權,從而更好地塑造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延安時期,國民黨在新聞領域實行獨裁統治,中共為向國際社會傳遞真實聲音,采取多種策略塑造正面的國際形象。中共通過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樹立了“以人民為中心”“民主自由”“愛國主義”“廉潔奉公”的政黨形象,讓國際社會如實了解其政治本色。本文基于歷史資料,從對外話語體系構建的原因、途徑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并從“兩個結合”的視域,對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話語體系的構建進行探析。這不僅幫助我們了解歷史上中共如何成功應對外部挑戰,還為今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供有益的歷史經驗借鑒,助力新時代中國更好地塑造國際形象,提升國際話語權。
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的緣由
延安時期,國內外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真實信息和相關政策了解十分匱乏。當時,中國共產黨綜合實力較為薄弱,加之國民黨多次對陜甘寧邊區進行封鎖活動,停發軍費,控制經濟發展,造成了共產黨開展正常工作的種種困難。通過建立強有力的對外話語體系,中共不僅可以向外界傳達其真實的政策和理念,還能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和歪曲報道,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中共在延安時期積極開展對外宣傳,利用各種渠道,包括邀請外國記者訪問、出版英文刊物、創辦廣播電臺等,向世界展示其在革命斗爭中的成就和決心。這一系列對外宣傳活動,不僅提升了中共的國際形象,也為其爭取到寶貴的國際援助,助力其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目標。
(一)打破國民黨“封鎖”和“污化”的迫切需要
國民黨為了更有效地控制思想,實施了嚴密的新聞監管措施,尤其針對中共的新聞出版領域,采取了原稿件審核政策,以此來控制共產黨對外宣傳的話語權和國際形象的建構,進而實現其對國內的獨裁統治。1938年7月,國民黨頒布了《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其中明確規定“在中國境內國民政府以外之任何偽組織,國民革命軍以外之任何偽匪軍之言論均為反動言論”[1]。此后,國民黨嚴加監管和取締有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相關組織和機構。1939年6月,國民黨中央政府正式成立了“戰時新聞檢查局”。各省市也相繼成立新聞檢查所,進行圖書雜志和新聞檢查,形成了對新聞領域的網格式嚴密把控。1947年2月28日清晨,國民黨當局出動2000多名軍警,包圍重慶《新華日報社》,迫使該報停刊。這些法令規定了新聞言論及思想需契合國民黨主導意識形態,要求所有新聞出版物需歷經嚴格審查流程,為國民黨在新聞宣傳領域的“封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報紙、廣播等媒體是政黨的“喉舌”,是讓國際社會了解其真實情況和相關政策法規的基本途徑。延安時期,國民黨在新聞領域實行“獨裁統治”,中共在國統區和境外缺乏有效的“發聲筒”,導致國際社會對中共的認識被國民黨錯誤引導,形成了對中共的錯誤認知。國民黨的頑固派報道中將中共稱為“土匪”和“亡命徒”,從而在國際形象塑造中對共產黨進行了“污化”。1941年1月中旬,國民黨顛倒是非,污蔑新四軍“叛變”,稱新四軍為“叛軍”,以此達到反共反民主的目的。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報道頗為“豐富”,所以國際社會大多依賴這種途徑來獲取相關信息,難以深入實地了解中共的真實狀況,只能接受被國民黨“污化”的形象。因此,中共迫切需要加強對外話語體系建設,向世界傳遞真實的共產黨聲音。
(二)積極爭取國際社會救援的迫切需要
在國民黨嚴密的“封鎖”下,中共的力量相對薄弱,迫切需要國外的援助以增強其實力,擴大其影響力。該時期,中共不僅要應對軍事與經濟層面的嚴峻考驗,還需直面國際形象受損的困境,故而贏得國際社會的支援與幫助顯得尤為關鍵。1937年11月29日,朱德總司令向印度國民大會黨領導人尼赫魯致信,詳述八路軍遭遇的重重困難。信中闡述:八路軍在全力投入抗日斗爭的過程中,尤其在醫藥資源與醫療設備方面需求緊迫,急切盼望獲得醫藥補給、外科手術器械及專業醫師的協助。對此,尼赫魯及印度國民大會黨積極響應。1938年9月1日,5名印度醫生攜帶超過60箱藥物及若干醫療設備抵華,投身援華醫療救助活動。這批援助及時緩解了八路軍的迫切需求,同時也加深了中印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情誼。通過主動開展對外宣傳工作,中共有效爭取到了國際社會包括國際紅十字會、美國援華醫療隊等機構在醫療衛生、軍事裝備及經濟資源上的廣泛援助。這些外部援助不僅顯著增強了中共的綜合實力,也為中共在國際舞臺塑造了正面形象,有助于中共贏得更廣泛的認可和支持。
(三)積極爭取實現民族解放的現實考量
日本帝國主義發起的侵華戰爭是對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公然挑釁。在此緊要關頭,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民族尊嚴及推動內部政經發展的迫切需求,鼓舞中國人民奮起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中國共產黨在對敵宣傳戰線上展開了大量攻勢,旨在削弱敵人士氣,從而加速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的進程。1937年10月9日,《解放》雜志刊載了《中國共產黨告日本陸海空士兵書》。文中激昂陳詞:“日本士兵們!起來吧!倒轉槍來吧!打倒壓迫你們的日本軍閥,與中國的工農弟兄們團結起來!”[2]此番呼吁深刻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同時力圖喚醒士兵們的良知,使他們意識到戰爭的非正義性,并促其加入到反抗共同敵人的行列中。抗戰期間,中共在前線采取多種形式,如分發傳單、張掛標語及廣播宣傳等,廣泛向日軍傳播反戰信息,揭露軍國主義的暴行,召喚日本士兵棄戰從善。[3]為進一步擴大反戰宣傳的效應,1941年12月3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增設日語播音的形式,該電臺不僅詳盡揭露了日軍侵華的殘忍行徑,還詳述了中共的政策方針,力勸日本士兵覺醒,反對無謂的戰爭。中共通過這些行之有效的反戰宣傳活動,顯著削弱了侵略者的斗志,破壞了其軍事力量。這些宣傳不僅令眾多日本士兵直面戰爭的慘痛與殘酷,還激發了他們對戰爭本質的反思,萌生厭戰心理,甚至促成部分士兵投誠。反戰宣傳的勝利,為中國的抗日大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援,也為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的最終實現鋪平了道路。
二、延安時期中共對外話語體系傳播策略敘事
為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和“污化”,中共采取了多種對外交流與溝通的方式,使國際社會能夠更加全面、客觀、真實地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這些努力不僅有助于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共的理解和信任,還能有效提升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
(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工作的內部建構
1.“走出去”:設立外宣機構
1936年1月26日,中國共產黨在西北辦事處內建立了外交部。外交部下設交際處,并在交際處下設總務科 、招待科和聯絡科。機構擁有15孔窯洞和35間平房,內部設有禮堂、餐廳和會客廳等設施。[4]從1938年至1941年的三年時間里,一共接待了7000余名中外友人,成為中共中央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1939年1月16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南方局通過各種渠道,積極爭取國際政黨和組織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并向各界人士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這一過程中,南方局不斷壯大黨的隊伍,從而增強了中共的影響力。[5]同時,南方局在香港開設了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與其他海外民主人士、國際組織和海外僑胞保持了密切的聯系和廣泛的接觸。[6]通過這些對外交往活動,中國共產黨成功地打破了國民黨的“封鎖”和“污化”,讓國際社會能夠更加全面、客觀、真實地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方針。這些努力不僅有助于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解和信任,還為中國的抗戰和革命事業贏得了寶貴的國際支持。
2.“走出去”:積極創辦報刊
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著手創辦了多樣化的對外報刊。這些報刊成為向世界展示其在抗日戰爭中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關鍵渠道。通過這些報刊,中共持續向海外傳遞其政策導向與法律法規信息,顯著促進了國際舞臺上中共正面形象的構建。《新中華報》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了廣泛的影響,諸多外國政黨借此報刊深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政策、理念以及革命根據地的真實面貌。該報的新聞報道有力地促成了中國共產黨正面國際形象的建立,促使國際社會對其更為全面且客觀的認知。1941年3月,《中國通訊》于延安問世。這是中共在國內首次發行外文宣傳的雜志,涉及英語、俄語及法語版本。這份雜志的創刊,標志著中共對外宣傳策略的專業化與國際化升級,為國際社會直接洞悉黨的政策立場提供了便捷,加深了外界對中共的信任與擁護。此外,延安時期在海外還發行了一系列報刊,諸如《先鋒報》《全民月刊》及《救國時報》等。它們致力于傳播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對國際戰爭的見解,吸引了眾多國際政黨及外國記者的密切關注。通過這些報刊的廣泛傳播,中國共產黨在海外構建了深遠的影響力,顯著增強了其在國際輿論場的影響力。
3.“走出去”:創建對外廣播
延安新華廣播電臺于1940年底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的一個全新紀元的誕生。在此之前,黨的新聞事業主要依托于報業與通訊社的力量,而無線電廣播技術的接入,則為信息傳播的途徑帶來了顯著的擴展。1941年12月3日,該電臺推出了日語廣播欄目。其內容主要源自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維持每周五一次的頻率,每次持續半小時。這一舉動不僅是我國對外廣播事業的雛形顯現,也彰顯了中共在國際傳播領域中的創新精神與積極作為。1944年9月1日yH6mS5jgD5S97uX+aTWCpEyycz1z0qmTOOzWUaAzkQ4=,新華社英語廣播正式啟動。目標受眾直指海外,側重介紹中共在抗戰中的政策、行動及陜甘寧邊區的發展情況等。[7]通過這些對外廣播的傳播,中共有效打破了信息壁壘,使黨的實際真實情況與抗戰方針得以向國際社會傳播。這樣的國際傳播戰略,不僅助力中共在國際舞臺上塑造了積極的形象,亦增強了其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影響力。
4.“走出去”:參加國際會議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期間,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參與了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憲法制定大會。在參會期間,董必武積極參加小組討論并公開演講、出席新聞記者招待會,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偉大成就。這些舉措深化了國際社會對中共在抗戰期間所扮演角色及其領導能力的認識,從而獲得了高度的贊揚與認可。董必武在該會議上的杰出表現為中共在全球舞臺上贏得了廣泛的尊重,有效提升了中共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從而有效地推動了中共積極、正面的國際形象的建構。參與聯合國憲章制定會議不僅是中共首次踏上國際重大事務的實踐舞臺,也成為展現其政治理念與實踐成果的寶貴契機,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地位,為后續的外交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工作的外部建構
1.將外國記者“請進來”,發揮對外話語體系建構的橋梁作用
1936年7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沖破重重阻礙,歷盡艱難險阻,成功到達延安。他成為首位踏足延安的西方新聞工作者,贏得了共產黨領導人的信任與重視。通過親赴現場的調研與采訪,斯諾獲得了關于中國共產黨及其紅色根據地的第一手資料,并運用新聞報道、出版著作等方式,向外界傳達了關于中共真實面貌的信息。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韋爾斯(Nym Wales)談話,回答她提出的關于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民主與自由等問題的見解。這個談話后轉載于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同年10月25日,毛澤東會見英國記者貝特蘭(James Bertram),并指出:“中國的抗戰不但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中盡了它的偉大責任。”[2](148)1944年6月9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21人到達延安。毛澤東多次會見參觀團并接受采訪,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建立以人民為中心、民主自由的主張。1944年7月至8月,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觀察組成員謝偉思(John Service)通過深入部隊進行細致訪談,對八路軍的軍事素養和作戰能力有了直接的了解,充分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他認為中共軍隊具有強大戰斗力的原因,是中共深知廣大農民的疾苦,本著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進行武裝革命,有了這樣廣大的民眾基礎,共產黨是不會被消滅的。[8]這些外國記者通過實地調研和采訪后,寫下了許多著作,全面、客觀地向國際社會介紹了革命根據地的情況,把延安和敵后根據地的新面貌如實地傳遞給全世界。
2.發動海外華僑的力量,推動對外話語體系的傳播
抗日戰爭時期,海外華人組建了眾多抗日援國組織,并著力創辦華文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在揭發日本軍國主義對華侵略行徑及分裂圖謀上起到了關鍵作用。通過豐富詳盡的報道與深刻透徹的剖析,它們成功吸引了國際社會的注意,贏得了國際團體及全球民眾的同情與支持。各國的華僑救亡團體紛紛組織愛國人士到陜甘寧邊區訪問,親身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斗爭和邊區建設情況。其中,陳嘉庚作為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是第一個將東南亞華僑利益與祖國命運緊密結合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來到延安進行參觀訪問,親眼目睹了邊區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回到新加坡后,陳嘉庚在南橋籌賑組織召開的萬人歡迎會上,激動地向華僑同胞們匯報了他在延安的所見所聞。他描述道:“延安城內頗繁榮,民眾安居樂業,衣被亦頗整潔,邊區民眾產業仍屬私有,三年新墾荒地三百余萬畝。”[4](133)陳嘉庚的演講不僅生動地展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邊區建設成就,還通過其個人的聲望和影響力,使更多的海外華僑了解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斗爭。陳嘉庚的演說在海外華人圈中引發了深刻的回響,他借助親身經歷與真摯情愫的傳達,增強了海外華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與擁護。在此積極倡導之下,海外華人愈發熱忱地參與到援助抗戰的行動中,為中華民族的抗戰偉業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這種超越國界的信息傳播與動員戰略,不僅鞏固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定位,也促使眾多國家及民眾對中國抗戰的整體局勢形成了更為客觀、真實的理解。來自海外華人的援助及國際社會的緊密關注,為中國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了穩固的基礎,并在構建中國共產黨正面的國際形象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 、“兩個結合”視域下的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探析
“兩個結合”為我們全面、系統地認識延安時期黨的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延安時期,中共對外話語體系的傳播內容樹立了“以人民為中心”“民主自由”“愛國主義”“廉潔奉公”的政黨形象,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中的“人民性”
馬克思的“人民性”理論為延安時期中共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提供了深厚的理論源泉。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書中指出:“無產階級革命不得不打破舊的國家機器,要獲得農民的支持,才能形成一種合力。若沒有這種合力,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立都成為沉痛悲劇。”[9]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也強調:“分配問題的根源在于生產力,而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力量就是人的因素;分配的真正目的是使人民能夠占有一定社會資料。”[10]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其博大精深的理論,為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提供了科學依據。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層面堅守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實踐中不斷融入中國具體國情,開拓出一條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革命路徑。在革命的道路上,中共逐漸探索出,只有團結廣大農民、工人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美軍觀察團成員謝偉思基于對延安的親歷考察與訪談,指出:“共產黨人堅持認為,要想取得抗戰的勝利,就需要充分動員人民,這就要求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給予他們政治權利,并進行有利于人民群眾的經濟、政策改版。”在他看來,中共軍隊之所以能展現出強大的戰斗能力,原因在于中共深切理解農民的困苦,能夠從農民的視角出發,用貼近他們生活的語言激勵他們武裝起來,共同對抗剝削與侵略。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征途中不斷汲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滋養,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本國國情的深度融合,堅定不移地踐行人民至上的原則。通過凝聚廣大民眾的力量,中共在國內贏得堅實的基礎,并經由外國友人及媒體的國際傳播渠道,樹立了一個以民為本的政黨形象。這一國際傳播策略不僅增強了中共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重,也為其引來更多海外援助與支持。這些廣泛的國際援助不僅在物質層面助力了中國對抗日戰爭的投入,同時在精神領域及國際輿論環境中,為中國共產黨博得了更廣泛的理解與認同。歷經持續的理論探索與實踐驗證,中共在延安時期成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構建出一套系統化的對外話語體系。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中的“愛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注重在革命實踐中傳承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的給養。中國共產黨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中構建的“愛國主義”形象,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忠君報國”“愛國之心”“報國之志”等觀念緊密相聯,這些理念為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的形成提供了養分。歷史上,不乏借由詩詞抒發個人報國情懷與堅定信念的英才。唐代詩人岑參在其作品《送人赴安西》中的“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彰顯了淡泊個人名利,將國家與民眾利益置于首位的精神境界。清朝徐錫麟的《出塞》云:“只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尸還。”該詩體現了作者甘愿為國捐軀,視死如歸的壯志豪情,展現了將戰場犧牲視為最高榮譽的價值觀,激勵后續眾多愛國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過零丁洋》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傳世佳句,展現了其面對生死考驗,仍堅守忠誠,誓死捍衛國家的崇高精神。此等氣節不僅貫穿其一生,亦成為后世無數仁人志士的精神燈塔。回溯至延安時期,對外宣傳工作是中共強化國際形象構建的關鍵舉措,旨在通過多元渠道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立體、客觀的中共形象,對外宣傳包括自主發聲和借助海外新聞媒體發聲。延安時期,中共邀請了許多國際組織、外國記者、海外僑胞等來延安實地調研、采訪,借助他們的力量將中共的真實聲音傳播給國際社會。斯諾通過長時間在延安的生活和采訪,將所見所聞陸續寫出了《復始之旅》《紅星照耀中國》《續西行漫記》等世界名著,被譽為研究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典的百科全書”。他的書正面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積極作用。中共還安排外國記者赴前線考察,通過實地調研和采訪,發表了許多宣傳中共抗戰的新聞報道、通訊。如《中共領導下的軍隊是強大的》《中國解放區軍民合作目擊記》等,客觀報道了中共的抗戰、團結、民主理念,彰顯了延安時期中共抗戰愛國的形象,充分展示了中共在戰爭中的正面作用。
(三)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與“兩個結合”
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中的“民主自由”政黨形象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馬克思指出:“只有民主制的國家制度才能更好地造福人類,服務人民。民主制形成的前提和基礎是社會個體成為自由的主體,當然,使每個個體都能成為自由的主體,即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11]在通過開展對外宣傳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原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倡導民主自由,不斷解決中國革命事業中面臨的實際問題。毛澤東指出:“對待來賓的宣傳工作,要放開他們到處跑,凡來邊區的客人,不管其政治態度怎樣,什么地方都讓他們看,包括監獄,客人自由行動,這樣做的效果很好。”[4](129)外國友人在訪問延安和邊區返回后,給予了熱情的稱贊。遠東權威學者畢爾氏說:“現在中國有兩個中心,一個封建中心在重慶,一個民主中心在延安。”
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中的“廉潔奉公”的政黨形象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十分注重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并具體運用到對外宣傳及國際形象建構中。有的外賓說:“邊區政府繼承了‘成由勤儉破由奢’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辦事雷厲風行,惜時如金,已成為邊區黨政、工作人員的風尚。”[12]外國友人通過自己的報道和著作將客觀真實的政黨形象展現給國際社會,讓國際社會真實地了解我黨的相關政策和舉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舜帝以身作則并教育后人要“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晏嬰把廉潔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并指出“廉者,政之本也”,管仲把廉與德作為支撐國家興盛的支柱,并指出“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馬克思、恩格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就無產階級政黨和政權如何防治貪污腐化問題進行了深度思考,深刻地揭示了腐敗產生的根源并為建設廉潔政治提供了意蘊深刻的廉潔文化理論指導和對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高度契合,加之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中不斷地推陳出新,從而形成了對外話語體系傳播內容中的“廉潔奉公”的政黨形象。
四、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話語體系建構的當代啟迪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話語體系的建構,對我們今天立足于新時代,傳播好中國聲音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作用。如今,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外宣人才培養體系,培養專業性人才,同時積極開展自主對外宣傳,發揮好“海外媒介”的橋梁作用,是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的重要途徑。
(一)培養專業人才,提高對外宣傳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建強適應新時代國際傳播需要的專門人才隊伍。”[13]這為我們在新時代進一步加強對外宣傳工作指明了方向。為此,著力打造新時代宣傳思想工作創新研討班、宣傳思想干部增強“四力”培訓班、文藝業務骨干培訓班等品牌培訓項目,進一步提升宣傳工作隊伍的理論水平和業務能力。這些培訓項目不僅注重理論學習,還強調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使宣傳人員能夠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游刃有余。同時,加強人才工作制度建設,開展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選拔培養工作,采取培訓研討、考察采風、實踐鍛煉、課題資助等多種方式,對入選人才予以重點培養和資助。[2](770)通過系統的培訓和實踐鍛煉,這些青年英才將成為新時代對外宣傳工作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專業素養和實踐經驗,將大幅度提升我國對外宣傳的水平和效果。總結延安時期對外宣傳工作的歷史經驗教訓,我們立足于新時代,只有擁有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化對外宣傳隊伍,才能在國際輿論場中占據有利地位,有效傳播中國聲音,提升國際話語權,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
(二)積極開展自主對外宣傳,引導正面輿論
對于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國民黨控制了大部分的傳媒資源和發聲平臺,導致中國共產黨在國際舞臺上的形象受到嚴重扭曲。面對此番困境,中國共產黨通過建立對外廣播、設立外宣機構、參加國際會議、發行《先鋒報》《華商報》《救國時報》對外宣傳報刊等渠道,積極開拓自主對外宣傳渠道,向世界傳播其真實聲音和理念,從而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和支持。
習近平在多個場合都強調了國際傳播的重要性和話語權的重要性。他指出:“傳播力決定影響力,話語權決定主動權。”習近平主持學習時,強調要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發揮新興媒體的作用,以增強中國對外話語的創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14]這些理論觀點與實踐舉措,繼承和發展了延安時期對外宣傳的精神和經驗,為當代中國在全球舞臺的形象構建賦予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與實踐導向。習近平的著作《談治國理政》和《擺脫貧困》,在中文原著的基礎上,被廣泛譯成多種語言并向全球發行,深刻展現了中國在國家治理與脫貧領域的政策導向與實踐成果。這一全球化的傳播策略不僅促進了國際社會對中國內外政策的深入理解和認識,同時也為世界各國借鑒中國經驗提供了實質性的參考與啟示。通過自主開展的對外傳播工作,不僅傳遞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治國理念與科技發展的新成就,還為國際社會搭建了一座客觀、全面洞察中國的橋梁,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了重要力量。
(三)發揮好“海外媒介”的橋梁作用
在對外宣傳工作中,善于利用“海外媒介”的力量進行宣傳和報道,是獲得國際社會深入了解與認同、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的關鍵。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就意識到這一點,積極通過外國記者的新聞報道和著作向國際社會傳遞真實的共產黨的方針和政策,為塑造中國共產黨“廉潔奉公”“愛國主義”“自由民主”“以人民為中心”的國際形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近些年來,我國在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都會舉行“總理答記者”問環節。這種面向全球的新聞發布會,正是我們利用“海外媒介”發聲的一個很好的機會。以此方式,國際社會能更真切、全面地洞悉中國社會的發展脈絡、政策導向及政府立場。這種高透明度的溝通模式有利于消除部分國際社會的誤解與偏頗看法,增強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信譽與形象建構。此外,應充分利用海外華人媒體與團體的力量。他們作為黨和國家對外傳播戰略的寶貴資源,利用地理優勢,能夠代表中國發聲,促進中外的互動,加深雙方的認知與信賴。通過他們的努力,中國的聲音能夠更加深入和廣泛地傳播到世界各地,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提供一個多元化、真實的視角。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話語體系的建構,對我們今天立足于新時代,傳播好中國聲音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作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我們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外宣人才培養體系,培養一批政治堅定、業務精湛、懂外語、熟悉國際傳播規律的專業性人才。經過系統化的教育培訓及實際操作錘煉,這批專業人士將成長為代表新時代的對外傳播主力軍,為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發聲注入強勁動力。此外,我們應積極主動地開展對外宣傳活動,誠摯邀請海外媒體訪問中國進行實地采訪與報道,以傳遞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意圖與政策導向。通過這些舉措,我們不僅向國際社會展現了中國的真實面貌,還展露了國家的發展成就與未來藍圖,為構lF0z+yDTIFX80rOXNl39ntsQTtoXPgxG9ubZ8GD/5rs=建和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奠定了堅實基礎。回顧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仍能通過高效的對外宣傳工作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與支持,這對我們在新時代傳播好中國聲音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啟示。唯有不斷創新對外傳播的策略與方法,培育高水平的國際傳播人才,方能更有效地向國際社會展現中國的真實形象,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參考文獻:
[1]劉哲民.近現代出版新聞法規匯編[M].上海: 學林出版社,1992:247.
[2]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簡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21.
[3]趙新利.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對日宣傳再研究——基于日本館藏檔案的考察[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7): 96-110.
[4]雷云峰.陜甘寧邊區史[M].西安: 西安地圖出版社,1993:128.
[5]涂凌波,張天放.延安時期中共與外國記者交往活動的階段、機制與觀念研究 [J].新聞與傳播研究,2023(12): 104-120.
[6]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M].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484.
[7]劉曉偉.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新聞輿論引導力建構[J].編輯之友,2019(5): 93-99.
[8]柳斌杰.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成功經驗 [J].新聞春秋,2021(5): 3-8.
[9]楊須愛. 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 [J].學術界, 2020(12): 112-121.
[10]寇清杰,肖影慧.馬克思對拉薩爾主義分配正義觀的批判與超越——以《哥達綱領批判》為文本的政治哲學分析 [J].思想戰線, 2024(1): 98-108.
[11] 李龍,凌彥君.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源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解讀 [J]. 理論月刊, 2015(3): 27-32.
[12]田建偉.延安時期陳云黨風廉政建設思想述論[J].思想教育研究, 2016 (12): 26-29.
[13]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 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N].人民日報,2021-6-2(01).
[14]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著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N].人民日報,2014-1-1(01).
[責任編輯:高辛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