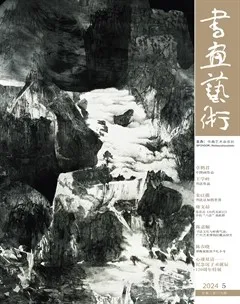書法認知的差異
一
有一種癖好就是把今人的書法作品與古人的書法比。似乎對此有興致的人多起來了。活人與死人比,決出高下的意見當然是活著的人才能表達的,古人無語。清人張問陶有一句詩說得很形象:“模宋規(guī)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今人還是做點實在的藝文之事,不必圖須臾之玩、耳目之娛。古人蓋棺論定,就是這個樣子——今人往往是自說自話,說得不同凡響,引起群體注意。為了熱鬧一下子,風散云移,毫無審美意義上的收獲。許多本該是書法藝術(shù)范疇內(nèi)的學理性論說、分析,后來都如同俗世之賣嘴皮子。清人金圣嘆曾批評今人不曉古人書中的種種奇妙,“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僅僅粗記前后事跡,是否成敗,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談快笑之旗鼓。嗚呼!”真是嗚呼!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有的見解是審美范疇的,有的則全然不是,只是日常生活中的認知。既然評說書法,也就要從審美上來說道才不離轍軌,而不是遠離審美而漫說漫議。誰都可以來論說,還是具有一些書法的學理性會更謹重。
宋人朱熹曾認為:“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清人吳喬認為:“蘇、黃以詩為戲,壞事不小。”這里所表達的是對文藝的某一些要求,就是著名文人也需要遵守——再有才華、靈性的人,也要循藝文之理路旨要,認真為作,倘若圖一時之快意,反藝文之大旨,那就非雅士之所宜了。每個人都要面對不斷在發(fā)生變化的文藝現(xiàn)象,不可能以不變來應(yīng)萬變,以自己固有的經(jīng)驗來套變化著的文藝。藝術(shù)經(jīng)驗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個人的精神財富,是長期積累起來的。倚仗藝術(shù)經(jīng)驗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也沒有什么錯舛。時日長了,經(jīng)驗就有了一定的局限,固化了、結(jié)殼了,永遠都是這么一種衡量、認定。同時對一些新的藝術(shù)現(xiàn)象缺乏感受、研究,卻每每以此去衡量、認定,也就給這些現(xiàn)象貼這個標簽、那個標簽,或者以“戲說”為快意,并沒有深入到作品內(nèi)部。這很像閱讀一部古典文獻,每一個字都認得,可以通讀,好像都讀過去了,卻對這么多字組合起來的意思全然不懂,不知其意為何,更無從感受到它的延伸義。書法作品也如此,拿今人和古人比,這種比就是比看得到的,而那些深層的看不到的,又如何比。書法經(jīng)典適用于任何一個時代,也更適宜后人用來學習,而不是相比。不比會比執(zhí)意要比更有益于我們的認知的延展。
對待古人書法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如清人魏禧之言:“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為優(yōu)孟衣冠。”這一弊端在于學習者持守不化,故無生機。雖然有對古法執(zhí)著的心境,卻不能活學,以至于只能得到皮相而不得深入。但這一類學習者的優(yōu)點在于對古法存有敬畏,誠心以學,只是學無當難深入,卻可以扭轉(zhuǎn)。另一類是“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其弊為野戰(zhàn)無紀之師,動而取敗。”這類人比上一類更危險,高標自許無視古法,以為師心便可。在無古法引導時,任性自為,即便不舍晝夜,也與審美目標相距甚遠。二者相比,泥古只是方法問題,師心卻是方向問題。那種無視古人,以為今人可以不倚仗古人而自任,只能是自斷生路。魏禧所言,揭示了一個道理,古人之所作,后人之所學。學有不足,不學更見舛誤。在古人作品面前,后人所知者多少,是否就可以輕率相比?這是可以追問的一個問題。
今人與古人不在同一個歷史坐標上,文化、社會背景相異。古人書法也不是一個固定體,具體到一個朝代一個書法家,差異不知多少。每個時段都有自己的特色,特色不是比高下的,是相互映襯而獨異的。如此才能稱得上妙賞。清人哈斯寶在《﹤新譯紅樓夢﹥回批》中分析道:“寫賈政活龍活現(xiàn)寫出一個氣急敗壞的父親。寫王夫人,逼真勾畫出一個疼子心切的母親。尤其是老夫人,寫得同老婆子毫無二致。”哈斯寶善于察覺其中不同的巧妙,卻不會比較誰高誰下。專注于對過往作品的解讀,逐漸深入,獲得啟迪,卻不必熱衷古今比、見高下。古人之作已為時間認定了,今人的審美能力只有提高,方能有更美好的期待。清人張竹坡云:“其各盡人情,莫不各得天道。”不同的書法家之情,和他們各自以為的天道,反而是我們需要探究的,在這方面役心勞神追大者遠者,方是正途。
二
舊日以信函形式作遠距離交流,以解空間遙遠不能面談之憾,便有“如面”“如晤”之語。有的文士在近距離也習慣以信函交流,以為信函較之言說更能固定此時的見解與態(tài)度。這也使舊日文士的信函書寫最勤,量也巨大。今人已疏離了信函的書寫,不能體驗寫信之趣味。和古代書法家相似的是臨摹、創(chuàng)作,與之不似的就是寫信這一形式已經(jīng)舍棄。
舊日的信函本私密,卻讓后人整理后出版了,進入公眾的視野,譬如《胡適書信集》《胡風家書》《蕭乾家書》《傅雷家書》都為人所閱讀。寫信的人和收信的人都故去,甚至信中所涉及的人事瓜葛也讓今人陌生,權(quán)當文學作品看待,設(shè)想當時的文化背景、個人交誼——作為兩個人探討的問題,當時以信函形式出現(xiàn),就是強調(diào)有限,不愿聲張。他們沒想到日后會公之于世,有錢就可以買一本來看,窺探里邊的隱秘。當時,寫信人在信函中使性子,自任不羈,甚至發(fā)表一些不合時宜的論斷,也沒有什么不可,畢竟不流通于大眾領(lǐng)域——如果連寫信也要小心翼翼顧左右而下筆,那身為文士真是毫無樂趣了。這也使信函最真實地展示了一個人此時的認知,哪怕是偏頗、不成熟的。只是寫信人不會想到,這些信函如今拿來出版、展覽、拍賣——尤其是拍賣,看寫信者的聲名、地位,價高價低無一定之規(guī),拍賣者覺得信函與商品無異。
信函是私人文本,初始是秘不示眾的,有明確的目的性,給張三,或者給李四,便自然寫去。信函價值有大有小,甚至全無價值,連書寫水平也很低下。它作為人之間相互連綴的一個形式,就是在信函中說人、說事。現(xiàn)在讀前人一些信函,真沒有什么微言大義,就是通消息而已。算起來它是文學的一部分,也是書法的一部分。斗轉(zhuǎn)星移,信函中的書法價值提高了,成了后人效仿的字帖。很顯然,時日過了,信函的延異性出現(xiàn)了——談不上隱秘了,由原先一個人閱讀到眾人閱讀。信函的內(nèi)容也因為背景遷變起了歧義。而信息過時,傳遞價值早已消失。這也使人閱讀時心思淡然,畢竟不是寫給自己的,干我何事,反而想著如何高價售出,或者用信函去交換其他的藏品。當信函的經(jīng)濟價值成為關(guān)注的要點,哪位舊日文士的信函高價成交,就會成為眾人的話題。
舊日文士的信函展覽讓人感受到時日流逝中的真實,信函是真實的,少有造作與粉飾。而今舉辦一個信函主題展,不善寫信的也要裝成善寫,仿舊時格式,豎寫;以文言文行之,意在古色古香。信函是最沒有必要刻意的——前人的信函表達了這一點,筆跡上涂抹畫圖全不在乎,只是順手為之。如果一個人寫信都用意、用力,想把信寫好,參加展覽,讓人看了真覺得是一封好信,那么這封信就難以避免雕琢。雕琢最是信函大病,也是需要長久書寫方可適于這類文體,得信函寫作之旨。朱熹曾批評黃庭堅:“后來如黃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沒有書法技能的人可能把信函寫得自然輕松——信函不是創(chuàng)作出來的,不必規(guī)劃、設(shè)計形式,就是寫而已。信函書寫也不必與人交流,就是寫私有之事,自個寫去。一幅書法作品可以進入品評等第,斷其一等二等,但信函不可評說,它是因為個人需要而完成的,給他需要的那個人看的。后人把它放在公共的視野下,讓毫不相干的人都來閱讀,已不把它當信函看待。
歐陽修稱贊魏晉人的信函:“初非用意,而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tài)橫生,披卷發(fā)函,爛然在目。”如此可視為寫信的最高境界,就是下筆無礙,行筆工拙不計,只是寫寫寫。有的字尚可讀懂,有的字只能依整句意思而猜度。書寫者寫了也不想修改,以為無甚不妥。除了書寫任意之外,每個人都顯示了在信函表現(xiàn)上的自家特色——傅雷長于說理議論;魯迅多雜文色調(diào),只是鋒芒稍減;沈從文把游記、情書結(jié)合起來作信函,使人讀之覺湘行快意方有如此美文。當然,有一些只是說事、議事,說完了事,簡約寥寥無多字,以此符合信函最基本的義務(wù)。的確,在信函中,或妍或丑,自寫來便不枉信函之稱。
信函寫作使人藝文兼有,否則就得請人代筆。后人抄古人詩文慣了,又無信函往來,越發(fā)不知信函之用,不能于信函中敘事、說理、抒情。生存的節(jié)奏使信函表達難以延續(xù),使寫信人和收信人隔空期待的心情,漸漸烏有。
三
宋代文士、平民學趙孟頫書法者為數(shù)甚多。趙書圓潤甜美,清神豐筋,除了具有很高的審美屬性之外,其親民的魅力也過于其他書家的作品。趙書脫胎于二王書風,其繼承合于人們所期待的正統(tǒng)轍軌。行于此路,自然是宜人宜己,生前就享受著受擁戴的快樂。一個人沿某條藝術(shù)路上行,也許是偶然的,持之久了,成了必然,成了自己的外在形象。現(xiàn)在提起趙孟頫,又幾人知其相貌,想到的反而是他筆下的書法作品的形態(tài)。
與趙孟頫同時代的楊維楨,在書法上走另一路徑。今日溯其源,未必周全,取章草、今草,又有畫意。露鋒尖峭,意念蕩漾,使變化無端,莫有常態(tài)。一幅趙書,無論筆法、結(jié)構(gòu)、速度,都是可以預(yù)期的,給了欣賞者一些欣賞的自信和快意。一幅楊書則使之捉摸無定,筆調(diào)延伸中涌出許多不確定的離奇,學不易,欣賞不易。若細數(shù)學趙學楊之人,顯然是趙眾楊寡。
但這兩個人心氣的特點都是一樣的,就是依己審美寫去,至于他人是之非之,并不關(guān)切。像楊維楨如此瘦硬奇矯脾性,自己寫,與卿何干。趙書風彌漫一朝,于他是不產(chǎn)生作用的——在他筆下無一與趙書相近,他的相遠是他的情性造成的,如此真是強大的自守之功。書寫唯適性方能逍遙自在,可以不計工拙,也可以遠離實用,只是2c32bdaa2fe59dfc38b89517ffca376f7facf51cc4df1e09c1d7e90036f0ee9e抒個人之意氣。楊維楨有詩:“按劍或為龍鬼奪,擲手自戲仙人杯。”“醒來不計墨淋漓,塵世隨風散珠玉。”人如此,書如此。
一幅書法作品進入欣賞場域,愛評說者蜂起,貶多贊少。書法家自然會留意這樣的現(xiàn)象——起始可能焦慮,而后安之若素,以為不干他人之事,任其評說,無易轍之心思7f31824e9264ba400706655039f0608fb8b83c0f5c26e40fd56790a8e204607c。書寫畢竟是私有之事,不必受外界擾攘。即便說對了,合于書寫之公共的道理,卻未必合于自己的書寫之道——這也是許多書者都采取無視態(tài)度的緣由。所謂的雅俗、美丑,各有各的理解,循古法者循古法,追時興者追時興。廟堂氣有之,書卷氣有之,江湖氣亦有之,人之所好漸行漸遠,相安相容。盡管有的書者在中心,有的在邊緣,人數(shù)多寡不一,卻不能說誰之高下、誰之主從。你之所是,他人所非;你之所非,他人所是,各持美感而創(chuàng)作,自適即可。淮南王劉安曾云:“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世如此,人亦如此,況藝文如此個人作為,還是與自個周旋為好。
正常反常,向雅向俗,個人之所求盡見差異。如楊維楨那種書寫表現(xiàn)手法,在元代就是一種反常。反常就是不合時流。但楊維楨不以為不妥,也就一以貫之。庾翼認為王羲之書為“野鶩”,就是由審美差異引發(fā)的沖突。沖突的結(jié)果如果不是雙方取得共識,其結(jié)果是各自為之。譬如黃庭堅學詩,他是很想生新出新的,為了這一大旨,即便句法、音節(jié)、聲律上出現(xiàn)不少問題,也均屬小疵,不足為道,實現(xiàn)大旨是其首要。黃庭堅有自知之明,知詩中之不足,他說過:“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其書風也大抵如此,長槍大刀斫陣,只是橫行,充塞空間,何曾斂約。黃庭堅詩書都有縱橫不羈之氣,氣之到處突兀奇險,往往用意用力過之。如此不足,卻也可以自成一格。
每個人自知其所處地位、身份,于藝文方向也就有所熟悉、陌生,各擇其熟悉者為之,久而久之便成其特色。如此則有自己比較固定的書寫空間,專注一隅,播弄錦繡。清人袁枚曾分析道:“廟堂宜沈、宋,風月宜王、孟,登臨宜李、杜,言情宜溫、李,屬辭比事宜元、白,巖棲谷隱宜陶、韋,詠古器物宜昌黎。”為何有的宜于廟堂之詩,有的則宜于風月吟詠?只能從一個人的經(jīng)歷、審美專注來探求,其中甚至就沒有什么道理可言,只能說就是這樣。既然不同的審美宜于此、宜于彼,那么各自做去,做好做絕,不論他人評說,不與之交流,如此更見個性。
明人王文祿認為“不奇則同,同則腐,不惟不愛,且生厭斁,理因之蕪,是以古作各不同。”相比于趙孟頫之正,晚于趙的楊維楨選擇了奇,也選擇了孤高自適,以另一種創(chuàng)造性探索前行,以個人的內(nèi)在性強大揭示、發(fā)現(xiàn)其存在的價值——有時候個性美的存在,不是要讓人洞見,而是要讓人未見。
四
讀《水滸》《西游》這類小說,少年時覺得暢快明了,中年后就覺得太過直白。后來人不少喜愛閱讀意識流作家的文字,有意去研究潛沉于文字深處的含意或隱喻,或無意地進入文字中的迷亂、錯位、郁而不明氛圍,覺得閱讀遠遠不是認字那般簡單。如伍爾夫、喬伊斯、普魯斯特等作家,都不是僅僅讓人從文字中就可以解讀的,文字的深層義充滿了意義指向、情感指向,總是在內(nèi)部保持最飽滿最富啟發(fā)性的狀態(tài),需要閱讀者有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掘本領(lǐng),才能有所獲得。這個獲得未必要與作者所表達得一致,也可能是歧義,歧義的欣賞也可以充滿美感。每個人理解不同,審美差異是分明的,最終各是所是,非所非,差異形成多元之美,也就使一個作家的表現(xiàn)不止于一種認知。寫這一類文字的作家的敏感度總是超越一般人,甚至他們的精神生活就生活在現(xiàn)實之外。
如果一件作品只是讓人看到公共認同的技能,寫得合于轍軌趨于范式,這只能說具備了寫作的本領(lǐng),泯然于一般的寫作手法。那種只把外表寫出來的作品,顯然不能揭示一些有價值的審美體驗,不能給閱讀者更深層的意味的引導。這樣,作品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只是合寫作規(guī)矩,徒為耳目之娛樂。譬如居廟堂之高的一些公卿大夫筆下,只追辭藻繁縟華麗,以至落入俗格。不是敘酣宴、述思榮,就是狎池苑、憐風月,長于美頌粉飾。盡管這些作品也是從其生活經(jīng)歷產(chǎn)生,但提供給閱讀者的都太直白,不必深味。李商隱的詩使人有不斷探魅的積極性,詩中意象不是直白端出,而是恍兮惚兮、隱顯不一的,不可能一眼洞穿并下結(jié)論。“無端”的幻象、夢思、超驗,詩行所寄寓的很大的跳躍性,使人依常規(guī)欣賞難以抵達。這也讓人感嘆看得懂和看不懂的作品不止于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guān)系,而是全然不在一個空間上。如伍爾夫的寫法,總是顯得那么復雜,文中那么多的沖突,那么多的變數(shù),那么多的創(chuàng)傷,何時可以廓清。她自己解不開,走向了那條后來很有名的蘇塞克斯的河流懷抱。后人繼續(xù)閱讀,繼續(xù)探討那些不確定的可能性,認知殊異,以至沒完沒了。
書法作品的表現(xiàn)方式當然與文學作品不同。從外表看,非點即線,點是線的縮短,線是點的延展。如果一本法帖被認可,那么里邊的技能都是可以學習重視的,使人欣賞時得知所學何處,是為何體。如果忠實于某一家學習、重現(xiàn),使人欣賞時就直接明了其所祖為何,因為相似、逼真說明了一切。有些書法作品是易懂的,平面展開,筆畫得宜、結(jié)構(gòu)協(xié)調(diào)、布局合理,可測可量,不悖法理。由于太合規(guī)范了,便無疑問,很宜于俗常生活中運用,實用價值也高——所謂的好看就是這樣,不像猜謎那般思索,一見即知。顏、柳、歐三體楷書為后人學書之首選,其美感有普適性,無欣賞難度,字面意思已表達完足。書法教育就是從這些普適性書法開始的,美感的同時也具備了安全感,即無舛誤,不入歧途。這也是《多寶塔》《玄秘塔》《九成宮》老少皆知的緣由。
如果以顏真卿《祭侄稿》來引導,就會生出許多矛盾,譬如看不懂、看不慣、不好看,諸多疑惑,紙面上潦潦草草、涂涂抹抹是什么意思?整體的倉促匆忙連清晰都做不到為何閱讀?這些對一些人是疑團,對另一些人則是大美,談他的心靈創(chuàng)傷、意識控制,再談格調(diào)、境界。說起來都很虛幻很難懂,無普遍性,甚至讓人覺得荒唐。
一些書法家從舊轍中開新境,探幽訪秘,筆下不復尋常書寫路徑,也就是不說透多含斂。如朱耷、弘一、謝無量之輩,書法話語中潛能深厚,需要捕捉、揭示。由于與平素欣賞路徑錯位,超出了通常的欣賞樊籬,再也不可能待從頭收拾舊山河那般輕易了。如謝無量書法所含有的意、趣、味,純乎個體而無可替代,它不直接,也不接地氣,公共形象并不佳,甚至以為近孩童之作。如果一個欣賞者自我設(shè)限,那就難以欣賞到更多樣的創(chuàng)作風格,也限制了個人的審視能力,從而湮沒個體的審美特征。一個需要重申的常識是,許多的優(yōu)秀作品是和我們的欣賞觀念、習慣、方法、方式相悖的,沒有那么多共識存在,每個人只能在自覺學習、研究的過程中,各說各話,建立起個體本位的認知。
五
當今的諜戰(zhàn)片總是會吸引一些試圖在屏幕上探魅的人,隨時發(fā)現(xiàn)其細節(jié)上的破綻,或者另辟一條思考的路徑。這類片子更能夠啟人參與,扣人心弦,跟著抽絲剝繭深入。如果上溯到20世紀50至70年代,那時所謂的反特片達不到當今的審美效果,人物一出場,觀者便大抵定其身份,由眉目神情、言行舉止知悉人物身份,不外二類,好人,或者壞人。臉譜化使審美判斷簡單,整個過程沒有太曲折復雜的遮掩,最后結(jié)局與觀者判斷相似,也就毫無懸念——簡單有簡單的效果。
越往后的諜戰(zhàn)片改變了這種做法。設(shè)置許多頭緒,許多包袱,甚至可以說多而雜亂。觀者臨到終結(jié)還云里霧里,就需要再觀賞。編者和觀者不在同一個脈絡(luò)走向上,也就無法看懂其中的玄機了,看不懂也是對作品的一種認識。如果用二分法,一種是一看就懂,合于自己的欣賞經(jīng)驗和路徑,解讀起來清暢順利。另一種是看不懂,他人的創(chuàng)作和自己的欣賞不在同一范疇內(nèi),于是無從欣賞,或者以舊框架套新形式,使欣賞掛一漏萬。
如果一個書法學習者專注于一家,反復摹寫窮及其技,最終就是逼真其形。多年來的心慕手追,由外入內(nèi),形進乎神,可見古今書家情性之相通。如此的學習方法雖然單一,行于直線,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幾,襲其裳,則漸抵目標,秉承一家之美而持守,相對簡單而有效。元人袁桷曾評曹伯明學詩:“其為詩文,如桑麻谷粟,切于日用,不求酸咸苦澀,以傷乎味之正。篤實渾厚,與其履踐見于事物者,實相表里。”學一家而以切日用,同時又不摻雜其他使味不正。這樣的做法是可以提供于普遍運用的——追求某一名家,單線進行,盡其心力學習,不旁騖其他。如此心系一處,也就骎骎行于深入。如元代學習書法路徑,追隨趙孟頫書風何其多也,居廟堂高者,處江海遠者,都不乏其人。此路足以行一輩子,使筆下珠圓玉潤。如此也是一種真實的收獲,有門庭,得優(yōu)雅,即便沒有什么創(chuàng)造性,能守其成也是很讓人欣慰的——寫一手嫻熟的趙書,既有藝術(shù)性又合于世俗需要的美感,真是再好不過。
有的學習者耐不住如此單調(diào),以為取法一家太單調(diào)狹隘了,傾向博采,得百家之法以成自家風規(guī)。書法文獻越來越多了,給人們提供廣大學習空間,每個朝代都有新的作品充實我們的閱讀庫存。所見之也多,所學之也雜,似乎不如此涉獵不足以自廣。如此就呈現(xiàn)出繁雜的表現(xiàn),所學皆高雅,學不深入,就成了駁雜之流,品位下降,全然不能體現(xiàn)所學之功。書法學習的駁雜在于心境之焦慮,總以為跟不上潮流而落于后。其實,跟上潮流,不及保守自我的節(jié)奏。世上的審美趣味總是變動不居,追不勝追,最終迷失自己。以草書論,忽而大草,忽而小草;有時風檣陣馬,有時楊柳依依,追此逐彼永遠都是沒結(jié)果的,說起來都是諧謔調(diào)侃的意味,都缺乏一種篤定自若的堅定。清人周濟認為:“遇一事,見一物,即能沉思獨往,冥然終日,出手自然不平。”即便所學多且精,那么如何融會貫通諸家,一個人有沒有具備融合的能力則是一個難題。
古人用時多,用心平順,日常書寫而已。今人用時已非舊日尋常,雖可效法碑帖甚多,卻不是博采可以成其家數(shù)。清人沈德潛以為:“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后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今人近古人技能,往往忽略與古人性情淺深的溝通。今人能否會心古人,在多大程度上會心?不是可以輕易達到的。倘若專一家,知人論世,論世知人,對一個古人是會有所會心的,知其不同時段的人生、情性、審美,這就不僅僅是手上功夫的磨礪,還有許多的精神上的功夫,絕非徒一時耳目之玩賞。這也使學習者隨古人聞見睹記、情緒感遇之淺深以遞進。對一個古人的深入尚須如此,要博采百家,更多的就是體現(xiàn)面上功夫的敷衍,有許多表現(xiàn)由于雜亂而難以進入審美范疇,也就難以說明審美品位——每個人的效法還是有一定的界限的。面對古代書法家這個或那個陌生人的心靈世界的細心和耐心,尊重其人與文本,而不是淺率而過。清人沈德潛曾批評文人:“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為。”
為文為藝,“雖多奚為”的人還是不少。
六
說起張愛玲、冰心、蘇青、白薇這幾位20世紀40年代的女作家,冰心當然享有最廣大的聲名,然后張愛玲,而蘇青、白薇若與人說道,有的人還不知其二人如何。聲名高下,這里的原因當然很多,但到后來逐漸就是如此俗成了,好像真的就是如此的名與實。有的作家未必優(yōu)秀,卻有許多人在消費,也就聲名不衰,時日更替就成里程碑了。而有的人留存作品并不遜色,就是引不起關(guān)注與研究——研究者的研究也是講究效益的,隨大流追時尚,錦上添花的熱情向來都不會減少。在許多人人云亦云時,有的人還是會有自己的認識,表達自己的不同見解。張愛玲認為:“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并論,我是心甘情愿的。”很顯然,張愛玲眼里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也對把她和冰心相比較的那個人的做法表示相異。可以說每一個人都有等級觀,自己處于何等位置,相同位置上的還有什么人,自己不愿與之為伍的又有什么人。張愛玲認可的蘇青,更多人不知,覺得比較還是冰心適宜,而這恰恰是張愛玲不愿的。至于為什么不引以為榮,只好各自猜去。一個時段,可能傾向于這些人,過一個時段,又傾向另一些人了,唯獨立審美者有定力。
今天我們言說的古代書法家,是不是在當時超越群賢者,現(xiàn)在來看只能說是,因為無從還原當時場景。當時未必就是如此,而是還有其他佼佼者存在。書法家中的官僚如此之多,處廟堂之高與處江海之遠是截然不同的,有的人名位皆高,對于展示個人并不高妙的筆下文字就大有空間,而有的底層人士則受囿多多,甚至就是靠后人來褒揚的。作品的流傳渠道,官僚總是比平民有條件留名,顏真卿的碑刻書法有多少生前具聲名,逝后廣流傳,官僚幾人顏真卿。底層人士本就籍籍無名,作品倏爾湮沒無聞,使后人難以尋繹其實際。同一個時代會有許多部書法史,書法史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就是都是那么一些書法家、那么一些書法作品、那么一些書法事件,寫史者沒有能力窺人之所不及窺,言人之所不敢言,因此就大同小異。譬如唐代,當時的名書家就今日史冊上的這么些人,被認可的就這么些作品?肯定要豐富得多。但到了現(xiàn)在,就是另一種面貌,是當代人認為的書法史,確定的這些書法家,在這個書法史里出現(xiàn),在那個書法史里也出現(xiàn),而遺漏的那些人,永遠不會被鉤沉而出,永遠上不了書法史。就如上述的四位女作家,當時在文學上的水準、影響,難道是今日我們所接受的?這四位女作家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有的要花一章來講解,有的則草草帶過。而在當時卻不是這樣,該重點表達的反而是另一個人、另幾部作品。這也使人不禁去思考一部文學史、書法史,它們離真實相差多遠。
對于史冊上的人物、作品的認識和界定,或者進行比較、評說,還是應(yīng)該倚仗個人的審美素質(zhì)、能力來判斷,通過細讀其作品,得出自己的答案。如果自己的判斷與史說不一,那么就不必隨眾說。重約定俗成還是重實際,是可以看出個人的藝術(shù)史觀的。史冊上留存的人、作品,未必與聲名成正比,個人只有循自己的認知,有獨異的辨別,才可能去蒙去蔽,學到真實,不為名困。優(yōu)秀作品都是值得學習的,矜其聲名大小是毫無意義的。譬如一位學書者取法無名氏之作,不傍名流,不徇大流,往往需要心中有自己的審美分寸方具穩(wěn)定性。
每一個時代的文藝追求者,于古賢各有熱愛和疏離的對象,于同時代的人亦如此。張愛玲明顯是重蘇青的,引以為樂意同行者,相互比較得出異同,而于其他人則未必。每個人有自己的審美遠近意識,每個人都是獨異,比較不免漏洞百出。明人李贄認為:“孟子說自家不動心,卻引出告子、北宮黝、孟施舍來;說管、晏不足為,卻引出曾西怫然不悅一段來。皆是拌法。”這也提醒后人,“拌法”未必是優(yōu)比法。每個文藝家都有自己的時段,岑寂與熱鬧是會轉(zhuǎn)換的,只是時機未至。有人認為蘇青是為文學史準備的,她的回來是對文學史負責。這樣說法的理由是——優(yōu)秀作品是不會長久被冷落的,回歸也是一種必然。
七
看著周星馳演《唐伯虎點秋香》,都有一種開心,似乎就是為了讓人開心才拍這個片子。有論者以為是后現(xiàn)代的表現(xiàn)手法在起作用,似古典又現(xiàn)代,似現(xiàn)代又古典。新與舊融一體,有理無理混一起。里邊許多矛盾與破綻,卻不妨礙情節(jié)往下推,認為本應(yīng)如此犯不著和你說法度、規(guī)矩。生計忙亂中的人于觀賞中得到短暫開心,并不計事態(tài)情節(jié)對錯真?zhèn)危瑲g喜就好。如果此時有一個唐伯虎研究專家跳出來批評,認為這也不合歷史場景,那也屬子虛烏有,估計沒有人理會他,還是開心要緊。
我們對許多作品的深入都是從個人喜愛出發(fā)的,并不執(zhí)意探究其教育意義、人生啟示、精神提升、思想深度。而像《唐伯虎點秋香》這樣的片子,不是提升人的精神高度的,而是紓解人的緊張程度的。
短暫消愁,就是如此。
一個人學文學藝伊始,一片空白全無認知,選擇個人開心地去做,如此更有可能持續(xù)下去。
都開心向?qū)W,但路徑不一。有人逢正統(tǒng)引導,行于正途,合于主流。他們選正宗法帖,閱讀臨摹,漸漸近古人,筆下有了些許古風,使人看得出是學顏柳,還是蘇黃。而另一道途者也興致勃勃而進,不師古賢,也不師今人,唯師心自任,愛怎么寫就怎么寫。如此書寫自由自在,不需要有法帖規(guī)范,也不必體規(guī)畫圓準矩作方,使用筆、結(jié)體、章法每一步都在法則之外。如此為,自己當如何寫,朝哪個方向?qū)懀环晟介_路遇水搭橋,自作主宰不倚外物。使人觀之不知其來處、往何處,無所謂體統(tǒng),便如入無人之境。這兩種表現(xiàn)方式最終顯示了結(jié)局的相反——前者可稱書法語言,后者只能是書寫語言了。前者行于公共認可之道,后者則自開道途,興致驅(qū)遣。
江湖是常見的說法,以此言說文藝之空間。江湖空間無限廣大,可容得下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鯤鵬,也容得下蠛蠓、瓦甓、稊稗之屑小。這個空間的包容性、含納量可以說藏無盡。江湖不是一個整體,細分至無數(shù)個體,文藝者各持見解行于實踐之差異的途中,自珍其珍。若以美丑言,有人求美,便以自以為的美展開,美中有異,美上加美。以美自居者視對立的表現(xiàn)方法為丑。丑也是紛繁多樣,丑上加丑,丑中有變,丑態(tài)有別,各極其丑法。由于各自開心,積極去做,漫延滋長,也就種類不可計數(shù)。江湖大空間,所謂的表現(xiàn),自生自長,各求主旨,形式不同,使江湖充滿不同的力量與活力。所謂的高雅、鄙俗、美書、丑書,就看如何認知——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所為無誤,因為每一種表現(xiàn)方法,都擁有其認同者,這就使興致不減。
所謂江湖體,就是與傳統(tǒng)體相對立。傳統(tǒng)體就是走傳統(tǒng)路線,有門庭、流派或者宗派,其中就含有宗師、序列,由遠及近可循譜系。江湖體的稱呼固然有貶低之意,但這么多人寫江湖體,甚至入了字庫成為公共場所的用字。顯然,不必在意他人的看法,寫字畢竟是讓人開心的事,繼續(xù)做去,不負此生勞。江湖體也是體中有體,并非只有一種,而是無數(shù)。具有江湖體的每一個人,都在為江湖體的不同表現(xiàn)、自樹一幟而思考。有人認為江湖體就是胡亂下筆,這是把江湖體看簡單了。如果有意感受、分析其心事,論江湖體可以寫一部書。
晚唐花間派留下那么多作品,讀起來可以察覺到書寫時的心緒開朗。《花間集評注》的李冰若認為:“其中不無憤發(fā)悱惻之詞,實多流連風月之作。蓋情既極乎閨闥,氣自少于風云。”是啊,這一派詩人沉潛于裙裾脂粉、繡幌嬌嬈之中,喜纖纖素手,腮雪皓腕的婉媚香膩。說起來從這些角度寫,不免格小境狹,但對于這些文士而言甚是開心,樂此不輟,便寫下不少,傳之后世。閑時讀來,頗為暢適。詩文之道,未必都“鐵馬秋風大散關(guān)”之蒼涼,亦不必“艱難苦恨繁霜鬢”之窮愁。各做各的,如溫庭筠那般:“鶯語,花舞,春晝午,雨霏微。金帶枕,宮錦,鳳凰帷”也甚好——既是江湖,各自開心寫,方有波瀾瀲滟。
所謂的主流,所謂的邊緣,各自的感覺而已。當一些人正襟危坐,一點一畫以帖為范臨摹時,一些人正在吼書亂書,以個人情性奮力為之,如果說如此這般不絕,正是雙方都對自己的表現(xiàn)充滿自信,開心而作,只是不懈地做去,各有其心靈安放處。許多的藝術(shù)行為不一定是向前的,可能是斜行的、橫行的、無規(guī)則之行的,就像《唐伯虎點秋香》,很少數(shù)的人論其意義,大多數(shù)的人獲得開心。
(作者:朱以撒,福建師范大學美術(shù)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
本文責任編輯: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