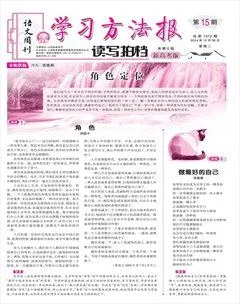角色定位
我們每個人一生中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場合,都要不斷變化角色,是幼兒的將會成長為成人,是兒女的將會成長為父母,在此處為人師長在別處就可能身為學生……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特點,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內涵。社會角色的瞬息萬變,會使我們聯想到我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在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某種角色亮相。你的角色,當由你來決定,做最好的自己。“我成為了我自己”不是一種口號,而是一種深度的生命覺醒。它教會我們,勇敢地追尋內心的聲音并不是一種叛逆,而是一種對自己內心世界的尊重和真實自我的追求。
品讀1
角 色
周國平
“成為你自己!”——這句話如同一切道德格言一樣知易行難。我甚至無法判斷,我究竟是否已經成為了我自己。角色在何處結束,真實的自我在何處開始,這界限常常是模糊的。
有些角色僅是服飾,有些角色卻已經和我們的軀體生長在一起,如果把它們一層層剝去,其結果比剝蔥頭好不了多少。
演員尚有卸妝的時候,我們卻生生死死都離不開社會的舞臺。也許,只有當我們扮演某個角色露出破綻時,我們才得以一窺自己的真實面目。
人在社會上生活,不免要擔任各種角色。但是,倘若角色意識過于強烈,我敢斷言一定出了問題。一個人把他所擔任的角色看得比他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無論如何暴露了一種內在的空虛。我不喜歡和一切角色意識太強烈的人打交道,例如名人意識強烈的名流,權威意識強烈的學者,長官意識強烈的上司等等,那會使我感到太累。我不相信他們自己不累,因為這類人往往也擺脫不掉別的角色感,在兒女面前會端起父親的架子,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要表現下屬的謙恭,就像永不卸妝的演員一樣。
人之扮演一定的社會角色也許是迫不得已的事,依我的性情,能卸妝時且卸妝,要盡可能自然地生活。
在人生的舞臺上,我們每個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比真的演員還忙,退場的時間更少。例如,我整天坐在這桌子前,不停地寫,為出版物寫,按照編輯、讀者的需要寫。我暗暗懷著一個愿望,有一天能抽出空來,寫我自己真正想寫的東西,寫我心中的那個聲音。可是,總抽不出時間。到真空下來的時候,我就會發現,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寫什么,我心中的那個聲音沉寂了,不知去向了。
人不易擺脫角色。有時候,著意擺脫所習慣的角色,本身就是在不由自主地扮演另一種角色。反角色也是一種角色。
一種人不自覺地要顯得真誠,以他的真誠去打動人并且打動自己。他自己果然被自己感動了。一種人故意地要顯得狡猾,以他的狡猾去魅惑人并且魅惑自己。他自己果然懷疑起自己來了。
對于有的人來說,真誠始終只是他所喜歡扮演的一種角色。他極其真誠地進入角色,以至于和角色打成一片,相信角色就是他的真我,不由自主地被自己如此真誠的表演所感動了。
如果真誠為一個人所固有,是出自他本性的行為方式,他就決不會動輒被自己的真誠所感動。猶如血型和呼吸,自己甚至不可覺察,誰會對自己的血型和呼吸顧影自憐呢?
由此我獲得了一個鑒定真誠的可靠標準,就是看一個人是否被自己的真誠所感動。一感動,就難免包含演戲和做作的成分了。
偶爾真誠一下、進入了真誠角色的人,最容易被自己的真誠感動。
做作者的靈魂往往分裂成一個戲子和一個觀眾。當戲子和觀眾彼此厭倦時,做作者的靈魂便得救了。
(摘編自2009年第7期《意林》)
【賞讀】
本文是一篇充滿哲理的散文精品。文中作者由“角色”這個問題剖析自己,反觀自己的內心,表達了“要盡可能自然地生活”的愿望。作者的感受是敏銳的,對自己的剖析是深刻的,更可貴的是,作者并沒有局限于此,而是由進一步剖析社會,提出了“做人要真誠”的主題。無論是“自然”還是“真誠”,作者都是緊緊圍繞“角色”這個話題展開的,所以在該文中,“角色”這個詞就像放風箏的線,既放得很開讓風箏飛得高遠,又收得很緊,讓風箏無論飛得多么高遠都必須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品讀2
做最好的自己
席慕蓉
如果你無法成為山頂上的一棵蒼松
就做山谷中的一叢灌木
但一定要做溪邊最好的一叢小灌木
如果你成不了灌木
那就做一棵小草
讓道路因你而更有生氣
如果你成不了海洋中的大梭魚
那就做一條鱸魚
但一定要做湖里那條最有活力的鱸魚
我們不可能都做船長
必須要有人做船員
總會有適合我們做的一些事情
有大事,也有小事
我們要做的就是眼前的事
如果你成不了大道那就做一條小徑
如果你成不了太陽那就做一顆星星
成功還是失敗
并不取決于你所做事情的大小
做最好的自己
【賞讀】
《做最好的自己》是席慕蓉的一首激勵人心積極向上的作品,詩人信手拈“字”,層層推進,娓娓道來,希望每個人都能敢于活出自己的光彩,天生我材必有用,勇敢地做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