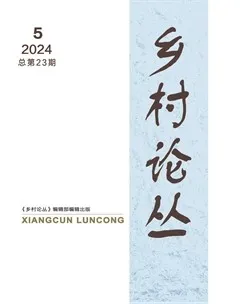濟南端午碧筒飲習俗及其農耕價值
摘要:碧筒杯飲酒作為濟南端午佳節的特有習俗,承載著文人之雅與民間之俗。自魏晉時期開始,文人墨客便有以碧筒飲為典故賦文吟詩的習慣,其雅興所依托的是濟南大明湖水域的蓮藕風物、種荷習俗與藕神信仰。時至今日,濟南地區以碧筒飲為代表的荷藕農耕文化,依舊發揮著調節農事的人文價值與傳承非遺的文化、經濟價值。
關鍵詞:碧筒飲 大明湖 端午節 農耕文化
端午節作為我國最重要的傳統歲時節日之一,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古代文獻對端午的研究大多側重于對端午節習俗的搜集整理,當代學者的研究集中于屈原傳說、具體的習俗儀式、端午節的源流與意義以及申遺相關討論,而對地方端午與農耕文化的探討卻大多散見于論著之中。碧筒飲作為濟南地區特有的端午風俗則偶見于地方志、文人筆記等文獻。本文將端午碧筒飲習俗與濟南特定的風物、農事相聯結,探討端午習俗所蘊含的農耕文化。
一、文人之雅:碧筒飲的文獻與文物
碧筒飲又稱為碧筒杯、荷葉杯、象鼻杯,是一種以荷葉制成或形似荷葉的酒器,其歷史最早可追溯至魏晉時期。《酉陽雜俎》記載:“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筒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于水。”其中的“歷城”與“歷下”即為現在的濟南地區,可見至遲在魏晉年代,濟南已經開始盛行以荷葉為杯飲酒的習俗了。使用碧筒杯飲酒的習俗一直傳承至明清乃至民國時期,刊刻于明代的《歷城縣志》記述了濟南地區端午佳節時“士大夫攜酒泛舟,作折筒飲,即小民亦攜一壺,劇飲樹下”的悠然之景。清道光二十年刊刻的《濟南府志》同樣記載“歷之士大夫攜酒泛湖作碧筒飲”。
除縣志以外,歷代墨客文辭中都頻現碧筒飲及相關詞句。唐代有曹鄴的“乘興挈一壺,折荷以為盞”與白居易的“疏索柳花碗,寂寥荷葉杯”。晚唐五代時期甚至還形成了以“荷葉杯”為名的詞牌,其中最負盛名的是溫庭筠的《荷葉杯·一點露珠凝冷》與韋莊的《荷葉杯·記得那年花下》。但碧筒飲真正得到廣泛流傳是在宋代,宋代及以后文人引用碧筒飲及相關典故的數量驟增。南宋石獅籍美食家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是中國歷史上經典的菜譜著作之一,為后人了解宋代士人的飲食文化提供了鮮活的文本,其中詳細描述了宋人蕩舟、食魚、以荷葉飲酒的雅興:“暑月,命客泛舟蓮蕩中,先以酒入荷葉束之,又包魚鲊它葉內。俟舟回,風薰日熾,酒香魚熟,各取酒及鲊,真佳適也。”顯然到宋代已經形成了用荷葉飲酒以及用荷葉包裹魚鲊烹飪的習俗。蘇軾有“碧筒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陸游有“碧筒莫惜頹然醉,人事還隨日出忙”,趙翼有“帶得余香晚歸去,月明更醉碧筒杯”,多位詩壇巨匠都受碧筒飲的啟發留下眾多文采斐然的名篇佳作。縱覽上述,以碧筒飲為典故的詞句,雖然難以推斷詩人究竟是使用碧筒杯飲酒,還是僅引用其典故,但都足以見得文人墨客對這一飲酒方式的喜愛。
除了以碧筒杯入詩,我國古代還演變出仿制荷花形狀制作而制成的銀質、玉質、陶質等各類荷葉形酒器。陜西西安出土唐代雙魚紋銀質荷葉杯,杯身呈卷攏的荷葉狀,杯口四曲,侈口,呈長圓形,有矮囿足。杯內鏨刻荷葉莖脈為紋飾,底部鏨刻兩尾胖頭花尾魚,首尾相對。杯長13.6厘米,高3.2厘米。浙江省衢州市南宋學者史繩祖的墓中出土一件玉質荷葉杯,杯體雕成周緣卷攏的荷葉狀,脈絡清晰,玉杯之表面雕刻花姿各異的蓮花,荷葉莖柄平伸而出,彎曲成杯把,杯把上覆有一張小荷葉,杯長11.5厘米。
更符合碧筒飲通過吸食荷莖的方式飲酒的器物要數山東省博物館珍藏的粉彩荷花秋操杯。該杯燒制于清光緒三十四年,高5厘米,長19厘米,寬15厘米,形如盛開的荷花,杯底花蕊間有一小孔,與花梗相連,花梗中空,可作為吸管,以此吸飲杯中酒。因此,這款粉彩荷花秋操杯也被稱為“吸杯”。
二、民間之俗:大明湖的種荷習俗
碧筒飲代表了文人飲酒的雅致,作為典故被廣泛運用于歷代詩詞中。可以想見,碧筒飲習俗或許來自民間,如同荷葉雞、東北大飯包等美食,使用植物葉片包取食物以豐富口感、提升風味的烹飪方式在民間屢見不鮮。作為文人之雅的碧筒飲,所依托的基礎正是民間的地方風物。我國種植荷、藕的歷史可追溯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周書》中“魚龍成則藪澤竭,藪澤竭則蓮藕掘”描述了蓮魚同澤、竭水掘藕的農耕場景。《齊民要術》則翔實地記載了古代處理蓮子的技藝:“八月九日中,收蓮子堅黑者,于瓦上磨蓮子頭,令皮薄……皮薄易生,少時既出,皮既堅厚,倉卒不能生也。”可見,我國種蓮技術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已經漸趨成熟,不僅在實踐中取得了有效的生產性成果,而且在文獻中也總結出一套系統而精細的操作理論。
具體到碧筒飲盛行的濟南地區,以大明湖為中心的水域是重要的荷藕產區,大明湖因此有“蓮子湖”的別稱。《酉陽雜俎》中記載:“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其中“蓮子湖”說的便是“大明湖”。明代的《歷城縣志》中指出,“荷花,明湖十里皆是也。有線蓮、白蓮、樓子、千葉諸蓮,不可勝紀。”至民國時期,大明湖中“湖地皆有主,種有白蓮數十頃。”“明湖白蓮數十頃無閑地,種荷者以葦為界,舟行不能見花為可惜。”當地士紳甚至將白蓮藕譽為濟南特色的風物,認為“北園及大明湖地方,除產蔬菜外,茭白、蒲菜、菱角產量亦多,藕以鐵公祠附近為最優”。老舍《大明湖之春》中也稱贊道:“大明湖的蒲菜、茭白、白花藕,還真許是它馳名天下的重要原因呢。”蒲菜、茭白與白蓮藕也被譽為“明湖三美”。
因此,濟南大明湖地區很早便形成了獨特的種荷習俗。民國年間經過孫寶生調查而作的《歷城縣鄉土調查錄》談到濟南地區“荷有紅白單復數,種宜黑色黏性之土,將水田尾干,掘取浮泥,植荷秧于其上,宜疏不宜密,將原有之泥覆其上,俟有曬干裂紋,始引水入內。五月間,即可開放。綠葉之田,映紅白之花,日光之下頗饒雅趣”,記述了濟南地區先將水田抽干,掘取浮泥,等到原本黏土曬干有裂紋后再引水入內的種荷技術。
大明湖蓮藕種植技術中最具特色的要屬“踩藕”。踩藕是指湖民用踩的方式收集蓮藕的收采技術。踩藕時,湖民身穿皮制的連衣褲,舉起雙手,立在水中,兩腳在淤泥中順著藕節找到根蔓,踩斷,再用腳將藕挑出水來,抓一塊藕上的黑泥,涂在斷口處,以免灌進水去。因藕內有空氣,能夠浮在水面上,否則就會沉入水底。一人一天可采三百多斤藕。采藕從立秋一直持續到來年夏至。冬至后藕價上漲,湖民往往穿皮衣作業。皮衣用鮮牛皮制作,保暖性能很好。
由于大明湖地區歷史悠久的種荷傳統,該地甚至形成了藕神信仰,藕神祠坐落于大明湖北岸西側。最早有關藕神祠的文字記錄始于王賢儀。王賢儀雖是浙江山陰人,但自幼客居濟南,大約生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卒于咸豐五年(1855)。他在《家言隨記》中說“陸梁廟在濟南北門內,俗稱藕神廟,甚隘,匾曰‘陸梁’,郡志未詳,土人亦鮮能道其稱名之實”,由此觀之,至遲到清代,大明湖地區仍存留有藕神信仰。
在文人的參與、運作下,藕神信仰與宋代詞人李清照相結合,這不僅因為李清照是濟南人,或許也是因為李清照有“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的名句。清代文人符綸兆作《明湖藕神祠移祀李易安居士記》記載“湖側舊有屋一楹,曰‘藕神祠’,不知所祀何神。神像久毀。同人以湖山佳麗,主持宜得其人,因以易安代之……生平煩惱,聊仗千佛為之懺除;無數謗誣,亦借明湖為之湔雪”,顯然是文人將李清照與藕神祠關聯起來。除了符綸兆以外,王大堉等人也都曾以藕神祠為題賦詩。王大堉也是清代著名詩人,天津人,但因其兄王大淮于道光十九年(1839)任曲阜縣令,因此隨兄游居山東。據此可見,以李清照為藕神大概始于清代末年。這一傳統也一直延續至今,1998年大明湖公園借原南豐祠房屋院落重新建成藕神祠,正中的藕神坐像為宋代仕女裝扮,手持卷軸。盡管祠中沒有介紹藕神即是李清照的說明,但祠門兩側懸掛著濟南學者徐北文所提楹聯:“是也非耶,水中仙子荷花影;歸去來兮,宋代詞宗才女魂”代為挑明。
實際上,可以推測,雖然文人將藕神建構為濟南才女李清照,但是在這之前,該信仰顯然與種植蓮藕的生產需求息息相關。大明湖邊種藕的人,每年大年初一早上,帶著香火、水餃,用桿子挑著紙糊的元寶,天不亮就到湖西北面的藕神祠燒香上供。到了藕神祠,燒香上供燒元寶,俗稱誰燒的元寶多,誰燒的元寶大,誰種的藕當年就會豐收。所以只要經濟上允許,都爭相多買元寶、買大元寶,有的元寶大到二尺長。雖然一年只祭一回藕神爺,但家家都指望蓮藕豐收過日子,所以對藕神爺特別看重。
三、雅俗之間:碧筒飲的當代價值
無論是端午用碧筒杯飲酒的風雅還是附庸至李清照的藕神祠,其物質與信仰基礎都是濟南地區悠久歷史、頗負盛名的“明湖三美”風物以及當地湖民獨特的“踩藕”技術。而口耳相傳、無文字記載的民俗又通過文人的記載與實體的碧筒杯得到了廣泛的流傳與跨時代的傳承。而在當代,碧筒飲依舊為泉城民眾發揮著其獨特的人文價值與經濟價值。
(一)端午閾限:調節農事節奏的人文價值
閾限是由范·熱內普與維克多·特納闡釋的儀式理論,在閾限階段,閾限人從固定的文化空間中的結構脫離,他們之前的身份和位置不復存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關系,即平等、簡單、一視同仁的關系,達到了一種精神的、靈魂的、情感的交融。端午節的相關習俗即反映了一種閾限的功能。在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古代,端午佳節所在的五月正值農忙季節,比如《濟南府志》記載“(五月)是月始種豆”,《歷城縣志》記載“是月也,麥始登,婦始絲”。
從五月開始,農民們便開始進入繁重的夏季農忙階段,體力、精神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而端午期間社區之間賽龍舟、合家團聚包粽子、使用碧筒杯飲酒等農耕習俗,無異于一場小型的狂歡,形成了與平時繁忙、辛苦的勞作所不同的閾限階段,給予農民一個難得的休息機會。在端午佳節,無論文人士大夫還是販夫走卒都可以使用碧筒杯飲酒,不論是精美的碧筒杯,還是隨手折一支荷葉用以飲酒,其內核都是利用酒的特性使人身體放松、心情舒暢。此外,從飲食平衡的角度,荷葉被認為“色青中空,得天地輕清之氣,新鮮者善清夏間之暑邪”。因此碧筒飲這一獨特的飲酒方式,可以借荷葉的涼中和酒的熱,使人在端午佳節享受美酒的同時消暑敗火。
(二)碧筒飲再現:保護非遺傳承的文化、經濟價值
在2023年端午佳節濟南明湖龍舟文化節開幕式上,濟南陶塑非遺傳承人王令濤展示了自己復原碧筒飲吸杯的制作技藝。大明湖景區還打造了實景演出《鵲華煙雨·碧筒飲》,使用現代的機械、聲光、音響設備,運用真湖、真景、真人復活了千年傳奇碧筒飲。利用非遺保護與舞臺劇的現代化方式,將傳承千年的碧筒飲引入現代生活之中,不僅有助于宣傳弘揚濟南地區頗具特色的優秀傳統文化,還通過經濟活動提供了就業崗位、培養了非遺傳承人才。更值得注意的是,濟南借助碧筒飲習俗建立了鮮明的城市品牌,拓寬了濟南的文化旅游產業鏈條,宣傳了本地特色的白蓮藕等農產品,將原本依托于農業的端午文化與碧筒飲習俗引入服務業與旅游業之中。
以荷葉為杯,飲端午之酒。碧筒飲作為流傳已久的濟南端午習俗,具有豐富的文獻記載與具體可觀的實體文物。看似僅是文人追求文雅的產物碧筒飲,其背后蘊藏的是濟南以泉、湖為特色的城市地貌、以明湖“三美”為代表的特產風物以及獨具特色的“踩藕”技術與藕神信仰,該習俗不僅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更在當今社會展現出其獨特的人文價值和經濟價值。碧筒飲的推廣和傳承也為濟南地區帶來了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新機遇,進一步提升了城市的文化軟實力,使傳統習俗在現代社會中重現生機,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橋梁。
參考文獻
[1]李亦園.人類的視野[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2]趙東玉.端午龍舟競渡民俗的文化選擇[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03):116-119.
[3]周大鳴,闕岳.民俗:人類學的視野——以甘肅臨潭縣端午龍神賽會為研究個案[J].民俗研究,2007,(02):70-79.
[4]田兆元.論端午節俗與民俗舟船的譜系[J].社會科學家,2016,(04):7-13.
[5]高丙中.端午節的源流與意義[J].民間文化論壇,2004,(05):23-28.
[6]蕭放.端午節俗的傳統要素與當代意義[J].民俗研究,2009,(04):229-238.
[7]楊琳曦.韓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對我國的啟示——以端午祭申遺成功為視點[J].廣西民族研究,2007,(01):185-190.
[8]謝桃坊.唐宋詞譜粹編[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21.
[9](宋)林洪著;黃作陣,胡賀峰校注.雅文食趣 山家清供[M].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22.
[10]萬偉成,丁玉玲.中華酒經[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
[11]杜金鵬,岳洪彬.古代文物與酒文化[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
[12]莊孔韶.人類學通論[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13]謝觀主編.中華醫學大辭典[M].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