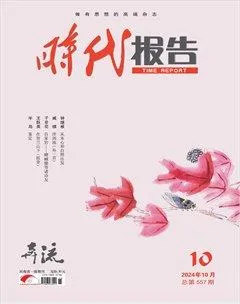那一抹淡淡的憂愁

在紅旗路口,人們幾乎每天早上都會遇到一位老人,80多歲,頭發花白。歲月在老人的臉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皺紋,眼眸呆滯無神。腰已彎至90度,四輪小竹車是她的拐仗,本該坐嬰兒的車座上放著幾棵青菜或者饅頭等吃食。
拐角處是一個炸油條的飯攤,兩根油條,一碗小米粥,一小碟咸菜,就是老人的早餐。老人顫顫巍巍地拿起筷子抄了一根油條,盡管小心翼翼,那油條仍然從兩根筷子中滑落了下去,老人又慢吞吞地用手捏起來,象征性地吹了一下,把油條扔進小米粥里,頭低下去,尋著碗邊輕輕地咂摸了一小口,頭上的花白頭發在晨風中有些散亂,她下意識地用右手抿了一下,抬頭望了一下眼前的梧桐,一滴渾濁的眼淚順著眼角慢慢地淌下來。
她叫李秀英,今年81歲,17歲嫁人,丈夫在學校做后勤工作,老伴生性孤僻,不善言辭,生養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兒子在老家務農,秉性耿直少言寡語。二兒子最小,做公務員,性格內向,女兒27歲煤氣中毒而亡。
一年前,老伴患肺癌撤手人寰,生活中少了一個知冷知熱,相依相偎的人,內心的寂寞在屋里蔓延,老伴的照片放在客廳的八仙桌上,還是那幅沉靜的表情,但更多的是觸及了她對往事的回憶,有時對著照片絮絮叨叨,抒發一下自己的怨氣。盡管是照片,但總算有個聽者。住在鬧市,面對熙熙攘攘的人群,卻鮮有兒女來往。忙?兒子們為了生活,為了他們的子女,誰都沒空看這個老太婆,門口茶幾上的電話已經很久沒有響了,上面布滿了灰塵,她直勾勾地盯著電話機,曾經多次聽到了電話的“叮呤”聲,忙走過去接,但是大多數都沒有,她知道這是錯覺。
有一次在早餐點,她分明見到了二兒子,但兒子仍像沒看見一樣,沒有招呼,只有冷漠的背影。原因很簡單,老太太的房子是學區房,而二兒子的兒子正上中學,夫妻倆想讓老人岀去租房,讓孫子上學住。但是老人不想離開老屋,因為那里有她半生的記憶,有老伴的味道,更有著自由的隨時可尋的熟悉。老人不想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去生活。于是便沒答應二兒子夫婦的請求,夫妻倆三個月來從未看過她,甚至沒有一個電話。她心里也明白,二兒媳想霸占房子,因為老大家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二兒媳經常說女兒遲早是別人家的人,只有男孩才是自己家的。她聽在心里,但她想:某天她走了,這房子要一分為二,她想一碗水端平,她不想讓在農村的大兒子吃虧。
一片黃葉飄過她的頭頂,順著發絲滑落到地面,梧桐葉的脈絡清晰可見,她想起了她那個唯一的女兒,離開她己經三十年了,就像這片黃葉從梧桐樹身上滑落,在地上流浪,然后化作塵埃,誰的命運不是如此呢?她那個漂亮的女兒,那個才剛剛工作幾年的女兒,那個剛結婚還沒來得及享受生活的女兒,在那個冬天,竟然煤氣中毒,悄悄地走了。那個小棉襖,那個家中唯一仿她性格的女人離開了她,留下她,面對三個沉悶的男人,為他們洗衣做飯,打掃衛生。木訥的丈夫,那個像影子一樣的男人,很少有自己的意見。她有時埋怨他不像個男人,有時又覺得自己很弱小,事事都依靠他,事實上最重要的決定往往是老頭子的主意。從前年夏天被查岀肺癌晚期,不到一年便走了,走得好,再也不用受罪了。只是孤孤單單地留下她一個人,如今連影子也沒有了,內心的孤獨像冬天的夜一樣漫長,床頭的那只白貓成了她唯一的伙伴,白貓蜷臥在她身邊,暖洋洋的,體溫傳遞著體溫,讓她感受到了些許安慰。白貓的呼嚕聲是她最好的安眠藥,“貓睡了,我也該睡了。”她常常自我催眠。
她想起清晨,第一縷陽光灑進窗戶,明晃晃的光線刺痛了她的雙眼,她醒了,起了三次,才勉強坐起來,頭有些痛疼,夜里睡得很不好,還做了惡夢,夢見老頭子要帶她走,她高興極了,心想再也不用一個人生活了。她拉著他走,他們走到了老家的小河邊,在一棵老柳樹下休息。一轉眼功夫,老伴不見了,她哭著喊著,卻找不到人。她哭醒了,睜開眼睛,眼前只有那只老貓靜靜地看著她,尾巴不停地搖擺,“喵喵”地安慰著她。
她想起傍晚,夕陽把她的背影拉得很長,她好像看到了一個正常的自己,她不再駝背了,身材高挑,神清氣爽地走在大街上,大家都看著她微笑,她自信滿滿地和大家揮手打招呼。她又仿佛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細眉長眼,辮子粗黑。那時候,媒婆擠破門檻。她嘖巴嘖巴嘴,告訴自己不要再瞎想了。她知道上天留給她的時間不會太長,老頭子在河對岸等著他。她慢慢地推著小竹車沿著寬敞的街道向前,沒有目的,她不知道該去哪兒,但不知不覺中她又來到了二兒子居住的小區,她想偷偷看上一眼,看看孫子,看看兒子。唯一的孫子今年15歲了,六月初六生日,她記得很清楚。她好像很久沒有見過他了,也許他超過180cm了,那孩子心氣高,班里成績總是第一,想到此,她的臉上浮出了微微笑意,那是發自內心真切的快樂。一陣風吹來,她打了個冷顫,也許明天再也來不了了,她一聲嘆息,緊蹙眉頭,一滴眼淚從眼角滑落,落到嘴邊,咸咸的。
天暗了下來,風雨要來了,這鬼天氣,說變就變。她得趕緊走,免得淋雨生病,她知道她可病不起。她慢慢轉過身,小竹車“吱呀吱呀”地唱著歌,她的背影越來越小,漸漸消失在昏暗的雨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