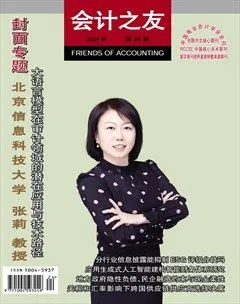分行業信息披露能抑制ESG評級分歧嗎
【摘 要】 ESG信息存在較為明顯的行業特征,中外較多行業正加緊制定ESG信息披露的行業標準,ESG信息的分行業披露制度體系建設具有現實緊迫性。文章使用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考察分行業信息披露對ESG評級分歧的影響。研究發現:分行業信息披露可以抑制ESG評級分歧。機制檢驗表明,分行業信息披露的規范和監督效應能提升企業信息透明度和抑制管理層語調操縱從而降低ESG評級分歧。異質性檢驗發現,在內部控制質量較低、分析師關注較少、碳信息披露質量較差的公司樣本中,政策對ESG評級分歧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拓展性分析發現,政策主要影響“G”維度的評級分歧;較重污染企業,非重污染企業“E”“S”維度的分歧受政策影響更大。研究結論有助于深入理解分行業信息披露影響ESG評級分歧的內在邏輯,為ESG信息披露分行業標準制定提供啟示。
【關鍵詞】 分行業信息披露; ESG信息披露; ESG評級分歧
【中圖分類號】 F27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4)24-0071-10
一、引言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對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1],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評級是同時關注公司治理、社會責任、環境績效的全方位企業評價體系。隨著資本市場的開放,這項評級成為企業各個利益相關方最為關注的評價體系之一[2]。ESG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設總體上可以分為兩步,第一步就是出臺廣泛適用的普遍準則,第二步是依據行業特點出臺行業適用準則。對于第一步建設,我國監管機構自2007—2022年密集出臺普遍適用的ESG信息披露政策,如《環境信息公開辦法(試行)》《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這些準則體系提供了一個衡量企業環境表現的客觀指標和低碳轉型的標準,成為ESG信息披露體系的基礎[3]。對于第二步建設,學術界還未形成廣泛關注,但由于ESG信息的復雜性,依據行業特點進行披露具有現實緊迫性,相關行業也著手制定ESG行業標準:如2023年12月21日,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了《中國汽車行業ESG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見稿)》;2023年11月7日,全國旅游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發布《旅游企業環境、社會和治理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見稿)。國際上,作為全球ESG發展的重要里程碑,2023年6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IFRS Foundation)正式發布了國際財務報告可持續披露準則,準則強調基于所屬行業,企業需要根據該行業特定的披露主題進行信息披露,向投資者展示與行業發展相關的并能影響企業價值的特定信息,準則還為這些披露主題設置了基于量化的披露要求和其他要求。可見,對于較為復雜的ESG相關信息,進行“分行業”針對性披露意義重大,是學術界應當關注的重點。
在我國資本市場信息披露制度持續完善的過程中,滬深兩市進行了分行業信息披露這一制度創新,分批次發布了不同的行業信息披露指引,要求企業按照行業特征進行更為精細化的信息披露,那么這項政策是否可以促進企業信息向ESG評級機構溢出?探究這一問題可以從ESG評級分歧的視角出發:在衡量企業ESG表現時,不同ESG評級機構對同一公司的評級分歧嚴重干擾管理者的戰略決策和投資者的投資選擇,因此如何減少ESG評級分歧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關注的問題。已有研究表明,ESG評級分歧主要來源于底層數據[4]。作為重要的底層數據之一,分行業信息披露改善了資本市場的信息環境[5],不僅使投資者獲得了更多有用信息,而且也使ESG評級機構等專業信息處理方獲得了評價企業經營成果的底層數據,這可能促使ESG評級更能反映企業真實表現,從而有助于減少各機構對同一家公司的評級分歧。因此本文以2011—2021年滬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探究分行業信息披露對ESG評級分歧的影響。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第一,豐富了ESG評級分歧影響因素的研究。已有文獻對ESG的研究多聚焦在ESG表現上,主要探究ESG表現對企業造成的經濟后果;也有部分文獻討論影響ESG表現的企業行為,如數字化轉型對ESG表現的影響[6],或側重于ESG信息披露的溢出效應[7],基于ESG評級質量提升的研究還比較匱乏,而本文關注到信息披露政策也可以作為ESG評級分歧的影響因素,這一發現為改善ESG評級的客觀性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拓寬了分行業信息披露的研究邊界。有別于已有研究集中關注分行業信息披露對財務信息質量的影響,本文深入分析分行業信息披露政策對企業ESG評級分歧的影響,論證了行業信息披露指引能降低企業ESG評級分歧,將分行業信息披露的研究邊界向ESG領域延伸。第三,為改善ESG評級分歧現象提供了經驗證據。有別于已有研究從評級中的權重和流程角度對ESG評級分歧現象進行溯因,本文通過實證研究率先發現外生沖擊也會對ESG評級分歧產生影響;利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分行業強化企業信息溢出,使其ESG評級更能反映企業真實表現仍是一項意義重大的課題,本文的研究結論為解決這一現實問題提供了具有創新性的經驗證據。
二、制度背景、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一)分行業信息披露相關制度背景
在注冊制改革的背景下,滬深兩市自2013年開始根據行業特征發布行業信息披露指引,要求上市公司聚焦于行業層面披露更多信息。具體而言,這些指引強調結合行業經營模式,披露行業關鍵指標和差異化信息,以提高財務報表的可讀性。同時,指引中設置了具體的量化披露標準。例如,針對零售行業,指引要求上市公司應當披露反映門店的信息,包括各類門店的平均銷售增長率、每平方米營業面積銷售額、每平方米建筑面積租金等。這些指引旨在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質量,幫助投資者更好地了解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從信息溢出的角度來看,分行業信息披露幾乎成為近年來對財務報表內容影響最為深遠的政策之一。
(二)ESG評級分歧相關文獻回顧
ESG評級分歧的后果方面,大部分文獻認為ESG評級出現差異會給投資者和管理者帶來困擾和阻礙。ESG表現的評價過程作為信息處理的中介行為,需要成本和投資,ESG評級出現差異和分歧是造成ESG投資需求減少的一大原因[8]。從信息接收方來看,ESG評級出現分歧使ESG本身的風險識別功能出現失靈,不僅提高了投資者接受和理解信息的門檻,而且可能會造成識別偏誤[9]。從企業管理者的角度來看,Christensen et al.[10]認為ESG評級分歧會干擾公司可持續發展,迫使企業進行更多的內部融資,從而減少外部融資。
對于ESG評級分歧出現的原因,Berg et al.[11]研究發現,ESG評級科目的體系建設以及指標度量方法上存在差異導致了ESG評級分歧。Dimson et al.[12]以及Billio et al.[13]研究發現,評級體系建設中,不同一級評級科目的權重分散差異造成了ESG評級差異現象。而Lopez et al.[14]從評級機構處理信息的流程出發,認為評級過程中的不公開、不透明使各機構產生得分的差異。另外,ESG評級機構所處地區的制度、文化、地域環境則對ESG評級造成了影響,由此產生了分歧[15]。針對國內上市公司,馬文杰等[16]認為企業所有權屬性的不同及其社會責任披露的差異造成了中外評級機構的分歧;巴曙松等[4]認為,ESG評級差異主要來源于底層數據。
綜上所述,ESG評級分歧不僅會給投資者選擇造成困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企業管理者進行戰略規劃,這將損害投資者和企業對ESG評級的信心,進而削弱ESG評級的權威性。在上述文獻對ESG評級分歧的溯因中,鮮有文獻探討降低ESG評級分歧的方法,對降低ESG評級分歧的外生沖擊也沒有進行探索。因此,找出改善ESG評級分歧的因素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有別于已有研究從ESG評級的指標、口徑、科目選擇和評級程序視角對ESG評級分歧現象進行溯因,本文率先發現外生沖擊也會對ESG評級分歧產生影響。本文擬考慮從分行業信息披露角度考察ESG評級分歧的影響因素以拓展現有文獻。
(三)理論假設
借鑒信息理論相關內容,本文根據Burgin[17]的評價框架②進行理論分析,認為分行業信息披露通過規范效應和監督效應,能提高信息透明度、抑制管理層語調操縱,進而降低ESG評級分歧。
ESG評級分歧的原因主要來源于底層數據[4],而分行業信息披露的直接效應就是強化了企業主業信息和行業橫向信息的披露,即“G”方面的信息披露,例如:指引要求汽車行業披露具體銷售情況,強化建筑行業區域項目信息披露。此外,鑒于投資者對環境和社會責任的關注,分行業信息披露始終根據行業特點促使企業強化“E”和“S”信息披露,例如:對固體礦產資源、化工等行業,指引要求企業詳細披露污染事故等信息;對民用爆破等發生安全事故可能性較高的行業,指引要求其細化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綜上,本文預計分行業信息披露可以降低ESG評級分歧。按照信息理論,分行業信息披露從以下兩點影響ESG評級分歧。
一是就信息內容和其格式本身特征來說,分行業信息披露政策具有規范作用,能提升公司信息透明度,提高ESG評級底層數據的透明度,進而降低ESG評級分歧。ESG評級機構進行評級時也存在信息源不足的情況,分行業信息披露會緩解這種信息不足,具體來看:第一,分行業信息披露要求披露關于公司經營的關鍵性指標以增強信息可比性和增加信息凈含量。例如,對于食品制造行業,分行業信息披露要求在基本財務數據的基礎上披露有關主營業務的具體信息,相比僅僅按金額披露主營業務收入等數字,分行業信息披露可以產生更多增量信息。可比性的信息是ESG信息披露的重要要求,具備可比性的信息能夠使評級機構和投資者在分析和評估企業的環境、社會和治理表現時,進行有效的橫向對比和縱向跟蹤,而ESG評級與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也息息相關[18],因此,標準化、可比且內容含量高的數據極大地提升了數據的可利用性,有助于評級機構全面掌握企業的ESG信息[19]和更多企業主業經營情況,從而降低ESG評分對于企業真實值的偏誤,各機構的ESG評級分歧也將因此降低。上述邏輯如圖1中驅動機制1中的“1”所示。第二,分行業信息披露通過規范指標披露口徑,強化信息的溢出作用,提升信息的“效率效應”。信息“效率效應”是指,信息本身含量和可比性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信息使用相關方的獲取成本,提升戰略選擇效率[20]。具體來說,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的發布不僅降低了上市公司與投資者、分析師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同時能有效提高會計師事務所和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工作質量[21]。通過分行業信息披露,企業可以根據其所在行業的特點和要求,提供更具針對性和詳細的ESG信息。這使得ESG評級機構在進行信息收集和追溯時,可以更高效地獲取與企業實際運營情況密切相關的數據,從而減少了在海量信息中篩選和核實的時間和成本,而信息追溯成本的降低可以減少ESG評級分歧[19]。上述邏輯如圖1中驅動機制1中的“2”所示。因此,分行業信息披露帶來的規范效應能提高企業信息透明度,進而減少ESG評級分歧。
二是就信息使用者(用戶)對信息的感知、使用者能力和其需要來說,分行業信息披露政策具有監督作用,能抑制管理層語調操縱,提高ESG評級底層數據的真實性,進而降低ESG評級分歧。自分行業信息披露在全國推進后,政策實施者加大了對經營行為和經營信息的監管,如果出現經營風險或者異常盈利,監管者會加大事后問詢[22]。上述邏輯如圖1中驅動機制2中的“1”所示。分行業信息披露作為一項制度創新,可以通過廣大信息使用者的監督效應抑制管理層的操縱,減少企業舞弊空間[5]。委托代理理論表明,管理層的薪酬、個人聲譽等私人目的和公司利益相矛盾的情況會使經理人存在操縱財報的行為,信息披露真實性因此下降[5],這成為ESG評級分歧的重要誘因。分行業信息披露要求企業披露更多實質性經營指標,可以從源頭上降低語調操縱的空間[23]。對于分析師等更為專業的信息接受者,分析師在進行財務分析和發布研究報告時,越來越多地將ESG因素納入考量范圍,這不僅是因為投資者對ESG的關注度提高,還因為監管機構和市場對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逐漸增強,其評級等級也與分析師行為息息相關[24],分行業信息披露后分析師更能通過行業的橫向對比,知悉企業經營中的異常行為和識別出利于投資者進行決策的經營風險,從而抑制粉飾行為。上述邏輯如圖1中驅動機制2中的“2”所示。基于此,ESG評級機構可以突破經理人語調操縱的限制,使各ESG評級機構的分歧減少。
據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分行業信息披露能降低ESG評級分歧。
H2:分行業信息披露能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進而降低ESG評級分歧。
H3:分行業信息披露能抑制管理層語調操縱,進而降低ESG評級分歧。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2011—202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參考王東升等[25]的做法,根據是否受到政策影響區分對照組和實驗組,以此構建雙重差分模型。其中上市公司數據來自CSMAR和WIND數據庫以及各ESG評級機構官方網站。在整理數據時,本研究剔除了:金融、保險業樣本;ST、*ST以及資不抵債的樣本;主要數據缺失的樣本。連續變量在上下1%處進行了縮尾處理。
(二)模型構建與變量定義
參考王東升等[25]的做法,構建如下雙重差分模型。
Disi,t=β0+β1DIDi,t+β2Controlsi,t+Year+Firm+εi,t(1)
其中:DID表示公司i在第t年是否受行業信息披露指引影響;Dis表示ESG評級分歧,由于不同機構ESG評級開展時間不一致,主流評級機構中部分機構數據起始時間較遲,為保證研究具有充足的樣本,本文參考劉向強等[26]的做法,采用華證、彭博、和訊評級機構的百分制評級的標準差作為本文被解釋變量。
另外,模型1中,Controls為控制變量,Year為年份固定效應,Firm為個體固定效應。具體的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公司規模(Size),公司總資產的對數;資產收益率(Roa),年末凈利潤與總資產的比率;企業年齡(FirmAge),企業成立年數的對數值;資產負債率(Lev),年末負債總額/年末總資產;公司成長性(Growth),營業收入增長額/基期營業收入;是否虧損(Loss),年末凈利潤小于0取1,否則取0;董事會規模(Board),董事會人數的自然對數;獨立董事占比(Indep),獨立董事人數/董事會人數;兩職合一(Dual),若董事長和總經理“兩職合一”,Dual取1,否則取0;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第一大股東持股數量/總股數;賬面市值比(BM),凈資產/市值;企業價值(TobinQ),市值/總資產;是否采用四大會計師事務所(Big4),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取1,否則取0。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1報告了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由表1可知,變量DID的均值在0.28左右,表明樣本期間共有28%左右的樣本受到了分行業信息披露的影響,與已有研究相近。
(二)基準回歸結果
表2報告了本文的基準回歸結果,所有回歸都控制了年份固定效應和個體固定效應。列(1)、列(2)顯示交乘項DID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數,無論是否增加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分行業信息披露都降低了ESG評級分歧,H1得到驗證。
(三)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為研究本次雙重差分模型是否滿足平行趨勢檢驗,本文繪制了平行趨勢檢驗的多期動態效應圖(圖2),橫坐標-1、-2等分別表示政策實施前1年、實施前2年。如圖2所示結果,政策前虛擬變量沒有在統計學意義上顯著,說明了分行業信息披露政策實施前兩組ESG評級分歧差異不明顯,符合本文雙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條件。
2.安慰劑檢驗。為了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影響,本文進行了安慰劑檢驗,重復檢驗對因變量的影響,圖3顯示了上述重復過程定在1 000次的T值核密度圖,相關虛擬回歸系數的T值接近0且符合正態分布,多數回歸結果不顯著,意味著本次雙重差分模型得出的結論比較穩健。
3.其他穩健性檢驗。考慮到受政策影響的處理組和對照組可能不是隨機選擇的,因而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本文將PSM模型引入到研究模型中,使用配對后的樣本進行回歸。表3列(1)報告了PSM-DID的回歸結果;考慮到標準化可以保證計算標準差時各評級機構得分量綱相近,本文將ESG不同機構的評級進行z值標準化處理后,再計算評級分歧(標準差和極差),估計結果見表3列(2)和列(3);考慮到分歧也可能來源于ESG評級機構的權重賦予差異,因此本文采用改變ESG評級機構數量的方法重新計算分歧進行回歸:剔除和訊評級后對評級結果進行標準化,再計算極差,相關估計結果見表3列(4);本文注意到,滬深兩市在2013年出現重大變化,可能對本研究因變量ESG評級分歧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需要排除這一變動帶來的影響,其中2013—2021年樣本的估計結果見表3列(5);本文注意到,有國外學者質疑了多時點DID可能在雙向固定效應(TWFE)下存在偏誤問題,本文又進行了Bacon分解,結果顯示,進行Bacon分解后,可能存在偏誤的處理效應權重僅為16.84%;考慮到政策效應所造成的財報改變可能在政策發布后一年對ESG評級分歧產生影響,本文重新將分行業信息披露與t+1期的ESG評級分歧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列(6)。上述結果表明本文結論成立。
五、進一步研究
(一)機制檢驗
1.分行業信息披露的規范效應:通過提升公司透明度抑制ESG評級分歧。行業信息披露指引不僅要求企業增加行業橫向方面經營成果披露,還直接增加了可供投資者和ESG評級機構使用理解的信息凈含量,從而使ESG評級機構可以更加高效地評價企業真實表現,進而降低ESG評級分歧。因此,本文借鑒王亞平等[27]的做法構建公司透明度(Opaque)指標(負向變量)。表4列(1)和列(2)顯示了公司信息透明度機制檢驗結果。列(1)所示,DID與Opaque的回歸系數為-0.016且在1%水平上顯著;列(2)顯示Opaque與Dis的系數為0.865,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上述檢驗結果證實,分行業信息披露對ESG評級分歧的影響是通過提升公司透明度這一路徑實現的,H2得以證明。
2.分行業信息披露的監督效應:通過減少管理層語調操縱抑制ESG評級分歧。分行業信息披露作為增加信息數量與質量的指導性政策,其信息溢出到投資者、分析師、ESG評級機構時,這些相關方也會直接形成對公司的監督。ESG評級機構作為更為專業的信息使用者,其更能通過行業的橫向對比,知悉企業經營中的異常行為和識別出利于投資者進行決策的經營風險,從而從主觀操縱動機和客觀操縱空間兩方面抑制委托代理矛盾帶來的粉飾行為。本文借鑒Price et al.[28]的方法通過模型2進行OLS回歸,用殘差表示管理層語調操縱程度(ABTONE)。
TONEi,t=β0+β1ROAi,t+β2RETi,t+β3SIZEi,t+β4BTMi,t+
β5STD_RETi,t+β6STDROAi,t+β7AGEi,t+β8LOSSi,t+
β9DROAi,t+εi,t (2)
表4列(3)和列(4)顯示了管理層語調操縱的作用機制檢驗結果。由列(3)可見,ABTONE與DID的系數為-0.02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由列(4)可知,管理層語調操縱與ESG評級分歧的系數為0.813,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上述回歸結果證明,分行業信息披露政策對ESG評級分歧的抑制作用也可以通過抑制管理層語調操縱這個路徑實現,驗證了H3。
(二)異質性分析
1.內部控制水平的影響。內部控制水平比較高的公司,其本身信息披露就更加規范和完善,ESG評級機構對其有更為真實和全面的認識,從而政策的邊際效應也相對較小。基于上述討論,本文預期內部控制質量較低的公司其政策效應更為顯著。本文利用迪博內部控制指數(IC)進行分組,根據內部控制指數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兩組,內部控制質量指數大于等于中位數的組為內部控制水平較高組,其余為內部控制水平較低組。如表5所示,列(1)DID的系數不顯著,但在列(2)中,內部控制質量較低組分行業信息披露虛擬變量和ESG評級分歧的回歸系數為-0.482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證明上述結論成立。
2.分析師關注的影響。分析師關注較少的企業,其受到的專業解讀也較少,分行業信息披露通過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抑制管理層語調操縱,使投資者和ESG評級機構更能輕易理解企業經營性信息,因此政策可能對此類企業改善ESG評級分歧的效應更為顯著。本文參考丘心穎等[29]的做法,利用該年內該公司分析師(團隊)跟蹤數量加1取對數衡量分析師關注度(Analyst),按是否高于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分析師關注度較高組和分析師關注度較低組。表5列(3)顯示,分析師關注度較高的組其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系數并不顯著,而在列(4)中,分析師關注度較低組其分行業信息披露與ESG評級分歧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在經過組間系數差異檢驗后,抽樣1 000次顯示的結果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分析師關注度較高和較低的樣本組存在顯著的差異。
3.碳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碳信息披露是企業通過年報、社會責任報告等形式,向外界詳細說明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采取的環境戰略及實施的環保和排污措施[30]。對碳信息披露質量較差的公司,由于行業信息披露將ESG理念寫入指引修訂要求,政策更加注重關于環境治理的信息,在政策實施后,碳信息披露質量較差的公司會受到更多效應影響,ESG評級機構對其“E”項得分的評估也更為準確。本文參考吳育輝等[31]的研究,得到碳信息披露質量(Score),該值越高說明碳信息披露質量越高。本研究按照碳信息披露質量的中位數分組,在表5列(5)、列(6)中,碳信息披露質量較高組分行業信息披露和ESG評級分歧的系數不顯著,但在碳信息披露較低組該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政策對改善ESG評級分歧的作用主要在碳信息披露質量本身較低的公司中體現。
六、拓展性分析
(一)分行業信息披露與單項指標評級分歧
為進一步探究政策對單項指標評級分歧的影響,參考劉向強等[26]的做法,將各機構的ESG評級拆分為“E”“S”“G”三個維度,并根據其得分進行標準化處理進而計算單項指標的分歧:Dis_E、Dis_S、Dis_G。表6報告了基于“E”“S”“G”單項分歧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僅有“G”指標的分歧(Dis_G)在5%的水平上顯著,因此分行業信息披露更多地減少了公司治理層面中各機構的評級分歧。這是由于政策對商業模式、競爭地位、經營風險與成果信息披露有大量要求,而這些經營性信息的披露促使企業更多專注于主業活動和公司治理,因此分行業信息披露可以使企業公司治理層面的信息更多向ESG評級機構溢出,從而降低該維度的ESG評級分歧。
(二)基于“E”“S”維度
基于異質性分析部分對分行業信息披露的討論,分行業信息披露對于一些非重點領域的行業企業可能有政策的“托底”作用,即對于一些“E”“S”領域信息受關注較少的行業,其信息的披露會在政策實施后具有更為顯著的影響。基于此,本文選擇是否為重污染行業進行“E”“S”維度的異質性分析:對于“E”維度,重污染行業由于眾多環境規制的存在,其“E”維度信息更為透明,政策影響也較小;對于“S”維度,重污染行業所包含的民用爆破行業、化工等行業發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可能性較大,其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也會受到較多關注,其“S”維度信息質量也就較高,政策影響也就較小。表6報告了基于“E”“S”維度與行業的異質性分析,非重污染行業的“E”“S”維度均在5%和10%的水平顯著為負,較重污染行業更為顯著,驗證了上述討論。
七、結論與啟示
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完善導致底層數據缺失,ESG評級分歧現象仍然存在,目前鮮有學者研究抑制ESG評級分歧的外生沖擊。同時,ESG信息存在較為明顯的行業特征,分行業對ESG信息進行規范理應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關注焦點。本文注意到,滬深兩市從2013年開始分批次、分行業發布行業信息披露指引,本文利用雙重差分模型,證明了分行業信息披露可以抑制ESG評級分歧。機制檢驗表明,分行業信息披露的規范和監督效應抑制了企業信息不透明度和管理層語調操縱,從而降低了該公司的ESG評級分歧。異質性檢驗發現,內部控制質量較低、分析師關注較少、碳信息披露質量較差的公司,政策對其ESG評級分歧的抑制作用更大。拓展性分析發現,政策主要影響“G”維度的評級分歧;較重污染企業,非重污染企業“E”“S”維度的分歧受政策影響更大。本研究為ESG信息按行業特征制定標準提供了經驗證據,但也存在部分不足,如:ESG評級的分歧并不一定是負面的現象,相反這種分歧可能為投資者帶來更多參考,未來研究可以在積極對ESG評級分歧溯因的基礎上,增加對ESG評級分歧更多樣的評價。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啟示如下:第一,我國應該繼續依據中國式現代化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強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升分行業信息披露的針對性、時效性并優化ESG信息披露,促使企業完善綠色治理機制和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第二,監管部門應加快建設分行業標準的ESG評級體系,促使ESG評級機構采用更加科學和客觀的評級指標,使ESG信息披露形成行業自律。由于目前ESG評級仍受到評級機構自身情況的影響,應限制資本市場的ESG評級投機行為,防止其評級權威性下降。第三,我國資本市場監管部門應強化規范并鼓勵社會監督,保障上市公司透明度的持續提高,減少管理層語調操縱空間。以投資者需求為出發點,有效促進上市公司信息對投資者公開透明;通過全社會的監督作用減少管理者舞弊行為,抑制管理層語調操縱,及時識別經營風險,著力推動上市公司整體信息披露質量邁上新臺階。
【參考文獻】
[1] 解學梅,韓宇航.本土制造業企業如何在綠色創新中實現“華麗轉型”:基于注意力基礎觀的多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2(3):76-106.
[2] 韓靜,羊顏.組織冗余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研究——來自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會計之友,2024(13):22-30.
[3] 谷豐,王越卓,姜煜,等.ESG表現、研發投入與企業競爭力[J].會計之友,2024(14):90-97.
[4] 巴曙松,張帥.ESG評價領域的共識與分歧[J].北大金融評論,2023(3):69-72.
[5] 趙玲,黃昊.信息披露模式變遷與股價崩盤風險——基于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發布的證據[J].財經論叢,2022(7):79-89.
[6] 王運陳,楊若熠,賀康,等.數字化轉型能提升企業ESG表現嗎?——基于合法性理論與信息不對稱理論的研究[J].證券市場導報,2023(7):14-25.
[7] 蔣藝翅,姚樹潔.ESG信息披露、外部關注與企業風險[J].系統管理學報,2024,33(1):214-229.
[8] KOTSANTONIS S,SERAFEIM G.Four things no one will tell you about ESG data[J].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2019,31(2):50-58.
[9] ABHAYAWANSA S,TYAGI S.Sustainable investing:the black box of 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ESG) ratings[J].The Journal of Wealth Management,2021,24(1):49-54.
[10] CHRISTENSEN D G,SERAFEIM A SIKOCHI. Why is corporate virtue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case of ESG ratings[J].The Accounting Review,2022,97,147-175.
[11] BERG F,K?魻LBEL J F,RIGOBON R.Aggregate confusion:the divergence of ESG ratings[J].Review of Finance,2022,26(6):1315-1344.
[12] DIMSON E,MARSH P,STAUNTON M.Divergent ESG ratings[J].The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2020,47(1):75-87.
[13] BILLIO M,COSTOLA M,HRISTOVA I.Inside the ESG ratings: (Dis)agreement and performance[J].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1,28(5):1426-1445.
[14] LOPEZ C,CONTRERAS O,BENDIX J.Disagreement among ESG rating agencies:shall we be worried?[D].MPRA Paper,2020.
[15] LIANG H,RENNEBOOG L.On the foundat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7,72(2):853-910.
[16] 馬文杰,余伯健.企業所有權屬性與中外ESG評級分歧[J].財經研究,2023,49(6):124-136.
[17] BURGIN M.Theory of information:fundamentality,diversity and unification[M].Hackensack: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2010.
[18] 張■,張靜嫻.ESG對會計信息可比性影響的雙路徑機制研究[J].會計之友,2024(9):73-81.
[19] 韓一鳴,胡潔,于憲榮.企業數字化轉型與ESG評級分歧[J].財經論叢,2024(7):59-69.
[20] FORSSBAECK J,OXELEHEIM L.The Oxford hand-
book of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transparenc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21] 黃昊,趙玲.分行業信息披露與審計質量——基于一項“準自然實驗”的研究[J].審計研究,2023(3):136-147.
[22] 李曉,張家慧,王彥超.分行業信息披露監管對審計師的溢出效應——基于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發布的證據[J].審計研究,2022(5):95-105.
[23] 林鐘高,劉文慶.信息披露監管模式變更影響企業投資效率嗎?——基于雙重差分模型的實證檢驗[J].財經理論與實踐,2022,43(4):67-77.
[24] 熊浩,侯瑞琳,侯菲.公司ESG評級有助于提高分析師預測準確性嗎[J].會計之友,2023(18):98-105.
[25] 王東升,李鵬偉,薛海燕.分行業信息披露能抑制管理層短視嗎——基于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發布的準自然實驗[J].會計之友,2024(11):63-71.
[26] 劉向強,楊晴晴,胡■.ESG評級分歧與股價同步性[J].中國軟科學,2023(8):108-120.
[27] 王亞平,劉慧龍,吳聯生.信息透明度、機構投資者與股價同步性[J].金融研究,2009(12):162-174.
[28] PRICE M K,DORAN J,PETERSON D R.Earnings conference calls and stock returns:the incremental informativeness of textual tone[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2,36(4):992-1011.
[29] 丘心穎,鄭小翠,鄧可斌.分析師能有效發揮專業解讀信息的作用嗎?——基于漢字年報復雜性指標的研究[J].經濟學(季刊),2016,15(4):1483-1506.
[30] 王彥林,張子璇,蓋玉風.“雙碳”與企業碳會計信息披露質量影響因素——基于鋼鐵板塊上市企業的實證研究[J].會計之友,2023(9):51-57.
[31] 吳育輝,田亞男,管柯琴.碳信息披露與債券信用利差[J].管理科學,2022,35(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