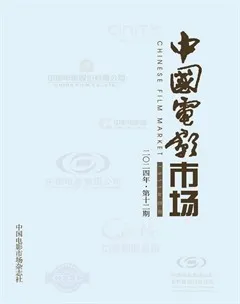中國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網(wǎng)感”特征的計(jì)量分析
【摘要】數(shù)字人文的出現(xiàn),為電影研究開啟了嶄新的視角。本文使用Python (計(jì)算機(jī)編程語言)等工具,利用計(jì)量電影學(xué)的方法分析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網(wǎng)感”特征的形成,迫近“網(wǎng)感”的本質(zhì)。通過篩選2018—2023年具有代表性的網(wǎng)絡(luò)大電影作品樣本,從敘事節(jié)奏、景別功能、色彩結(jié)構(gòu)等方面拆解其網(wǎng)感特征。其中,“網(wǎng)感”的形成離不開視聽語言組合形態(tài)的作用。快速拼貼與碎片縫合的鏡頭序列引發(fā)對“網(wǎng)感”節(jié)奏的再度思考,高純低明與重疊同質(zhì)的色彩結(jié)構(gòu)為“網(wǎng)感”的模糊化與同質(zhì)化傾向提供了隱性對話的機(jī)會(huì),近景快感與全景隱匿揭示了“網(wǎng)感”的去中心化趨勢及其與青年亞文化認(rèn)同的聯(lián)系。
【關(guān)鍵詞】計(jì)量電影學(xué) 網(wǎng)絡(luò)大電影 “網(wǎng)感” 視聽語言
[課題項(xiàng)目]電子商務(wù)福建省高校應(yīng)用技術(shù)工程中心2022年度開放課題重點(diǎn)項(xiàng)目“計(jì)量電影學(xué)視域下的中國網(wǎng)絡(luò)電影研究”(項(xiàng)目編號: DZSW22-03)階段性成果。
網(wǎng)絡(luò)大電影是專為網(wǎng)絡(luò)生產(chǎn)和發(fā)行,以網(wǎng)絡(luò)分賬為主要盈利方式,在各個(gè)新媒體終端放映的完整敘事性視聽藝術(shù)作品。[1]2018年,網(wǎng)絡(luò)大電影開始邁向精品化、系列化的發(fā)展軌道,其獨(dú)特的網(wǎng)絡(luò)特性與商業(yè)屬性共同構(gòu)筑了其核心特質(zhì)。其中,網(wǎng)絡(luò)特性成為與傳統(tǒng)院線電影最顯著的區(qū)分點(diǎn)。這一屬性不僅使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繼承了傳統(tǒng)院線電影的文化傳播、娛樂宣傳等功能,更重要的是,網(wǎng)絡(luò)大電影憑借其獨(dú)特的觀眾點(diǎn)擊欲(前6分鐘)[2]和即時(shí)性、交互性的網(wǎng)絡(luò)特性,發(fā)展出一套獨(dú)立的生產(chǎn)運(yùn)行機(jī)制,呈現(xiàn)出與傳統(tǒng)院線電影明顯不同的一種觀看特征。有人將其稱為“網(wǎng)感”。然而,時(shí)至今日,網(wǎng)感還沒有一個(gè)明確的定義。廣義上的“網(wǎng)感”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中,生產(chǎn)者、傳播者、接受者針對網(wǎng)絡(luò)媒介、文化、形象等不同內(nèi)容而產(chǎn)生的具體觀感、體感以及綜合感知。狹義上的“網(wǎng)感”往往立足于網(wǎng)民視角,指代具有網(wǎng)絡(luò)化、碎片化、現(xiàn)代化的審美體驗(yàn)過程及交互反饋活動(dòng)等。中國電視劇制作產(chǎn)業(yè)協(xié)會(huì)秘書長王鵬舉對“網(wǎng)感”一詞曾作出解釋,他認(rèn)為網(wǎng)感是對市場、對年輕人的思維和欣賞習(xí)慣的敏銳追蹤,或者說是適應(yīng)。[3]本文使用“網(wǎng)感”一詞指稱網(wǎng)絡(luò)大電影因?yàn)樯鲜龇N種原因,在文本層面所表現(xiàn)出的不同于傳統(tǒng)院線電影的藝術(shù)特征。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語言模因是“網(wǎng)感”得以產(chǎn)生的基礎(chǔ),組接重構(gòu)的敘事規(guī)則與沖擊閃切的視聽范式成為“網(wǎng)感”的具體表現(xiàn)。[4]因此,視聽語言的組合形態(tài)影響著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網(wǎng)感”的形成。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發(fā)展經(jīng)歷過開端、裂變等時(shí)期,文本數(shù)量的增幅、落幅差異懸殊,卻沒能造就經(jīng)典,反被指責(zé)。現(xiàn)階段,逐漸進(jìn)入精品建設(shè)期的網(wǎng)絡(luò)大電影,需要不斷尋找自身的藝術(shù)風(fēng)格特征,不能以點(diǎn)擊率作為唯一目標(biāo),逐漸擺脫“速朽”的標(biāo)簽。
計(jì)量電影學(xué)基于量化的統(tǒng)計(jì)學(xué)思維,以電影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將定量與定性緊密結(jié)合,主要通過開發(fā)和利用算法及數(shù)據(jù)平臺(tái),結(jié)合多樣化的視覺識(shí)別技術(shù),挖掘電影形式元素的數(shù)據(jù)化與可視化。主要代表人物有巴瑞·索特(Barry Salt)、大衛(wèi)·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尤里·齊維安(Yuri Tsivian)、戈內(nèi)斯·賽維揚(yáng)(Gunars Civjans)等。學(xué)者楊世真認(rèn)為,中國計(jì)量電影學(xué)的發(fā)展,需要擴(kuò)大影片文本種類、形式元素及參數(shù)的提取范圍。其中,他將網(wǎng)絡(luò)電影劃分為需要被擴(kuò)充的影片文本種類。[5]本文便是嘗試用計(jì)量電影的方法,對平均鏡頭時(shí)長、鏡頭的中數(shù)時(shí)長、景別數(shù)量、節(jié)奏樣式,以及色彩分布等進(jìn)行數(shù)量化的統(tǒng)計(jì)和視覺化呈現(xiàn),從而對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網(wǎng)感”特征的形成進(jìn)行量化的解析,以彌補(bǔ)純理論分析的不足和文本形式解析的缺失。依據(jù)貓眼票房榜單、燈塔榜單以及豆瓣評分榜單等的相關(guān)排名(主要以2019—2023年上映作品為主),共計(jì)提取貓眼榜單與燈塔榜單樣本庫影片總量為2361部,調(diào)查影片樣本票房區(qū)間為0萬-5000萬,參照豆瓣評分區(qū)間標(biāo)準(zhǔn)(7-9分為高分段, 5-6分為中分段, 5分以下為低分段)。樣本篩選主要標(biāo)準(zhǔn)為分賬票房數(shù)據(jù),同時(shí)確保樣本涵蓋了豆瓣評分榜單上高、中、低不同評分區(qū)間的電影,最終篩選出《東北警察故事2》《目中無人》《硬漢槍神》《靈魂擺渡:黃泉》《東北警察故事1》《浴血無名川》《興安嶺獵人傳說》《狙擊之王》《奇門遁甲2》《四平警事之尖峰時(shí)刻》《惡到必除》《陰陽鎮(zhèn)怪談》《開棺》《陳情令之生魂》《狄仁杰之飛頭羅剎》《鬼吹燈之南海歸墟》《張三豐》《新逃學(xué)威龍》《重啟之蛇骨佛蛻》《無間風(fēng)暴》等20部網(wǎng)絡(luò)大電影,使用DaVinci Resolve (視頻調(diào)色軟件)、Excel (電子表格軟件)、R語言(計(jì)算機(jī)編程語言)、Python (計(jì)算機(jī)編程語言)、CCKSCinemetrics[6](電影計(jì)量軟件)等計(jì)量工具,統(tǒng)計(jì)每部影片的平均鏡頭時(shí)長、色彩結(jié)構(gòu)、景別(前6分鐘)等形式元素,在此基礎(chǔ)之上形成對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網(wǎng)感”特征的初步認(rèn)識(shí)。由于所選樣本數(shù)量較為有限,以下是有限樣本下的結(jié)果。
一、鏡頭序列的“網(wǎng)感”特性:快速拼貼與碎片縫合
從大眾傳播的角度來說,“網(wǎng)感”強(qiáng)調(diào)關(guān)注網(wǎng)絡(luò)用戶的信息偏好和分享偏好,從而預(yù)測和評估一項(xiàng)內(nèi)容產(chǎn)品能否能帶來網(wǎng)絡(luò)用戶的流量。[7]這也意味著,網(wǎng)生代電影作品受眾群體的審美取向與觀影需求,會(huì)直接影響網(wǎng)絡(luò)大電影內(nèi)容與形式的生產(chǎn)。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視聽語言系統(tǒng)首先需要考慮的便是“網(wǎng)感”的傳達(dá),設(shè)計(jì)不同的視聽范式來吸引更多的流量。鏡頭序列的設(shè)計(jì)首先呈現(xiàn)出的“網(wǎng)感”節(jié)奏往往與速度的感知密不可分。法國哲學(xué)家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io)認(rèn)為:“速度不只是讓我們更舒適快捷地移動(dòng),更重要的是改變我們觀看與構(gòu)思世界的方式。”[8]通過對20部網(wǎng)絡(luò)電影類型關(guān)鍵詞進(jìn)行分析,發(fā)現(xiàn)評分較高的網(wǎng)絡(luò)電影類型多集中于動(dòng)作、犯罪、懸疑。其中,“動(dòng)作+”的“網(wǎng)感”設(shè)定,在不同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榜單中頻繁出現(xiàn)。通過表1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含有動(dòng)作元素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平均鏡頭時(shí)長(ASL)[9]相對較短,普遍時(shí)長在2秒到3秒之間,其中,《東北警察故事1》平均鏡頭時(shí)長已經(jīng)低至1. 71秒。鏡頭的快速拼貼成為一種不可被忽略的事實(shí),這與其文本中動(dòng)作屬性的“網(wǎng)感”偏好具有一定的相關(guān)性。以《東北警察故事2》中的一組鏡頭來看:
鏡頭1: (特寫, 0. 11秒)啤酒瓶被從箱子中拿出,切———
鏡頭2: (中景, 0. 12秒)婚托混混拿起酒瓶砸向李紅旗,切———
鏡頭3: (中景, 0. 17秒)李紅旗轉(zhuǎn)身看到,切———
鏡頭4: (近景, 0. 2秒)李紅旗直接用拳頭打碎啤酒瓶,切———
鏡頭5: (中景, 0. 19秒)李紅旗打碎啤酒瓶,婚托混混被嚇傻,切———
鏡頭6: (近景, 1. 18秒)相親女孩被嚇到擠出正在喝的牛奶
這組鏡頭動(dòng)作呈現(xiàn)被濃縮在較短的時(shí)長之內(nèi),快速給出動(dòng)作場景內(nèi)角色的反應(yīng),相親女孩被嚇到并擠出牛奶的行為反應(yīng)本不屬于動(dòng)作過程中的片段,但是這一反應(yīng)與動(dòng)作結(jié)果進(jìn)行拼貼,使得情感在瞬間得到宣泄,這樣的處理方式,符合“網(wǎng)生代”群體在尋求感官刺激過程中,對速度的審美需求。
細(xì)究表1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從整體的區(qū)間幅度來看, 2018—2023年的中國網(wǎng)絡(luò)電影,整體平均鏡頭時(shí)長的差距并不明顯,不同類型網(wǎng)絡(luò)電影的平均鏡頭時(shí)長也具有趨同性。20部網(wǎng)絡(luò)電影的平均鏡頭時(shí)長為2. 8秒,其中,以動(dòng)作類型為主的網(wǎng)絡(luò)電影平均鏡頭時(shí)長同樣為2. 8秒,以奇幻類型為主的網(wǎng)絡(luò)電影平均鏡頭時(shí)長為2. 96秒,懸疑類型則為2. 84秒,上下浮動(dòng)不超過0. 2秒。評分位列前10名網(wǎng)絡(luò)電影平均鏡頭時(shí)長為2. 605秒,而后10名的網(wǎng)絡(luò)電影平均鏡頭時(shí)長為2. 989秒。從總體趨勢上看,評分較低的影片,平均鏡頭時(shí)長較長;評分較高的影片,平均鏡頭時(shí)長相對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觀眾對于快速節(jié)奏的接納程度愈來愈高,觀看習(xí)慣與審美趨向反作用于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快”,也帶來“看”的方式轉(zhuǎn)變。需要特別提及的是,計(jì)量電影學(xué)領(lǐng)域中諸多學(xué)者提及, ASL的變化并不能完全反映變化趨勢,需結(jié)合MSL (the Median Shot Length)[10]的數(shù)值來綜合討論。MSL是將影片內(nèi)所有鏡頭的時(shí)長按照順序依次排列,取中位數(shù),作為重要的鏡頭數(shù)據(jù)參考。通過統(tǒng)計(jì)20部網(wǎng)絡(luò)電影的MSL的數(shù)值,并與ASL進(jìn)行詳細(xì)對比,可以看到, 20部網(wǎng)絡(luò)電影的MSL值均低于ASL值,《東北警察故事1》的值最小,低至1. 14秒,其次是《狙擊之王》(1. 19秒)和《惡到必除》(1. 19秒)。三部影片的MSL值都低于1. 5秒,對于鏡頭時(shí)長來說,這是一個(gè)相對較小的單位時(shí)長,這也意味著,網(wǎng)絡(luò)大電影開始依靠快速的剪輯節(jié)奏完成文本內(nèi)容,觀眾難以形成延長且專注的審美行為,在游戲化、娛樂化、多元化的雜糅拼貼之下,網(wǎng)絡(luò)大電影逐漸形成具有“網(wǎng)感”基因的鏡頭序列。


此外,將MSL值與ASL值進(jìn)行深入對比(如表2),可以更加直觀地看到鏡頭時(shí)長之間的差異程度。國內(nèi)青年學(xué)者周鼎[11]提出,在進(jìn)行MSL值域觀察的過程中,還須注意各影片鏡頭時(shí)長在四分位距。這也是描述統(tǒng)計(jì)學(xué)中的一種常見方法。按照鏡頭時(shí)長從小到大排序之后,均分四份,由第三四分位數(shù)與第一四分位數(shù)求差而得出四分位距,該數(shù)值反映了中間50%數(shù)據(jù)的離散程度,其值越小,說明中間的數(shù)據(jù)越集中;值越大,說明中間的數(shù)據(jù)越分散。從表2的數(shù)據(jù)中可以發(fā)現(xiàn), 20部網(wǎng)絡(luò)電影四分位距值整體趨于穩(wěn)定,普遍處于1—3之間浮動(dòng)。其中,《東北警察故事1》《東北警察故事2》《浴血無名川》《硬漢槍神》的四分位距值相對較小,都接近于MSL的數(shù)值,這說明四部影片的鏡頭時(shí)長具有一定的集中趨勢,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網(wǎng)絡(luò)電影的動(dòng)作類型作品的鏡頭處于一種強(qiáng)節(jié)奏的運(yùn)動(dòng)狀態(tài),鏡頭與鏡頭的組接快速而頻繁。其中,《狙擊之王》使用了大量快閃鏡頭,最小鏡頭的時(shí)長只有1幀。急速的快閃與音效的配合,能夠讓觀眾對于主人公內(nèi)心的掙扎產(chǎn)生共情。這些碎片式的鏡頭不斷縫合著快節(jié)奏的鏡頭序列,這種看似邊緣的存在,卻支撐著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網(wǎng)感”的跳躍性表達(dá)。同樣在《東北警察故事1》《惡到必除》等影片中也出現(xiàn)了最小鏡頭時(shí)長為1幀的現(xiàn)象。與中國武俠動(dòng)作電影1秒1個(gè)鏡頭的“暴雨剪輯”[12]相比較,這已經(jīng)是“極速閃現(xiàn)”的剪輯節(jié)奏。細(xì)讀不同影片的剪輯節(jié)奏,發(fā)現(xiàn)低于1秒的鏡頭與不同時(shí)長的鏡頭彼此穿插,且散落于整個(gè)影片的不同階段,時(shí)而承接漸進(jìn)性的過渡,時(shí)而凸顯斷裂性的差異。其中,在《硬漢槍神》中,低于1秒的鏡頭511個(gè);《張三豐》中,低于1秒的鏡頭384個(gè)。這些碎片式的鏡頭序列,將不同的敘事元素進(jìn)行拼接,最終,生產(chǎn)出難以凝視的網(wǎng)絡(luò)大電影文本。結(jié)合表1可知,三部電影的評分相對靠前,豆瓣評分都在6分以上。且MSL鏡頭時(shí)長相對較短,說明電影鏡頭時(shí)長集中于MSL所代表的鏡頭時(shí)長。這種快速頻繁的鏡頭節(jié)奏使觀眾的“凝視”不斷被分散、分解、分化,視覺節(jié)奏在消費(fèi)時(shí)代的文化語境下不斷被推動(dòng)著朝向更加快速的方向發(fā)展,伴隨著的是“彈幕”創(chuàng)造出的共時(shí)存在感和即時(shí)評論功能使網(wǎng)絡(luò)電影的娛樂性和隨意性被進(jìn)一步放大。[13]受到擠壓與刺激的影像文本,在奇觀化、淺顯化視覺經(jīng)驗(yàn)的影響下,形成一種無需過度思考的“瀏覽”。


二、色彩結(jié)構(gòu)的“網(wǎng)感”表現(xiàn):高純低明與重疊同質(zhì)
電影色彩作為視聽語言的元素之一,通過彼此之間的互相交錯(cuò)、互文對話,逐漸產(chǎn)生意義的增值或消解的變更。[14]因此,網(wǎng)絡(luò)大電影色彩的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觀眾的“網(wǎng)感”體驗(yàn)。在色彩影響下的“網(wǎng)感”,逐漸走向同質(zhì)化。影片的色彩結(jié)構(gòu)可以通過數(shù)字研究實(shí)現(xiàn)可視化的可能,從而進(jìn)一步辨析出網(wǎng)絡(luò)電影的色調(diào)分布趨勢。通過截取20部網(wǎng)絡(luò)電影每個(gè)鏡頭的中間幀畫面,并使用Python的Scipy、Matplotlib、OpenCV等工具,詳細(xì)分析影片的基礎(chǔ)色彩結(jié)構(gòu),經(jīng)過聚類算法分析后,將圖片從BGR轉(zhuǎn)換到HSV[15]顏色空間,捕捉每幀圖像里最頻繁出現(xiàn)的色相值域,包括場景色彩、空間色彩、道具色彩、服飾色彩、燈光色彩等,并將最終色彩信息繪制成影片色相直方圖。其中, Python的OpenCV庫中, H (色相)的取值范圍為 0—180,其中, 0與180對應(yīng)紅色, 30對應(yīng)黃色, 60對應(yīng)綠色, 90對應(yīng)青色, 120對應(yīng)藍(lán)色, 150對應(yīng)粉色。S (純度)和V (明度)的取值范圍為0—255.其中純度越趨近于零,則表示色彩的鮮艷度愈低,影片的情感基調(diào)相對冷靜。明度越趨近于零,則表示色彩的明度愈黑,影片整體的光調(diào)相對較低,沉悶低落的情緒氛圍愈重。以《硬漢槍神》的色彩結(jié)構(gòu)圖為例,第一個(gè)子圖中不同色相的線譜越長,說明該類色調(diào)在影片中出現(xiàn)頻率越高,色條彼此之間距離越近、越貼合,則表明色調(diào)的分布越集中。由圖可知,《硬漢槍神》的色彩分布純度多分布于100-255區(qū)間,明度多分布于0—150區(qū)間,以黃橙色調(diào)為主,藍(lán)綠色調(diào)相對較低。這與其自身的游戲化敘事視角密不可分。游戲化網(wǎng)絡(luò)電影運(yùn)用跨媒介的敘事方式,形成了一種互文性的文本,并以游戲的方式表現(xiàn)了大千世界與社會(huì)人生以及人物心理等。[16]故事空間場景圍繞射擊競技活動(dòng)展開,色彩以“吃雞”游戲視角體驗(yàn)感的呈現(xiàn)為主,既有對野外破敗蕭瑟生存環(huán)境空間(沙漠、谷地等)的模擬,也涵蓋對射擊過程、游戲道具、戰(zhàn)術(shù)玩法的還原。觀眾也被高純度與低明度的色彩氛圍共同塑造的游戲化空間感所吸引,在凝視游戲文本的過程中,逐漸剝離電影與游戲之間的界限,形成新的“網(wǎng)感”觀感。與《硬漢槍神》的色彩分布具有一定趨同性的是《靈魂擺渡:黃泉》,影片同樣形成高純度與低明度組合的色調(diào)氛圍,以兩大基本色調(diào)“紅黃色調(diào)”與“藍(lán)綠色調(diào)”為主。其中,孟婆與長生于焃鴠日成親時(shí)的場景之內(nèi),謊言即將被揭破,花凝雪化為長生之象,所著的服飾色彩便是飽和度較高的青藍(lán)色。此外,紅黃色調(diào)的使用最為頻繁,色彩明度也相對較暗。與《硬漢槍神》不同的是,影片的故事圍繞世代孟婆的愛恨情仇及命運(yùn)的無奈緩緩展開,與母系社會(huì)中女性權(quán)力機(jī)制的隱性表達(dá)形成外互文。以暖色調(diào)描摹開篇,但并不濃墨重彩,這與女性視角看待悲歡離合的基調(diào)相吻合。“孟婆”作為傳說中的一個(gè)想象性存在,她身為故事的主角,一開場的旁白就與觀眾已有的認(rèn)知零距離吻合。[17]雖然這部影片作為《靈魂擺渡》系列網(wǎng)絡(luò)劇的番外續(xù)寫,與前文本對現(xiàn)實(shí)感的描繪不同,顯在文本更加注重異域感的描摹,荒蕪的孟婆莊(土黃色調(diào)),幽深的冥府(灰黃色調(diào)),都是被逐漸遺忘的角落,對女性生存困境的邊緣化再次形成隱喻。在觀看借助東方志怪文化所塑造的“黃泉世界”情境中,經(jīng)歷經(jīng)典藝術(shù)的互文敘事后,觀眾在具有壓抑感明度的視覺引導(dǎo)下,對陰間與陽界的界限凝視也變得模糊起來。
不同作品中同一類別空間的色調(diào)特征呈現(xiàn)也愈發(fā)重疊。《狙擊之王》《東北警察故事》系列及《四平警事之尖峰時(shí)刻》《無間風(fēng)暴》《開棺》的色相結(jié)構(gòu)分布具有趨同性。這六部電影的色相結(jié)構(gòu)都集中于“紅黃色調(diào)”與“藍(lán)綠色調(diào)”的并行,并都呈現(xiàn)出以藍(lán)綠色調(diào)分布集中的態(tài)勢。且明度都以低沉為主,飽和度以鮮明居多。故事發(fā)生的空間都以現(xiàn)代城市空間為主要載體,雖然地域環(huán)境各不相同,但是塑造城市感的色調(diào)分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東北警察故事》系列的城市空間是具有方向感的構(gòu)塑,角色的服飾中的藍(lán)色與環(huán)境色彩的藍(lán)色加強(qiáng)著“東北”的地域方位感,《四平警事之尖峰時(shí)刻》也同樣使用此類色彩處理方式。《狙擊之王》的城市空間是被邊緣且遺忘的,大面積的藍(lán)色與綠色加重主人公命運(yùn)的失重感與失落感。《無間風(fēng)暴》的城市空間聚焦于港口,無論是道具色彩還是燈光色彩,都運(yùn)用藍(lán)青色來加深邪惡背后的冷酷與殘忍。《開棺》的城市空間被塑造成地上空間與地下空間的并行,輔以大量藍(lán)綠色調(diào)的分布,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割裂感與疏離感。不同的城市空間都被不同層次的藍(lán)綠色調(diào)所描摹,雖然空間彼此獨(dú)立,但相互之間借由色彩這一顯在文本的呈現(xiàn),輔以高飽和與低明度的色彩組合方式,都在加劇網(wǎng)絡(luò)大電影城市空間之間悵惘與異化的隱性對話。
與現(xiàn)代城市空間不同的是,懸疑武俠空間的紅黃色調(diào)占比相對較低,但藍(lán)綠色調(diào)被大量使用,且為主要表達(dá)的色彩空間氛圍。《重啟之蛇骨佛蛻》《張三豐》《鬼吹燈之南海歸墟》《狄仁杰之飛頭羅剎》這4部電影的色彩結(jié)構(gòu)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重啟之蛇骨佛蛻》中的色調(diào)以綠色為主,藍(lán)色為輔,紅黃色調(diào)多出現(xiàn)在原始洞穴場景之內(nèi),飽和度相對較低,清冷克制的視覺畫面與探秘的懸疑情境設(shè)定相互交織,彼此影響。《鬼吹燈之南海歸墟》中亦真亦假的尋寶探險(xiǎn),在深藍(lán)色調(diào)的塑造中,為觀眾帶來奇觀化的想象。《張三豐》中武俠空間透過江湖空間與山林空間的穿插交織,藍(lán)色與綠色的色調(diào)所創(chuàng)造出的疏離感,以及低飽和度的肅清感,正對應(yīng)著游離于秩序之外的文化意蘊(yùn)。《狄仁杰之飛頭羅剎》以神怪武俠為引,大面積的藍(lán)色鋪陳,隱喻著特殊環(huán)境下的廟堂等級。4部電影類型都含有懸疑的元素,故事情節(jié)空間的設(shè)定都圍繞懸疑玄幻或者是動(dòng)作武俠展開,藍(lán)綠色調(diào)的反復(fù)重疊,為未知與隱秘交織的視覺想象埋下伏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網(wǎng)感”色彩表現(xiàn)的同質(zhì)化傾向發(fā)展。
三、副文本的“網(wǎng)感”化傳達(dá):近景快感與全景隱匿
副文本的概念,由法國敘事學(xué)理論家熱拉爾·熱奈特(Gerard Genette)提出,他認(rèn)為副文本是“為文本的解讀提供一種(變化的)氛圍”。[18]一般來說,在院線電影、網(wǎng)大中,海報(bào)、片頭等都是影片的副文本。[19]相比付費(fèi)以后獲得的“正品”,可以把網(wǎng)絡(luò)大電影免費(fèi)的前六分鐘看成廣告型先導(dǎo)片,看為“副文本”。網(wǎng)絡(luò)大電影前六分鐘具有“宣傳”“吸引”的廣告性質(zhì),也真正區(qū)別了院線電影的特質(zhì)。對于院線電影來說,整個(gè)電影是完整的“商品”,買票即交付。對于網(wǎng)大來說,前六分鐘定“生死”,決定是否“買票”,前六分鐘起到廣告效應(yīng)。前六分鐘所呈現(xiàn)的文本形式深受點(diǎn)擊率的影響,而這一副文本所創(chuàng)造的“網(wǎng)感”,似乎已經(jīng)成為觀眾在決定是否繼續(xù)付費(fèi)觀看時(shí)的一個(gè)重要考量因素。副文本所營造的“網(wǎng)感”在不斷滿足著年輕受眾的觀看訴求,去中心化的視聽語言組合形態(tài)也逐漸顯露出來。
因此,研究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前6分鐘,有助于探究激發(fā)觀眾點(diǎn)擊行為的‘網(wǎng)感’特征及其機(jī)制。數(shù)字人文背景下的文本細(xì)讀可被稱為“數(shù)據(jù)細(xì)讀”[20],通過借助CCKS-Cinemetrics (國內(nèi)第一款專用計(jì)量電影研究工具)對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前6分鐘進(jìn)行細(xì)致的景別分析(表3)可以發(fā)現(xiàn):近景鏡頭主要支撐起前6分鐘的視覺表現(xiàn),占據(jù)著相對較高的比例,但是全景鏡頭幾乎處于一種隱匿狀態(tài)。在《興安嶺獵人傳說》《東北警察故事1》《東北警察故事2》《鬼吹燈之南海歸墟》等影片中,近景鏡頭占據(jù)了超過一半的比例,而對應(yīng)的全景鏡頭所占比例還未超過3%。且這些影片逐漸生成一種以近景為核心支點(diǎn),以“近特”為輔助系統(tǒng)的鏡頭語系。這也意味著,網(wǎng)絡(luò)大電影前6分鐘的鏡語體系逐漸轉(zhuǎn)向以近景、特寫鏡頭為主導(dǎo)的沉浸式快感傳達(dá)氛圍之中。主體和客體被框入鏡頭的方式會(huì)產(chǎn)生特定的含義,鏡框中的景別大小就像對話一樣可以表意。[21]近景鏡頭是景別語系中,可以使觀眾的關(guān)注重點(diǎn)從背景轉(zhuǎn)向被攝對象局部、從環(huán)境空間轉(zhuǎn)向動(dòng)作關(guān)系的景別,于接受者而言,相對于全景而言,近景可以更快地拉近觀看距離,制造臨場感,讓觀眾更加容易沉浸于故事敘述的氛圍之中。而“近特”景別語系,可以在有限的時(shí)間內(nèi),營造出具有感官刺激的顯在文本,放大感官的刺激功能,使觀眾近距離地貼近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網(wǎng)感”情境,在快速拼貼與碎片縫合的鏡頭序列等綜合影響下,形成觀看快感,進(jìn)而觸發(fā)點(diǎn)擊購買欲望。


巴瑞·索特曾在分析瑞典導(dǎo)演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電影作品的風(fēng)格時(shí),依據(jù)鏡頭與被攝對象之間的距離來判定鏡頭的類型,全景鏡頭意味著展現(xiàn)被攝對象完整的高度及范圍。[22]但是通過以上數(shù)據(jù),有一個(gè)現(xiàn)象不可以忽視,全景幾乎隱沒于前6分鐘的鏡語體系之中。20部影片中有超過一半的影片,在副文本的呈現(xiàn)過程中,都沒有選用全景鏡頭來完成敘事,引用全景鏡頭最多的也只是借用游戲化的視角來模擬戰(zhàn)斗情境的《硬漢槍神》,這也表明全知視角逐漸進(jìn)入沉默狀態(tài),被攝對象呈現(xiàn)的完整性被忽略。經(jīng)由銀幕到屏幕的網(wǎng)絡(luò)大電影,其顯在文本視覺風(fēng)格的轉(zhuǎn)變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結(jié)果。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開篇開始抗拒全知視角的代入,吸引觀眾真正點(diǎn)擊觀看的要素,不再是客觀全面的聚焦講述,而是片段式的拆分、消解,局部的暴力、懸疑、血腥等感官的刺激成為點(diǎn)擊欲的開關(guān)。這種現(xiàn)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觀眾觀看視角與觀看距離的改變。在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開篇段落中,全景鏡頭已經(jīng)無法滿足青年亞文化急需宣泄個(gè)人情感的精神訴求,全面客觀的中心表達(dá)不再吸引隸屬于“網(wǎng)生代”的觀眾群體,“敘述性”的景別系統(tǒng)不再適應(yīng)于具有反叛性、消解性的“網(wǎng)感”氛圍,全景的隱匿也成了一種必然選擇。在點(diǎn)擊欲主導(dǎo)的盈利模式下,視覺權(quán)力愈發(fā)回歸到觀眾手中。如何在最短時(shí)間內(nèi)引導(dǎo)觀眾進(jìn)入購買階段,是影響網(wǎng)絡(luò)大電影風(fēng)格塑造的重要因子。因此,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前6分鐘,不再以傳統(tǒng)的敘述為主要任務(wù),反而更注重視覺的奇觀化表現(xiàn)。統(tǒng)一、完整的故事氛圍,有距離感的主人公對于網(wǎng)絡(luò)觀眾而言的吸引力不復(fù)存在。恰恰相反,局部、破碎的想象空間,與觀眾近乎“零距離”的草根角色,在“近特”景別系統(tǒng)的強(qiáng)勢渲染下,讓網(wǎng)絡(luò)觀眾沉浸于“網(wǎng)感”化審美體驗(yàn)之中。但是,近景鏡頭所創(chuàng)造的快感與全景鏡頭逐55497304eb9bde1e7d18372bae5729bd665b076193fccec63fec10ce0fc1642e漸隱匿的氛圍,也間接導(dǎo)致觀眾對于電影思考停留的時(shí)間、空間被壓縮,對于敘事與情感的統(tǒng)一性感知被忽略。在觀影環(huán)境以及技術(shù)產(chǎn)物(倍速播放)的雙重影響下,“網(wǎng)生代”觀眾群體追求“短、平、快”的觀影習(xí)慣于潛移默化之中生成,卻也導(dǎo)致網(wǎng)絡(luò)大電影不斷被觀看,無法被銘記。
四、結(jié)語
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網(wǎng)感”經(jīng)由視聽語言組合形態(tài)的動(dòng)態(tài)重組,日益顯現(xiàn)出快感與碎片并置、模糊與同質(zhì)糅合、直觀與消解摻雜的趨向。其中,“網(wǎng)感”的節(jié)奏依托于鏡頭序列來呈現(xiàn),在快速拼貼與碎片縫合的聯(lián)合作用下,逐漸被渲染成無需過度用腦思考的“瀏覽”。“網(wǎng)感”的模糊化與同質(zhì)化傾向出現(xiàn)在色彩結(jié)構(gòu)之中,逐漸形成一種“異曲同工”的單向重疊。“網(wǎng)感”的去中心化趨勢在前6分鐘副文本的景別設(shè)計(jì)之中顯得尤為突出,在近景快感與全景隱匿的感官刺激下,不斷回應(yīng)著“網(wǎng)生代”觀眾對青年亞文化的認(rèn)同。在拼貼縫合、模糊重疊、淡化中心等合力的作用下,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網(wǎng)感”逐漸成為一種復(fù)雜的綜合觀感。這種觀感,既映射出年輕化、情緒化的審美偏好,又不斷重塑著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生產(chǎn)機(jī)制。計(jì)量電影學(xué)所帶來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拓展著網(wǎng)絡(luò)大電影文本基因測序的手段和路徑。計(jì)量的過程以及經(jīng)歷,甚至計(jì)量的本體都不是最終的目的,實(shí)現(xiàn)藝術(shù)與技術(shù)的雙向融合與擁抱才是每一個(gè)人文學(xué)科研究者所堅(jiān)持的意義。與此同時(shí),需要時(shí)刻警醒,要及時(shí)避免研究落入單一的形式化、扁平化陷阱之中,唯有不斷思辨理論與實(shí)踐之間的關(guān)系,才能真正促進(jìn)中國電影史學(xué)研究范式的轉(zhuǎn)型與突破,正如法國學(xué)者喬治·迪迪-于貝爾曼(Georges Didi-Huberman)所言:“理論從來不會(huì)脫離實(shí)踐,也不會(huì)脫離體現(xiàn)理論的具體事物。”[23]
注釋
[1]曹娟,張鵬.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身份界定、生產(chǎn)機(jī)制與類型化特征[J]. 當(dāng)代電影, 2017, (08): 132-135.
[2]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前6分鐘具體指代視頻平臺(tái)設(shè)定的免費(fèi)試看的時(shí)間區(qū)域。
[3]黃啟哲.“網(wǎng)感”正悄悄改變中國電視編劇[J]. 文匯報(bào), 2016, (6).
[4]馬英新.分蘗與湊泊———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網(wǎng)感”的語言基底[J].電影文學(xué), 2023, (03): 115-119.
[5]楊世真.計(jì)量電影學(xué)的理論、方法與應(yīng)用[J].
當(dāng)代電影, 2019, (11): 32-38.
[6] CCKS-Cinemetrics,別名PyCinemetrics。由中國傳媒大學(xué)李春芳教授團(tuán)隊(duì)研發(fā),可針對電影平均鏡頭時(shí)長、節(jié)奏分布、字幕、景別、物體提取、色彩等進(jìn)行深度詳細(xì)的計(jì)量分析。
[7]趙云澤,曾雷霄.“網(wǎng)感”: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下媒介內(nèi)容價(jià)值要素分析[J].當(dāng)代傳播, 2023, (06): 19-25+38.
[8] [法]保羅·維利里奧.消失的美學(xué)[M].楊凱麟,編譯.鄭州: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 2018: 9.
[9] ASL,平均鏡頭時(shí)長。是影片的總時(shí)長,除以全片有效鏡頭總數(shù),最終所得到的結(jié)果。平均鏡頭時(shí)長數(shù)值越大,意味著影片節(jié)奏逐漸變緩,平均鏡頭時(shí)長數(shù)值越小,意味著影片節(jié)奏逐漸加快。但易受到鏡頭時(shí)長數(shù)值中部分存在的極端數(shù)據(jù)影響,例如長鏡頭等。
[10] MSL,中位數(shù)時(shí)長。是將影片所有鏡頭的時(shí)長,按照從小到大依次排列后,取所有鏡頭時(shí)長數(shù)列的中位數(shù)。不受極端值影響,常與ASL結(jié)合進(jìn)行判斷影片節(jié)奏。
[11]周鼎.后疫情時(shí)代的青年視覺形象變遷(2019—2022)———計(jì)量電影學(xué)視角下的情節(jié)量化分析[J].電影文學(xué), 2023, (18): 98-103.
[12]賈磊磊.“暴雨剪輯”中國武俠動(dòng)作電影的剪輯技巧及“標(biāo)志性”節(jié)奏[J].北京電影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2005,(04): 52-56.
[13]崔文龍.“凝視”的轉(zhuǎn)向:審視中國網(wǎng)絡(luò)電影的一種視角[J].電影評介, 2020, (22): 80-85.
[14]王燕子.電影色彩的互文性[ J].藝苑, 2010,(03): 19-22.
[15] HSV (Hue, Saturation, Value)是由阿爾維·雷·史密斯(Alvy Ray Smith)在1978年提出的一種顏色空間,也稱六角錐體模型。
[16]張智華,宿瑛倫.游戲化網(wǎng)絡(luò)電影的價(jià)值表達(dá)與敘事機(jī)制———以《硬漢槍神》為例[ J].藝術(shù)廣角, 2022, (02): 47-52.
[17]彭翠,畢光明.傳播符號學(xué)視域下網(wǎng)絡(luò)電影的價(jià)值面向———以《靈魂擺渡·黃泉》為例[J].長江文藝評論, 2020, (05): 52-59.
[18] [法]熱拉爾·熱奈特.熱奈特論文集[M].史忠義,編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1: 71.
[19]齊偉,王笑.寄生性、偽網(wǎng)感與點(diǎn)擊欲 當(dāng)前網(wǎng)絡(luò)大電影的產(chǎn)業(yè)與文化探析[J].北京電影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2017, (05): 9-14.
[20]喬潔瓊.重寫電影史視域下史東山電影風(fēng)格的計(jì)量學(xué)考察[J].當(dāng)代電影, 2023, (04): 53-62.
[21] [美]蘇珊·海沃德.電影研究關(guān)鍵詞[M].鄒贊,孫柏,李玥陽,編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2013: 204.
[22] Salt B. The style of Ingmar Bergman?s films [J]. New Review of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es, 2020, 18 (2): 127-150.
[23] [法]喬治·迪迪-于貝爾曼.《影像·歷史·詩歌:關(guān)于愛森斯坦的三場視覺藝術(shù)講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