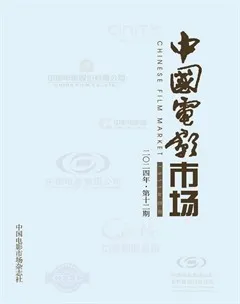一幅20世紀(jì)江西電影歷史拼圖
沈魯教授擁有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學(xué)科背景,這讓他在面對歷史研究時先天地?fù)碛杏^照當(dāng)下的意識。《江西電影史》描述了“歷史深處的江西電影風(fēng)景”,勾勒了一個個具有濃郁贛鄱文化精神氣息的電影現(xiàn)象,是一次構(gòu)建江西電影史料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嘗試,也是一次“在地”電影研究者“之所從來,明其所往”的深情打撈。
讀者對于一本電影史理論著作的要求不會停留在梳理和呈現(xiàn),而是深刻的創(chuàng)見、一針見血的提煉、對一時一地整體藝術(shù)風(fēng)貌的捕捉。本書不會辜負(fù)讀者,它的一大貢獻是對一時期的江西區(qū)域電影特色做了較深刻的總結(jié)概括。比如,讀完第三章“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江西電影”,從楊佩瑾、畢必成、王一民到張剛,讀者可以輕易捕捉到1980年代江西電影創(chuàng)作的整體風(fēng)貌———契合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電影美學(xué)的時代主題,積極探索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表達,紛紛擁抱強調(diào)主體性和社會責(zé)任感的現(xiàn)實主義電影美學(xué),深層文化心理上均具有強烈的鄉(xiāng)土認(rèn)同,審美情趣上注重對江西優(yōu)美自然景觀的呈現(xiàn),主題意蘊上注重揭示傳統(tǒng)倫理的人情美和心靈美。這些都彰顯了論者的功力。
本書最打動我的是它的不拘泥和對普通讀者的赤誠之心。正如電影直面觀眾、無須中介,這本電影史研究專著也沒有對非專業(yè)讀者設(shè)置晦澀的閱讀門檻或理論架構(gòu)。它的語言開闔有度,對電影創(chuàng)作的解析動情。它一改不少史論研究專著中措辭的謹(jǐn)慎,敢于袒露個人觀點和批評的鋒芒,讓書寫有了誠懇,也增添了幾分可貴的生動氣息。
首先,它提供了較廣闊的鮮明文化史研究視野。比如,在第一章《電影進入江西:放映業(yè)的肇始》一節(jié),讀者可以從翔實的文化史考證和配圖中真切地感知九江過往的傳教士傳統(tǒng)和中西文化交流風(fēng)氣之盛,可以清晰地拾掇起我們熟悉的百花洲、八一公園等地標(biāo)上百年來流動的電影故事及城市文化生活集體記憶,也就解答了為什么江西電影最早在九江落地生根,又在南昌風(fēng)靡一時;又如《論改革開放四十年國產(chǎn)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的審美流變》一篇,從“南昌建軍”這一題材40年間的創(chuàng)作美學(xué)變遷為切入點,讀者得以管窺當(dāng)代主旋律電影中的美學(xué)嬗變及大眾文化傳播中的接受心理軌跡。
其次,對當(dāng)下江西電影發(fā)展的經(jīng)年關(guān)注,以及對江西電影未來可能性的滿腔希冀,讓本書有了風(fēng)骨。不妨試著從后半部往前讀。論者在史料研究和對近年來江西電影細(xì)致耙梳的基礎(chǔ)上,對江西電影文化心態(tài)上偏狹的觀察鞭辟入里,也不回避江西電影創(chuàng)作新一代領(lǐng)軍人物缺失、內(nèi)容創(chuàng)作同質(zhì)化、過度重視教化功能等問題,能結(jié)合當(dāng)下江西電影產(chǎn)業(yè)困境提出組建聚焦于電影技術(shù)與產(chǎn)業(yè)的二級學(xué)院,打造教、研、創(chuàng)作實踐為一體的電影人才培養(yǎng)創(chuàng)新基地的構(gòu)想,并基于當(dāng)下江西電影內(nèi)容創(chuàng)作現(xiàn)狀提出創(chuàng)作應(yīng)有更普遍價值立場的人性和情感書寫、應(yīng)經(jīng)受得起時間考驗的江西電影“藍色論”,展現(xiàn)出積極投身江西電影“現(xiàn)場”后的理性洞察。從某種角度看,本書亦是一面對江西電影有積極現(xiàn)實意義的“正衣鏡”。
本書還是一幅鮮活的百年江西電影人的“群像圖”。生于南昌的但杜宇和妻子殷明珠,這對中國電影史上最早的夫妻店,在為中國電影觀眾造夢、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的同時,讓中國影片第一次登上了挪威的銀幕;靖安人陳方千創(chuàng)作出《小鈴鐺》等優(yōu)秀影片,也成了河北電影藝術(shù)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畢必成創(chuàng)作于改革初期的“廬山戀”全國范圍內(nèi)回響不絕,富有時代隱喻,迄今仍是豐饒廬山文化故事講述中最欲說還休的那一部分;王一民的“鄉(xiāng)土三部曲”,具有悲喜交加的美學(xué)特色,深沉而質(zhì)樸,恬靜且深刻;用二十幾年塑造了“阿滿”形象的張剛,創(chuàng)造出獨具中國特色的喜劇,豐富著當(dāng)代中國喜劇電影的創(chuàng)作理論,也因拍攝手法的先鋒性被稱為“第一個電影個體戶”,成為體制改革中“先行先使”的典型……此外,還有祝希娟、呂玉堃、潘鳳霞、鄧超、陳紅、石蘭、彭昱暢、張慧雯等贛籍演員;有雷磊、易寒、周筍、陳志敏、趙經(jīng)見等中青年導(dǎo)演;有何闖、安以沫、盧磊等新銳編劇;有組建過包容所有、來去自由的公共放映空間瓦子角17號、瓦子工廠,舉辦了瓦子影像周等的江西第一個電影策展人周一……而就在本書完稿后的短短時間里,這份名單里的有些人已經(jīng)又創(chuàng)造出了一些新的成績;這份名單也因有新生力量的加入而被拉長不少。
電影是造夢的藝術(shù),它挪騰天地萬物和時空虛實,流動、包容、開放,這也許才是影像的獨特魅力。誠如本書作者所言:“對‘歷史’的電影化書寫,注定要書寫的恰恰是‘未來’”。喜歡和關(guān)注江西電影發(fā)展的朋友,不妨讀一讀這本誠意滿滿的《江西電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