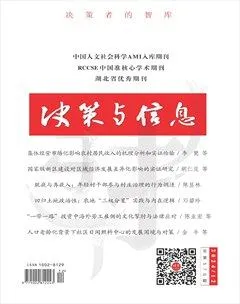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振興的治理表達與實現路徑
[摘 要] 隨著國家對體育助力鄉村振興的提倡和基層群眾性體育賽事的蓬勃發展,群眾性體育賽事為當前鄉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通過對桂中地區以“W鎮春節籃球賽事”為中心的治理實踐進行考察,發現群眾性體育賽事生發于國家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務下鄉行動和村民自下而上的自組織運動,并存在“治理對象”和“治理工具”兩重屬性,前者是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基本前提,后者是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內在動力。從實踐來看,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實現前提是體育場所作為治理場域,其合法性、正義性和公共性的嵌入;而內在動力源自體育賽事通過集體化情境和鄉村控制機制的再生產,對村莊慣習的喚醒。由此,以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治理的實現邏輯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體育場所作為體育活動的物理空間,使得群眾性體育賽事傳導了鄉村治理的總目標,形成了治理的合力,并推動了村莊公共性的生產;二是體育賽事再造了村莊集體化情境和鄉村社會控制機制,激活了村莊臉面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使得村莊慣習得以激活,促進了村莊內生動力的形成。
[關鍵詞] 群眾性體育賽事;鄉村治理;體育下鄉;“村BA”;鄉村振興;鄉村文化事業;健康中國
[中圖分類號] D422.6;G8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4)12-0053-10
鄉村社會是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場域,鄉村社會的治理效能直接影響著國家治理的整體效果。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1]。“治理共同體”的提出,凸顯了社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內在要求,意味著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既要依靠多元主體的協同共治,也要使差異主體施展出自身的多維策略。為此,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加強和創新基層社會治理”[2],采用多種途徑創新社會治理機制具有必要性。2023年,國家體育總局等十二部委印發的《關于推進體育助力鄉村振興工作的指導意見》指出,體育可以助力鄉村建設、賦能農業發展、促進農民健康、豐富鄉村文化[3],這闡明了體育賦能鄉村治理的價值意蘊。近年來,以貴州“村BA”和“村超”為代表的群眾性體育賽事成為體育助力鄉村治理、推動鄉村振興的典范,其核心在于透過體育賽事將人凝聚起來,將組織動員起來,從而找到村治的主體。可見,體育之功效在于“塑形鑄魂”,是促進村治的有效途徑。因此,在治理的理論框架下,探索如何更好地發揮群眾性體育賽事的治理功能,使其有效促進村治,并討論如何將體育吸納到國家治理體系中,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在此背景下,本文關注的是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何以可能,并圍繞“W鎮春節籃球賽事”為中心的治理實踐,討論群體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實現邏輯,為豐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相關研究提供支持。
一、文獻回顧
事實上,鄉村治理的路徑研究始終是村治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研究主要形成了四種分析視角:一是國家嵌入論,認為村莊治理無法脫離國家的力量,要通過完善村規民約[4]和發展村集體經濟[5]等路徑使國家的權威、資源和能力進一步嵌入村莊,實現治理有效。二是社會內生論,強調鄉村治理要圍繞村民做文章,通過宗族組織[6],借用熟人社會、“面子和人情”[7]等載體,形成村民間的情感聯結紐帶,從而生成村莊內生動力。三是市場助推論,該視角認為完善的村治體系需要重視市場主體的力量,要使“市場”進入村治網絡,推動社會組織的自主性成長[8]。四是黨建引領論,黨建引領鄉村振興的力量展現,使學者們意識到當前中國鄉村治理離不開政黨,要進一步推動基層黨組織以提能賦權、組織動員、上下聯動等形式引領村莊治理[9]。除此之外,還有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鄉村治理的推進路徑,提供了類如協商民主[10-11]、文化治理[12]、公共空間[13]等具體的推進方案。上述研究成果具有啟發性,表明了有效的鄉村治理既要充分發揮國家、社會、市場和政黨等多元主體的力量,也要借助不同的治理機制推進鄉村治理。然而,在當前積極推動群眾性體育賽事發展和倡導體育助力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少有學者去探討群眾性體育賽事何以助推鄉村治理,如何利用群眾性體育賽事推動鄉村治理應當成為學術研究的重點關切。
一般來說,群眾性體育賽事是“以一定數量的群眾為參與對象,以強身健體、豐富生活和倡導良好生活方式為參與目的,以不同的體育形式,按照一定的競賽規則開展的體育競賽和體育活動”[14]。圍繞群眾性體育賽事,相關研究多集中于體育人文社會學學科,主要聚集在群眾性體育賽事的治理主體、治理方式和治理向度三個方面。一是在治理主體上,當前我國的群眾性體育賽事已然從“管理”走向“治理”,是政府、社會和公民集體參與下的多元共治[15]。二是在治理方式上,就當前群眾性體育賽事的賽事監管、內部管理和安全保障等現有問題,要通過明確政府監管職責、制定行業標準和強化風險應急管理等手段推動我國群眾性體育活動賽事發展[14]。三是在治理向度上,群眾性體育賽事旨在實現體育的“善治”,即“緊扣社會主要矛盾,服務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16],強調真正將“人”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除此之外,部分學者關注到群眾性體育賽事的其他功能屬性。作為現代體育的重要組成,群眾性體育賽事出場內生于國家市民社會中的“體育化”,是基于現代社會的教育和文化需要,將休閑性、娛樂性的身體活動轉化為現代體育的過程[16],是集中了“世界性和民族性、日常性和體驗性、競爭性和休閑性”的文化綜合體[17],攜帶著教化[18]、塑造[17]、動員[19]等多重功能。同時,群眾性體育賽事所具有的競爭性、群眾性和身體性,使其成為公眾參與的載體,推動了個體的身體意識覺醒,進而能夠產生國家認同的文化聚合力[20]。
就研究現狀而言,有關群眾性體育賽事的研究在概念界定、治理現狀和功能屬性方面具有較強借鑒意義。但與此同時,仍存在一些視角上的缺失。一方面,在體育學領域群眾性體育賽事大多被視為治理對象,主要討論如何實現群眾性體育賽事的善治,其治理工具的一面往往被忽視。另一方面,部分研究雖然關注到了群眾性體育賽事在道德教化、認同塑造和社會動員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并認為這些功能對于鄉村治理具有重要意義,但相關研究并未指向群眾性體育賽事的治理屬性。因此,有必要充分挖掘群眾性體育賽事中的治理屬性,找到群眾性體育賽事對于提升基層治理效能的價值意蘊。
二、“W鎮春節籃球賽事”的實踐情境和治理演進
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治理術是“制度、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得這種特殊然而復雜的權力形式得以實施的計算和手法組成的總體”[21] 91。因此,鄉村治理術是使治理理論在鄉村社會運作的具體方法,更多強調其治理工具的一面。將群眾性體育賽事視為一種鄉村治理術,了解其在地化運作是理解以群眾性體育賽事促治理何以可行的前提。為此,本文通過案例研究法,選取桂中地區的W鎮為案例進行研究。該鎮總人口約5萬人,其中少數民族人口約占總人口的3/4。大約從21世紀初①開始,W鎮就有在春節期間舉辦籃球賽事的傳統,僅在2020、2021年因疫情被中斷。“W鎮春節籃球賽事”已成為L市X區內較具知名度的春節籃球賽事,村莊參賽積極性高,常常吸引其他鄉鎮的村莊報名。籃球賽事從大年初一舉辦至初七,每日大量村民前往觀賽,具有良好的社會效益和傳播效益。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并不局限于對“W鎮春節籃球賽事”的治理活動進行考察。這是因為在傳統帝制時期,鄉村主要作為生產空間而存在,體育并非農民不可或缺的活動,而是士人貴族的專利,被作為統治階級對鄉村生產屬性的控制及論證合法性的工具。因而,體育在農村的出現是“下鄉”的。在此過程中,存在各級黨政機關、行政村、自然村和村民等多個主體的博弈。因此,有必要考察該鎮春節籃球賽事的緣起、發展以及治理演進。除此之外,選取單個鄉鎮的群眾性體育賽事作為分析對象,是希望通過以小見大的形式,呈現出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具體樣態。
本文的經驗材料主要源自筆者于2023年1月、10月和2024年2月在該鎮的田野調查。資料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筆者對W鎮黨政工作人員、籃球協會成員、退休干部、青年頭人、籃球隊隊長、村民等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得來的深度訪談紀要;二是于2024年2月參與賽事籌辦期間和上述三個時間段內作為參賽隊員進行參與式觀察所形成的調研日志。同時,搜集了部分與“W鎮春節籃球賽事”相關的數據信息和網絡報道等資料作為補充。資料情況如表1所示。
(一)兩種運動并存:體育賽事的緣起和發展
1. 體育的下鄉運動。帝制時期的中國鄉村,并無“體育”之概念,部分鄉村存在著“鄉射”“蹴鞠”等帶有體育色彩的活動,往往零散且源自農民的自發組織。體育活動在村莊的大規模普及,是伴隨著國家公共服務下鄉專項行動而形成的。進入21世紀,“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照耀農村”成為新時代財政支持“三農”的基本指導思想,在農村地區大力興建一大批公共基礎設施成為現代體育得以下鄉的重要前提。2010年,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開展了以村衛生室為重點的村級公共服務中心建設,該政策包含了村級公共服務中心、村衛生室、人口計生健康服務室、新家庭文化屋、籃球場、農村書屋六個項目(20101223-B1-SX)。
自治區政府的高位推動,實質是一定自主性范圍內的行政發包制。一方面,提供了“依據村級公共服務中心的規劃,建設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做到便民實用,保證質量,提高效益”(20101223-B1-SX)的發包空間,間接推動L市建設重心由衛生室轉向籃球場,也誘發了在村級公共服務中心建設上的擴包,L市的“八個一”建設客觀上增加了鄉鎮執行任務的總量(20131227-B2-SX)。另一方面,上級政府的建設目標是L市作為接包方的必然遵循,L市以“全民健身示范城市”為契機,在724個村建成1535個籃球場,并推動農村體育場建設重心由行政村向自然村轉移(20131227-B2-SX)。
就此,現代體育得以進入鄉村,其前提是國家通過制度、結構和認知對農民公共空間的“干預”。在此過程中,籃球場是國家下沉至鄉村社會的資源,具備著項目制的基本特征。與傳統的進村項目不同,籃球場作為一種村民潛在需要的公共服務產品,行政邏輯和科層邏輯需要通過協商和溝通,來塑造村莊資源整合和矛盾調解的能力,以避免“錢花了,農民不叫好”的現象。在此過程中,激發了主體間的合作與博弈:
“我們現在每個自然村至少都有3個籃球場,分下來的錢其實是不夠的,有些人喜歡,有些人不喜歡,你在這里建,不在那里建,意見都很大,辦法就是只出一部分錢,然后想辦法去動員村里籌錢來建,多建幾個,或者把建綜合樓、文藝舞臺、公廁的錢勻出來一部分搞籃球場”。(20240213-LSH-M1)
不僅如此,籃球場也成為國家權力介入村莊治理網絡的重要符號。對于W鎮居民而言,籃球場是現代性的具象展現,意味著村莊與外部社會的連接,也潛在地成為國家制造認同和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實然工具:
“我們都是農民,也不是說沒有見過籃球場,但大部分都是在學校里面,而且球場也很爛,村里面剛修的籃球場比中學修的都好”。(20240214-LHX-W1)
2. 村民的自組織運動。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在《社會權力的來源》中將國家權力劃分為“專制性權力”和“基礎性權力”[22] 69,并強調了基礎性權力的積極效果在于村莊內生動力的生成。籃球場不應簡單被視為國家專制性權力的向下嵌入,“W鎮春節籃球賽事”能夠聚攏人氣的根源,是村民經由一系列自組織運動而形塑的基礎性權利。
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制在客觀上剪斷了村民和村集體、村民和村民間的利益聯結紐帶,農民越發重視個體利益,公共事務往往難以組織,也少有人參與。籃球賽事在W鎮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由部分W鎮中學教師所舉辦的籃球賽事,這意味著一種嶄新形態的集體活動雛形就此出現(20240213-LSH-M1)。
以鎮中教師為代表的鄉村知識精英、以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為代表的體制內精英和以早期外出務工群體為代表的鄉村致富群體為核心所舉辦和參與的籃球賽事(20240213-LSH-M1),再現了村莊舊有的集體化情境,使得基層社會的共識得以擴展,形塑了從精英群體到普通農民的體育活動引領機制,籃球賽事得以在W鎮傳播。
村莊臉面是“W鎮春節籃球賽事”的助推器,使得體育聯結了W鎮居民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個體在籃球賽事中的貢獻成為區分村莊內部地位的新方式,并塑造了一條村莊彰顯自身優勢地位的新路徑:
“拿冠軍的時候,我們買了3萬塊的煙花來放,放了很久很久,其他村就算沒看比賽,也知道我們拿了第一”“男的除夕晚上都需要去跟舞獅一晚上,因為初一有比賽,球員就不用去,代表村里去打比賽不僅有補貼,2018年的時候,村里還出錢送球員去柳州集訓”“鎮上搞比賽,我們村青年一起捐了5888元,捐的錢比獎金還多”。(20231002-HJR-M1)
與此同時,“W鎮春節籃球賽事”的出現復蘇了以村莊精英為導向的村治系統。村莊精英在籃球賽事中具有特殊的權威,并能將其優勢地位轉化為村莊治理的聲望:
“每年我都給村里和鎮里的籃球賽事捐錢,村里拿了名次,我個人再給一筆獎金,鎮上的籃球比賽,我掛名了副主席,看比賽的時候坐在主席臺,場場都去,村里有什么事,也會來找我討論”。(20240212-HZH-M1)
而國家將體育空間匯入W鎮,使得“W鎮春節籃球賽事”這一周期性的集體儀式被嵌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方面,個體突破了村落范圍,使得交往交流不單局限于同鄉同族的人際關系;另一方面,個體又需要回歸村集體。在此過程中,體育文化中積極向上的部分也被傳遞至鄉土社會:
“小的時候還會去SJ廟‘拜公’,但再大一點的時候,老人就叫你打籃球,就算不打,也要去看,一看就是一整天,去廟里‘拜公’的,我家就只有我老婆和我媽了”。(20240211-HWZ-M1)
基于村莊的自組織運動,“W鎮春節籃球賽事”不僅融入居民日常生活,而且能夠影響L市和W鎮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政策。在體育賽事中,W鎮發現了農民的共同需求,不斷在鎮“街上”(經濟中心)修建籃球場,比賽場地也從鎮中學籃球場轉移至露天燈光籃球場,再轉移至風雨籃球場(20240213-LSH-M1);另一方面,“想健身沒場地,想建卻建不來”的樸實訴求,以及“由農民自發成立的籃球隊就超過400支”的現實基礎,客觀上也助推了L市在全市范圍內推行以籃球場為主的“八個一”建設(20131227-B2-SX)。
(二)兩種范式轉換:治理對象和治理工具
1. 作為治理對象的群眾性體育賽事。在W鎮早期的實踐中,群眾性體育賽事被視為治理對象,主要圍繞“W鎮春節籃球賽事”的組織及其所引發的各類現象而進行。在2022年前,W鎮的目標是黨政領導下多元治理主體推動群眾性體育賽事實現善治。
國家資源的下鄉,是W鎮黨政機關吸納村民自組織運動形成的籃球賽事的重要前提。行政吸納作為基層治理主體調整治理結構的主要路徑,其向度是對其他治理主體的同化和村治過程的控制。一方面,出資修建籃球場地、捐獻賽事舉辦資金、協助賽事籌辦等具體行為,逐步將“W鎮春節籃球賽事”演變為W鎮官方每年“迎新春”系列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賽事中冠以“美麗鄉村杯”“鄉村振興杯”等稱號,推動了“W鎮春節籃球賽事”的規范化,改變了過往籃球賽事主要由村民創設的情境。另一方面,為了預防由籃球賽事引發的村斗,通過介入賽事組織和參與賽事籌辦,間接推動了“W鎮春節籃球賽事”的標準化,同時將W鎮籃球協會納入到鄉村治理體系(20240212-HZH-M2、24240213-LSH-M2、20240130-B4-SX)。
與此同時,對籃球賽事本身及周邊的治理是早期W鎮體育治理的主要內容。首先,針對賽事舉辦期間周邊大量聚賭現象進行整治,通過聯合X區政府相關部門對賭博現象嚴厲打擊,并以行政村為單元開展宣傳教育,軟硬皆施,推動體育善治。其次,針對觀賽期間所引發的環境污染進行治理,以志愿服務、村級動員和政策宣傳推進環境保護。最后,提升賽事影響力和知名度。一是擴展賽事內容,青少年籃球賽事應運而生,三月三、五一和國慶等節假日也不定期舉辦籃球賽事;二是主動邀請其他村莊和知名球隊隊員跨鎮參賽和下鄉比賽;三是圍繞籃球賽事打造春節游園、農民大晚會、壯歌比賽等系列文體活動;四是邀請縣級融媒體中心參與賽事的錄制、傳播和推廣(20230128-LL-W1、20240212-HZH-M2、24240213-LSH-M2)。
總之,早期的群眾性體育賽事經歷了從行政吸納服務到公共服務提升的過程,旨在實現“W鎮春節籃球賽事”的有效治理。此階段的群眾性體育賽事被視為治理對象,但已然出現黨政機關借由群眾性體育賽事參與鄉村治理的現象。
2. 作為治理工具的群眾性體育賽事。2022年后,“村BA”賽事在全國范圍內引發巨大關注,W鎮黨委政府開始意識到群眾性體育賽事的重要價值(20230128-LL-W1)。由此,“W鎮春節籃球賽事”開始了由“治理對象”到“治理工具”的轉變。
相較于其他地區,民族地區承擔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特殊治理使命。對于民族地區鄉村社會,民族團結的話語表達和輿論傳播往往停留于新聞媒介中,并不具體,也不深刻。有必要構建現實的輿論傳播空間,使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變得有形、有感、有效。在W鎮黨政機關看來,籃球賽事可以成為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載體:
“比以前更好了,可以看到自己的親朋好友在場上比賽,這是黨和國家的好政策”(20240214-LHX-W1);“2022年,我們黨委在頒獎典禮上搞了升旗儀式,這是我們鎮很多村民人生中的第一次升國旗”(20230128-LL-W1)。
籃球場不僅是村民的活動空間,亦成為多元主體承接部分治理功能的治理空間。借由籃球賽事和籃球場,政府在“W鎮春節籃球賽事”中將文娛活動、司法教育和衛生政策宣傳等各類公共服務進行嵌入。W鎮新時代文明實踐所、S村村委等差異治理主體所開展的人居環境整治、文明鄉風建設、典型模范事例宣傳、志愿服務等具體活動也不斷成為村民組織文娛鍛煉和學習宣講的場域,并帶動了一大批具有公益精神的鄉村志愿服務者(20231020-B3-SX、20240130-B4-SX)。
與此同時,籃球賽事形塑了新的場域,將黨政機關、行政村、自然村、社會組織、鄉賢群體和普通村民匯聚其中,這種影響力又擴散至其他的治理活動中。一是籃球賽事的出現,使得鎮村兩級重新倚重鄉村精英,并將其帶進公共事務;二是籃球賽事提供了社會組織參與治理的土壤;三是再次激活了鄉村社會間的道德義務和集體情感,從而推動了村民的再組織化(20230128-LL-W1、20240212-HZH-M2、231002-HJR-M1)。
三、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實現邏輯
(一)空間建構: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場域基礎
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實現前提是體育場所作為治理場域的建構。體育場所蘊含的合法性、正義性和公共性,使得體育場所不僅是體育活動的物理空間,更是實現體育賦能治理的場域基礎。
首先,經由W鎮黨政機關的規則滲透,在階段性、規范性和程序化的體育空間中能夠為參與者持續輸入政治權力話語,生成對統治系統政治認同的合法性力量。空間從來就不僅僅是抽象的象征,它往往還蘊含著某種特殊的意蘊。體育場所隱含著治理屬性,W鎮黨政機關作為體育空間建構的主導者,擁有空間規則的主導權,使得體育場所呈現出一種高度的規范性,暗含著國家權力的規則建構,體育活動有序地開展,并將參與者秩序性地融入到體育賽事中,共同建構了體育活動的規范性。在這種具備規范性效用的集體活動中,體育賽事的周期性開展,又潛在地使參與者被納入到標準化和高度結構化的規訓體系,參與者循環往復地獲取了“程式化感知”,并在體育賽事中確認和維持有關“共同體”的情感和理念。
其次,體育空間的正義性嵌入,使得群眾性體育賽事導向提升人的素質和全面發展的價值向度。空間作為一種價值判斷,既是空間生產活動的評價尺度,也是評價結果。在體育場所的空間生產中,正義性不只是由W鎮黨政機關所確定,村民亦是空間建構的主要參與者,村民的自組織運動暗含了體育場所中重建主體性的客觀訴求。空間規則的主導者也并未忽視這種以主體發展為歸宿的正義性,使得W鎮居民在籃球賽事中處于“以人民為中心”的支配地位。正是這種空間正義的核心要求,體育活動中的良善價值才得以傳遞至空間中,形成了先進文化同落后文化的對抗。
最后,體育場所的共建、共治和共享屬性使其成為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既是公共性形成的社會基礎,也是村莊公共性生產的物理基礎,這種公共性會進一步遷移到村莊內部。W鎮籃球場的空間建構,改變了過往僅僅由政府自上而下或市場由外到內的供給方式,而是依靠政府、社會和村民的合作生產。多元參與的空間構建前提,使得體育場所和體育賽事的利益相關者均能處于參與管理的公共規則中,進而能夠通過情感聯結和利益協商的方式形成社會共識。在這種合作生產和共同治理的空間形態中,消除了空間的非正義性,形成了空間的可達性,實現了空間的共享。在后續圍繞體育場所開展的治理實踐中,包括W鎮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等在內的“外地人”也被融入到W鎮的日常生活中,差異主體的公共性被喚醒,并積極地參與到W鎮志愿服務、文明鄉風建設等日常治理事務中。
(二)村莊慣習: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內在動力
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治理的內在動力源自村莊慣習的喚醒。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場域-慣習”理論,認為慣習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化”[23] 33。慣習的真正特征在于它是群體所習慣的,即使村民未必能理解,作為一種村莊社會的內在習性,也會引導村莊主體將其形塑為所渴望的形態。群眾性體育賽事形塑了集體化場景,激活了面子和人情在村治中的積極作用,使得鄉賢再造。由此,村莊慣習被喚醒,生成了村治的內生動力。
在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的描述中,“共同體”源自“持久的、真實的共同生活”[24] 71,村莊應屬于“共同體”,其顯著特征是共同體的集體化特征。傳統的鄉村社會,由于“皇權不下縣”,公共事務主要由宗族長老、鄉紳或村落精英在宗祠、廣場或議事廳主持協商。新中國成立后的集體化時代,以生產隊長為代表的主體將村民統一至公共空間開大會,這種集體化情境是村莊集體的共同記憶。然而,伴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集體化情境在村莊中逐漸消逝。群眾性體育賽事使得村莊集體化情境得以再生,并使集體想象不斷得到確認和維持,從而推動了村治。一方面,在“國家在場”形塑的場域中,不論是村民、社會組織,還是黨政機關,均能夠使得其構筑的空間得以顯現,并在其中形成互動儀式,打造出一種獨特的身份生產,感知到自身所處的“范圍”,并創造了一種獨特的認同建構機制,在實然存在的場所中形成臨場感和空間想象感,能夠建構起相關的“同感”場域,從而將其納入被組織化的共同體之中。另一方面,在體育賽事中,呈現出村中鄉賢資助村落參賽、普通村民加油助威和青年才俊參與比賽的場景,這恰是過往村落共同體的生活回溯。雖然這與過去的集體化情境并不等同,但“社會記憶的傳承是通過身體實踐和紀念儀式來實現的”[25] 40,通過群眾性體育賽事,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基礎上形成了對過往特定時空趨同經驗的共同回憶。在這種共同在場的治理參與中,集體情感和集體記憶也在集體化情境中生成,有關“集體”的認知是村莊凝聚力形成的關鍵,導向了治理合力的共同生產。
除此之外,群眾性體育賽事中強烈的競爭性將以臉面為核心的鄉村控制機制激活,推動了個體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和融入村莊公共生活。西方政治學者常用“競技場”(arena)來形容人們參與競爭的領域:“社會中存在著競技場,人們在其中從事政治活動,互相角力和彼此斗爭,以決定誰是主導者,誰是附庸。”[26]體育賽事在鄉村社會儼然成為了競技場,村莊不惜投入大量資源參與競爭,在賽場上勝利,便能夠在氣勢上壓倒其他村莊,從而顯示出自身的優勢地位。這種非理性化的行為,正是由于體育賽事重新激活了以村莊臉面為核心的軟性社會控制機制。為了爭奪村莊臉面,在群眾性體育賽事這種社區性的公共生活中,村莊產出一套強有力且與體育賽事相適應的社區規范,村莊臉面和個人臉面相互重疊,助推個體積極參與社區性和競爭性的公共生活。在“從俗即從心”的社會控制機制中,體育賽事中的個人貢獻也成為了村莊中個人地位的評判指標,新鄉賢得以產生,其合法性權威和利益支配性權威也不斷在體育賽事中得以穩固。群眾性體育賽事客觀上使得臉面成為一種軟約束,這種村莊慣習又不斷地引導村民積極參與公共生活,村民也再次被吸納到村莊共同體之中。在此過程中,一張相互制約的微觀權力關系網得以形成,這張權力網發揮著強大的村治功能,通過村莊的輿論和個人的臉面告誡著人們既要遵循社區規范和融入共同體,也要積極地參與、管理村莊公共事務和維護公共價值。
四、結語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也是現階段黨和國家推動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當前鄉村社會正朝著結構分化和多元化的方向轉變,已然處于“后鄉土社會”階段,鄉村治理的技術規范和知識體系也迎來了變革,客觀上要求加強和創新鄉村社會的治理方式。群眾性體育賽事緣起于國家外部權力嵌入的公共服務下鄉行動和鄉村內生的村民自組織運動,擁有著組織動員、制造認同和道德教化等多重功能,可以成為創新鄉村治理模式、實現有效治理的重要抓手,它對賦能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就“W鎮春節籃球賽事”的治理表達來看,以群眾性體育賽事促治理的實現邏輯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體育場所作為體育活動的物理空間,是實現群眾性體育賽事賦能治理的場域前提,體育場所中的合法性滲透、正義性嵌入和公共性生產,使得群眾性體育賽事傳導了鄉村治理的總目標,形成了治理的合力,并推動了村莊公共性的生產;二是體育賽事再造了村莊集體化情境和鄉村社會控制機制,激活了村莊臉面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使得村莊慣習得以激活,促進了村莊內生動力的形成。
本文主要以“W鎮春節籃球賽事”為例,關注群眾性體育賽事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然而受到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的影響,未能深入分析鄉村社會變遷對鄉村治理方式的影響、不同歷史階段中群眾性體育賽事的具體表達、功能呈現以及如何協調群眾性體育賽事與其他治理方式間的關系。未來的相關研究應進一步結合本土化實踐的經驗,對群眾性體育賽事在鄉村治理中的實效進行評估,分析差異地域群眾性體育賽事治理價值的弘揚情況,深入探索群眾性體育賽事助推鄉村治理的發展趨勢、存在問題和推進路徑,從而辯證地認知群眾性體育賽事的作用和貢獻。
[參考文獻]
[1]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N].人民日報,2020-11-04.
[2] 習近平.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于民統一起來 推動“十四五”規劃編制符合人民所思所盼[N].人民日報,2020-09-20.
[3] 軋學超.體育總局等十二部門協力推進體育助力鄉村振興工作[N].中國體育報,2023-06-26.
[4] 袁方成,桓寧.從規約有效到治理有效——以村規民約中的懲罰性規條為研究對象[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1,(5).
[5] 郭忠華,王榕.集體經濟與村莊有效治理:基于河北省X村的分析[J].江蘇社會科學,2020,(1).
[6] 馬華,王紅卓.宗族底色下的大型村莊治理研究——以粵西黃村為例[J].地方治理研究,2019,(2).
[7] 嚴紅.熟人社會、面子與村莊公共性再生產[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
[8] 陳曉運,王敏.規則嵌入、市場建構與鄉村有效治理——以廣州市番禺區龍美村為例[J].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
[9] 曹海軍,曹志立.新時代村級黨建引領鄉村治理的實踐邏輯[J].探索,2020,(1).
[10] 馬華.村治實驗: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樣態及邏輯[J].中國社會科學,2018,(5).
[11] 周興妍.人民性治理:積極發展基層民主 助推鄉村治理有效 —— 湖北省枝江市村灣夜話創新民主協商機制的調查與思考[J].決策與信息,2023,(9).
[12] 吳理財,解勝利.文化治理視角下的鄉村文化振興:價值耦合與體系建構[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
[13] 賀雪峰.鄉村治理中的公共性與基層治理有效[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1).
[14] 黃明濤,張勇勝.我國群眾性體育活動治理問題與完善建議[J].體育文化導刊,2022,(1).
[15] 馮劍.群眾體育賽事從管理到治理:動力、邏輯與路徑[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18,(3).
[16] 任海.中國體育治理邏輯的轉型與創新[J].體育科學,2020,(7).
[17] 朱全國,肖艷麗.貴州現代鄉村表演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呈現——以貴州“村BA”與“村超”為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4).
[18] 路云亭.教化的權力轉移——作為中國進入現代社會典型儀式的大型體育賽事[J].體育與科學,2017,(1).
[19] 洪長暉.參與·地方·情感聯結:貴州村BA的傳播學解讀[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2).
[20] 陳家明,蔣彬.符號學視野下體育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構建[J].民族學刊,2020,(5).
[21] [法]米歇爾·福柯.安全、領土與人口[M].錢翰,陳曉徑,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2] [英]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第2卷上[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23] [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24]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張巍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25] [英]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M].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6] A.M. Orum. Social constraint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 theoretical inquiry into their form and manner[J].Political Behavior,1979,(1).
[責任編輯:汪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