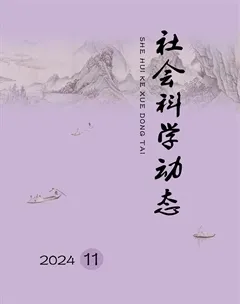數字工匠主體性何以可能?
摘要:數字工匠是秉承工匠精神并通過數字技術從事生產實踐的新型勞動群體。從歷史語境出發,數字工匠的興起放大了以技術替代論和技術工具論為主流的人與技術關系的探討。技術替代論者認為數字技術的出現與高速發展帶來了人被技術所取代的主體危機,技術工具論者則認為人作為數字工匠的永恒主體,對技術擁有絕對的控制權。然而,在此視角之下的雙方都未曾看清人與技術辯證關系的本質。由此,必須重溫“勞動創造了人本身”這一馬克思主義經典命題,并從“機器體系”概念出發理解主體性,方能擺脫二元對立的思想桎梏。具體來說,作為決定勞動表現方式的技術,必然直接參與到人的主體性及其社會關系的本質構造之中,而不同的生產關系所決定的社會制度下的勞動主體具有完全不同的屬性,此即數字工匠勞動主體的技術構造論。由此著眼,才能更深入地把握技術與人的主體性生成間不可割裂的復雜關系。
關鍵詞:數字工匠;主體性;技術替代;技術工具;技術構造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哲學社會科學青年學者托舉計劃”基金資助項目“中華匠道所蘊含的勞動精神與人格修養論研究”(20CX05006B)
中圖分類號:F014;A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4)11-0073-06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加速擴張的科學技術逐漸演變為當今世界百年變局的最大內生變量。技術范式概念立足于自然科學原理,為解釋技術與人類社會的相互構建、形塑提供了一種新模式。所謂技術構造,是指技術與人類社會之間的相互建構、形塑的發展過程。當下,數字技術早已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生產之中,人類正是憑借著數字技術開創了虛擬空間,并構建起新的生存場所,催生出新的勞動形態與實踐活動。然而,數字技術也日益被視為是威脅人類主體地位的一種客觀存在。圍繞著數字工匠主體性而展開的探討,加劇了以技術替代論和技術工具論為主導的論爭,前者認為數字技術終將替代人類,后者認為數字技術只是為人所操控的工具,形成一種二元對立的局面。而數字技術的深度拓展實際上是機器體系由自動化邁向智能化的過程,根本上仍未超越“機器體系”概念的基本邏輯。站在“機器體系”的理論視野和分析框架來看,上述雙方在技術與人的問題上的對立,均源于其厚此薄彼的理論傾向。因此,重新梳理勞動、勞動者與技術的關系,厘清勞動主體性的“技術構造”本質,仍然是數字時代思考并解決這一論爭的方向。如果擺脫單向度的、純機械的認知束縛,則能以更開放的姿態展望數字技術,并應對其在未來對人類社會所可能帶來的巨變。
一、數字工匠主體性的概念與論爭
深入理解數字工匠主體性的前提在于了解數字時代工匠概念的內涵變化及其新形態。傳統社會中的工匠明確指向手工業者、手藝人。《考工記》認為,“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1),意即古代社會工匠群體扮演著“智者”創造新鮮事物與“巧者”世代傳承并守護技藝的雙重角色。(2)數字工匠的概念由傳統社會的工匠概念發展而來,卻又區別于傳統工匠的工作模式。數字工匠是指按照新興信息技術標準,從事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商品創造,并且具備傳承以往社會向善利他的道德品質與追求極致的敬業理念的一切勞動群體。與數字勞動者相比較,該群體不僅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為生產資料,以提供數字產品和服務為目標,還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團隊協作精神以及人機共生潛能,進而能夠勝任各種數字化的高技能工作。(3)數字工匠的主體性問題涉及身體的內外兩面,意指按照人的內外尺度原則從事生產勞動實踐的客觀特性,亦即具備信念、記憶、情感、價值、欲望等身體屬性的個體,在勞動的過程中可以自主、自由地將人性有意識地灌注到沒有生命的物體之中。
隨著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具體形態流變,由數字技術構成的虛擬世界通過數據化、電子化、信息化等手段實現了與工匠主體在勞動、社交、身體系統上的密切融合,“技術—工匠”之間的關系日益復雜,并構成了當下社會數字工匠的主體新形態:一是數字技術作為人類感知能力、社會標識以及背后權力關系延展的一部分,開始介入工匠的現實身體,“除非由技術媒介介入和審查,否則不可能進行人類活動”(4)。二是數字技術構建了信息載體下工匠所從事勞動的情境元素、勞動效能與勞動意義的虛擬場景,數字技術成為數字世界的底層邏輯,日益規訓著工匠的生產勞動、生活方式及其維系社會關系的實踐活動。三是數字技術作為一種“他者”,創造了諸如“數字工廠”“云帝國”“全景監獄”等新的支配力量。
早在工業革命時期,“機器體系”的興起就被視作一種顛覆性的勞動力置換力量,數字技術亦使得現代工匠表現出更為復雜的形象特征,并伴隨著潛在的風險。這使得關于勞動主體與數字技術之間相互關系的預測層出不窮。通過考察,可以將目前所有預測的內涵觀點劃分為兩大類:一是技術替代論,技術拜物教與技術恐懼者共同塑造了關于技術替代人類的多維觀點,甚至會異化人類勞動,并最終將人類從生產實踐的過程中淘汰。二是技術工具論認為,數字技術只是人類從事社會歷史實踐的產物之一,只是服務于生產實踐的工具手段而已。總之,在數字技術、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當下,人們不免對數字技術的歷史屬性、統治潛能有所討論,對其究竟會向何處發展亦成為人們至為關心的議題。無論是技術替代論還是技術工具論,雖然都能在激烈的爭論中提供支撐各自觀點的論據,但也都存在著各自的理論缺陷和現實局限。
二、數字工匠主體性的論爭焦點及其局限
技術替代論在當今國內外的主流研究中,技術的不可預測性、對人類勞動者的可替代性以及成為勞動主體的可能性三個方面。雖然技術替代論者強調技術對勞動者大腦、實踐情境、人類情感的替代,但其關于被夸大了的技術力量及潛在的導致社會不安與風險的論點仍受到普遍的質疑。這種觀點忽視了人類自然肉體系統的復雜性,也就是工匠的身體將技藝儲存于肌肉記憶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技術特性。肌肉記憶事實上是一種以腦神經元連接的方式將人的重復訓練動作刻畫到大腦乃至全身的方式,需要長久訓練才能形成的一種近乎條件反射的效能,是當前任何技術手段都無法模擬的。例如,央視紀錄片《大國工匠》中的胡勝能夠將數控機床的加工精度控制在4微米以內,徐立平雕刻火箭固體燃料形面的誤差不超過0.5毫米,顧秋亮組裝蛟龍號潛水器零件可以達到“絲”級要求,等等。而這正是技術替代論者目前所不能完全復制甚至解釋的領域。此外,技術替代論構想了一種將人類發展寄托于數字技術的烏托邦社會,其所強調的數字技術的威懾力和它強大的社會統治潛力更像是一種對技術的污名化指控。技術替代論過分強調技術的自然屬性、工具價值以及技術規則的資源稟賦對于社會環境的絕對控制,卻忽視了那些“無法被改制為程序化的勞動”的“非常規性”,而這些勞動卻恰恰“主要取決于勞動者的創造性”。(5)可見,雖然當前的數字技術能夠替代某些領域的人類活動,但這并不意味著在可以有效預見的時空范圍內的全面性替代。
與技術替代論不同,技術工具論的積極作用在于能夠正確認識到技術可以為人類所限制,并成為人類及人類社會發展的工具或助推器。實際上,聚焦于工匠實際操作的具體技術時,技術工具論者的論調似乎更能站得住腳。這是因為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雖然曾經付出過極大的代價,但最終的結局是,人類總能有效地將各種技術規制起來。從這一角度來講,人類不僅創造了技術,而且更有方法能夠做到了解技術,包括其屬性、價值與弊端等各個方面,因此,我們也就可以始終將技術規制于人類社會的秩序和道德的框架之中。然而,將視野放大到人類歷史發展的范式更新的格局之時,技術工具論亦會暴露其不足之處。顯然,技術在文明發展的尺度中具有慣性,一旦產生便難以完全按照人類的主觀意愿演進。數字技術似乎并不依據人類的主體意愿而存在或者消滅,甚至還會成為人類文明演化為新形態的關鍵因素。這樣一來,技術又具有了構造人性和改變人類生存環境的力量。不僅如此,由于技術并不能完全為人類所操控,這也說明人類并不能完全保證技術本身不向惡或操控它的人不作惡,這也意味著任何使用數字技術的勞動者都將面臨風險。這些風險已經不再是人類當前所構建的社會治理框架可以完全解釋并提供勝任的解決方案的,數字技術強大的自然屬性及其衍生的社會道德、倫理風險必須受到重視。因此,在超越技術工具主義的視野中,可以觀察到技術工具論者始終堅信工匠創造的產品必須以人類需求為核心。而這種以人為中心的自大態度簡化了人與技術關系的復雜互動性,可將之歸結為人類對技術具有絕對控制權的單向主導。
三、技術與人的交互構造:一個重新審視數字工匠主體性的視角
“人是主體”的論斷應當置于“對象—主體”復合形式的特征框架中去考慮。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這樣論述:“人通過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現實的、對象性的本質力量設定為異己的對象時,設定并不是主體;它是對象性的本質力量的主體性,因此這些本質力量的活動也必定是對象性的活動”(6)。馬克思所理解的“對象性”,并非簡單地描述主體與客體的單向度關系,而是打破“二元論”的思考范式,將“我”和“對象”關聯在一起。技術既是人的延伸,又在塑造著人;人既是技術的創造者,又是技術的受益者和被影響者。數字技術介入工匠的身體,其共生關系超越了傳統的工具與使用者的關系,這種主體性構造是動態的,數字工匠能夠以全新的方式與自然互動并改造自然,這伴隨著工匠對技術的掌握程度而不斷演變,也可以被視為是“勞動創造了人本身”(7)這一命題的新內涵。而且,“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8)。所謂社會關系是指廣泛涵蓋一切屬人的關系,而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則是生產關系,是以勞動的不可分解的共同性為基礎的本質所在。在數字時代,雖然人的本質仍然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但數字技術的融入為生產關系帶來了新的維度,從而影響了人的主體性的實質性構成。即“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的命題有著全新的體現——數字技術的進步不僅重新定義了勞動過程,也重塑了勞動者的身份和社會互動模式,進而構造了全新的工匠樣貌、社會生產形式及其社會關系的具體形態。
第一,數字技術參與構造數字工匠勞動的具體形態。機器的出現“使人的勞動,使力量的支出縮減到最低限度。這將有利于解放了的勞動,也是使勞動獲得解放的條件”(9)。與之類似,數字技術、數字工具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到高級,數字工匠的勞動形態也變得更加多樣。在這個過程中,現代工匠在知識儲備、思維視野、技能水平、大腦結構等各方面都得到了長足的改造與完善,也使工匠不斷呈現出與之適應的身體狀態和勞動形態。換言之,當下社會所擁有的不同于以往的虛擬身份、虛擬人生、虛擬感官等新事物,數字世界連接個人身份信息、社交信息、消費信息等多元屬性,展現了工匠主體將物質性工作置于虛擬社會的特性,數字世界的工匠的身體和心智的“重組”“再造”,構成了人類新形態的社會變化乃至生產方式變革的基本要素,并呈現出數字世界可以獨立運轉的新狀態。
第二,技術參與并構造人類當下社會勞動的生產基礎。技術對人的構造絕對不是只停留在初步形成“人”的原始社會,現代社會技術對工匠和勞動的影響可以說更為廣泛和深刻。數字技術極大滿足了人類的物質資料生產需求,以極高的機器作業效率將人從重復性勞動中解放出來,使人們可以更專心于從事思維活動,進一步提升了人類大腦的抽象能力和邏輯能力。“技術及其組織化應用不僅用‘奢侈品’——以及我們今天自鳴得意地稱之為‘高生活水準’的東西——誘惑我們,而且向那些知道如何操縱它們的人提供了連過去最專橫的暴君都無法知曉其程度的權力。”(10)例如,工匠可以利用拓展現實(XR)技術提升情境感知能力、直觀交互能力與編輯現實能力,以形成與“新技術融合共生”的生產實踐平臺。(11)即便機器曾短暫替代工匠參與施工、生產作業,但工匠隨后便將大腦和技術工具結合,進而用“龐大的數據來生成人腦難以處理的復雜形式”(12),這反映了只有通過數字技術與人腦復雜的交相映射關系才會形成的勞動形態和社會生產基礎。
第三,技術參與建構人類社會關系的具體聯結。數字技術作為聯結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媒介隱形影響著人類及其社會關系,而這種影響的實現,首先體現于“資本—技術”的聯合運動之驅使。“資本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13),對此,馬克思認為“推廣機器和分工”使得“無產者的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14)在數字社會,勞動者通過團結合作的方式來抵御技術侵蝕,進而避免技術替代論所描述的“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15)。可以為之例證的是,人機協作進行工藝設計便是技術、工具不斷與工匠身體匹配融合的過程,同時也是工匠主體性不斷被技術、工具參與其中并不斷進行新的構造的過程。在智能環境下,數字化的表達代替人與人的交流,人類社會正是在技術構造的社會關系下開始了具體而又生動的全新的現實聯結活動。“數字經濟不僅在生產力方面推動了勞動工具數字化、勞動對象服務化、勞動機會大眾化……構建數字組織模式成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驅動力。”(16)從某種意義上講,數字技術對人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交往影響日益加深。一旦離開數字技術,人類社會的交往將變得混亂、無序,甚至倒退。
雖然數字技術會在上述三大方面對人的主體性乃至本質產生直接的構造作用,但如果去除了人的參與和影響,那么自動運轉的數字技術工具及其體系最終也將遵循物理學中的熵增原理,逐步走向無序和瓦解。即賦予它們特殊地位的共生關系的人類,才是這些技術工具作為人造物的邏輯基礎,更是其避免淪為自然界中無意義的元素的物質基礎。雖然數字技術塑造了人類的主體性,但人類也會通過消費選擇、制度制定和技術創新對數字技術施加反向構造。
首先,人的創造性是技術存在的尺度和意義。數字技術的規模效應的確會取代現在的一些勞動者,但是由新技術生產的產品也必須要通過人類來實現最終的消費,也只有消費才能實現產品及其賴以生產的技術的意義本身,這才能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完美閉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技術發展往往是為了增加剩余價值,即利潤。然而,如果技術創新導致大量工人失業,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那么生產過剩的危機就必然出現。換言之,脫離了人的技術將變為無價值的虛空之物,只有形成消費閉環、接受人類制度規制和跟進人類形態演進才能避免技術自身走向虛無。“由于繁雜的物質生產活動已經由人工智能來承擔,那么人類的消費活動就可以看作一種休閑性工作,或者說是人的有用性的彰顯,而生產就是人工智能的有用性的體現。”(17)所以,人的勞動不僅僅是為了生存,還是人類本質力量的體現。“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構造,而人卻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18)工匠在利用技術的過程中,使其從被動的自然存在轉變為主動的、有意識的文化參與者,讓人類不再僅僅被動物本能所驅使,而是成為具有創造性的存在。同樣,工匠利用數字技術將自然界的勞動對象(物質資源)轉變為文化價值,實現從被動接受自然條件到主動塑造文化環境的轉變。人類的文化身份得以構建,便會促進“人類個性和社會價值自我繁衍”,繼而超越動物的本能生存追求,邁向更富于文化內涵的生活方式。(19)
其次,主動的社會制度建構可以規范技術在一定的規制框架內不向惡的一邊滑落。技術在不同的社會制度框架內呈現出不同的樣貌。技術構造下的社會生活是社會關系的集中反映,在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指導下,技術也會通過獨特的方式改變人的勞動形式、活動習慣并且構造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人性特征。人類通過構建具有獨特技術標志的新的社會關系,又可以在新的社會關系中去進一步認識技術、把握技術、利用技術,并創造新的技術推進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馬克思尤其批判技術與資本的結合所形成的那種侵害社會的力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科學對于勞動來說,表現為異己的、敵對的和統治的權力”(20),列寧也認為“十分之九的勞動群眾都懂得:知識是他們爭取解放的武器”,但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才能夠改變曾經被‘知識—權力’所歧視和規訓的命運”。(21)不同的文明形態掌控技術的手段、能力皆有差別。“從馬克思那個年代使用機器的影響來看,人類還遠未使自己適用于機器技術的應用,對機器使用的反思依然必要。”(22)因此,技術構造論所呈現的技術創新與人的進化之間的螺旋式上升之運動的狀態,需要主動的社會制度建構方能達到良性的平衡。
最后,數字技術必然參與到人的現實存在樣態的構造之中,但不會改變人作為數字工匠之主體的地位。誠如馬克思所論述的那樣,“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23),那么數字技術將產生以誰為首的社會,尚未可知。但無論如何,不同社會形態或社會發展階段的社會主體,新的人性的構成部件無論如何翻新,但總歸是人的本質屬性在新的生產力、生產關系條件下的具體呈現。數字技術也許可以實現默里·布克欽所向往的“充足的生活資料不再需要日復一日的辛勤勞作”的社會圖景。(24)從這個意義來講,人相對于技術的文明程度決定了技術是否具有“工具性”,技術不是不能被人類所控制,而是必須由相應形態的“新人”來加以管控。一旦人類中的部分個體落后于社會技術的發展,便有可能會被迅速發展的技術所淘汰,正如當下社會“數字弱勢群體”“數字鴻溝”等現象的產生。人類落后于數字技術發展就會引發新的未知風險,使社會倫理道德陷入混亂境地,或者人類文明形態落后于數字技術應有的主張,則會表現為人利用技術“作惡”。
總之,數字技術與數字工匠之間的關系可以被描述為一種動態且相互構成的互動關系。這一互動關系的核心在于人類主體的能動性與技術客體的可塑性之間的對話。數字工匠通過其專業技能、知識基礎和創新實踐,不斷推動數字技術的演進,而技術的發展又反過來塑造工匠的認知結構、工作方式和社會互動模式。在這種互動中,技術不僅是工具,更是人類意志和智慧的延伸。數字工匠通過對技術的操控和應用,實現對現實世界的干預和改造,同時也在虛擬世界中構建起自己的存在和身份。技術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它既反映了工匠的主體性,又構成了工匠社會實踐活動的物質基礎。技術構造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技術與人類主體之間存在著一種本質上的相互依賴關系。技術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同時也是這些實踐得以實現的條件。數字工匠通過與技術的互動,不斷重構自己的實踐領域,而技術領域也在這些實踐中被不斷地重構。
四、人的解放微光初現:數字技術與未來人類共生的圖景展望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要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就必須要揚棄當下社會這種對待技術的極端論斷。技術對人的構造從未停止,數字工匠在未來或可開創出當下社會所無法想象的新圖景,進而加速人類在更高級的社會關系屬性上的大團結,甚至給出人類未來社會邁向徹底解放的現實路徑。
首先,數字技術在替代人類工作的同時,也會為社會創造出更多意想不到且充滿價值的新崗位。數字技術的發展并非只有使大批傳統行業消失與從業者失業這一種后果,從一個更廣闊的發展格局來看,數字技術必然使勞動形式產生變革,與此同時還會催生出更多更新的崗位。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滲透到原本難以滿足公眾需求的行業,而這些技術一旦有了新的突破,就可能會對現有的社會體系產生沖擊,進而打破原有的行業發展進程,催生出更具潛力的勞動方式與產業格局。未來社會的數字工匠內涵絕不僅止于此,大規模的智能機器生產的確會取代現在的一些勞動者,但人工智能的物質生產亦將由人類共享。從這個角度而言,利用新技術“生產什么”“怎么生產”“生產的環境如何”都將由人類做主,數字工匠將會由自主勞動轉為人機共生式的勞動,這未嘗不是新技術的價值延伸。
其次,新技術對人的構造離不開人類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復雜的生產活動也必然會催生與之適應的社會活動。社會制度的不斷優化或許可以為人提供更為舒適的環境,工匠無論是借助技術提升自身技能也好,還是利用技術掌控機器人也好,其本質都是為了及時適應不斷發展的技術生產力,并推動生產關系與之匹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提出的解決方案并未將人類從新技術所帶來的困局中解放出來,反而使社會陷入更深層次的技術混沌,乃至現實政治與烏托邦的雜亂之中。“從長遠看必將突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束縛,瓦解資產階級越來越殘酷的剝削統治,推動當代社會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進,逐漸解放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25)蓋·蘭道爾也認為:“另一個選擇似乎就是新技術的分配。這將潛在地給廣大群眾提供工具,讓他們打造各種勢力形式和勢力范圍,與技術集權對抗”(26)。在未來,數字工匠無疑是新技術的利用者,在推動社會關系的變革進程中必然會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
最后,數字時代的人類應該享有極為豐富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人類社會的解放運動也終將如火如荼地展開。數字技術的強大工具價值,將會推動社會生產力朝著實現按需生產與分配的方向不斷前進。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國家可以更加智能地、系統地調配產品生產。當社會可以真正做到按需生產,則可以使勞動者獲得充分的自由時間以發展自身。數字技術可以解放工匠大腦面臨的繁雜細節之苦,探索出更多的自由時間和自在空間,使得廣泛意義上的數字共同體的出現具備了潛在可能性,這也會進一步促使全人類邁向聯合。當然,單靠數字工匠個體的、自發的團結難以取得最后的勝利,通過技術實現人類解放還必須由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無論是數字技術的加持,還是數字工匠和網絡用戶的推動,人類解放的實現必然會面臨持續而又廣泛的斗爭。因此,“這一現實的數字共產主義運動只有以無產階級政黨的帶領作為支援背景,才能真正得以實現”(27)。換言之,只有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廣大的數字工匠才能更廣泛、更深入地投入到人類解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之中。
五、結語
數字技術融入當代社會的生產生活過程,離不開對數字工匠主體性的思考。由此來看,人的主體性在經歷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體系”的短暫替代之后,終將實現人對更高級“機器體系”的主體性回歸。此問題的關鍵顯然不在于技術本身的進步與否,而在于與技術配套的制度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立足于馬克思的“機器體系”理論,技術構造論則是一種從不畏懼任何未知和挑戰的思維方式,也是將人類社會推向更加高級的存在形態的文明主張。
注釋:
(1)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2頁。
(2) 石超、鞠巧新:《新時代創造性勞動教育再思考》,《教育評論》2021年第8期。
(3) 胡景譜、陳凡:《新時代中國特色數字工匠的角色期待及其實現》,《科學技術哲學研究》2023年第2期。
(4) Ellul Jacques, John Wilkinson trans.,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Alfred A. Knopf and Random House, 1964, p.418.
(5) 黃靜秋:《人工智能算法賦能勞動的新樣態——基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視域的研究》,《經濟學家》2023年第10期。
(6)(8)(18)(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505、163、108頁。
(7)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頁。
(9)(20)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358頁。
(10) Sam Francis, Nationalism: Old and New, Chronicles, 1992, p.19.
(11) 褚樂陽、陳衛東、譚悅等:《重塑體驗:擴展現實(XR)技術及其教育應用展望——兼論“教育與新技術融合”的走向》,《遠程教育雜志》2019年第1期。
(12) 袁烽、朱蔚然:《數字建筑學的轉向——數字孿生與人機協作》,《當代建筑》2020年第2期。
(13)(15)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7—878、88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頁。
(16) 戚聿東、丁述磊、劉翠花:《數字經濟時代新職業發展與新型勞動關系的構建》,《改革》2021年第9期。
(17) 武豹:《人工智能技術下人的解放問題論析》,《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
(19) А. В. Бузгалин, А. И. Колганов, Глобальный Kапитал Tом 1, URSS, 2015, ст. 66.
(21) 《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頁。
(22) 廖興興:《論馬克思機器思想的轉變——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到〈資本論〉》,《理論界》2023年第12期。
(24) 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Black Rose Books, 1986, p.12.
(25) 李保艷、劉永謀:《智能革命與共同富裕:走向“AI的社會主義應用”》,《云南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
(26) [澳]蓋·蘭道爾:《創客時代:3D打印、機器人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的未來》,高宏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年版,第178—179頁。
(27) 韓秋紅:《數字資本主義視域下的異化勞動批判與共產主義構想》,《求是學刊》2023年第2期。
作者簡介:石超,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山東青島,266580;王英明,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 山東青島,266580。
(責任編輯 陳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