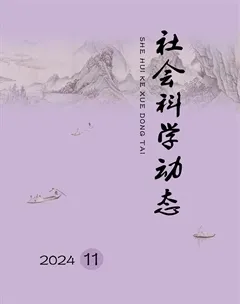文明互鑒視野下的中外文學關系新論
2024年8月16—20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十四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于遼寧大連召開。本屆年會由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和大連外國語大學共同主辦。來自中國、美國、英國、加拿大、葡萄牙、巴西等10余個國家近200所高校的40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主題是“新文科建設與跨文化視閾中的比較文學”,設有20個分議題。其中一個重要的分組,是以“文明互鑒視野中的中外文學關系”為主題。在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歷程中,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分別代表了影響研究與平行研究兩大范式,跨文化研究作為中國比較文學參與這一學科的標志之一,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成為相互影響并彼此依存的對話主體。那么,在文明互鑒視野下,如何看待中國文化與文學在西學東漸、中學西漸中的主體性,并發掘其現代價值與現實意義,是值得不斷深入探討的經典話題。來自20多所高校的20余位專家學者以及博士生參加這一小組的討論,進行學術交流分享。
一、主題發言:在跨文化研究中發掘中國文化與文學的現代價值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副會長、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高旭東是大會這一分組的召集人,并在會上進行了主題發言。高旭東教授多年來深耕中國現代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對中西方文學文化研究頗有造詣。在文明互鑒視域下對中國文化與文學現代價值的發掘與重估,是他關于中西跨文化研究的最新思考。他認為,近代以來從“西學東漸”到胡適的“全盤西化”,都是西方文化以強勢姿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然而,當中國人在現代虛心學習西方文化的時候,西方文化卻出現了衰落的跡象。在充分肯定新文化的西化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上,他認為中國的當代是確立了中國的文化主體性(以尋根文學以及遍布世界的孔子學院為標志,與現代反傳統與打倒孔家店迥然不同),而且隨著跨文化研究的興起,人們會越來越發現中國文化所具有的現代價值,以此可以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西方文化是根植于宗教的文化,中國文化則是以倫理為精神核心的文化。從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西方文化是從神話、宗教而走向實證科學,中國文化則自古以來不太注重神話宗教,而以現實世界里家國族類的興旺為第一要務,并因其早熟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西方文化從“為知識而知識”的注重理論科學到倡導“知識就是力量”的注重科學實用性是一個轉折,中國文化則一向忽視理論科學而注重實用技術;西方文化從注重客觀到強調主體性,中國文化則一貫注重主體;西方文化從一元排他性的宗教信仰到現代的文化多元化又是一個轉折,中國文化則一向兼容并包,所謂“三教同源”;西方文學觀念從重摹仿到重情感,中國文學則一向注重抒情。這些都體現出西方文化與文學向中國的靠攏,并且凸顯出中國文化的生機與活力。
中國文化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儒家文化用倫理代替了宗教的職能,以倫理的整體性超越了個體生命的短暫,使民族精神得以流傳延續。西方則因“上帝死了”而陷入精神幻滅,進而透支財富而追求享樂,以至于造成次貸危機;中國人則將子女視為生命的延續,因此注重子女教育,傾向于儲蓄和財富積累,因而即使沒有圈地運動與海外掠奪,也能夠在現代化上起飛。在文化傳承模式上,西方文化詩學的精確性使后起詩學的發展必然要對前者進行批判否定;中國詩學的模糊性和靈活性則可以使后起詩學對前者不斷闡釋補充,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得以延續。在文化發展的成熟期,承傳與保存文化比創造文化更為重要,以倫理和傳承為根本的儒家文化所具有的現代價值便體現于此。“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表面上打著全盤西化的旗號,然而倡導者那種強烈的使命感卻來自傳統文人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并且儒家文化不以信仰為重而注重振興家國社稷的精神也是倡導者輕易拋棄傳統的深層動因,因為世界上各大文化都沒有在民族危機時拋棄文化傳統,只有儒家文化背景的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生了這種文化景觀。
中和是中國最重要的文化觀念,并且外化到民族性格、審美情感等各個方面,這一點與以二元對立為核心的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中國二元融合的文化傳統既以寬容的姿態,將不同文化彼此兼容,并反對戰爭愛好和平,以懷柔策略協和萬邦。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西方文化經歷了從征服自然再到回歸自然的過程,而中國的儒道文化則向來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是西方后現代生態文明的知音。最后,高旭東教授還從文化的角度對西方20世紀文學理論進行了反思,認為其雖然擁有眾多流派,但各種理論往往只計一點不計其余,具有片面性;而中國中和的文化傳統能夠從整體上將各個批評流派進行溝通,形成全新的批評整體,這有待于中國批評家的進一步整合與探索。
二、以中釋西的文化主動性:西方文學與文化在中國的傳播
從晚清到當代,西方文學的傳入深刻影響了中國文學的變革和發展,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有所差異的文化特征。中國作家對西方文學文化的接受與其自身的思想傾向有所關聯,也留下了社會歷史背景的濃厚烙印。在本次分組討論中,共有7位與會代表聚焦西方文學與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對其文本變異、接受路徑與文化影響進行細致分析,并突出強調了中國作家在接受時表現出的文化主動性。
西方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離不開社會背景與文化環境的影響。南京大學董曉教授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俄蘇文學在中國的三種不同境遇。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作為中國當代作家的楷模,到“反修防修”時遭到徹底批判,再到新時期以來受到重新關注,他認為俄蘇文學在當代中國的不同境遇一方面源自不同歷史階段的意識形態話語,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當代文學自身發展階段的特殊呈現。中國人民大學陳睿琦則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分析了林紓漢譯莎士比亞歷史劇與民初政治的關系,認為林紓的實用主義政體思想與愛國情懷使他在翻譯中將國家命運放之于羅馬劇中君主制與共和制的矛盾之前,并通過中國傳統君權觀調和了英國歷史劇中弒君篡位的合法性問題,反映出他在政治動蕩時期對社會穩定的期望。
除了基于社會政治因素對西方文學在中國接受展開考察以外,還有很多學者分析了西方文學譯介對中國作家文學創作的影響。天津大學許謹教授認為譯詩對于中國新詩的意義比其他翻譯文學對于其他文體的意義重大得多,并運用扎根理論建構了外國詩歌譯介影響中國新詩的多維整合模型,將其歸納為外部要素、內部要素、過程要素和結果要素四個關鍵點。通過大量樣本的整理與分析,發現譯詩不僅改變了中國詩歌的發展方向,而且是中國新詩的模仿對象和重要創作資源。北京郵電大學的陳曲以《食草家族》為例,分析了卡爾維諾對莫言小說創作的影響。她認為大多數學者忽略了后現代小說大師對莫言小說的深層影響,事實上卡爾維諾與莫言小說具有相似的創作背景與寫作困境。卡爾維諾“輕”的小說觀啟發了莫言的創作視野和創作維度,并在他的《食草家族》里得到充分體現。聊城大學趙文蘭教授聚焦魯迅與西方作家的關系,認為相較于學界普遍關注的果戈理、安特萊夫與屠格涅夫等作家,魯迅與曼斯菲爾德、狄更斯的小說在主題意旨、人物形象與敘事形式方面也存在諸多共性。她在文本對照細讀后得出結論,認為魯迅在對這幾位作家的接受中進行了創造性轉化,使其作品具有中西交融的特點。
中國作家對西方文學與文化的接受,一方面體現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其文化思想層面。北京語言大學于偉以老舍1930年代在齊魯大學授課時編撰的課程教材《文學概論講義》為對象,分析了老舍在這一時期的文學觀念。老舍1920年代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授漢語,期間他接觸了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小說技巧,以及巴西爾·沃斯福爾德與馬修·阿諾德等人的文學理論。這些閱讀經驗對老舍文學觀念的形成影響深遠,是他自身詩學體系的重要文化資源。中國人民大學朱浩然分析了赫爾岑對巴金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經由克魯泡特金《俄國文學史》對赫爾岑的推薦,1936年巴金因為翻譯《往事與隨想》,從而接受了赫爾岑反對封建專制主義、強調個人自由以及對人類的愛的思想,并在《隨想錄》中體現出與《往事與隨想》的相似性。
三、中學西漸的文化價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海外傳播
16—18世紀,歐洲逐漸對中國文學文化與哲學思想產生強烈的興趣,并在啟蒙運動達到了學習中國的頂峰。直到當代的西方文學與哲學理論中,我們依然能夠看到許多中國文化思想的影子。那么,如何在文明互鑒視角下發掘中國文學與文化的世界意義,并重估其在中學西漸不同歷史階段內的文化價值,這對于我們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建構中國文化自信有著重要啟示。一批學者聚焦中國文學與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傳播問題,分別從中國典籍、文學作品在西方世界的翻譯、西方文論中體現出的中國思想等方面,探討了中國文化對西方世界的意義。
中國典籍翻譯是中學西漸進程中的重要文化橋梁,較早對于西方發生影響的是傳教士對中國典籍的介紹,后來隨著《論語》《道德經》等經典作品的翻譯,這種影響逐步加深。中央民族大學高志強聚焦于《論語》的第一個英文譯本《孔子的道德箴言》,分析了它的源流及其對西方世界的影響。該譯本由《中國人的哲學家孔子》一書的法語節譯本轉譯,僅有25頁80則,但對英美啟蒙運動,尤其是對富蘭克林,乃至對美國精神的形成都起到重要的作用。這種文化經典的翻譯和傳播既是西方世界了解古老東方智慧的重要源泉,也顯示出中國典籍在異質文化下的強大生命力。
法國文論是西方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國學者與漢學家的理論思想不僅源自西方文化傳統,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這為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提供了新的視野。華東師范大學吳攸教授論述了法國學者謝閣蘭、朱利安根植于中國問題的文論話語,認為謝閣蘭建構的“多異美學”與朱利安主張的“多元共生”文化觀均是西方文論闡釋中國問題的重要范式。正是中國文化的“他者”視角,啟發了法國文論的自我反思與知識生產,并在強調多樣性文化價值的基礎上,推動了中西文明互鑒。湘潭大學蔡熙教授探討了德勒茲詩學中的中國元素,認為德勒茲與中國文化的相遇是一種富有開拓性的精神對話。德勒茲的差異哲學和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存在暗合其“混沌宇宙”概念又和道家的“虛”“無”思想有所關聯。德勒茲重視“他者”,而中國作為西方的“他者”,為德勒茲的文化詩學提供了思想資源。
除了文化思想在西方世界的接受之外,文學作品也承載了中國文化的世界性意義,是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重要載體。西安交通大學魏琛琳副教授探討了李漁劇作與劇論在德國漢學界的傳播,對其近100年的接受歷程進行了梳理。從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艱難德譯,到60—70年代的逐步復蘇,再到70—80年代以來的多元繁榮,李漁在德國的傳播與研究顯示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征,并與德國漢學界的發展同步。以此為例,她認為漢學視野的引入對中西文明互鑒具有雙向意義,既能夠觀察中國文學“外化”的傳播路徑,也能夠檢視他者“內化”中國文化的深層動因。
中國文化在異質文化的傳播不僅體現在文學經典的外譯,從外來者跨越文化差異對中國社會的融入也可見一斑。山東財經大學高婷教授梳理近代以來抵達上海的猶太人的歷史,并基于以色列漢學奠基人伊愛蓮的《上海之聲》,闡述了猶太人努力跨越語言、信仰體系和民族傳統障礙融入中國社會的心路歷程。《上海之聲》匯編了猶太難民二戰期間散居中國后創作的信件、日記、詩歌及短篇小說,是對流散文學的充實。中國既為他們提供了躲避戰火的容身之地,其對中國的融入也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包容性。
四、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視野:在跨文化中重構他者
“他者”的概念源自于柏拉圖的《對話錄》,經由薩特、拉康、福柯與列維納斯等人的不斷充實,在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與生態批評等諸多理論話語中都有所重釋。以往西方文論中的“他者”往往指代和主體相對的客體,強調其異質性。在當代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我們一方面要認清“他者”話語所隱含的霸權思想,反對這種文化與主體間的二元對立,注重文化平等對話交流;另一方面,“他者”也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視野。本次分組討論多位學者聚焦跨文化對話中的“他者”意識,從生態文學研究、國別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等不同角度展開論述。
“他者”不光指代不同的文化主體,在廣義上也能延伸到生態的層面,用來指代除人類之外的自然環境與動植物。集美大學王坤宇教授聚焦“人類世”這一融合了人類文明發展和自然演化規律的概念,認為將其作為研究視野能夠為我們重新審視“我者”與“他者”的關系提供新的契機。他分別從人類世中的文學書寫、文化宗教、生態意識與人工智能的角度,探討“他者”的概念邊際如何得以拓展,并深刻影響我們的生活與思維觀念。上海大學苗福光教授將“他者”的概念延伸到了人與動物的關系上,以袁博的《內伶仃島上的獼猴》等一系列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動物小說為對象,探討了其中所蘊含生態倫理的內涵與未來。他認為當代動物小說既建構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關系,也批判了人類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惡行,已經成為覆蓋全年齡讀者的小說書寫體系。當代動物小說雖然面臨許多挑戰,但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
除了基于跨文化、跨學科視域下的比較文學研究,“他者”這一關鍵詞也能為國別文學研究提供理論視域。中國政法大學宋慶寶副教授探討了沃萊·索因卡《死亡與國王的侍從》中的社會悲劇主題。他認為小說中艾雷辛的死亡既源自皮爾金斯基于西方價值觀的失敗拯救,也與其非洲的文化宗教觀念有關。小說中描繪的殖民主義者和非洲民族主義者的文化沖突對非洲社會與世界的接軌具有參考價值。作為西方世界的“他者”,非洲在融入世界的過程中應當對自身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并建立民族文化自信,這對中國新時代文化建設也有著借鑒意義。遼寧師范大學谷野平教授從新歷史主義的視域解讀了愛德華·P·瓊斯的《已知的世界》,小說描繪了美國內戰前夕黑人奴隸主對奴隸的殘忍壓迫,直面了美國蓄奴制度的復雜性,表現了奴隸的生存困境。正是非人道的社會制度造成了一個個社會悲劇,小說雖然是虛構的,卻又是當時美國南方無數個城市的真實寫照,體現出文本與歷史的互動關系。
在世界各國與不同文化之間交流愈加緊密的歷史背景下,我們應當拒絕狹隘的自我中心主義,以開放性的視野來認識“他者”,接納“他者”,并且與“他者”積極交流對話。國際關系學院康毅副教授將露西·伊利格瑞的思想與道家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西方思想中的“邏各斯”推崇理性中心,在壓抑非理性的同時也壓抑了女性和自然。伊利格瑞的思想策反邏格斯、反對二元對立并揭示了西方傳統話語對人的壓制,這一點與道家思想中主張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有所類似。上海大學肖寒則從中西不同物質文明所造就文化意識差異的角度,對中西莎士比亞接受與研究進行了對比分析,認為由于中國歷史、宗教、價值觀與莎士比亞戲劇文化語境的巨大差異,使得莎士比亞戲劇在中國的譯介接受與藝術改編中產生了諸多變異。清華大學閆學詩探討了老舍與康拉德南洋書寫中的族裔身份認同問題,認為兩位作家都著力表現了不同種族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文化身份認同的困惑。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兩位作家的南洋書寫也為如何實現跨文化的相連相通提供了重要參考。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與世界多極化都對我們提出了新的歷史要求。“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展”,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世界文明共同發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方式。本場分組討論聚焦中外文學關系這一經典話題,但眾位參會代表并未被既有學術范式所束縛,而是在傳統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新的學術理論、文獻材料與思考視域,對既往學術觀點進行了反思與重構,體現出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傳承性與創新性。文明互鑒既要求我們尊重世界文學與文化的多樣性,也需要我們重視中華文明之根基,發掘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現代價值,進而重新審視中外文學關系的歷史與現狀,為未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提供了參考方向。
作者簡介:陳睿琦,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責任編輯 莊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