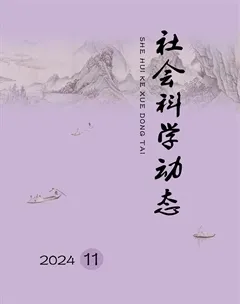全祖望治學傾向探析
摘要:在朱學重新獲得清廷政策支持、社會秩序趨于穩定的時代背景下,全祖望擁有一套對立統一的治學傾向:他提出要破除理學內部的狹隘門戶之見,綜合地、批判地認識與理解理學各大分支的學統;要辯證地看待儒學思想中的佛學要素,反對儒佛合一和盲目排佛的極端學術傾向;要踐行并弘揚儒家忠孝節義的道德規范,重品行而輕學力,進而維護儒家主導的道德秩序,提升“圣學”的現實影響力。全祖望的思想吸納了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等前人的學術旨趣和治學路徑,直面朱學獨尊于朝、文化管控收緊等新的社會現實特點,為明末以來的經世致用精神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和現實意義;然而其中和、寬容的學術傾向決定了他搖擺不定的思想立場,在失去其歷史語境之后,后世研究者容易管中窺豹,最終背離全祖望的學術意圖和理想。
關鍵詞:全祖望;治學傾向;朱學獨尊;經世致用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982(2024)11-0085-08
對于全祖望學術特點、治學傾向等問題的探討,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已產生一批學術成果,但總體多聚焦于全祖望思想的某一方面,評價上強調其學術歸屬與學術成就,將全祖望視為黃宗羲思想的傳人,或是“浙東學派”“浙東學術”等學術共同體的一部分(1);至21世紀,隨著研究的深入,學界多已認識到全祖望較黃宗羲、顧炎武思想的差異性和獨立性,且進一步認識到全祖望思想的局限,將全祖望思想研究推進到了新的高度(2)。基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結合全祖望所處時代的政治、學術背景,通過追溯全祖望所利用的思想資源,重新對全祖望的治學傾向進行綜合評估,以期更全面、客觀地認識全祖望的學術立場與態度,豐富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成果。
一、破除門派成見,綜合各家學統
理學(3)自宋代誕生以來,就產生了朱熹與陸九淵的學術分歧,及至明中葉,王陽明建立心學,朱學和陸王心學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終于在明末爆發出來,理學內部的門戶之爭走上臺面。全祖望說“吾鄉之學,朱、陸二派并行”(4),就指明了他家鄉朱學、陸學兩派長期對立的學術格局;比他稍晚面世的《四庫全書總目》更是直接點破,理學自宋以來分成數派,而各派之間彼此仇視,有不少學者只知“各尊所聞,格斗而不休”(5) ,造成了毫無營養的思想內耗,這一學術生態顯然不利于理學的持續發展。
對此,全氏繼承了黃宗羲的態度和立場,反對程朱陸王之間黨同伐異、墨守成規的偏激之見。黃宗羲在思想立場上強調“一本萬疏”,即遇到“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6) ,就應當沉心梳理其差異處,促成“萬殊總為一致”(7) ,而非止步于互相攻訐;全祖望更進一步認為,理學既然自南宋以后就分為朱學、陸學和呂學三派,且這三家都可“歸宿于圣人”(8) ,就不應該墨守一端、顧此失彼。他認為“門戶之病,最足錮人”(9) ,反對學者以“門戶”的尺度度量他人思想的優劣。他對近來一味墨守成規的朱學之人嗤之以鼻,認為他們作繭自縛,“錮其神明,塞其知覺”(10) ,只會將朱學帶向衰落;而那些因門戶而結黨之人,在他看來更是只屈從于“分軍別幟”(11) ,對學問只知盲從,或是沉迷于口舌之辯,他們在學問上恐怕不會有所成就。
因而,他推崇朱熹“去短集長”的方法,呼吁學者應客觀認識到理學內部各派的長處,這樣才能繼承更為完整的“圣人之學”。他指出朱、陸二學在治學方法上多有互通之處,只是由于切入的思路不同,便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后人在追溯朱、陸思想時,由于未能洞見前人思想的根本,往往僅憑一己之見妄自揣度,最終陷入誤區。他進一步提出期望,“古人”治學,在學術路徑上可能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向“圣人”尋求學問,這里的“古人”他沒有明確指代對象,但從他的態度來看無疑是他所期許的理想學者。(12)
于是在方法論上,他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只要某個思想能夠投諸實踐,就不應該計較該思想的學派歸屬——即其所述的“門戶”。用他的詩文來說,“陋儒門戶妄相攻,言朱言陸總朦朧;試問生平踐履果何似,尚其泥首三江東”(13) ,這是他在程朱陸王問題上學術傾向的集中寫照。因而,他十分推崇保持思想獨立、“不以茍同為是”(14) 的學者。全氏在記述人物時,往往喜歡強調其人思想的獨立性和獨特性,如楊守陳(1425—1489)“于先儒多異同”(15) ,陳汝咸(1658—1716)“不徒為雷同之口”(16) ,錢光繡(1614—1678)“并非隨波逐流之謂”(17) ,史蒙卿(1247—1306)“非墨守……諸書以為茍同者”(18) ,都是在輸出與強化這一精神。全祖望縱使討厭毛奇齡(1623—1716)的為人,惡其“自尊大”“無忌憚”,但毛奇齡對朱熹為首的宋儒痛恨得咬牙切齒,他也只能先退一步承認自己同意毛氏“朱子亦未嘗無可議”的質疑態度,再譏諷毛氏的語氣如市井無賴一般惡俗,認為他毫無儒者風范,這也是由他看重實踐的學術精神所決定的。(19) 用全祖望自己的話說,“夫圣學莫重于躬行,而立言究不免有偏”(20) ,后進的儒者應該將主要精力集中于效法先儒的實踐精神,倘若只沉浸于紙面文字,最后就會淪為紙上理論的奴隸,在實踐層面難堪大用。
與黃宗羲相較,黃、全二人在程朱陸王問題的方向和態度上都趨于會同與調和,然而在落腳點上本同末異。簡言之,黃宗羲側重于“求同”,尋求程朱陸王在學術上的共通點,以調和理學內部的門戶矛盾;而全祖望側重于“存異”,強調程朱陸王的差異性,且各派理解都各有其合理之處。他客觀上固然也有調和分歧的意思,但更旨在強調學術之“異”而非學術之“同”,他推崇不輕易茍同他人意見的學者,即是明證。
黃宗羲和全祖望在程朱陸王問題上表現的細微差異,可追溯于他們所處時代理學發展特點的區別。黃宗羲身處明末清初的社會動蕩時期,程朱之學失去了朝廷的政治庇護,與陸學、王學等理學其他分支處于相對平等的地位,因而程朱陸王之間的學術分歧成為黃宗羲面對的主要矛盾;但隨著清廷的統治走向穩定,自康熙朝中后期開始,清廷在程朱陸王之中獨尊程朱之學,“祖濂禰洛,宗朱社張”(21),以陸學、王學為首的其他理學之見被遏制,這使得程朱之學成為陸、王等其他學派眼中的眾矢之的。全祖望提倡破除門戶之見,理論上當然是面向當時含程朱陸王在內的理學眾學派,但其攻擊之對象一旦指明門派,無不是獲得政治話語權的朱學之人,沒有陸學、王學之人,這是全祖望思想立場的暗線,也是后來學者鮮有注意的。換言之,針對康熙朝以來清廷獨尊朱學的理學政策,也可以認為全祖望是在嘗試為陸王之學、呂學等弱勢理學分支謀求政治上的平等地位,至少也是試圖論證陸、王之學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以謀求生存空間。
二、掃除佛學空疏,理性抵制佛學
明末清初以來,與程朱陸王“門戶之爭”同時進行的是理學對自身與佛教、佛學關系的自我反思(22) ,這是自宋代以來一直存續的思想議題,又與清初明遺民的“逃禪”之風息息相關。及至全祖望所處時代,這批“逃禪”的明遺民已經幾乎全數辭世,不可能再發揮直接現實影響,但全氏在整理晚明史時涉及大量時人,其中不乏有“逃禪”經歷者,因而不得不對他們的“逃禪”經歷表態。從這一角度看,全祖望既要繼承前人的思想議題,對“圣人之學”的興衰問題進行思考,又要在現實中“圣學”對佛家、佛學的態度問題上給出己見;既要對清初的“逃禪”風波蓋棺定論,又要在自身所處時代的現實學術環境中選邊站隊。
首先,在治學問題上,一方面,全祖望繼承晚明以來的“反理學”思潮,反對理學內部的狂禪之風。在梳理南宋陸九淵和楊簡的學脈時,他認為二人思想各有其精華之處,但他們的弟子在效法先師時往往盲目照搬、不懂變通,致使“一往蹈空,流于狂禪”“泛濫洋溢,直如異端”(23) ,不僅扭曲了陸、楊的本意,也給二人惹來了后世無端的非議,這里全氏把“狂禪”與異端相類,表明全氏對兩者皆不認同。因此在對待佛學的問題上,全祖望強調“正學”的概念,重申儒佛之間的界限,反對沒有儒佛邊界感的“喜禪”旨趣,更厭惡儒家內部“儒佛合流”的危險論調。(24)
反映在現實環境中,全祖望積極強調佛家在社會層面上的負面影響,告誡世人從儒遠佛,這說明其治學傾向中保留了宗教意味的對抗色彩。他大量抄錄李世熊(1602—1686)在《狗馬史記》中批駁佛家“委蛇塵劫,文之曰忍”、欺騙世人的論述,認為佛家思想蠱惑人心,只會把人的思想推向虛無(25);他對信奉佛家鬼怪之說的人不屑一顧,認為他們所言所見的“如來”“大士”之像不過是“幻景”“蜃市”(26);他強調佛家“塵視世界”的價值觀違背了人道,會摧毀儒家致力構建的綱常秩序(27)。
于是在回顧明末清初“逃禪”風潮的時候,全祖望追隨黃宗羲的腳步,在總體上給予否定的評價。他將黃宗羲“不甘為異姓之臣,乃甘為異姓之子”(28) 的駁斥之語當作自己的信條,將背離儒家、服膺佛家的行為與甘為貳臣的背節之舉等同起來加以批判,足見這觸及到了全氏的底線。在記述明末人物的“逃禪”之舉時,他往往先要強調“逃禪”性質之惡劣,指斥這種行為必然會被世人所非議(29),以表明自己對“圣學”的堅定態度;在記述之余,他往往還要表達對事主“逃禪”選擇的惋惜,認為他們學識之淵博,不是佛門所能承載或吸納的,以再度宣揚自己的儒者立場。(30)
然而,全氏的對佛態度也有包容的另一面。在評析前人的學術思想時,他常運用梳理學脈的手段,將宋儒之學與宋儒后學相區別,批評后者而維護前者,其意是在表明自己只愿意反對理學“空談性理”的極端做派,無意于沖擊理學“言性”的根本特征。除了上文所舉的陸九淵和楊簡的例子,這一立場也可以從他對顧炎武思想的反應和理解中看出。顧炎武曾比較“理學”和“經學”,提出了“經學即理學”的著名論斷,其本意是,宋代以來的“理學”拋棄儒家義理而空談性理,于是走向了“禪學”的邪路,他對這一走向表示不滿。于是,他追求回歸“古之理學”,用宋代之前的“義理之學”來修正宋代之后的“性理之學”。全祖望對這一系列論斷加以帶有原創性價值(31) 的闡釋與評價:
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溪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于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32)
暫且擱置顧炎武的原意若何,全祖望想要說明理學與經學密不可分,不能偏執一端。因此,與顧氏相較,全祖望一方面承認空疏之風是理學存在的缺陷,應該加以修正,并對顧炎武“經世致用”的精神比較信服;但另一方面,他認為顧氏矯枉過正,不認同顧氏對理學價值的整體質疑與全盤否定,尤其是拒絕把“理學”與禪學異端等同起來,因而比較委婉地表示自己對顧氏論點的反對。
反映在對待佛學的態度上,全祖望在強調儒佛邊界的同時,又坦然承認佛學的學術價值,主張汲取佛學思想中的精華,在“排佛”的問題上留有余地。他反對吹毛求疵式的“排佛”手段,強調縱是宋代伊洛之學的大儒,到了晚年也無不與僧人交游,要求儒者思想與佛學絲毫不沾已不現實(33) ;有人攻擊唐代的李翱思想主張不夠純粹,有時還言行不一,“言道而其言未純于道,辟佛而其言時或染于佛”,全祖望認為這不過是“學力稍未至”的問題,不應由此求全責備,否定李翱的學術成就。(34)在論述儒、釋、道三家的關系時,他雖然言明自己“不信二氏之學”,但也表示自己能認識到佛家思想的精深,且對佛法高深、積極救世的僧人表示敬佩——他認為有些佛徒與道人獲得了“驅役鬼神之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應該為了維護“圣學”而顛倒黑白,一味貶低和否定佛、道兩家的獨特能力。(35)
在生活中,全祖望有時不但不回避佛家要素,甚至還涉獵佛家典籍,佛家和佛教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浸潤他的生活。在自傳中,他樂于記述家鄉的佛地與佛事,稱家鄉為“仙釋之場”(36) ,言語中飽含自豪之意;他一再強調自己不道“二氏之說”,但也不忌諱“偶或因文獻而及之”(37) 。他對佛教阿育王舍利的來龍去脈進行考證,最終定論家鄉甬上所供奉的“阿育王寺舍利”只不過是“佞佛”之人胡亂捏造出來的,不足以信(38) ;好友李紱問他某詩句的出處,他回答說“二語元不見于佛書”(39) ,這側面說明他閱讀了不少佛書。
全祖望在對佛問題上欲拒還迎的態度要回溯到理學的產生歷程。有學者已經指出,宋明以來的理學,“既是反佛老的產物,又是融合佛老的產物”(40),中肯地指出了理學在思想傾向上的矛盾性。反映在全祖望的身上,他在對待佛學問題的看法既有斗爭性又有妥協性,既一再呼吁儒者在儒佛關系問題上要堅持與佛家的思想邊界,不要把理學與佛學攪在一起,又不愿放棄佛學思想中的精華,認可佛道的長處,且反對因“學力”問題對他人“染佛”求全責備。這一矛盾一方面源于理學自誕生以來就攜有的本質特點,另一方面全祖望廣博中和、反對極端的學術氣質客觀上也加劇了其在對佛態度上的搖擺性。
三、表彰忠孝節義,論學必先論德
作為清代浙東經史學術傳統的開山學者,針對空疏學風,黃宗羲提出了治史的解決方案,全氏則繼承了這一學術路徑。黃宗羲強調“受業者必先求經”,先把思想從近世的語錄中解放出來,返諸時代更為遙遠的六經;但“求經”又容易陷入只知考辨、不問世事的窠臼,于是黃氏又“兼令讀史”,要求通過回顧歷史的方式間接獲得現實經驗,以提高處理現實事務的能力,這是黃宗羲“經世致用”精神的集中體現。(41) 全氏同樣重視史學的現實指導作用。他回憶自己擔任端溪書院的主講之前,書院學生多沉心于練習科舉寫作,最后無法“脫然自拔于時風眾勢之中”,寫就的文章也墮于流俗;于是他“稍以經史之學導之”,提倡在習經之余讀史,一些學生聽取了他的意見,果然文風大變,于是繼續鼓勵他們,希望學生們擺脫辭章小技的束縛,以繼承明代陳獻章、黃佐等書院前輩的學問與學風。(42)
不過,全祖望雖然與黃宗羲都致力于保存南明歷史,但在現實層面的意圖上,目的又有所不同。黃宗羲治史除了緩和性理空疏、提倡經世致用等學理上的考量以外,還有與清廷分庭抗禮的政治意圖。他親歷明末戰亂,目睹了清軍南下的過程,拒絕與清廷合作,因而他表彰故明遺臣,也有以明己志的意思在。對此有學者指出:“黃宗羲在順治十年(1653)秋撰成的《留書》,其中充溢著‘華夷之辨’思想,……書中有許多反清言論。另外他……對抗清志士及保持民族氣節的‘亡國遺民’‘備加謳歌’。”(43) 雖然黃宗羲晚年轉入治學后對清廷的態度有所緩和,但黃氏保存南明隱史、記述抗清人物的目的沒有改變。
相較之下,全祖望的出發點絕不是與清廷的意識形態對抗,主要應該是出于道德秩序上的考慮。在全祖望的史論中,隨處可見儒家的忠孝節義精神,這放在整個清代來看都是極為罕見的,一定程度上啟迪了后世的學者。李慈銘對全氏的《鮚埼亭集》愛不釋手,在日記中記曰:“謝山尤關心鄉邦文獻,其文多言忠義,讀之激發,自十八九歲時即觀之忘倦。”(44) 晚清的劉師培高度贊譽全氏的治史工作:“說者謂雍、乾以降,文網森嚴,偶表前朝,即膺顯戮,致朝多佞臣,野無信史,其有直言無隱者,僅祖望一人。”(45) 客觀而言,后世學者多注意到了全祖望表彰抗清志士,尤其是在道德上加以評判、“激發”忠義之心的特色做法,且這一做法無意間成為晚清“反清”思潮的思想資源。
全氏表彰忠孝節義的道德意圖集中體現在他對于清初“逃禪”問題的認識上。在回顧明末清初的“逃禪”之風時,全祖望總體對其持否定態度,但其意旨又不止于此:他雖然反對“逃禪”行為,但樂于凸顯逃禪者身上符合儒家道德規范的忠孝節義品質,這是他記述明末“逃禪”人物事跡的一大目的。他認可趙秉文(1159—1232)“佞佛不害其為君子”(46) 的判斷,就是因為這一點,在他看來,“佞佛”只會影響一個學人的學術態度,而不會從根本上決定這個學人的全部言行是否符合儒道的標準。換言之,“佞佛”的學者也可能以實踐的方式貫徹儒道,這為全氏記史提供了動機與方向。劉宗周門徒惲日初晚年出家靈隱寺,一面指責他“逃禪”的行為一定會“為世所譏”,一面又補充“然其人終屬志士也”(47) ;徐啟睿出家后“粥粥如真道者”(48) ,沉默寡言,但全氏又刻意突出他關切時局的心態和出關從軍抗清的義舉;忍辱道人朱金芝抗清失敗,亡命深山,不知所終,全祖望感慨道:“(道人)死于兵耶?死于餓耶?死于緇黃耶?要之不愧于師門,其仁一也。”(49) 在忠孝節義的道德標準下,這些清初人物的特殊社會身份、學術思想立場等都居于次要地位,只要能夠“無愧師門”——符合儒家道德標準,便值得為其稱頌。總之,在明末清初的“逃禪”問題上,全氏是希望借助南明“逃禪”人物身上的忠孝節義事跡,弘揚符合傳統儒家規范的忠孝節義品質,最終實現壯大“圣學”現實影響的目的;至于他們“逃禪”行為本身,當然應該在立場上予以批評與反對,但由于彼時“逃禪”思潮已經幾乎平息,對現實中的儒學不再構成威脅,全氏沒有在影響問題上繼續深入。
正是出于對忠孝節義精神的重視,全祖望在點評人物時往往將人物品行之好壞與學術之“純疵”、高低相分離,表現出重品行而輕學力的學術品味。他為唐代李翱的辯護前文已述,正是本著這一原則進行的;他反感名儒李光地(1642—1718)、毛奇齡,同樣也是由于他首先對二人的品行表示厭惡。他為毛奇齡學術上的才氣而惋惜,認為他雖然在思想上的確有過人之處,但由于脾氣火爆,“以其狡獪,行其暴橫”(50) ,得罪了太多人,才難以在理學史上留名;對于李光地,他怒罵李氏在朝日久,對于治國安邦卻毫無作為,即使受到了康熙帝的重用,于其根本不過是沽名釣譽。他進一步解釋說,李光地人品有虧,并歷數李氏“賣友”“奪情”“以外婦之子來歸”三大罪,他對李氏的學術表現貶多于褒,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他首先對李光地人品“惡劣”的抨擊。(51)
全氏為什么要極力地突出南明志士身上的忠孝節義精神?這應再次回到明末清初以來的思想背景和儒學巨大變動。林聰舜認為,學界對于明清之際儒學發生巨大變動原因的分析理路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中“社會經濟變遷說”認為,明末社會經濟的發展沖擊了傳統的思想認知,進而激起了巨大的思想變革和社會秩序變革。(52) 雖然“社會經濟變遷說”在涉及具體問題時還存在一些未盡人意、不完全適用的缺陷,但其所著眼的社會問題,譬如明末義利觀的悄然變化、士人對商業態度的劇烈轉折等都是實際存在的,且最后都指向了一大議題:明末清初儒家道德秩序、社會秩序的毀壞與重建。
全氏在論著中對于明末清初儒家道德秩序動搖情況的直接記述較少,但亦能從他的只言片語中窺見他心中近來的儒學樣貌,以及他在這一問題上的悲觀態度。沈近思(1671—1727)早歲因家貧出家,還俗后考中進士,全祖望帶有嘲弄意味地感嘆道,“予嘗謂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而佛者,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沈)端恪始”(53) ,認為當時的儒學與佛學相比,已處于衰敗境地;南宋慶元路大嵩城的學田在元代被當地寺僧改為寺田,全祖望悲從心起,“嗚呼!天下最健者為沙門,而諸生為弱,豈徒慶元為然?”(54) 他回顧明末清初的“逃禪”風潮時談道:“星移物換之際,逃于西竺者多矣。然當其始也,容身無所,有所激而逃之;及其久而忘之,登堂說法,漸且失其故吾。”(55) 明清之際,一批儒者遁入佛門,起初還能歸因于時勢所迫,但久而久之,他們漸漸忘卻圣人之道,所謂“失其故吾”,失去的便是儒者本色。學界對于明末清初的“逃禪”思潮多從社會思想史的視角加以闡述,有時卻忽視了其對于當時學術界,尤其是儒者群體的力量削弱與心靈震動。綜上可見,全祖望對于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末以來的儒學發展趨勢是比較悲觀的,這一心態某種程度上刺激了全氏對于儒家忠孝節義言行的追溯與弘揚。
另外,清廷文化政策的收縮客觀上也刺激了全氏對南明史的搶救性發掘,這是外緣上的誘因。清廷在全國統治地位的穩定推動政治氛圍走向和緩,但彼時驟起的文獄之風又說明清廷的文化政策反而日趨收緊,全祖望作《江浙兩大獄記》,就記錄了他所親見的南山案和莊廷鑨案,希望能“為妄作者戒”(56) ,表明他對于文化風氣的變動已有所警覺。全祖望為黃宗羲作碑文,開篇交代了碑文的創作背景:“其子百家為之行略,以求埏道之文于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作,既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余年無墓碑。”(57) 由于黃宗羲曾加入反清隊伍,黃氏去世后,他的后人曾先后求文于黃宗羲門徒鄭梁(1637—1713)、朱彝尊(1629—1709),均遭婉拒,以至于黃宗羲都已去世了40多年,還沒有人敢為其墓立碑。到了全祖望寫碑文的時候,雖然他目睹了黃宗羲三子黃百家留下的黃宗羲行略,但行略之中仍多有缺失,如果不再作彌補,則有因時過境遷而無可查證的風險。黃宗羲被康熙帝所賞識,他的生平事跡尚且無人敢于整理,其他不屑于與清廷接觸的清初遺民生平事跡的保存情況更是可想而知,這客觀上激發了全祖望搜集南明人物事跡的欲望。就當時的社會現實來看,他表彰南明志士,是為了重建儒家主導的社會道德秩序,這并不違背清廷的訴求,也是《鮚埼亭集》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
總體而言,全祖望表彰南明志士的言行,是為了宣揚他們身上忠孝節義的精神,進而嘗試改變明末清初以來“圣人之學”的頹勢,重建并鞏固儒學主導下的社會道德秩序。這與他重視實踐的學術理念相契合,既是他補史證經學術路徑的成果與目的,也是他實現復興“圣學”學術理想的重要依托。正因如此,全祖望對于德行的重視要高于學術水平,這亦與儒家“修齊治平”的傳統學術理念相匹配。
四、結語
全祖望的治學傾向總體上繼承了黃宗羲、顧炎武等清初大儒,但保留了其個體思想的獨特性。由于時代變遷,“經世致用”精神的內涵發生變化,全氏雖與顧、黃一樣也講求“經世致用”,反對空言性理,但全氏對于“經世致用”的理解相較于顧、黃已經開始有了潛在的變化。全氏所處的時代,程朱之學已在程朱陸王之中超越其他各派,成為清廷尊奉的理學“正宗”,客觀上加劇了朱學與其他門派的矛盾。全祖望的學術訴求重心由黃氏的“求同”轉向于“存異”;對“狂禪”極端傾向的批判已幾乎成為理學內部的共識,于是顧炎武“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的論斷失去了思想背景,全祖望未能完全領會顧炎武的初衷,把重心放在了顧氏對理學的破壞傾向而非建設傾向,認為顧氏貶低“今之理學”的存在價值實在太過;明末清初的“逃禪”思潮據全氏所記述,大部分“逃禪”者都是在各種主客觀原因下懷著郁悶、無奈的心境脫離儒門的,且并非是由于不認可儒道,但即便如此,或許是為展露自己的立場,在了解了“逃禪”的思想背景之后,全祖望仍對“逃禪”行為表示嘲笑,這也是由于歷史語境的巨大差異。
學界對全氏學術傾向的評價總體趨于正面,這毫無疑問是源于全氏思想的寬容和樸實的學風。然而,全祖望兼收并蓄、力求中立的治學觀仍有其矛盾之處,其思想傾向的模糊不定有時甚至引導后人理解走向誤區。他對于佛學的態度既非認可,又不完全否定,在思想深度上沒有超出前儒的認知和努力。在理學“門戶”問題的獨特見解上,全祖望主張拋棄門戶之見、匯集各家之長,但他或許沒有意識到,自己從未逃離“門戶思維”的藩籬,自然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門戶之見。用他自己的話說,儒者講學論人當然“不應各持其門戶”,但作為學術后輩又“不可不知其門戶”(58) ,“門戶”思維在全氏看來仍不可拋卻。這固然是為應對朱學獨尊的現實背景,但一旦失去了歷史語境,后人評述全氏就難免如同他論述顧氏思想一般,偏離作者的本意。比他稍晚的章學誠評其“宗陸而不悖于朱”,已經在用“門戶”思維衡量全祖望的學術歸屬,因為章氏在強調“必不可有門戶”的同時,也在強調“學者不可無宗主”(59) ,于是陸九淵和朱熹就成了全祖望的共同“宗主”;今人學者評價全祖望“學術思想和傾向不出王學和梨洲的范圍”(60) ,也是在用“門戶”的思維加以限定,即便這一結論的確反映了全祖望難以言明的情感傾向。由此觀之,后世學人似乎既理解了全祖望恪守中道、寬容廣博的學術旨趣,又背離了全祖望超越理學“門戶”、重振“圣人之學”的學術理想,這無疑應歸結于全祖望給自己設下的思想陷阱,也是全氏學統觀念的局限性。
注釋:
(1) 參見方祖猷:《全祖望民族思想辯》,《寧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顧志華:《試論全祖望在歷史文獻學上的成就》,《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呂建楚:《全祖望學術特點淺論》,《寧波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等。相關研究成果頗多,且覆蓋經學、史學、文獻學等各個方面,不一而足。
(2) 崔海亮認為全祖望“經學即理學”的言論曲解了顧炎武的本意,這源于全祖望心學的立場與廣博包容學統觀念之間的矛盾,參見崔海亮:《經學詮釋與學統觀——以全祖望對“經學即理學”命題的詮釋為中心》,《船山學刊》2012年第2期;亓嬌、張凱總結了現階段全祖望思想研究的現狀與不足,認為學界對全祖望的研究多關注于其史學方面,在思想史、文學等其他方面著墨不多,對后來者具有指導意義,詳見亓嬌、張凱:《全祖望經學思想研究概略》,《社科縱橫》2017年第11期;韓書安指出,全祖望在“去短集長”思路的引導下將陸世儀置于程朱道統之中,但如唐鑒、錢穆等晚清學人沒有領會“去短集長”精神,從程朱道統的本位對陸世儀“不立門戶”的思想予以褒貶,背離了全祖望立傳的初心,這有利于研究者重新認識全祖望的學術訴求,參見韓書安:《不立宗旨與建構道統——全祖望〈陸桴亭先生傳〉的價值及其反響》,《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23年第6期。
(3) 此處所言之“理學”,是指包括程朱陸王在內的宋明“性理之學”,而非通常意義上的“程朱理學”或“朱子理學”。為避免概念混亂,本文將后者稱為“朱學”“朱子學”“程朱之學”等,以與“理學”概念相區別。
(4)(10) 全祖望:《橫溪南山書院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7、1057頁。
(5)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著,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第94卷,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237頁。
(6) 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載黃宗羲著、吳光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3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頁。
(7) 黃宗羲:《明儒學案序》,載黃宗羲著、吳光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9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頁。
(8) 全祖望:《同谷三先生書院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048頁。
(9)(11) 全祖望:《杜洲六先生書院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2、1052頁。
(12) 全祖望:《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005—1006頁。
(13) 全祖望:《楊文元公舊里》,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398頁。
(14) 全祖望:《馮丈南耕墓碣》,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875頁。
(15) 全祖望:《題楊文懿公諸經私抄》,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286頁。
(16) 全祖望:《大理悔廬陳公神道碑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99頁。
(17) 全祖望:《錢蟄庵征君述》,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50頁。
(18) 全祖望:《甬東靜清書院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054頁。
(19)(50) 全祖望:《蕭山毛檢討別傳》,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88、988頁。
(20) 全祖望:《奉臨川先生帖子一》,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684頁。
(21) 全祖望:《三后圣德詩十二篇·尊經》,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45頁。
(22) 學界傳統以來多套用“反理學”的研究范式,認為理學形成得益于援引佛、老,衰敗也歸罪于援引佛、老,理學發展一旦陷入瓶頸,就難免懷疑自身與佛、老的距離過近,最終“開出導致自身衰亡的新的理路來”,參見姜廣輝:《走出理學: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周啟榮提出了儒家“凈化主義”(purism)的理論,認為清代儒家在內部發起了排斥異端思想和佛學思想的思潮,這一理論本質上也是傳統“反理學”研究范式的延伸,其觀點詳見周啟榮著、毛立坤譯:《清代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以倫理道德、儒學經典和宗族為切入點的考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頁。筆者認為,由于反對理學內部玄思要素而產生的“排佛”口號在出現之初的確得到了理學內部的廣泛認同,即使是被攻擊為“染佛”的學者,多數也不得不自證自己沒有“染佛”,而不是反過來質疑“排佛”口號的正確性,因此“排佛”思潮的定論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末清初以來的思想環境;但另一方面,“反理學”研究范式乃至“凈化主義”理論的局限性在于,其在無意間站在理學中排斥佛學者的本位,將那些被定性為“染佛”的聲音從理學者群體中剔除出去了,因而這一論調客觀上只能反映部分理學中人的意志,不足以概括整個理學家群體的全貌。事實上,如果“排佛”口號能在明末清初的理學學界得到一致通過,那就不會存在所謂的“染佛”之人,當時也更不可能涌現“逃禪”之風。
(23) 全祖望:《城南書院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046頁。
(24) 楊海英:《全祖望“正學”思想初探》,載陳祖武主編:《明清浙東學術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03頁;全祖望:《五岳游人穿中柱文》,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379頁;全祖望:《雪庭西舍記跋》,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41頁。
(25) 全祖望:《李元仲別傳》,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545—546頁。
(26) 全祖望:《破惑論》,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545頁。
(27) 全祖望:《囊云先生云樹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2頁。
(28) 這句話在《鮚埼亭集》(含《鮚埼亭集外編》)中總共出現過三次,前兩次是對黃宗羲之言的直接引用,最后一次出現于自己所作的哀辭,足見全祖望對黃宗羲觀點的一貫堅持。詳見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24頁;《周思南傳》,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496頁;《剡源二哀》,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848頁等。文中所引為全氏自述。
(29)(47) 全祖望:《子劉子祠堂配享碑》,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448、448頁。
(30) 全祖望:《五岳游人穿中柱文》,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380頁。
(31) 后世的部分學者在表述顧炎武思想時,容易順著全祖望的理念與思路,用“經學即理學”的說法概括顧炎武的洞見。如梁啟超認為“‘經學即理學’一語,則炎武所創學派之新旗幟也”,參見梁啟超著,夏曉虹、陸胤校:《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頁;錢穆說“亭林‘經學即理學’一語”“亭林‘經學即理學’一路”,也是自然而然地把“經學即理學”當作顧炎武思想的一部分,參見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59頁。至侯外廬提出質疑,認為全祖望曲解了顧炎武的意思,“全氏所述‘經學即理學’,則把(理學和經學)二者混一”,侯外廬的觀點已被現在的學者廣泛接受。參見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頁。
(32)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27—228頁。
(33)(34) 全祖望:《李習之論》,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513—1514頁。
(35) 全祖望:《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塘江事》,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816—1817頁。
(36)(37) 全祖望:《湖語》,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8—99頁。
(38) 全祖望:《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834頁。
(39) 全祖望:《答臨川先生雜問》,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768頁。
(40) 姜廣輝:《走出理學:清代思想發展的內在理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頁。
(41)(57)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19—220、212頁。
(42) 全祖望:《帖經小課題詞》,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234—1235頁。
(43) 蔡克驕、王春容:《民族精神與浙東史學》,《溫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
(44) 李慈銘:《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十四則》,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760頁。
(45) 劉光漢:《全祖望傳》,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734—2735頁。
(46) 全祖望:《蔡忠襄公傳后論》,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0頁。
(48) 全祖望:《明錦衣徐公墓柱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頁。
(49) 全祖望:《忍辱道人些詞》,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67頁。
(51) 全祖望:《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699—1700頁。
(52) 參見林聰舜:《明清之際儒家思想的變遷與發展》,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7—200頁。
(53) 全祖望:《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后》,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368頁。
(54) 全祖望:《慶元路學宮涂田碑跋》,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745頁。
(55) 全祖望:《周思南傳》,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496頁。
(56) 詳見全祖望:《江浙兩大獄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0—1172頁。
(58) 全祖望:《端溪講院先師祠記》,載全祖望撰、朱鑄禹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9頁。
(59) 章學誠:《浙東學術》,載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第5卷,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606頁。
(60) 王永健:《全祖望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頁。
作者簡介:樂勝奎,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湖北武漢,430062;陳先,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北武漢,430062。
(責任編輯 劉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