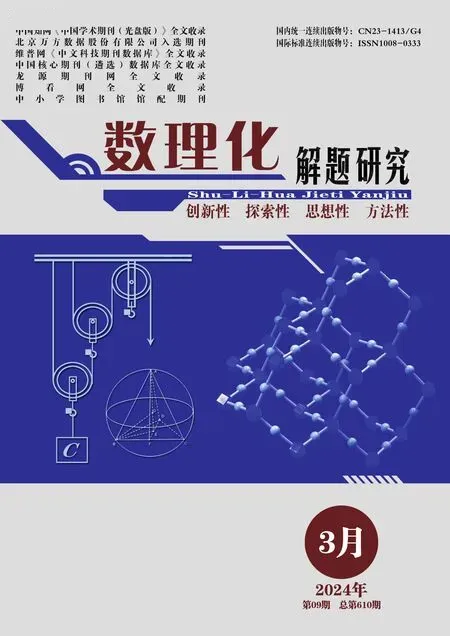生活元素與數列思想融合的高中數學教學方法探索
曾石東
(福建省平和廣兆中學,福建 漳州 363700)
數列思想主要包括函數思想、方程思想、遞推思想以及歸納思想等.但是由于數列思想對部分學生來說較為抽象,規律尋找存在一定的難度.而生活元素來自學生的生活日常,學生對其較為熟悉,所以將生活元素融合數列思想,能使抽象的數列思想立體化,更為直觀地展現數列的規律,便于學生在較短的時間內掌握數列思想的本質內涵.再加上,高中數學傳統數列思想教學較為直接,大多通過大量的案例講解以及海量的練習訓練完成,并沒有與生活實際建立有機聯系,使學生對數列思想的理解停滯于理論層面,難以掌握數列思想生活化實踐運用的方法,這顯然已無法滿足新課程對數列思想教學改革的要求.對此,筆者將基于個人對生活元素融合數列思想的認識,簡述對相關教學方法的見解,以供參考.
1 明確融合教學目標,落實數列函數思想融合生活元素
為進一步強化數列函數思想的應用效能,教師可先設置明確的生活元素融合目標,再根據融合目標導向篩選生活元素,并將其運用到數列函數思想的實踐教學中,對數列函數思想進行補充說明[1].這樣學生就能通過生活元素剖析數列函數思想,掌握函數思想處理數列問題的方法技巧,發揮數列函數思想簡化題目附加條件,凸顯立題思想內涵的效能.而教師也能在融合目標的指引幫助下,落實數列函數思想與生活元素的融合目標.

第一年投入為800萬元,


又∵第一年收入為400萬元,


2 建構融合教學情境,促進數列方程思想融合生活元素
數列方程思想作為數列解題思想的重要組成,在處理數列中蘊含未知條件的相關問題有著較大的應用優勢,同時也是學生所必須掌握的數列思想.而通過建構生活情境促進其與生活元素融合,能帶給學生一些啟迪與幫助,使學生更加迅速地找到已知量與未知量的關系,建立相對應的方程關系,羅列出符合數列解題方程,繼而解決數列問題.對此,教師不妨通過生活化情境建構,促進數列方程思想融合生活元素,利用情境生活元素對數列未知量進行科學合理的補充說明,為學生建立未知量與已知量方程的方程,讓學生能通過情景生活元素推理出各種量之間的關系,并建立未知量與已知量的數列方程,求出數列中所出現的未知量,繼而達到解決數列問題目的.這樣教師就能通過生活情境建構,促進生活元素與數列方程思想的深層次融合[2].
例如,教師可先借助多媒體技術播放視頻“人們在貸款、儲蓄、購房、購物等經濟生活中運用數列方程思想的案例”,建構數列方程融合教學情境,使學生從不同角度切入感受數列方程運用于生活實際問題.然后教師再提出一些基礎性方程思想數列問題,促使學生由生活情境過渡到方程思想的基礎知識學習中,嘗試處理“已知{an}為等差數列且公差d>0,假設{an}的前n項和為Sn,且a1=1,S2·S3=36,試求(1)公差d和Sn,(2)若am+am+1+am+2+…+am+k=65,試求m,k具體的值”等問題,解題步驟如下:
(1)根據題意可知(2a1+d)(3a1+3d)=36,
代入可得d=2或d=-5(舍去),
(2)根據題(1)結果可得:
am+am+1+am+2+…+am+k=(2m+k-1)(k+1),
∴(2m+k-1)(k+1)=65,
又∵m,k∈N*,
∴可得2m+k-1>k+1>1,
可得方程組2m+k-1=13,k+1=5,
解得m=5,k=4.
最后教師只需要將情景中的貸款、儲蓄、購房以及購物等問題條件稍加改變,設計出一些生活化的數列方程問題,用于后續進一步鞏固提升學生對數列方程思想的掌握程度,以保障學生能靈活運用數列方程思想處理不同場景的數列問題.而教師也通過生活情境創設,幫助學生深入理解方程思想求算公差、首項、公比、前n項和Sn等思路方針,為學生切實掌握方程思想處理數列問題的方法提供有力保障,最終達到情境建構助力生活元素融合數列方程思想教學目的.
3 采取逐步融合手段,助力數列遞推思想融合生活元素
逐步融合手段的運用,能順應數列遞推思想的融合訴求,使生活元素按照遞進思想逐步融合到各個階層,以輔助學生由淺入深地理解數列題目的立題思想[3].對此,教師需要先對數列進行逐步遞推分析,明確各個階段層次的生活元素融合需求,然后再通過逐步融入的方式,將所篩選引進的生活元素滲透各個層次階段中,掌握解決處理所遇到的數列問題的方法,避免一刀切融入生活元素情況的發生.

4 師生對話促進融合,引導數列歸納思想融合生活元素
數列歸納思想主要是指學生在數列日常解題學習中,發現、總結及理解數列所出現的各種規律,借助特定的數學方法論證其合理性,繼而歸納得出具有通用性的數學結論.教師便可以此為切入點,借助師生之間的對話互動,予以學生一定的幫助指導,促進生活元素的融入,使學生通過生活元素來發掘數列的特點特征,驗證所得出的歸納結論是否合理.這樣學生便能在師生互動的引導下,靈活運用生活元素來發掘數列的特點規律,輔助自身理解數列歸納思想,掌握數列歸納思想運用的具體方法.而教師也能在此過程中培養學生主動歸納總結、分析所發現的各種規律的能力,并借此來提升學生運用歸納思想處理現實生活數列問題的效率,最終達到師生對話促進生活元素融合數列歸納思想目的[4].

5 結束語
教師自身應當掌握數列思想教學傳授的核心重點,根據新高考對數列思想的考查要求,設置與之對應的生活元素滲透目標,篩選符合訴求的特定生活元素,通過生活情境建構、生活化教評等多項舉措促進二者深層次融合,以達到充分發揮生活元素融合數列思想的教學手段育人效能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