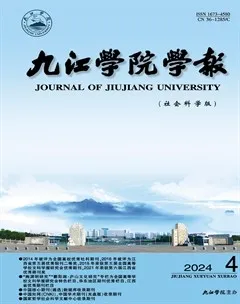歷史語境與決定性結構
摘要:作為特定歷史語境下的產物,《桃花源記》是陶淵明于動蕩之世,以魏晉玄學思想為指導,在“人的覺醒”年代中創作而成的。從小說的“決定性結構”看,該作品又是對理想“人居”的探尋。陶淵明采用“誤入異境”的傳統敘事模式,虛構了一個有著“小國寡民”“大同”色彩的東方“烏托邦”——“桃花源”。它已成為中國文化特有的符號印記。桃花源不僅象征著人們的理想生活,還暗含著對黑暗亂世的批判,更是逐夢華夏盛世的不竭動力之源,其內涵豐富,意義深遠。
關鍵詞:《桃花源記》;歷史語境;決定性結構;符號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4580(2024)04-0007-(06)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4.002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創作的經典名篇,在陶淵明的全部作品中,知名度最高,影響最大[1]。而較早將其納入現代學術研究軌道的是陳寅恪先生,他在《桃花源記旁證》中認為《桃花源記》既為寓意之文,又為紀實之文,并以紀實立說。陳先生指出該文是作者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并且真實桃源本在北方弘農或上洛,而非南方武陵,而且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當為苻秦[2]。稍后的唐長孺先生則對此提出了質疑,其在《讀lt;桃花源記旁證gt;質疑》一文中指出陳說立論的證據仍然不夠充分,他認為桃花源的故事本就是晉、宋間流傳于荊襄一帶的傳說,后由陶淵明根據所聞加以理想化,寫成了《桃花源記》[3]。兩位大師的隔空對話,帶動了《桃花源記》的研究發展。從整體上看,目前學界對《桃花源記》的研究主要包括體裁、原型、哲學思想等幾個方面。
其中,關于《桃花源記》是為游記,或是為序,或是為小說的體裁歸屬問題,研究者們聚訟不休。實際上,胡適先生早在《論短篇小說》中指出:“比較說來,這個時代的散文短篇小說還該數到陶潛的《桃花源記》。這篇文字,命意也好,布局也好,可算得一篇用心結構的‘短篇小說’。” [4]梁啟超先生也指出該文“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說,在文學史上算是極有價值的創作”[5]。胡、梁二位先生關于《桃花源記》為“小說”的觀點是為確論。此后,蕭東海、盧英宏、張鈞、韓春萌、朱玉麒、袁書會等研究者都遵循這一論斷。可以說,作為魏晉時期志怪小說典型代表的《桃花源記》,在中國小說史乃至中國文學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因此,筆者欲借助歷史語境和決定性結構理論,挖掘和闡釋文本中豐富的人文內涵及其文化意義。
一、歷史語境:動蕩、談玄感喟與覺醒
所謂語境,是指“語言環境,又稱為情境”[6]。歷史語境即為歷史上的語言環境,也可以稱為歷史情境,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觀念、創作動機、身份修養等要素的集合,是“敘事作品賴以完成的全部規定”[7]。任何文學作品(包括那些具有超前理想的作品)都是特定歷史語境下的產物,文學作品的闡釋首先就要回歸到歷史語境當中去。雖然《桃花源記》創作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但作者陶淵明的生平則有史可查,其生卒年大致為公元365—427年。陳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記旁證》中指出“桃花源紀實之部分乃依據義熙十三年春夏間劉裕率師入關時戴延之等所聞見之材料而作成”[8]。義熙十三年為公元417年,又據《晉書·陶潛傳》“義熙二年(406),解印去縣”的記載可知,該文是歸隱田園的陶淵明于公元417年至公元427年間,即晉宋(劉宋)兩朝更迭之時所作。
(一)動蕩的社會圖景
“戰爭與動蕩”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時代主題。東漢末年,黃巾起義拉開了中國歷史上長達四百年“潮起潮落”的動蕩局面的序幕,先是董卓專權,群雄割據;后有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操去世后,其子曹丕廢漢獻帝以自立,改號為魏,進入魏蜀吳“逐鹿”的“三國時期”。曹魏世族司馬氏專權,先滅蜀漢,后廢魏以自立,建晉伐吳,統一中原。晉朝在維持十幾年的穩定局面后,又經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宗室被迫南遷,史稱東晉。北方大地則進入了五胡十六國的征伐時期。
南遷的東晉朝廷,偏安江左,皇權旁落,國勢衰微,內有方鎮割據之憂,外有“苻堅舉國出西秦,東晉危如累卵晨”(胡曾《詠史詩·八公山》)之患。雖然在面對亡國之局時,君臣一心,擊敗了苻秦,但頹勢已難挽回。至陶淵明所生活的東晉后期,朋黨相爭以及桓玄、孫恩、盧循等作亂,加速了亡國之勢。劉裕更是在平定諸亂后,代晉而立宋,開啟了南北朝時期。宋齊梁陳,朝代更迭,直至隋朝建立才結束這幾百年的混亂局面。
無論是以宏觀視角考察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是對陶淵明生活的時代進行具體關照,“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戲劇畫面都在不斷地被搬演上歷史舞臺,將華夏“亂世”詮釋得淋漓盡致。朝代更迭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兵燹戰亂是“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隨之而來的饑餓逃荒、疾病瘟疫、人口遷徙以及頻發的自然災害,更是促使這亂世圖景殘破不堪,陶淵明《歸園田居·其四》中“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余”,即為真實寫照。
(二)談玄感喟的時風
魏晉時期,政權更迭。社會風云突變之時,思想領域也在相互激蕩。東漢末年群雄逐鹿的混亂局面,打破了儒家一統的社會秩序,向著讖緯陰陽封建迷信方向發展的兩漢經學也不斷遭到抨擊,兩漢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隨著王朝的衰敗已不再具有威懾力,取而代之的是儒釋道三教并立。三教的不斷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一種以魏晉玄學為理論形態的嶄新世界觀與人生觀。這種思想是以文士為主導的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所進行的哲學思辨,衍生出了“有與無”“自然與名教”“言與意”“形與神”“名與理”等眾多論題[9]。其中的“自然”思想與老莊哲學中“把‘自然’視為宇宙萬物的最高法則”的觀點一脈相承,“崇尚自然”成為魏晉玄學的“基本精神”[10]。魏晉玄學家“援道”以“入儒”,以“自然”之精神拯救名教,如嵇康強調“越名教而任自然”,這是對傳統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價值取向和“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理想模式的質疑,也為傳統士人的精神解脫開辟了道路。
魏晉玄學是對兩漢時期經學神化行為和繁瑣解經方式的反駁與修正,也是對儒家傳統名教危機的補救。玄學家們“援玄以入道”“援道以入儒”,致使“儒道從對立走向融合”[11],呈現“以道釋儒、儒道兼綜”的主要特征[12]。除此之外,又融合了佛教成分。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東土以來,在與中原文化的激蕩中逐漸本土化。玄學名士傾心釋教,與名僧論道,在交流與碰撞中吸納佛學思想,由“儒道合流”發展為“三教圓融”,成為風靡一時的哲學思潮,使得談玄感喟之風彌漫整個時代。
(三)人的“覺醒年代”
從文學史上看,研究者們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稱作“文學的自覺時期”。文學作為人類特有的精神活動,其自覺的背后則是人的覺醒。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中概括,“魏晉南北朝三百年學術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個人自我之覺醒,是已。”[13]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魏晉玄學》中也指出漢末魏晉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覺醒”[14]。
東漢末年群雄并起之時,長期桎梏人們思想的以神學目的論和讖緯宿命論為代表的兩漢經學體系已轟然瓦解,而“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萬歲更相送,賢圣莫能度”(《古詩十九首》),對亂世下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嘆構成了時代的基調。到了魏晉時期,社會更是風云激變,“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曹植《贈白馬王彪·并序》);“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于百年,何歡寡而愁殷”(陶淵明《閑情賦》),唱出了人生苦短、生命脆弱、命運難卜、福禍無常而又無能為力的哀傷之音。這種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生哀嘆看似頹廢、悲觀,實則是個人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15]。人們不再信奉宿命論,視鬼神為生命的主宰者,而是在否定和懷疑鬼神迷信和傳統道德節操的基礎上,追求內在人格的覺醒和獨立。“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龜雖壽》)的豪情、“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建安風骨、正始名士的不拘禮法、“何意百煉剛,化為繞指柔”(劉琨《重贈盧諶》)的政治悲憤,都是“魏晉風度”下人對自我生命意義的探尋和人格自主的彰顯。
陶淵明正是在這風起云涌、世積亂離的時代里,以超然的玄學思想為指導,任性自然,堅守心中凈土,追求屬于自己的理想世界,創作出了照耀史冊的千古名篇,也為千百年來那些在黑暗與苦難中徘徊掙扎的人們建造了精神家園。
二、決定性結構:理想“人居”的探尋與建構
“決定性結構”是西方文學領域大師級人物勒內·韋勒克與奧斯汀·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中所提出的:“一件藝術品的結構也具有我必須去認知的特性,我對他的認識總是不完美的,雖然不完美,但正如在認識任何事物中那樣,那種決定性結構仍是存在的。”[16]韋勒克的“決定性結構”深受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的影響。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和“言語”是人類言語活動中需要區別的因素,“言語是語言的一種社會化現實的存在,而語言是一切言語活動中有決定性作用的符號結構。”[17]“決定性結構”則與“語言”性質相同,是一切文學活動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本質結構”。“決定性結構”是韋勒克在西方文學語境下所提出的理論,但對于同為“語言符號”構成本體的中國古代小說的解讀,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桃花源記》是一篇文言小說,語言凝練,結構緊湊,故事線索簡潔,全篇文字不過六百字。小說采取順敘的手法,主要敘述漁人無意中發現桃花源及與桃源人交往的故事,刻畫了武陵漁人、桃花源人以及結尾處的太守和高士劉子驥等人物形象。它的“決定性結構”很容易捕捉,就是對理想“人居”環境的探尋,也就是陶淵明在文后的桃花源詩歌中“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愿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的表述[18]。那么陶淵明是如何探尋自己的理想世界的呢?他所探尋的“理想王國”又是什么樣的呢?他又是怎樣呈現小說的“決定性結構”的呢?這需要我們回歸到文本的本體層面。
首先是陶淵明對理想世界的探尋方式。《桃花源記》開篇寫道:“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19]敘述了漁人無意中誤入景色優美的桃花林異境。“忘”“忽逢”為關鍵之筆,突出無意,而后文的“異”字更是以心理描寫突出桃花林景色之奇異,以至于使得漁人“欲窮其林”,這是漁人探尋的動力。實際上這種誤入異境的敘述手法并非陶淵明所獨創,是中國文學史上傳統的敘述模式。如劉晨阮肇誤入天臺山的故事,據劉義慶《幽冥錄》載:“漢明帝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臺山,迷不得返。經十三日,糧食乏盡,饑餒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有子實,而絕巖邃澗,水無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數枚,而饑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見蕪菁葉從山腹流出,甚新鮮,復一杯流出,有胡麻糝。相謂曰:‘此知去人徑不遠。’便共沒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20]雖不如陶文語言精美,但敘述性更強,且二者有相通之處,或是“迷不得返”,或是“忘路之遠近”,都是峰回路轉,得遇異境。再如《聊齋志異》“嬰寧”故事中王子服發現嬰寧居所時的描寫:“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余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21]誤入異境的例子在中國古代小說中不勝枚舉,其敘述模式多是無意進入一個奇特異常的世界,表現出了“好奇尚異”的心理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誤入故事大多以“遇仙”為主題,如“劉晨阮肇”和“嬰寧”的故事,它們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桃花源記》中陶淵明雖然以“詩化”的語言塑造了一個“落英繽紛”、景色秀麗的桃花林,并以“好奇尚異”的心理探尋奇境,但這篇小說內含的結構卻迥異于“劉晨阮肇”等故事,他以“遇人”為主旨,即探尋一個“人居”而非“仙居”的理想國度,追求浪漫想象的同時又不失現實主義色彩。
那么,陶淵明的“理想國”又是什么樣子的呢?陶淵明“以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手法設置了一個奇異秀美的桃花林屏障,既為敘述者提供了講述故事的動力,也為接受者做好了心理預設:宜人之景中也必然會有宜人的生活。也的確如此,漁人穿過山中狹窄的山口,他所見到的“桃花源”是“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22]的。這里沒有壓迫,沒有戰爭,有的是平曠的土地、豐富的物產、恬美的景物以及安居樂業的人們,這是一個清新自然、幽美如畫、祥和溫馨的田園世界,與外面混亂污濁的世界形成鮮明對比。
桃花源里人們過著辛勤耕作的樸素生活,也保持著淳樸的性情。當他們見到漁人這個闖入者時,即便是“見漁人,乃大驚”,但當他們“問所從來”,漁人“具答之”后,“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他們本是“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避世隱逸”之人,非但沒有驅趕這個打擾了他們平靜生活的外來者,而是“余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23]。“桃花源”里民風淳樸、熱情好客,生動地詮釋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儒家處世原則。“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是一代詩圣杜甫的政治抱負,而生活在幾個世紀前的陶淵明就已經在他所構建的理想世界中作了生動的詮釋,可見古今賢人之心一也。
“桃源望斷無尋處。”(秦觀《踏莎行·郴州旅舍》)對于本文的“決定性結構”的呈現,陶淵明則是以浪漫主義的方式虛構了“桃花源”這個理想國,向世人展示了他對理想“人居”環境的探尋。《桃花源記》被稱作為志怪小說,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虛構”。若說文章開篇漁人“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只是對異境的渲染,虛構不甚明顯,那么漁人離開時和離開后所敘述的事情則足以為明證。先是漁人欲告辭而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24]其中固然有桃源人不希望隱逸之所被泄露的心理,也有可能是作者故意留下的一個“破綻”,因為本身就是自己虛構的,不值得也沒有必要對外人說明。當然這只是筆者的臆測,而后文的敘述則更有說服力,并為讀者提供了虛構為文的兩條直接證據。“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25]離開的漁人非但沒有遵從村人“不足為外人道也”的告誡,反而是沿途做好標記,向太守告發此事,然而怪異的是,再去尋找標記時,不僅不能尋見標記,就連進入桃花源之路也不見了,桃花源仿佛憑空消失,此為一證。二證則是高尚士劉子驥的探尋“未果”。劉子驥實有其人,晉書有傳,與淵明為同時代人,且志趣相投。蕭統在《陶淵明傳》中將其與陶淵明、周續之稱為“潯陽三隱”。陶淵明以劉子驥探尋收束全篇,一方面是要突出漁人進入桃花源事之真實性,另一方面則是以“未果”的結局宣告桃花源的不存在。
至于陶淵明為什么要探求理想的“人居”環境,不難推測其是受“戰爭與動蕩”時代主題的影響,實際上作者在文本中也為讀者解讀留下了一把秘鑰。村人“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前文確是“男女衣著,悉如外人”。桃源人隱秘在此地,不再與外界交流,那么為什么會在經歷了幾百年后衣著還如同外人呢?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這個文本內部的矛盾恰恰就夾雜著作者對時事的見解,以及創作文章的直接動因。至于是什么時事,則如宋代洪邁在《容齋隨筆·三筆》中所云“予切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于劉裕,托之于秦,借以為喻耳”[26]以及明代黃淳耀“余意陶淵明居晉宋溷濁之間,感憤時事,寓言桃源,以嬴秦況當時,以避秦自況,如記中所云‘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看法[27]。陶淵明借助“秦時亂”來抨擊劉裕弒君篡權所引起的社會動亂以及給人們帶來的災難,作者創造出沒有戰亂、沒有壓迫、與世隔絕的理想“人居”——桃花源,就是要給亂世無依的生靈尋找避難之所。
三、價值旨歸:“桃花源”符號的恒久精神力量
作為魏晉時代的志怪小說,《桃花源記》既是漢魏洞窟傳說故事書寫的集大成者,又推動了桃源體小說敘事模式的定型。除此之外,作者還自出機杼,重構了意蘊豐富的“桃花源”意象。“桃花源”象征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暗含著對黑暗社會的批判,為苦難時刻的中國人民筑造了精神家園。在千百年的流傳中,“桃花源”已演化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永恒符號,直至今日,它依然迸發著強大精神力量。
“桃花源”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唯物史觀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28]人們的精神生活滿足程度,往往取決于物質生活需求是否得到了充分滿足。理想生活的標準是建立在當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上的,意味著在物質極大滿足的同時,精神層面也實現了愉悅。在以男耕女織為主要經營模式的社會里,人們向往的莫過于“桃花源”式的生活:在外沒有動亂的迫害、徭役賦稅的壓力,在內則擁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民豐物阜,各有所居,老有所樂,幼有所養,怡然自得。“桃花源”遺世獨立,飄然若仙境,是陶淵明于濁世之中構建的東方“烏托邦”,既展現了《老子》八十章中“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的“小國寡民”理念[29];也體現了儒家“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大同”社會愿景[30]。因此,“桃花源”不僅是陶淵明避世歸隱的個人情懷的抒發,也寄寓了探尋理想“人居”的美好夢想,更承載著“小國寡民”“天下大同”的傳統社會理想,并在“以其道易天下”的傳統精神的理想和實踐中促進了中國文人共同的國家“理想認同”,成為歷代文人墨客道不盡的話題。
“桃花源”暗含對黑暗動蕩社會的批判。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陶淵明“于世事并沒有遺忘和冷淡”,“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31]。即便是脫離樊籠,回歸自然,寄情于山水,紛亂的時事仍然縈繞在心間。陶淵明時逢亂世,親眼見證了動蕩之下的社會圖景:“荒涂無歸人,時時見廢墟”(《和劉柴桑》);“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寒餒常糟糠”(《雜詩·其八》),生靈涂炭,民不聊生。歸去躬耕的陶淵明“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32],早年“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擬古·其八》)、“猛志逸四海”(《雜詩·其五》) 的豪情壯志、不平棱角也早被這黑暗的世界所磨滅;“肉食者”不顧百姓存亡的權謀相爭,致使社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然財殫力竭,無以至此”[33],也使得他大失所望;而劉裕的篡位弒君,改朝換代,故國被滅,更導致陶淵明心灰意冷。面對這個暗無天日,血與火交織的時代,陶淵明深感無力,他只能將目光投到虛幻縹緲的“世外桃源”。“桃花源”是陶淵明筆下構建的理想人居,代表著作者對美好光明的向往,也是陶淵明為這亂世所開的“急救方”,暗含著對黑暗動蕩的現實世界的失望。“桃花源”的世界有多么美好,也就意味著現實世界有多么殘酷。
縱觀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到文明從低級向高級的逐步演進。中國所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推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新形態,是中華文明的當代形態,是在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賡續傳承中形成發展的。從這個視角出發,以精神與物質雙重滿足為標準的“桃花源”式的理想追求依然具有時代價值,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不斷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但對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的雙重追求始終不變,這也是“桃花源”的題中應有之義。“桃花源”是陶淵明為亂世無依的人們建造的精神之舟,也是他為蕓蕓眾生所探尋的理想“人居”環境。他于黑暗之中點亮了一盞明燈,也為中華民族鑄造了一個千古未竟之夢——“桃花源”。這個帶有東方印記的“烏托邦”,已由魏晉時代的一束火炬,在眾生對理想生活向往的愿力下,化為閃耀在中國歷史長河上方的“新星”,它寄托著中華民族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華夏盛世的無限憧憬,也為一代又一代的逐夢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桃花源”之路漫漫,需要上下而求索。
總之,陶淵明“志深筆長”,以玄幻幽深的手法、清新自然的筆調,于“風衰俗怨”之世為苦海中爭渡的人們筑造了一個遠離塵世、怡然自得的“桃源仙境”。“桃花源”既成為士人理想中的精神樂土,也成為中華民族“上下求索”之夢。
參考文獻:
[1]顧農.從孔融到陶淵明:漢末三國兩晉文學史論衡[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693.
[2][8]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199.
[3]唐長孺.唐長孺文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19-220.
[4]胡適.胡適文存[M].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108.
[5]北京大學中文系.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1962:278-279.
[6]吳翔宇.在動態歷史語境中透析“魯迅形象”:評陳國恩《經典“魯迅”:歷史的鏡像》[J].學術評論,2021(3):66-75.
[7]巴爾特.美學文藝學方法論:下[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535.
[9]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2-13.
[10][11]卞敏.魏晉玄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162-163,16.
[12]許杭生,等.魏晉玄學史[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22-27.
[13]錢穆.國學概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144-145.
[14][15]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90,92.
[16]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M].劉象愚,等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169.
[17]劉濤.決定性的結構:韋勒克文論思想的關鍵詞[J].文藝評論,2018(2):34-39.
[18][19][22][23][24][25]陶淵明.陶淵明集[M].逯欽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165-168.
[20]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97.
[21]蒲松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張友鶴,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49.
[26]洪邁.容齋隨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37.
[27]黃淳耀.陶庵全集:卷二[M].四庫全書本.
[2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29]老子道德經注校釋[M].王弼,注.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8:190.
[30]禮記[M].陳澔,注.金曉東,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69.
[31][32]魯迅.魯迅全集:3[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537-538.
[33]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2208.
(責任編輯 吳國富)
作者簡介:呂行(1994— ),男,滿族,遼寧綏中人,遼寧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元明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