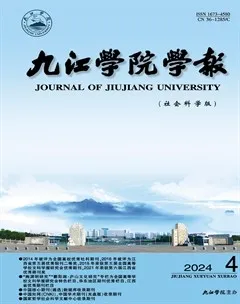白蛇故事祭塔情節的生成邏輯



摘要:白蛇故事的流變經歷了相對漫長的歷史時期,于清代方成培的《雷峰塔傳奇》中終于衍生出祭塔這一情節。祭塔情節的衍生是在晚明以來“主情”社會思潮影響下,廣大民眾對于白蛇故事團圓結局心理期待的結果。它順應白蛇形象嬗變的時代需要,通過孝道親情與果報思想合情理地進行建構,白蛇在此過程中逐漸凈化,轉型為一位慘遭殘酷壓迫的善良女性與慈母良妻形象。祭塔情節的生成是白蛇故事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重要演變,同時為后世白蛇故事的情節建構確立了較為固定的范式。
關鍵詞:白蛇故事;祭塔;民間心理;果報
中圖分類號:I207.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4580(2024)04-0059-(05)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4.010
從圖騰符號到神話傳說,從作家文學到民間文藝,白蛇故事屢見于文人傳奇、小說演義、民間傳說、市井話本、民間說唱、戲曲、歌謠等諸多文學樣式當中。白蛇故事在不同的時代呈現不同形式以及文化內涵的藝術表達,同時情節內容上作出了相應的改編與設計。
從研究主題上看,白蛇故事的起源、發展演變、人物形象、文化內涵,甚至是傳播媒介、接受情況都可以作為研究對象。從研究角度上看,既有整體研究,也存在對白蛇故事個別文本的研究及比較研究。如陳毅勤的《從〈西湖三塔記〉到〈白蛇傳〉》論述了白蛇故事的發展與演變;蔡春華的《中日兩國的蛇精傳說——從〈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與〈蛇性之淫〉談起》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分析了中日蛇女故事的異同,可見學界研究方向趨于多元化,成果頗豐。本文則通過爬梳宋話本《西湖三塔記》以來歷代頗具代表性的白蛇故事文本,得見至清代方成培《雷峰塔傳奇》,白蛇故事衍生出一個嶄新的故事節點:夢蛟祭塔。故事敘說白蛇被鎮壓在雷峰塔下,其子許夢蛟長成,得中狀元,衣錦還鄉,知母親事,乃至雷峰塔前祭拜,夢蛟孝心使白蛇得以出塔,母子團圓。在方本傳奇之后,白蛇故事重心趨向情節內容的倫理化,故事結局也傾向圓滿化,在這一變化背后,祭塔情節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祭塔情節的文本內容并非憑空生成,它的衍生有其作為民間故事生成的底層邏輯,具體表現為:白蛇形象嬗變的時代需要、民間大眾的心理作用以及孝道親情與佛教果報思想的原始動力。
一、凈化與轉型:白蛇形象嬗變的客觀需要
在白蛇故事的流傳過程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白蛇這一多情聰慧、溫柔顧家的鮮明形象。然白蛇從妖嬗變為人乃至仙,直至演變為自由熱烈、可愛大方的女性形象,卻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過程,接受了無數文人與民間藝人的藝術改編。白蛇形象嬗變的過程中,其身上的妖性被不斷凈化,漸而轉型為具有熱烈情感與高尚品性的正面形象,其嬗變過程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它依托于廣大文人以及民間藝人對白蛇故事情節的不斷設計與改編才得以實現。
白蛇形象的凈化與轉型并非一蹴而就,其歷經了千載的傳承演變,最終才完成由妖向人的轉變。白蛇故事脫胎于南北朝梁代任昉《述異志》,其記載的“蛟妾”常變為大蛇以食人肉;唐代《博異志·李黃》(又名《白蛇記》)中李黃為蛇女所害,“身漸消盡”化為血水,“惟有頭存”[1],蛇女形象盡顯兇殘一面,其毒辣之心腸、殘忍之手段眾目昭彰,以致人蛇難以共處的古老命題由此產生。
白蛇故事萌芽于宋代話本《西湖三塔記》,基本成型于馮夢龍擬話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直至清代方成培《雷峰塔傳奇》為民眾普遍接受,使白蛇故事獲得了比較固定的形式,后相繼出現《白蛇寶卷》《白蛇傳》等極具代表性的故事文本,白蛇故事最終積淀成型。白蛇故事祭塔情節最早生成于《雷峰塔傳奇》,其后的諸多民間白蛇故事也都承繼了方本傳奇中的這一故事情節,出現產子、祭塔的環節。白蛇形象從方本傳奇開始逐漸擺脫妖氣,被賦予了更多人性層面的情感與品性。
宋本《西湖三塔記》雖已形成白蛇故事的完整情節,但故事情節相對簡單,且故事中的蛇女仍舊是損人利己的負面形象,人們利用蛇的惡的一面,將女人與蛇相提并論,極力丑化貶抑女性的社會價值。馮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的白蛇形象雖已初現轉型,但白蛇身上的妖性依然明顯,如與小青共盜府銀以供享用;法海點破其身份時,白蛇以水漫全城威脅許宣,其人性情感更多的是與晚明中后期的“主情”思潮以及馮夢龍個人思想相關。在李贄“童心說”影響下,馮夢龍文學創作也開始表現人的純真與本心,注重闡發個體的獨立人格與主體精神。其思想觀念體現在白蛇形象上,則是為爭取個人感情自由的實現而反抗以法海為代表的封建禮教束縛。
透過幾個文本的白蛇故事主要情節,我們發現,方本傳奇之前的白蛇故事,白蛇形象雖逐漸轉型,但并未走出亦妖亦人的矛盾狀態,尤其是許宣的幾次坐案,都與她的妖法有關,且一旦危及白蛇自身利益時,那么她身上的妖性便占據了上風。直至方本傳奇祭塔情節的生成,神話色彩與現實氣氛開始統一起來,祭塔情節極力淡化了白蛇身上的人蛇沖突,模糊了觀眾與讀者人蛇的分界與對比感覺,最終使白蛇形象的蛇性統攝于人性之中,從而使之成為一個和諧完整的統一體[2]。鎮塔情節的設計,是對白蛇水漫金山過錯的懲罰,而祭塔情節的生成則是寫盡人世間母子親情的感人力量。在增加祭塔情節的白蛇故事中白蛇形象已凈化為一位慘遭殘酷壓迫的善良女性與滿懷愛子之情的慈母形象。
白蛇故事中祭塔情節的生成是白蛇升華為慈母形象的客觀需要,祭塔情節始見于清代方成培編寫的《雷峰塔傳奇》。祭塔一事從故事發展脈絡上實則是由白蛇產子衍生出的情節,生育作為白蛇故事新的平衡節點,將降妖主題轉變為救贖主題,蛇妖害人的故事由此開始逐漸逆轉,演變為滿足白蛇在現實框架下的合理訴求:即成為合法的賢妻良母[3]。祭塔情節在白蛇由妖到人的轉變過程中承擔著重要作用。
總之,增加產子、祭塔情節的白蛇故事作品為其增添了慈母的形象特征。方本傳奇及后續白蛇故事作品均以大量筆墨描寫母子分離的痛苦與母子相見的喜悅,這種動人心脾的情感力量足以使得觀眾忘卻白娘子是蛇妖。《雷峰塔傳奇》中白蛇雖仍是異類,卻通過與許宣的美好愛情,與夢蛟的母子親情塑造了一個賢妻良母的形象,完全融入了人類世界之中。在由妖到人的轉型過程中邁進了一大步。
二、調適與平衡:民間文化心理的情感訴求
“白蛇故事”祭塔情節在民間敘事角度上可視作在普通民眾情感訴求潛移默化影響下衍生出的一個新的故事節點,它對于調節情感、意志和理性之間的沖突和張力,消解內心生活的障礙,維持身與心、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均衡關系,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4]。民間故事的調適與平衡功能是在社會生活與民眾心理的角度運作的,祭塔這一情節正是依附于晚明以來“主情”的社會思潮與崇尚圓滿的民間文化心理而生成的。
晚明以來的啟蒙思想引發了一些有識之士關于情與理的探討,反思程朱理學,試圖擺脫其束縛,肯定甚至贊揚情欲,在文學領域中掀起了“主情”的進步文藝思潮。雖有各種局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思想,人的正常欲望得以正面化表現。因而在明代馮夢龍《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中得見白蛇對愛情的自由追求。至于清代,政權的更迭和家破人亡的慘痛現實促使更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批判晚明的哲學社會思潮。即便如此,是如黃宗羲、王夫之等猛烈抨擊晚明異端學說的大儒也同樣認可了“情”的地位和人對情感需求的正當性[5]。正是出于這樣一種普遍認識,清代初期的一些文學作品依舊高揚著“情”的旗幟,《雷峰塔傳奇》在小說問世以后演變為我們如今熟知的白蛇傳故事正說明了當時的普遍意識中已經延續了晚明以來“情”得到肯定的傳統[6]。祭塔情節是方成培在前代白蛇小說出現后,在民間不斷潤色、增補、修改的基礎上所生成的,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情節正是民間意志和心理的反映。概括而言,就是不再將白蛇作為妖來對待,而是作為自由追求愛情、彰顯人性光輝的正面形象對待。白蛇與許宣之間擁有了愛情的結晶,白娘子最終能夠出塔,表現了當時社會思潮下人們對愛情的肯定。正是因為對情的推重,不斷調適著文人與民間藝人的創作思想與心理,祭塔情節以禮教為框架、以母子親情力量為情感內核才得以實現。
白蛇故事基于人的精神、心理需求以及對于美好事物的心理期待,逐漸衍生出了祭塔情節。以生活為旨歸的廣大中國民眾之所以傳承演述民間敘事和口頭傳統,一是為了滿足精神、心理之需求,二是為了服務、裨益現實生活。基于上述兩個方面的原因,廣大民眾憑借生活智慧開辟了行之有效的路徑:以傳統的生活觀念和文化心理建構為基礎,遵循生活的和想象的雙重演述邏輯,形成既能滿足人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又能以生活為旨歸的民間敘事范式與形象體系[7]。
祭塔情節生成的一大邏輯是出于民間廣大民眾的樸素愿望。白蛇故事中的祭塔情節是作者對民間傳說借鑒的結果,民間傳說的流傳與戲曲小說的創作都深深根植于底層民眾之中,作為主要消費者的廣大民眾,他們的情感訴求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通俗文學的情節變化。倫理思想介入文學創作使得日常生活也成為道德的場域,并且扮演著一系列“審判者”的身份。白蛇被鎮壓塔下是因為它對蒼生的迫害,水漫金山的過失終究要以自由的代價償還,但是道德律令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活處于形而下的境地,世俗價值必須被承認,高于藝術的生活必須傳達普通民眾心中的樸素愿望。換言之,現實生活無論多么悲苦,藝術上的圓滿卻是必須的。祭塔情節實則是一出“圓夢”式的悲劇,也是對于民間大眾而言的一種心理補償。白蛇得以出塔則是對于自幼與母親分離的許狀元的補償。正是為了服務、裨益現實生活的情感需要,流傳于我國的民間傳說故事多設置相對圓滿的結局,如牛郎織女雖相隔銀河也有了鵲橋完成一年一度的相會;梁祝二人的愛情雖被殘酷的封建制度葬送但最后人們也賦予二人雙雙化蝶比翼而飛的浪漫結局。民間敘事的心理平衡和精神調適機制,能夠緩釋甚至消解人們精神上的疲勞和心理上的饑渴,有效改善人們的情緒與心境,鼓勵人們的意志和激情,從而讓人們以良好的精神狀態更好地生活下去。因此,在炎涼世態中、于冷暖人情間,面對生活的凄楚與無奈、現實的殘酷與無情,民間敘事的精神調適和心理平衡機制,自然使得白蛇故事走向了團圓式的結局,由此祭塔情節的生成才顯得合乎情理。
清代初期,政權的更替給民間百姓帶來了家破人亡的深重苦難。民眾期望安定和諧而美好的社會環境,也向往承歡膝下的美滿家庭,而結婚生子正是普通民眾觀念中愛情的最好結果,戲曲或小說的“大團圓”結局也成為慰勞他們艱辛苦難生活的精神產品。然而,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標志著白蛇故事成型之后,被永遠壓在雷峰塔之下的白蛇反而引起了讀者、觀眾對弱者的同情。方本傳奇之前,原本佛祖交代白蛇的結局是永鎮雷峰塔下,事實上劇情也是照此發展的,但是方成培卻在《歸真》一出后又安排了《塔敘》《祭塔》《捷婚》和《佛圓》幾出,續寫上天被許士麟孝心所感動,最終賦予了白蛇升仙得道的大團圓結局。可見白蛇故事增加祭塔情節反映了民間意志,而廣大民眾的“大團圓”理想在白蛇故事的演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融情與果報:祭塔情節衍生的原始動力
融情于敘事是文學作品設計情節的一大有力手段。“人的內在情感生活與外部事物結構之間,存在著某種‘同行’或‘同構’。”[8]祭塔情節正是廣大觀眾或讀者內在的心理(情感)結構與外物的形構之間達成動態平衡的產物。
仁孝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是促成祭塔情節生成的原動力。一片孝心的許夢蛟在高中狀元后來到雷峰塔祭奠母親,不因異類之分而改變的母子之情是符合廣大民眾的情感需要的。祭塔情節為解救白蛇而出現,但是沒有違背“理”的規范,孝道在不違背禮教規范的前提下,為白蛇出塔提供了有力解釋,許夢蛟符合儒家思想的孝道是解救白蛇出塔的重要推動力。見于印度《佛說盂蘭盆經》而在我國流傳甚廣的“目連救母”故事,異文不可謂不多,故事核心是身負罪業并陷在十八重地獄中的凡人母親,僅因仁義孝順的尊者目連得以平地飛升,由狗化為人進而升天長生;流布民間的“沉香救母”故事也得益其子孝道之心,最終得以劈開華山救出三圣母。在這類故事中孝道提供了動力強勁的情感支撐,有些情節甚至超越現實的行為邏輯,但卻是充滿破綻的自洽,這些破綻體現了“仁孝”主題下,真摯親情與現實困境的融合。仁孝作為三教一致的普世價值,使得我們能在文學史上看到那些歷經歲月仍閃耀光芒的“救母”題材文學作品。
母子之間的親情羈絆是白蛇故事祭塔情節衍生合情性的一大有力手段,但在邏輯建構上仍缺乏合理性,這一方面則來自佛教因果報應的思想。早在春秋時期,中國社會就已形成了普遍的報應觀。佛教傳入中國之后,佛教果報思想與中國本土報應觀融合、調適,不斷世俗化和民間化。在古代諸體文學中,果報在小說戲曲中表現得最普遍,并深刻地影響了古代小說戲曲的創作意圖與敘事模式。
清代官方把神道設教和果報信仰推到了極致,官方不但對包含果報的小說戲曲有意倡導,冀以教化:“善惡感應,懔懔可畏者,編為醒世訓俗之書,既可化導愚蒙,亦足檢點身心,在所不禁。”[9]民間勸善運動的推波助瀾加之傳統果報信仰的深厚積淀使得果報成為小說戲曲主題的穩定模式,因而明清小說戲曲多以果報來揭示主旨、勸善懲惡。
白蛇故事祭塔情節的生成是果報思想盛行的結果。佛教宣揚有因必有果,一旦作惡不論大小必有惡果要承受,白蛇為她的惡行付出了自由的代價,被鎮壓在雷峰塔之下。但是佛教又宣揚懺悔、廣結善緣可以抵消犯下的罪惡,所謂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正是因為白蛇誠心悔過,其子夢蛟又為她多做善事,所以才能感動上天,修得正果,不僅能夠出塔,還能白日飛升。祭塔救母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因果報應思想的基礎上的。
果報作為中國人的基本信仰,屬于“中國社會中根深蒂固的一種準宗教觀念”[10]。清代上至帝王,下至官吏,皆倡導神道設教。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即記述了一些因果報應的故事,如“尼說倫理”“受恩必報”“雷殛長舌”,故事旨歸多是為勸善懲惡。可見直至近現代,果報信仰在中國社會仍牢不可破。在果報信仰深厚的社會,果報被視為道德勸懲之利器,其效非凡,因而有言:“善之成于圣賢之書籍者十得一二,而勸于果報之說者十有八九,雖謂其功將于經傳可也。”[11]
在《紅樓夢》中,果報思想的影響也是隨處可見,“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里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12],《紅樓夢》十二曲收尾《飛鳥各投林》短短幾句,便將紅樓夢的哲理與核心思想揭示得透徹了然。孫楷第言:“且藉小說以醒世誘俗,明善惡有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則凡中國舊日小說,亦莫不自托于此。”[13]從創作心理上看,明清小說戲曲教化主題中果報思想的盛行,是小說戲曲教化功能的突出表現。
四、結語
白蛇故事中的祭塔情節是白蛇產子一節的延續,也是白蛇形象完成凈化并由妖向人轉型的重要一環。從白蛇產子到夢蛟祭塔,以孝道親情為紐帶由此形成了母子關系在情感建構中的閉環。白蛇其子的至誠孝心以及佛教善惡有報的思想觀念成為促成祭塔情節合情合理的原始動力。祭塔情節符合民間生活的普通邏輯和廣大民眾所能接受的家庭倫理,觀眾與讀者以同情的態度,意圖為白蛇安排一個幸福美滿的“團圓”式的結局,這種民間文化心理直接影響了通俗文學中白蛇故事的發展演變。由此,至方本傳奇之后,祭塔情節逐漸成為白蛇故事創作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谷神子,薛用弱.博異志·集異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0:46.
[2]段美華.白娘子形象的嬗變[C].陶瑋.名家談白蛇傳.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219.
[3]謝燕清.由妖變人:白娘子轉型的人類學辨析[J].民族藝術,2009(1):45-49+65.
[4][7]葉舒憲.文學與治療:關于文學功能的人類學研究[C].葉舒憲.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273.
[5][6]王永恩.色戒·情理·對抗:從題材的演變看“白蛇故事”主題的變遷及意義[J].戲曲藝術,2009(3):14-20.
[8]劉守華.故事學綱要[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146-147.
[9]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增訂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84.
[10]葛劍雄.中國人為什么會有“因果報應”觀念[N].北京日報,2010-02-01,(20).
[11]李嘉端.人生必讀書十二卷[M].鄒祖堂,輯.清同治五年仁和周氏雪堂重刻本.
[12]曹雪芹,高鶚.紅樓夢(上)[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4:57.
[13]許建平.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文精粹:小說戲曲卷[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08.
(責任編輯 程榮榮)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廳青年項目“民間文學視野下湖南漁鼓民間敘事形態研究”(22B0477)。
作者簡介:張艷(2001— ),女,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文藝美學;方建民(2001— ),男,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元明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