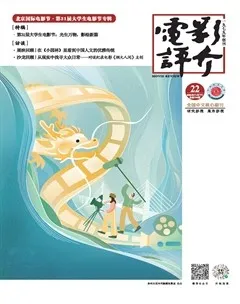展映回顧|在《小園林》里看到中國人文的優雅傳統


【對談人】" 史哲宇,男,遼寧沈陽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影視
藝術、公共文化研究;
倪祥保,男,江蘇蘇州人,浙江傳媒學院電視藝術學院院長,蘇州大學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
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影視藝術和紀錄片研究;
周洪波,男,江蘇揚州人,紀錄片導演,代表作品《小園林》;
張同道,男,河北邯鄲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紀錄片中心
主任,主要從事影視藝術和紀錄片研究。
【整理人】" 姚紫玥,女,河北石家莊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碩士生;
陳旭彬,男,山西太原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碩士生。
2024年5月25日,第31屆大學生電影節·南國(珠海)電影周“以影育人,以美培元”系列電影展映及映后沙龍活動在北京師范大學珠海校區南國劇場舉辦。首場沙龍放映的是紀錄電影《小園林》(周洪波/盧震宇,2023),映后對談由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講師史哲宇主持,該片制片人倪祥保、導演周洪波,以及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張同道親臨現場,與觀眾展開了深入的交流互動。
一、“《小園林》把中國人文的優雅傳統在生活中復活”
史哲宇:剛才我們共同欣賞了《小園林》這部紀錄片作品,這部作品的導演用兩年時間奔波于三戶人家,以四季輪轉的方式,記錄下蔡家、紀家、王家各自的造園故事,讓我們從園林日常生活當中體會到責任、親情和人性等豐富情感,引發我們的文化共鳴和豐富聯想。首先有請《小園林》的制片人倪祥保老師,倪老師,您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這部片子的創作緣起?
倪祥保:我們做這個紀錄片最早是因為前幾年中共蘇州市委宣傳部、蘇州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蘇州廣播電視總臺聯合主辦了一個名為“紀錄中國·紀錄蘇州”的紀錄片選題征集大賽。我和我的一個朋友以為這個是有贊助的就參加了。因為我對蘇州園林有點研究,我就出了這個選題。選題最后通過了,專家評論很好,但是當時沒人愿意投資。我們后來就決定自己找人來制作,我就請來了周導。我和周導是在上戲的一次紀錄片專題會上認識的,他本科就讀于蘇州大學,研究生就讀于北京電影學院,我覺得他很有人文情懷,《小園林》的片頭片尾都是周導寫的。
蘇州園林之所以揚名海內外,主要是以私家園林為主。你不能說拙政園比頤和園更好,也不能說留園勝過避暑山莊。那些都是皇家園林,它們和蘇州園林有重量級和輕量級之別,不能同臺競技。現在我們一般所說的蘇州園林已經不是私家的了,它是一種公共文化產品,里面沒有人住,沒有充滿煙火氣的生活。如今的蘇州還有沒有過去那種私家園林了呢?還有沒有自己建造后自己生活的呢?是有的。不僅有從過去傳下來的,也有現在新建的。我們覺得這就是一個看點。那些非常有名的蘇州園林,其實都只是美麗的標本。而我們給你們呈現的這些蘇州園林,這些小園林、私家園林,可能沒那么漂亮,但卻是鮮活的。它們和那些有名的園林的標準是不一樣的,這就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創作概念,也是我們創作的原始想法。
周洪波:剛剛倪老師在說的時候,我就回想起一個朋友說他在上海看完這部片子后,在自己微信里寫下了一句話:“我們都是失去了院子的現代人”。我覺得這句話挺有意思的。現在人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掙錢,我們買的僅僅是一個幾室幾廳的房子,就是為了住而已,而不是這樣一個可以用來休憩養生,有閑情逸致的地方。我們失去了這種古典情懷。所以我們這個片子表面上是在講園林,實際上是一個關于生活的片子。它可能是在告訴我們,除了每天在外面忙碌奔波,我們或許還可以過上另外一種生活。
史哲宇:張老師能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看了這部片子之后的感受嗎?
張同道: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在倡導我們做影視教學的先要會拍,而且要拍出專業水準,其次才是討論拍得好與壞。電影和電視不是說出來的,也不是寫出來的,再好的劇本拍不出來也不叫電影。影視行業是個高度實踐性的行業。就如不會看病、不會開方、不會開刀的醫生就不能稱之為醫生,學影視就得會動手。所以我認為倪老師做出了一個勇敢的、了不起的嘗試。
過去我們只在詩歌、在美術作品中看到中國古人是如何優雅地生活。王維為什么能寫出那么多好詩?大家知不知道王維的詩在哪寫?他有一個山莊,輞川山莊,他就是在那個地方“坐看云起時”。藝術和人生在中國古代一直是一致的。中國人曾經如此優雅地生活,如此審美地生活,如此有文化地生活,但很遺憾,后來的戰爭、饑荒、動亂,把古代中國美好的日子給破壞了。曾經那樣一個文明的、文雅的、審美的中國還在不在?今天看了《小園林》后,我非常欣慰地感到我們偉大的中國文明還在,至少還保存著。《小園林》把中國人文的優雅傳統、中國偉大的文明在生活中復活。這是這部片子了不起的地方,它用鮮活的生活再現了中華文明的精髓。
我現在評價紀錄片時有兩個詞用得最多。第一是豐富性,即有沒有展示人的豐富性;第二是復雜性,復雜性就包括了喜怒哀樂。如果一部片子全是在說好好好,這是溜須拍馬之作,這種作品毫無價值,不管這個作品調多高、投資多少、鏡頭多少,藝術價值卻不高。但《小園林》展示的不是空洞的園林,小園林里是有人在其中交往、生活、體驗、爭吵的,這就是我要致敬的第二點。這是非常艱難的,因為那些園林的主人非常愛惜自己的羽毛。假如一個紀錄片拍的像瑪瑙,像琉璃,這個片子就失敗了,因為它沒有活力。真實的人生就是像《小園林》里這樣時有爭執的,不是說住在這樣一個美好的花園里就沒煩惱了。就憑這一點這個影片就勝過很多裝腔作勢、富麗堂皇的用形容詞堆砌的紀錄片。而那樣的紀錄片在當下大行其道。現在很多紀錄片投資很多,鏡頭拍得很美,內容卻很空洞,沒有人間煙火氣。相比之下,《小園林》里雖然有很多美好的部分,但同時也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復雜性、多面性,這很了不起。
第三再說藝術表達。如果我來拍,我當然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但是我依然對他們的處理表示高度認可。《小園林》表現的是生活,是園林,是人和自然的合一,所以選用了中國的季節、節氣作為切入點。而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很多早都把節氣忘了。節氣是中國先民生活的智慧,我們是生活在節氣里的。每一個節氣對應著物候、氣候乃至我們心靈的節奏。現在的城市生活打亂了人們的心理節奏,所以大家才會郁悶、煩躁、抑郁和貪婪。假如我們回到節氣里,回到天地交融的環境中,假如我們的生活中有天有地,你的生活就會吹過自然的風,而不只是空調的風,生命就會健康很多,你的精神就會健康很多。這也是這個影片傳遞出來的一種我認為非常好的中華文明的精神。因此我覺得這個影片還值得再看,我爭取找機會再來觀賞學習。
史哲宇:感謝張老師高屋建瓴的分析。我也做一些紀錄片,所以非常好奇,之前其實看了一些類似題材的紀錄片,包括《蘇園六紀》《園林》其實都有涉及蘇州園林,就像剛才幾位老師提到的,大家可能會更容易去選擇這種已經變成公共文化產品的這樣的園林。在看這個電影之前,我想同學們和我可能都一樣,很難想象今天還有人生活在這樣一個詩意的環境中,所以想請教主創團隊是如何選擇這樣的一個切入點和這樣的表現形式?
倪祥保:我們寫文章做事情,總是追求能找到一個新奇的角度,或者是一個比較好的點子,那我想,園林這個點也許是可以以小博大的。我是土生土長的蘇州人,以前我帶個饅頭、冷開水、咸菜、蘿卜干,就可以在一個小園林里面待一天。所以不怎么謙虛地說,我對蘇州園林有非常深入的體會。蘇州的這些園林本來是人家的家園。它們體現出中國人親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有中國精神的傳承在里面。正因為有這樣一種認識在里面,所以我們選了這樣一個選題。我覺得創作者要想尋到一個好題材,前提是要有儲備。雖然一個好選題被想到要看機遇,比如是受到了一個刺激而突然想出來,但是它一定是基于平時的積累。機遇是給有準備的人。我能想到這個選題也是因為我對蘇州園林一直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在里面。
二、“園林是關于空間的,但《小園林》是一部時間的電影”
史哲宇:請問周導,《小園林》中這種四季輪轉、極具中國特色的表達方式,這種節令的表達,是我們在創作開始之前就預設的,還是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由于對園林的認知不斷深化而逐漸形成的呢?
周洪波:我覺得您說得很好,前面張老師也說我們是用季節、節氣,用生活的時間來串聯這個片子。園林是關于空間的,但是《小園林》其實是一部時間的電影。過去的一些紀錄片把園林作為敘事主體,園林的所有景觀都是被觀察的客體,刻畫的是它的美、它的抽象力、它的空間流動性。但是我和倪老師就在商量,我們要做一個不一樣的紀錄片。除了挖掘園林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外,我們要回到園林里面的具體生活。
當我們回到園林生活的時候,其實就把“時間”提取了出來。我們不再是看園林了,而是在看園林里邊的人。假設我們是一塊石頭,或者我們是園林的某一處風景,我們用另外一種眼光去看園林里面這些流動的人,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愛,他們的美好、矛盾、流逝。這些都是我們在一開始就定下的調子。
不過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對園林這個拍攝對象也不是那么懂。我雖然是在蘇州大學念的本科,但那個時候的我跟大家一樣,還很年輕。園林對年輕人來說不是那么吸引人。我們雖然在里邊談戀愛,在里邊玩,甚至在里邊復習功課,但對于園林的真正審美其實不太懂。所以我也經歷了一個在拍攝過程中不斷觀察園林的元素和人的關系,不斷地互動從而加深理解的過程。
其實園林是動態的,我們在看園林和人的關系的時候,會發現每一個園林都是在不斷變動的,園林不是一個亙古不變的固定的審美對象,它會受主人的愛好、性格的影響。主人喜歡什么樣的植物、喜歡什么樣的假山,就有了它自己的特點和色彩在里面。這個特點恰恰是我們在拍攝過程中慢慢發現的,最后成為剪輯中的一種構思。
倪祥保:我們現在很多人講到西方的凝視觀點的時候,只是單向的,其實這是不對的。周導剛才講的視點有這個意思,園林應該就是我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這才是真正的審美,真正把園林當做跟我可以相看兩不厭的一個對象。
史哲宇:剛才倪老師講話的時候,張同道老師發出了贊嘆,您是特別認可倪老師的這種觀點嗎?
張同道:一個沒有深刻理解的人是拍不了這個題材的。剛才倪老師講到了藝術創作中一個十分重要的一個問題——要想拍好一個片子,不是帶著攝影機滿街找選題,而是你的生命有沒有同你要拍攝的這個人、事有交集,有沒有生命體驗。《小園林》里面彌漫的情感是珍貴的,是金錢根本買不到的,這也是這個片子讓人有感觸的地方。當片中的孩子從英國留學回來,把那幅200年的古畫拿去做訂婚禮,我看到之后為之一震: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傳統的人格?當把這件文物去交給對方時,那就是在托付他的情感和命運。
這些細節其實是有含義的,所以這個影片它是一個生命情感流,到處都是可愛的細節,包括老人從樹上去摘柿子。這絕不是在超市里買點水果,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水果的來歷,你對它一無所知,它只是價值幾塊錢。所以當你吃這個東西的時候,你其實是沒有情感的。我知道柿子是怎么來的,我看到它經歷了風雨,我親手去修剪它,然后我摘下來。當我吃柿子的時候,我飽含著對柿子的生命記憶。大家意識到這里邊都有一餐一飯、一盒水果、一片樹葉的記錄,這是一種深刻的生命體驗,我看到這些是無比感動的。
所以當我們喪失了院子,喪失了土地之后,我們丟掉的是我們和自然和生命相溝通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看這個片子為什么那么觸動,就包括他們吃飯洗菜——蘇州人是那么細膩地對待那一棵菜,透過這個片子,我對蘇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為什么蘇州人代表了中國美好生活,因為他是有一種對自然的親近和敬重。這個片子沒有刺激的情節,沒有講述愛情,但是它有生命的緩緩地流動。
倪祥保:謝謝張老師,說實在的有些場景我們是等到了,比如說貓主人跟我們講它自己會開門,居然可以等到機會拍到。但是有的我們很想拍的東西,沒辦法拍到,很多場景我們都很珍惜,但也有遺憾。
史哲宇:非預設和不可預知性可能恰恰是紀錄片顯著的特征,紀錄片因此有了獨特的魅力。下面我們把時間交給現場觀眾,看看大家對這個影片的創作有什么感想和問題想要同各位老師交流。
觀眾:周導您好,除了您方才說的更注重時間感外,您還做了哪些工作去平衡生活感與園林藝術大主題的厚重感?
周洪波:這個問題還是蠻有意思的。雖然我們一開始就確定了用記錄時間的方式去展現生活感,但是這片子畢竟是針對園林拍攝的,所以說在園林的展現上的確也是花了一些功夫,包括我們片子里可以看到有軌道的拍攝,有航拍,都是去展現它的空間的豐富性。
但是正如剛剛張同道老師說的要警惕用精致的方式去完美地展現一個空洞的軀殼,我們特別害怕影片流于形式。為此我們沒有一次用逐格的方式。其實煙霧、樹木這些元素用逐格的方式是很容易展現美的,但是我們為了挖掘來自自然和生活的美,采取了一種比較中庸的方式。當時我們還有一個導演叫盧震宇,他是攝影師,我們覺得如果用一些特別雕琢、特別形式感的方式去表達園林的話,它可能還是同我們之前看過的那些拍園林的片子沒什么兩樣,所以說我們是盡量往回拉,收到生活這一面。我們去拍四季的花開,拍院子里一顆爛掉的木瓜,去拍下雪時素顏的園林——未經雕琢的東西才可以和生活產生很好的流動性。
另外,這些園子和拙政園、留園相比,在園林藝術的審美方面差距很大,畢竟財力、空間、藝術方面還是有限的。所以我們用自然的也就是剛才說的素顏的方式,跟有煙火氣的生活更加契合。如果我們把它拍得過分美輪美奐,過多的技法,就像張老師講的,也不是我們的初衷和職責,但這個也形成了影片獨特的一種美學風格。
觀眾:倪老師、周老師好!我看到《小園林》的海報英文上寫的片名是“Time in the Garden”,周老師剛剛也提到了這是一部以時間為主題的作品,我在觀看這個作品的過程中感覺這個英文名字反倒更貼合我們這部作品。我想問兩位老師,《小園林》的中文作品的名字為什么沒有像英文名字一樣體現時間呢?
倪祥保:我一開始想的片名很笨,叫《蘇州小園》。《小園林》是周導改過來的,我認為改得非常妙。
周洪波:其實《小園林》這個名字受到了電影《小森林》的啟發。那部電影講述了一個女孩回到了她的故鄉農村里面,四季流轉,獨自生活的故事,而《小園林》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去講一個時間的觀念。“Time in the Garden”是影片完成之后才起的名字。我們覺得英文名字應該更直觀地去表達這個片子的內涵,但是如果中文名也這么起,就有點像學術論文的感覺,缺少了一點抒情和生活的感受性在里面,情感張力少了一點點,所以兩個名字想強調的點是不一樣的。
三、在《小園林》里看到“天人合一、適宜棲居的生活方式”
觀眾:各位老師好!影片里面提到的三個家庭都有做不同的藝術創作,我想問蘇州的那些更加普通的市民也會因為受到環境的影響有這樣一些精神文化的追求嗎?
倪祥保: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完全肯定的。這就是蘇州作為一個文化歷史名城的重要表現。現在蘇州像這種建造私家小園林里的人至少是有三位數的。很多人賺了錢以后就會去傳承,去營造這種天人合一、適宜棲居的生活方式。其實影片里的人也不都是藝術家,真正算得上藝術家就是蔡先生,他是非常著名的美術大師。而王先生,他是園林技校畢業的,還算不上是一個藝術家,紀先生就更不是了。但是紀先生他這個人對園林有一種天生的感悟能力。他們每個人對園林的理解也不太一樣,體現了蘇州很多普通百姓的樣貌。蘇州歷史上園林最多的時候在清代,大概有360所,很多家庭不僅僅兩三間房子,都有一個比較像樣的花園。有普及才有提高,大江大河是由很多的小溪匯成的,正因為蘇州百姓都有這樣的園林情結,才會有拙政園、留園這樣的名園。
觀眾:老師們好!我特別注意到第三個家庭出場的場景,是家族的爸爸和他的小兒子對著照片在祭拜。這個場景一出來,我就感覺這是一個非常注重家族觀念的家庭,而且這三個家庭都有各自的特點,在片中也都能看到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庭觀念的表達。所以想請教老師們,這個點是在創作之前就有希望在片中展現的,還是說在了解了這些家庭之后想要加入片中的一個元素?
倪祥保:我們沒有事先了解,也沒有刻意地安排,都是完全取之自然的。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你可能對我們蘇州當地的文化不太了解。你看蔡家每年要過十幾個節,包含爸媽的生日、忌日。他家孩子每一次采果子,第一個一定要奉獻給他的父母親。我們小時候都有這樣的傳統。比如蠶豆剛出來了,首先要盛一碗放到家里的祠堂,沒有祠堂的人家就放到房間的堂桌上,仿佛就是給我的祖先、我的爺爺奶奶先供奉一下,這種傳統一直被繼承,盡管方式可能有一點改變。所以那些素材完全是取之自然,沒有任何安排,我們也沒有事先了解。我們拍下來周導覺得很好就用了。
周洪波:我想你可能問的是創作方法吧?想問我們是隨機拍到,還是說有目的地拍到。其實我們有大量的素材都是非常接近于在回答“園林到底是什么”的。對于我們來講,園林是家。打從一開始,園林和家的關系就確定下來了。每個園林都不只是風景的寫照,它還是家庭的反映。有一家人他那天既拜了佛,也拜了家里的祖宗牌位。我們剪輯的時候商量了一下,最后選擇把拜牌位這種體現家的元素留了下來。我們先把體現三家人內部關系的鏡頭確定下來,后面再去做其他的變化性的東西。
觀眾:請問導演,您在創作過程中有變更過您最初的創作設想嗎?會不會因為跟拍拍攝對象時的一些感受而改變最初的邏輯框架?
周洪波:我覺得做紀錄片是很難在最開始的時候就定下邏輯框架的。因為紀錄片它是一直在發生的,所以在發生過程當中,如何去提煉自己的結構和自己的思想,這對導演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一般來講,紀錄片拍攝在前2/3的過程當中,都是在嘗試,直到最后1/3才是最有效率的部分。因為你在拍前面2/3的時候就基本上把這事想明白了,到后1/3你已經知道要拍什么,不要拍什么,甚至要補拍什么。
其次我覺得如何去呈現一個導演的想法,這個東西主要在后期。前期的時候每個導演都會有不同的方式去觀看拍攝畫面。比如我自己有一個規矩,每一場戲拍到后面的時候,我都會要求攝影師往后走,拍全景,甚至更大一點的全景,我一定要有一個退開看的距離。因為鏡頭往前走的時候情緒過于充滿張力,他可能失去了一個導演觀看的冷靜的部分。這只是我個人在前期時的一些習慣,我如何去觀看這個東西。在后期剪輯的時候,有的時候是我自己剪就比較好辦,我會不斷地去剪輯以形成一個自己的想法。有剪輯師的時候,我們會一起去討論這場戲要表達的是什么,著重的是什么。
在這部片子里,我們主要想展現兩件事。一個是把我們的傳統文化接續上。比如在春夏秋冬的四個部分里面,我們都放了中國畫。其實中國畫細看都是園林的故事,里面講的都是園林山水。這個部分目的性就很強,就是要把曾經的園林和現在的人物接上關系。這一點是我同剪輯師爭執后決定的。
另一個就是展現家庭生活瑣碎的部分。我們不厭其煩地去表現他們吃什么,紅燒排骨是怎么做的,果子是怎么摘的,獅子頭是怎么做出來的。雖然用了很大的篇幅,但這些篇幅是很重要的。每場戲的時間長短其實會默默影響觀眾對片子的認知。我們把“吃”和日常生活當中的瑣碎,作為去表達園林的生活氣息的重要呈現,這個是在后期達成的,因為我們的素材量特別大,需要在后期里面去思考一個去呈現它的方法。
史哲宇:特別感謝幾位老師將來自于創作當中的這種真切的體會和同學們來分享。相遇總是很短暫,就像這個片子里四季流轉一樣,我們今天三個多小時的交流倏忽而過,希望同學們通過對這部影片的觀摩和學習開啟大家對優秀紀錄片作品更多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