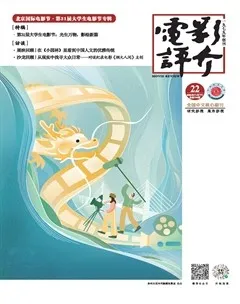自動機與后人類:生成式藝術的“技術圖像”理論
【摘 要】Sora、GPT-4等AI系統的不斷“涌現”,推動了以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的系統科學理論也從自然科學應用向人文社科廣泛轉移,促使當代藝術概念與載體不斷更迭。人類仿佛正處于當前技術革命的風口浪尖,要想在這輪時代洗牌中感受未來藝術的脈搏,或許可以率先理解通過系統創作帶有明顯自動生成的“生成式藝術(Generative Art)”。本文在技術圖像視域下審視“生成式藝術”的技術圖像理論,揭示生成系統(自動機)和技術圖像異質耦合下的自主性和動態性,探究未來藝術語境的本質;進一步審視在后人類主義視角下,“生成式藝術”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挑戰,積極尋找未來藝術復雜智能演進過程中新的期待和可能,即在藝術與其他學科的認識邏輯對照中嘗試發現技術圖像的未來,從而引發人類與非人類的一種關系思考。
【關鍵詞】 生成式藝術; 技術圖像; 自動機; 后人類; 復雜性
在數字藝術領域,人們發現驚喜的并不是PS、PR等計算機應用程序對傳統藝術工具的替代,而是計算機有時似乎可以直接自己創造藝術作品,即“生成式藝術(Generative Art)”。顯然,這是一個自21世紀初期以來蓬勃發展的藝術實踐陣地,人類正處于技術革命的風口浪尖,要想在這輪時代的洗牌中把握住未來藝術的脈搏,或許可以先試圖理解將技術與藝術緊密相連的生成式藝術。換言之,關注在當下技術圖像宇宙中正在開展的事實:一切都發生在一個由人與非人相互關聯的機構組成的復雜網絡中,對生成式藝術中生成系統的研究正是一種開始思考宇宙的方式。
一、技術圖像視域下生成式藝術的概念界定
1968年,美國藝術家、評論家和策展人杰克·伯納姆(Jack Burnham)在《系統美學》中提出:“我們現在正處于從一個面向對象的文化向一個面向系統的文化的轉變中。在這里,變化不是來自事物,而是來自做事的方式。”[1]隨著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人們正在經歷一種從歷史性思維(基于線性文本和敘事)向技術圖像思維(基于視覺化和編程)的轉變。這種轉變要求人們重新考慮人類與技術圖像的關系,技術圖像不僅僅是被動地接收信息的媒介,還具有主動地塑造和引導人類看待世界方式的能力,以及人們如何在一個由技術圖像主導的社會中維持人類自由和尊嚴。在此背景下,技術圖像視域成為一個關鍵的概念,它不僅關系到人類如何理解周圍的世界,還關系到人們如何在加速變化的媒介環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生成式藝術”正是在此情況下,被廣泛地視為一種異質的藝術方法領域,其基礎是在概念化、生產和呈現藝術作品的過程中,將預定義的元素與不同的不可預測因素相結合,從而形成創作過程的不可控性,強調審美化藝術的語境本質。作為一種創造性方法,生成式藝術隨著數字媒介的飛躍式進展出現在大眾視野中,在數字化語境中與計算機程序和數據處理緊密交織,成為藝術家在探索創作途徑中的新路標。賦予生成式藝術單一的定義較為困難,因為它涉及藝術的各個方面,不僅包括建筑設計、計算機圖形學、影像創作和音樂繪畫等;也具有類比性、系統性、隨機性、無限性等復雜的理論基礎;同時應用了細胞自動機、分形、人工生命(a-life)、林氏系統(L-系統)、混沌(chaos),當然還有隨機化等多種因素。較為重要的是,生成式藝術總是隨著技術創新而自我更新。
當代生成式藝術根植于20世紀中期現代主義對創作過程的本質、藝術作品的材料、語義和語境身份的探索,從理論溯源上講,這種新的藝術形式受到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和符號學的影響。[2]后來國際新媒體藝術之父羅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將這種新奇的活動定義為“一種控制論的視覺”。控制論是一種涉及系統、反饋和自我調整的理論,在藝術領域“控制論視覺”強調藝術作品中的反饋機制、參與性和互動性。阿斯科特認為,藝術不僅僅是一種靜態的展示,更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與觀眾、環境和信息流有關。[3]很快,“控制論視覺”就得到來自計算機科學界關于結構和過程的想法支持。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英國抽象畫家哈羅德·科恩(Harold Cohen)放棄以前的繪畫實踐,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覺得計算機藝術可以幫助他理解自己的創作過程。[4]另外,在過去20年里,生成式藝術這一領域也受到涌現、進化和自組織等思想的啟發,追溯到20世紀中葉的控制論和自動化理論,旨在研究簡單的生命形式(如細胞自動機)到復雜的生命體(如虛擬生物、機器人等),探索生命系統的自組織、自適應、進化行為以及生命和環境的相互作用。[5]
從歷史梳理來看,對生成式藝術的定義主要有兩種看法。第一種來自最早提出“生成式藝術”這一概念的意大利米蘭工學院的塞萊斯蒂諾·索杜(Celestino Soddu)教授,他并沒有為生成式藝術下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是將生成式藝術描述為人類對自然的效仿方式;同時,他認為在計算機泯滅人類創造力的時代,生成式藝術通過代碼在藝術與科學間開辟了一條通路,使人類有新的空間通過計算機來發揮創造力。[6]索杜還在2012年生成藝術大會的提案中呼吁:“生成式藝術是一種將人工事件的遺傳密碼作為實現理念,構建能夠產生無盡變化的復雜系統的藝術。每個生成項目都是一個概念軟件,可以盡可能地產生獨特且不可重復的事件,如音樂或3D對象,以及作為藝術家/設計師/音樂家/建筑師/數學家愿景的生成想法的多種表達。”[7]第二種是2003年米蘭國際生成式藝術會議上,紐約大學菲利普·加蘭特(Philip Galanter)教授提出了迄今為止被廣泛引用的生成式藝術的定義。加蘭特認為生成式藝術的定義應該:(1)包括過去和當前生成式藝術活動的集群;(2)允許尚未發現的生成式藝術形式;(3)允許“藝術”定義被整合,同時作為所有藝術的子集存在;(4)清晰辨認,并非所有藝術都是生成式藝術。[8]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生成式藝術的定義似乎是使用自主的藝術制作系統進行創作的藝術形式。加蘭特常在其教學中提出:“生成式藝術是指藝術家使用非人類創作者(如一套自然語言規則、計算機程序、機器或其他程序性發明,其以某種程度的自主性開始運動)來共同合作或獨自創造藝術作品的藝術形式。”[9]這種對生成式藝術理論廣泛而開放的定義反映了一種包容性的方法,生成式藝術作為計算過程和自主系統的藝術,獨立于任何特定的過去或未來的技術,是一種基于規則的藝術形式,其理論框架深深根植于人工智能和控制論——無論是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中。[10]由此可見,算法和規則集是生成式藝術的沃土——無論是語言學(索爾·勒維特Sol LeWit)、物理學(漢斯·哈克Hans Haacke–冷凝立方體,1965)、生物繪畫(約瑟夫·內赫瓦塔爾Joseph Nechvatal)還是建筑(塞萊斯蒂諾·索杜Celestino Soddu)及藝術都在自我生存的系統(自動機)中運行。生成式藝術受制于可控的指令,能夠自我控制和預測,因為它依賴于一套規則來進行創作,藝術創作往往從有意識地選擇這些規則開始,但這并不局限于任何媒介、主題或技術背景。
生成式藝術的概念本身與它所倚重的生成系統(自動機)一樣充滿未知的復雜性,這一領域的深奧之處在于,藝術創作的本質涉及無窮的創意可能性和情感表達,而這些因素往往超越了單一的規則或模型,因此,單從某方面去探討其特征都無法管窺其全貌。在藝術的長期發展中,有以下三種創作中介模式。
一是基礎工具中介。藝術家用身體或身體的某些部分來塑造物體,或者使用一些基于身體的工具,如鉛筆、刷子、鑿子等。這種簡單基礎的中介作用發生在傳統繪畫、雕塑及陶瓷制造中。從史前舊石器時代頂壁繪畫到19世紀和20世紀的前衛藝術,從許多著名的書籍、手冊、目錄、展覽和活動中都能看到,很大一部分藝術都與這種創作模式有關。
二是控制與協作。藝術品借助某種設備或機器中介,最終結果是由一個或多或少延伸、復雜的自動過程決定的。這種模式在基于2D和3D打印、攝影、電影、視頻、計算機模擬、數控設備等技術的藝術形式中較為典型,在傳統設計以及大部分平面藝術中更是如此。典型代表如攝影,基于一種設備只要通過按鈕激活,攝影師選擇視點或將場景、物體/主題安排在相機前,就會生成自動圖像的藝術方式。
三是自主性機器。藝術品的進一步制作是使用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機器或設備,即自動機。在這種模式下,可以進行自主的、可能開放的過程,限制或消除人類干預,使其在運行過程中受到新的輸入的影響,從而產生一個動態演變的結果,而不是通過簡單的工具進行直接或間接中介的建構過程,也不是通過設備中介的受控過程。在這種藝術創作模式中,藝術家是過程的激活者,藝術生成取決于外部變量(如來自環境/用戶的輸入)和內部變量(位于過程內部本身)。因此,最終結果是開放的,永遠無法完全預測,因為它取決于逃脫藝術家控制的變量。
要而言之,本文旨在討論的研究范圍是在第三種模式下基于生成系統(自動機)創作的生成式藝術。結合加蘭特的定義,可以看出基于技術圖像視域下的生成式藝術是一種通過在藝術家和生成系統(工具、軟件、硬件、機器人和機器等)合作中執行一套規則來產生藝術形式的藝術實踐。一般來說,藝術家通常是控制一個創造性的系統來授權一個自動機,藝術家和生成系統(自動機)共同探索各種迭代的選擇,結果最終由藝術家的評價決定。正是因為藝術家與生成系統(自動機)對話和協作的原因,生成過程能夠充分地傳達一個藝術家的身份和特性,藝術家能夠將個人的審美觀念和哲學思考編碼進生成系統(自動機)的邏輯中,從而創造出具有深度和內涵的藝術作品。因此,創造和后來識別藝術家印記的可能性是生成藝術及其結果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這非常接近人工智能的起點,創造一個永不停止讓你驚訝的藝術作品,并逐漸聚焦人類想法前所未有的方面,這無疑是想象力的終極。
二、生成系統(自動機)和技術圖像的異質耦合
本文所指涉的自動機,是一種在生成式藝術中按照自身邏輯運行的生成系統。自動機(Automata)一詞源于希臘語,意為“自己行動”。在技術發展史中,自動機的概念經歷了從簡單的機械裝置到復雜的算法和程序的演變。最初的自動機,如古希臘的赫羅(Heron)的氣動裝置和中世紀的鐘表,展示了人類對于模擬自然現象和生命活動的早期嘗試。隨著時間的推移,計算機科學中自動機理論主要關注能夠執行特定任務的系統。圖靈機和馮·諾伊曼結構是自動機理論的兩個基石,它們為理解計算過程和系統內部狀態的轉換提供了數學模型,也為理解復雜系統的行為和動態提供了重要的視角。
在生成式藝術創作中,生成系統(自動機)作為一種抽象的計算模型,其核心功能在于根據一系列預定義的規則進行狀態轉換,這些規則可以是藝術家根據創作意圖設定,也可以通過學習大量藝術作品后自動習得。在生成系統(自動機)的框架下,藝術創作被視為一系列狀態轉換和規則應用的過程,生成系統(自動機)通過感知輸入(如藝術家的初始設定、觀眾的互動等)并根據內在狀態和規則進行計算,最終產生輸出不僅是靜態的視覺呈現,還可以是動態的、互動的,甚至是多感官的視覺體驗,即技術圖像。技術圖像(Technical Images)作為藝術與技術耦合的產物,廣義上是指過技術手段生成的視覺表現形式,然在狹義上其概念隨著自動機理論的應用而不斷擴展,早期的技術圖像主要指代通過技術手段創造的視覺作品,如攝影和早期的計算機圖形。而后,隨著自動機理論的融入,技術圖像開始包含更多由系統自主生成的圖像。技術圖像的核心在于其生成過程的自動化和算法化,藝術家通過編程和算法設計,將創作過程中的某些決策權交給了生成系統(自動機)。此時,生成系統(自動機)能夠根據預設的規則和參數自主地生成圖像,甚至在與外界互動中不斷演化和改變。技術圖像的這種動態特性,使得每一幅作品都具有獨一無二的生命力和變化性,圖像能夠超越靜態的展示,成為一種動態、互動和可演化的藝術形式。
生成系統(自動機)在藝術領域的應用嬗變不僅推動了技術圖像的生成,也再定義了藝術創作的過程和意義。生成系統(自動機)與技術圖像兩者異質耦合的產物——生成式藝術,依賴于生成系統(自動機)對藝術創作過程的模擬和再現,生成系統(自動機)不僅僅是一個概念工具,而是藝術創作實踐中的實際參與者,通過其預設的規則和算法與技術圖像相互作用,生成獨特的藝術表達。吉恩·揚布拉德(Gene Youngblood)在《電影與代碼》(1989)中預測了電影中形式元素基于代碼處理的算法基礎的創造性后果,但從未對此進行解釋。[11]生成系統(自動機)與技術圖像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動態的。一方面,生成系統(自動機)通過算法生成圖像,技術圖像作為創作結果,展現了生成系統(自動機)的計算能力和藝術創造力表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技術圖像作為輸入,可以反饋給生成系統(自動機),影響其后續的狀態轉換和規則應用。這種反饋機制使得藝術創作成為一個流動的、不斷進化的過程,每一次創作都是對前一次創作的超越和重構。這種互動關系也使得藝術創作過程呈現出一種自我迭代、自我演化的特性。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和安德烈亞斯·克拉基(Andreas Kratky)在《軟電影:數據庫導航》(2002-2003)項目也展示了馬諾維奇將電影視為數字(離散)媒介和數據庫的觀點。該項目基于對一組存儲的視頻片段進行分類和標記,通過算法實時創建編輯場景,并設計用于排列、導航和播放材料的用戶界面。[12]其中,生成系統(自動機)根據觀眾的互動反饋調整其生成圖像的算法,雖然算法本身具有一定的確定性,但由于其處理的數據和環境因素的復雜性,最終生成的技術圖像往往具有不可預測性。這種不可預測性則是生成式藝術的魅力所在,它打破傳統藝術創作中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為藝術創作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
生成系統(自動機)為藝術創作引入了系統化的新方法,改變了藝術作品的生成過程,并擴展了藝術理論和哲學的討論范圍。系統化方法貫穿于藝術創作過程中的各環節,包括構思、設計、執行和評估全流程。在構思階段,藝術家需要明確作品的目標和主題,并設計出相應的生成系統(自動機)模型。這一模型應當能夠捕捉藝術家的創意,并將其轉化為可執行的算法。在設計階段,藝術家需要選擇合適的技術和工具,搭建出生成系統(自動機)。這可能涉及編程語言的選擇、硬件設備的配置以及用戶界面的設計。譬如倫敦科幻電影節48小時電影挑戰賽的參賽作品《陽春》(Sunspring,2016),創作者依據獲得的一系列須在48小時電影制作中出現的提示(道具、對白等),編程了一個長短期記憶遞歸神經網絡智能機器,通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以科幻電影劇本為語料的訓練,生成作品《陽春》。電影充斥著笨拙的臺詞和上下文不一致的情節,但它成功入圍了電影節的前十名,并激勵一位評委:“如果他們承諾堅持這樣做,我會給他們打高分。”[13]執行階段是系統化藝術創作的核心,生成系統(自動機)在這一階段開始運行,并根據預設的規則生成藝術作品。這一過程可能需要藝術家的監督和干預,以確保系統的運行符合預期。在評估階段,藝術家和觀眾對生成的藝術作品進行評價,這一評價不僅基于作品的審美價值,也考慮作品的創新性和技術實現的復雜性。如藝術家徐冰協同香港科技大學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利用GPT-3模型和互動排列組合,首次制作并展示了完全沒有人類參與劇本、拍攝和剪輯制作的“三無電影”—《人工智能無限電影》(AI-IF,2020),該項目可使觀眾在電腦頁面上挑選一個電影類型(戰爭、愛情、科幻、犯罪和前衛五類),并設置片長,再通過輸入關鍵詞或句,即可生成由AI出品的永不重復的電影。[14]其生成系統主要由四部分構成:一是電影劇本生成系統,如常見類型片:犯罪、浪漫、科幻等;二是視頻生成系統,可以根據電影腳本檢索、拼接視頻;三是腳本和字幕的匹配生成;四是對話和背景音樂的自動匹配。哲學家科西莫·亞卡托(Cosimo Accoto)曾在《數據時代:可編程未來的哲學指南》斷言:這種不可預測性源自數字技術“……作為一個關鍵要素激活并通過生成性運行將空間同構為代碼/空間……使人成為生態和環境的一部分”[15]。端倪可察,生成式藝術中的所有系統化創作方法都指向強大的算法系統概念,用于隨機、參數化分析生成藝術的結構、敘事、構圖、編輯、呈現和交互,預示著一種能夠結合使用計算機視覺、語義分析和機器學習,以識別各類類別,并能從一系列隨機收集的鏡頭、序列或完整影像中重構情節的復雜生成路徑。[16]
藝術作為一個微觀宇宙,反映了整個社會對技術的不同立場。在這種情況下,人類與生成系統(自動機)合作變得極為有趣。因為這是一種以超越單純的迷戀或厭惡的方式處理技術圖像的復雜方式,一種探索人類和非人類生成系統(自動機)可以在創造性合作中協同工作的方式。生成式藝術遠非完美控制思想對物質的理想,它是關于啟動不可預測并“放手”的過程:即賦予生成系統(自動機)自由。正如與外星物種的相遇,這種場景在科幻電影中被多次預測,但現在正在人類眼前發生。只是目前外星物種還未從不明飛行物上下來,它們不是來自于外太空,而是人類自身發明了它們——來自人類的雙手和大腦,以人類創造的“工具”為幌子征服了世界。因此,人類經常主觀性認為:它們于人類而言應該是熟悉的,是很容易被理解和控制的。但事實并非如此,人類現在所經歷的局勢正具備時代變化、文明沖突的所有標志,試想:當你使用電腦或拿起手機時,“第三生命”的親密接觸正在悄然發生——其后果深不可測。
三、“技術圖像”理論與生成式藝術的復雜性機制
人工智能的出現將人類帶入了一個全新的藝術維度,其生成圖像的能力完美貼合了“未來藝術”的一切特征,這也預示著“后人類”的到來。在后人類主義視角下,人類不再是自然界和其他非人類行動者的中心,而是眾多相互作用的實體之一,這挑戰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強調了技術、環境、動物、機器等非人類實體在構成所處世界中的重要作用。生成式藝術在作為裝置的生成系統(自動機)下,蘊含著一種機械化的隱藏機制,而這背后是后人類鞏固文明果實的愿景。這一過程中生成系統(自動機)既不是“奴隸”也不是“主人”,而是同事或玩伴。系統可以是軟件、機械裝置、化學過程或社會動態等等,所涉及的技術手段并非都是數字化的。系統如何具體化很重要,其靈魂在于它所體現的規則:在哪種程度上,它可以自主行動;也就是超越藝術家的直接控制。可以將生成系統(自動機)看作是一種游戲,游戲的存在是因為一組規則,同樣也可以換言之為算法,游戲過程中的可能性作為子集在每次玩游戲時終將會被實現。威廉·弗盧塞爾(Vilem Flusser)的“技術圖像”理論就曾暗示,對于技術圖像接收者來說,那些編入裝置中的負熵會轉換成熵①——以一種隱蔽的方式。這樣一來,裝置的根本矛盾就產生了,因為裝置和宇宙一樣都是自動運作的,會持續地運行編入其中的任務。宇宙會通過運行任務最終奔向“熱寂”,而面對必然走向混亂無序的宇宙,人類的回應便是應用裝置“賦予信息”[17]。于是“自動化”就出現了:為了建造一種加快偶然事件發生速度的裝置,并規定(編排)這種裝置,使它在人們期望的偶然事件發生后停止運轉。仔細觀察就會發現,自動化具有巨大的革命性,因為從現在起,人類的自由將不在于依照自己的心意來塑造世界(裝置能做得更好),而在于指示(編排)裝置達到自己期望的狀態,并能使它在達到這種狀態后戛然而止(控制)。[18]
除此之外,生成式藝術常提及的“隨機”(Zufalls)一詞,更是摒除“衰朽”(Zerfall)、“事故”(Unfall)和“廢物”(Abfall),允許“想法”(Einfall)進入網絡的變體。顯然,所有這些“隨機”的變體都是負熵的:在談論規則時,談的實際上就是負熵。[19]這種自動機制保證了所有藝術創作中的對話都是負熵的,它不僅會自動去除所有多余之物,而且還能從存儲器中清理它們,就好像意外事故與多余之物從未出現一樣。例如在生成式藝術中常使用的系統模型GANs(生成對抗式網絡),就仿若蘊含在生成器和判別器之中的“麥克斯韋妖”。弗盧塞爾認為“麥克斯韋妖”是一種自動機制,它不僅會自動過濾,還會自動決定允許哪些分子通過,使其根據低溫分子和高溫分子之間的差異作出決斷,借助溫度計來自動識別分子的情況。[20]因此,在生成式藝術的本體論問題上,首先面對的就是一個自動的審查器和評判器。當然,這個“麥克斯韋妖”(自動的評判機制)必須事先是由麥克斯韋編排好的。當前的技術正大步朝著人工智能如何可以用更快的速度完成考量和計算的方向發展,那么在可預見的將來,“麥克斯韋妖”這種自動評判器將不僅會取代人類評判者,而且會比人類評判者擁有對情況更深刻全面的認知。
藝術創作自古以來就是不斷迭代、發展、行動和感知的過程,然后再概念化——以此類推。藝術家通過對作品的反復修改和思考,逐步接近心中的理想形態,其中不僅體現了藝術家對美學和技術的探索,也反映了他們對文化、社會和個人經驗的深入思考。相比之下,AI時代的生成式藝術,規則必須是建設性的,這里與數理位邏輯有相似之處,也就是說,它們必須提供或暗示一個可以導致預期結果的特定過程,這就是生成式藝術的定義特征。[21]只有當規則具有建設性時,藝術家才會將決策的關鍵元素交給生成系統(自動機)。眾所周知,自然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生成系統”,沒有完全一樣的兩棵樹,也沒有同一棵樹的兩片葉子完全相同。生成系統就是技術努力越來越接近自然的一部分——從工業機器的僵化和頑固,轉向復雜系統的適應性和可變性。但隨著人類發明一步一步為自己獲得“特權”,“創造性協作”中的力量平衡發生了變化,生成系統(自動機)變得更加自主,人類的參與變得越來越少。假使當生成系統(自動機)根本不需要人類來它們的生活和發展它們的創造時,那時技術將成為一種“第二天性”,藝術將不再是純粹的人類事務。如今,這一趨勢在AIGC領域發生的一連串驚人發展中顯而易見。在高智能語境下,生成系統(自動機)的自主性和多樣性都突破了人類曾經的想象,由微軟公司(Microsoft)主導的“下一幅倫勃朗(The Next Rembrandt)”項目,通過一幅算法生成的倫勃朗風格的畫作,模糊了藝術和技術之間的界限。[22]倫勃朗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畫家之一,“下一幅倫勃朗”畫作如同倫勃朗本人的風格——通過典型的17世紀元素、人物富有表現力的面部特征和其深邃、悠長的眼神,引起觀賞者一種深刻的情感反應。然而,畫面中的男人其實并不存在,整幅作品都是通過收集、分析其作品數據,由算法根據其構圖、風格、用色、筆觸等多方位的特征,通過3D打印“創作”的。這個革命性的項目實際上是通過生成算法模型,多維度全方位“模擬”倫勃朗的風格。而“風格”曾作為經典藝術中個人化、獨一無二、無法解釋的事情被輕而易舉地“遷移”了。藝術的頂峰被簡化為一種算法——盡管無法直接看到或分析。
在后人類主義背景下,生成系統(自動機)作為中介角色,削弱了傳統藝術中藝術家與作品之間的緊密聯系。藝術家的地位被降級,角色從直接創造者轉變為系統的設計者和引導者,通過調整系統的參數和規則來影響最終的藝術成果。藝術家與自動機之間形成一種對話機制,系統每次運行都會根據人類指令調整做出不同反應,這種互動推動了藝術創作的進化過程,朝向事先無法預見的目的地發展。簡言之,生成式藝術可以被視為人類和非人類主體之間的創造性合作,結果是二者都無法獨自完成的事情:一種混合藝術作品。它不是對給定設備的技術能力的展示,也不是對人類意圖的直接外化,而是介于兩者之間,處于后人類的文化狀況(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就像一個“藝術智能體”。目前的人類仿佛正在不可阻擋的技術變革列車上,似乎沒有明確的引導者,發明者和企業家雖有話語權,能決定技術開發和市場進入,但他們無法預示未來,甚至不知道人類最終會走向哪里,生成系統(自動機)將如何被改造,以及兩者終將共同構建什么樣的世界。
結語
生成式藝術是來自20世紀自然科學理論、計算機技術和人文藝術共同催生的結晶,提倡將萬物作為整體、有機的系統來看待。這不僅能與科學理論一并構建當代藝術的新范式,也能通過系統的觀點用理性的視角來看待后人類藝術實踐活動產生的深刻影響。技術圖像復雜性的需求加速了系統邏輯方法的重新發現,即人工智能領域的“奇點”。這為人類與AI的關系提供了新視角,生成式藝術實踐也表明計算機與人、觀眾與作者、準自治系統和訪客參與之間的關系比它們的主要定義似乎更為復雜,其藝術形式同時挑戰兩者:生成系統(自動機)的自主性和人類藝術家的自主性。
思考人類當前所生活的時代復雜性,已經進一步超越了人類對技術的熱情接收和偏執拒絕的單一態度。在后人類主義視角下,身體與機器、技術、媒介結合在一起的主體的改變,形成了一種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生成式藝術中對自身生成系統(自動機)的研究正是一種進入技術圖像宇宙的方式,它推開了藝術創作神秘外殼的大門,讓機會、不確定性和缺乏控制(熵)進入其中,人類不再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和起源,而是后人類(人與非人)主體復雜網絡中的另一個節點。這是一個開放的實驗過程,探究了在后人類想象的終極環境中,整個人類共同體在自動機不斷增長力量的情況下,走向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和混沌化的世界中可能產生的一種新的認知方式、行為方式和合作方式——非生物體、植物、動物和人。
參考文獻:
[1]Burnham J. Systems esthetics[ J ].Artforum,1968(01):30.
[2]Boden M A.Précis of the creative mind:Myths and mechanisms[ J ].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994(03):519.
[3]Ascott R.Behaviourist art and the cybernetic vision[ J ].Cybernetica,1966(04):247.
[4]Malina R F. Aaron's Code:Meta-Ar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Work of Harold Cohen by Pamela McCorduck[ J ].Leonardo,1991(05):628-629.
[5]Boden M A. Mind as Machine: A History of Cognitive Scienc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4.
[6]Soddu C. Città aleatorie[M].masson,1989:58.
[7]C.Soddu,E.15th Generative Art Conference opening[EB/OL].(2012-11-30)[2014-01-18].http://www.generativeart.com/.
[8][9]Galanter P.What is generative art?Complexity theory as a context for art theory[C]//In GA2003-6th Generative Art Conference.2003:4.
[10]Boden M A, Edmonds E A.What is generative art?[ J ].Digital Creativity,2009(1-2):21-46.
[11]Youngblood G. Cinema and the Code[ J ]. Leonardo.Supplemental Issue,1989:27-30.
[12]Manovich L, Kratky A. Soft Cinema:Navigating the Database[M].The MIT Press,2005:5.
[13]Newitz A. The Multiverse/Explorations amp; Meditations on Sci-fi[ J ]. Ars Technica,2016:9.
[14]李巖.人工智能電影:一次未來考古學研究[ J ].當代電影,2022(08):7.
[15][意]科西莫·亞托卡.數據時代:可編程未來的哲學指南[M].何道寬,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21:93-95.
[16]Berga Q C. Code as a Medium to Reflect,Act and Emancipate:Aase Study of Audiovisual Tools that Question Standardised Editing Interfaces[C]//Interface Politics: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2016:36.
[17][18][19][20][巴西]威廉·弗盧塞爾.技術圖像的宇宙[M].李一君,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11,51,84,85.
[21]Goodstein R L. Constructive Formalism Essays on the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s[ J ].Mathematical Gazette,1951(325):78.
[22]By|.The Next Rembrandt[EB/OL].(2016-04-13)[2023-12-20].https://news.microsoft.com/europe/features/next-rembrandt/.
【作者簡介】" "蒲 璐,女,甘肅蘭州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媒介技術、新媒體影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