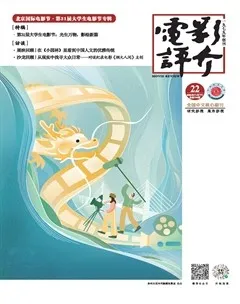沙龍回顧|從現實中找尋大眾日常


【對談人】" 尹一伊,女,重慶合川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流行文化、媒介受眾研究;
王 靜,女,上海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制片人,從事影視傳播、紀錄片創作與研究,代表作《煙火人間》《零零后》;
胡 偉,男,北京人,電影導演,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講師,代表作butter lamp What tears us apart;
謝福坤,男,北京人,導演、剪輯師,代表作《煙火人間》《大學》。
【整理人】" 胡瑋玉,女,江西景德鎮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碩士生;
周 靜,女,河南漯河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碩士生。
尹一伊: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煙火人間》(孫虹,2020)的兩位主創代表——制片人王靜老師、剪輯指導謝老師,以及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的胡偉老師做客沙龍。《煙火人間》是一部很有生命力的紀錄片,我看了很多遍,常看常新。我想請問王靜老師,是什么樣的契機讓你想要做這樣一個項目?
王靜:我們這部影片的靈感起于2018年,當時整個中國短視頻平臺正處于爆發式騰飛的階段,大家刷抖音和快手的頻率急速上升。我們這個團隊一直都是做紀錄電影的,曾經紀錄片拍攝的門檻較高,所以我們具有稀缺性。但是到了現如今,人人都可以拍,可能普通人拍得比專業團隊更好,更加深入田野,更讓被攝對象感到放松,能拍到更好的內容。這已經是一個影像過剩而不是影像稀缺的時代,那么我們如何去處理這些海量的素材?讓這些海量的素材在整個人類的影像歷史中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去呈現?這就是我們當時從學術角度出發思考的一個問題,我們想要對這個問題去做一個影像實踐的回應,所以我們就和快手平臺一起發起了《煙火人間》項目。
快手平臺上老百姓記錄自己生活的素材很豐富。現在大家可能覺得抖音和快手越來越像,這兩個平臺奇觀性的內容和老百姓拍攝自己日常生活的內容已經都有了。在我們這個項目之初,尤其是我們集中創作的2019年到2020年期間,這兩個平臺之間還是有差異的。我們一方面想要去呈現一些奇觀性的內容,比如大家看到的黃袍加身、穿著漢服溜滑板等,但另一方面我們希望更多地去呈現一些老百姓自己拍攝的生活素材。而這類素材當時在快手相對較多。具體的創作過程有點類似于紀錄片拍攝的前調,主創團隊每天刷快手,了解上面的內容,并且因為每個人的興趣點不同,最后刷到的內容也不盡相同。
隨后我們又開始思考如何解決豎屏和橫屏的問題,如何用一個敘事結構把它們串聯起來?如何能讓觀眾愿意一直坐著看短視頻?我們先出了一個11分鐘的實驗段落,發現大家可以接受,再慢慢擴展到80分鐘。在這個過程中,創作結構設計和素材檢索交替進行。直到素材基本上都獲取了之后,我們才開始聯系用戶獲得授權。
尹一伊:這部影片無論是創作流程還是最后呈現出來的形式都具有實驗性。胡偉老師,不知道您看過之后是什么樣的感受?
胡偉:我本人是做當代影像研究的,看到這樣的片子我真的挺感動、挺驚訝的。這個片子具有非常典型的實驗影像特征,完全不同于過往的電影。所謂的實錄電影、編纂電影,例如最近我看到的帶有標桿性質的《現實是過去的未來》(黃偉凱,2009)、《蜻蜓之眼》(徐冰,2017)等,它們也都是收集了民間影像,但它們可能更傾向于found footage film的特征,不具有影像特征。它們雖然都是對既有影像、對原始文本的一個回訪和再挖掘,但是今天的這部影片它在對既有影像的重組、拼貼、質疑的過程中帶有明顯、強烈的作者傾向,每個篇章都有著不同于原始文本的創作理念——它完全抽離出來了。影片大概有“衣”“食”“住”“行”幾個板塊,這些板塊幾乎涵蓋了我們所有的日常。我大概可以看出它的用戶肖像是怎樣的,它展現出的用戶群體有一種特別強烈的社會主義人物光環。我非常不認同邊緣化、底層化的說法,我認為這些人物是非常重要的,他們是我們自己國家的基石群體。“行”的板塊里有一個人在去西藏路上因缺氧而死,當我看到他的朋友們后來的行動時,我真的非常感動。我相信作者在創作的時候是有著很強烈的思考,所以他才會去選擇這樣的影像表達。這是一種真正的對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自我反思,或者說是一種批判。這是我覺得非常感動的一點。
我第二個感動點在于,在今天這樣一個復制和重組泛濫的時代下,《煙火人家》讓我看到了一種對工業電影和主流敘事語言的強烈抵抗。這種抵抗是對影像自身的消解,它讓我們看到了新的可能。它是一種具有非常純粹的作者意識的實驗影像的創作方式。
尹一伊:我有幸看過之前的版本,其實和現在呈現出來的風格有一定的差別,我想請問謝老師,這部影片在剪輯上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謝福坤:我舉幾個具體的例子。第一個就是幾乎所有短視頻都帶有節奏強烈的背景音樂,但我們希望呈現的是一個紀錄片,一種相對真實的狀態。所以我們第一個工作就是先要把音樂關起來,嘗試用語音來給影片增添紀實感,就是大家看到的聲音的數據;第二個就是畫面的分辨率、碼流、幀數的問題。比如我記得當時有一條卡車司機喝可樂的視頻,內容也不錯,沒有背景音樂,不用就可惜了,但是那個視頻大小不到1MB,你就能想到那個視頻的畫質是什么樣的了。還有一些丟幀的,幀數最低的素材1秒只有12幀,正常的話應該最少23-25幀,所以在一個25幀的時間線上那些低幀率的素材就會卡頓。再比如畫幅,我們遇到非常多9:16、9:18各種比例的畫幅。所以都不用到剪輯那一步,光是處理這些素材就已經有難度了。
另外還有這個橫屏豎屏的問題。我們最開始時剪過一個不到10分鐘的版本,當時內部審片的時候大家就覺得雖然看著挺新鮮,但看完什么都沒記住,就只見那五個屏一直在閃,確實挺實驗也特別花,切分的時間點也不一樣。但放一個屏肯定也是不行的,總不能把一個豎屏往一個橫屏上放90分鐘吧?既然選擇要在橫屏的大銀幕上放,就肯定需要多屏,并且屏與屏之間得有互動。那什么時候互動?是三屏互動還是五屏互動?是四屏還是兩屏?這個其實是我們當時面臨的最大的一個困難。我們嘗試過《我不是潘金蓮》(馮小剛,2016)里面的那種圓形的,四分屏的,異形的。但最終我們還是決定用五分屏,和剛剛胡老師說的有一點挺相關,因為我們希望純粹地呈現他們視頻本身的樣子。在刷了足夠多的視頻之后,我們其實希望把自己藏到幕后來。而5個9:16的豎屏差不多剛好可以鋪滿一個21:9的橫屏,這種方案對原始素材的變動最小。我覺得這個片子的形式已經足夠吸引人了,不要讓它的形式大于內容更多,只需要把核心內容呈現出來就好。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困難。比如我有一個朋友跟我說,別人片子的復雜程度都按時間線的長度算,你這個是按高度算。光語音就有5層,另外還有音樂。圖像也有好幾層,你看著是只有五屏,但其實它底下還有一層航拍,再加上字幕、包裝,最后高到變成了一個方形的工程,挺有意思。
觀眾:請問老師們,你們在選取原始素材的時候是否會擔心快手平臺的內容過于獵奇?或者說是不是會容易讓觀眾感到無聊等等。如果有過這樣的想法的話,是如何平衡的?
王靜:我們剛開始刷快手的時候,映入眼簾的大部分都是這些奇觀性很強的內容素材。所以我們中間也曾有過一個方案,具有魔幻現實主義色彩的,但這個方案沒兩天就被大部分的主創否定了,因為清影工作室從2006年開始就專注紀實影像,從最開始的紀錄片,到后來的紀錄電影,我們的價值取向一直是用影視人類學的視角呈現普通人的生活。《煙火人家》雖然看起來和清影過去做的影片大不相同,但是內核還是貫徹著呈現普通人日常生活,讓勞動者的勞動被看見的價值取向。
我們在快手上可以看到兩類視頻。一類就是光怪陸離的,這一類的流量顯見的多。還有一類就是我們更覺得珍貴的——那些普通人記錄自己生活的視頻,這一類視頻大量存在,但流量很少。快手在2018年的推流邏輯之一就是希望普通人的生活能夠被看見,平臺會給普通人記錄自己生活的、相對缺乏戲劇性和奇觀性的視頻做一點點小小的推流,讓它們能夠被人看見,以鼓勵更多的人在這個平臺上記錄自己的日常。所以這兩種視頻是同時存在的。
我們不否認奇觀性視頻的價值,它也是當今媒介社會現實的一部分。這些光怪陸離的視頻代表了當今中國的一種文化心態,這部分內容我們也希望有一定的呈現,但肯定不是這個影片的主體。我們會去把這部分內容和我們所想要描述的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結合起來。目前的這個比例也代表了我們的創作選擇。就像剛剛胡老師提到的,這些看似被影像遮蔽的內容其實反映的才是中國的大多數。比如大家看到的紡織女工、卡車司機等,這些普羅大眾的媒介形象在其他平臺似乎很少見到。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存在,他們反而才是中國95%的人。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會有一個平衡。我們認為奪人眼球的短視頻也是現實的一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把這類視頻和我們所期待的那種紀實感在這個作品里面做一個融合。
謝福坤:我也簡單的補充兩句。大家看到這個片子用了很多的“神曲”。很多人可能會覺得神曲聽著稍微有點低俗,有點駕馭不住紀錄片,但它放在這個片子里反而合適。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展現的就是短視頻,我們不希望把它加工成另一種樣式,搞得很感人、很煽情或者怎么樣。因為你可能換一種音樂,就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所以我們堅持插一部分神曲在里面,就是希望能保留那種刷短視頻的感覺。
觀眾: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想到了另外一部電影叫《浮生一日》(Kevin Macdonald,2011),那部電影是按照時間的順序,展示了世界各地的人間百態。相比之下《煙火人間》的敘事邏輯很割裂、很跳躍。想請問各位老師怎么看待《煙火人間》跟我們一般的商業電影在表達技巧、敘事邏輯上的差異?
胡偉:我還是會把這兩者區分開來,《浮生一日》對我來說是一個電影,而《煙火人間》是有著重要文獻意義和無限價值的當代影像作品。《煙火人間》所篩選出的影像,其實是對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記錄。它不是為了完成一個一天或者四季的流轉,也不是為一件具體的事情的敘事而服務。這個片子對影像的選擇和使用消解了影像本身,因此它的文獻性更重要。今天所謂的一些神曲在幾年之后都會從你的記憶中消失,會被新的神曲取代。但這些神曲都記錄了它所誕生的那個時代。你可能會聽到一些有些年頭的“神曲”,覺得它們已經過時了,但那就對了,因為它們記錄的是曾經那個時代。
回到紀錄片本身,其實許多知名的紀錄片作者,像王冰,他們更多的是在扮演一個見證者,一個時代的在場者。這反而成為紀錄片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煙火人間》這種對影像的二次創作,先拉開了同原始影像之間的時間和距離,再去對原始影像做出回訪挖掘。所以它創作出來的東西更傾向于考古,而不僅僅是復刻。所以我認為從價值角度上來看《浮生一日》和《煙火人間》完全不是一類作品。當然從敘事層面上,《浮生一日》會更加完整,《煙火人間》可能會讓人感覺有些割裂,有些跳躍。但我覺得后者沒有必要去模仿那種線性的敘事,它的跳躍恰恰是它的價值所在。
謝福坤:我們在做這個片子之前就做了一些調研,包括《浮生一日》,還有剛剛胡老師說的《蜻蜓之眼》。徐冰老師那個收取了很多監控素材,但我也覺得那個片子更像是電影,它是通過旁白去串聯故事。《浮生一日》和《煙火人間》的區別之一是它的那些素材是應該向用戶收集的,而我們這個其實是從互聯網上扒下來的。也就是說用戶分享了這些素材之后,他意識不到他的素材將來會被放到一個電影里。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覺得我們的工作量肯定會更大一點,狀態也更真實。至于你剛剛說的割裂感,我覺得這是很多人看完之后都會有的感覺,因為它沒有一個主線串起來。
我們之前其實有過一個版本,就是把主要的幾個主人公他們這幾年的素材有機串聯起來,那種敘事策略其實能講出的故事會相對完整一些。比如說大橙子那個人,我們開始拍的時候她還是個剛剛跑船的小姑娘,到我們結束拍攝的時候,她剛好結婚,正要去她老公的那條船上,還有很多博主是像她這樣長線記錄自己生活的。我們從中挑三四個主人公,然后用這些主人公的素材串聯起我們的短視頻電影。但我們會覺得這樣做有一點可惜,很顯然這幾個人的故事并不能代表大部分中國人。所以我們還是決定多加一些進去,比如奇裝異服的展示,比如吃播。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盡量把它做成一個大雜燴。割裂就割裂了,我們就放棄這部分。如果為了敘事完整只放那么幾個人的素材實在是太可惜。
王靜:《浮生一日》很出名,它是眾創式影片的經典案例。還有像胡老師剛提到的《蜻蜓之眼》,這些我們都學習過。對于我個人來說,紀錄片是一種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我們做任何紀錄片其實都是要去處理作者和現實之間的關系。比如說作者的成分體現多少?現實又體現多少?是利用現實去呈現自己?還是盡可能地、完整地去呈現現實?這些其實都是流動的。《浮生一日》《蜻蜓之眼》和《煙火人間》這三部作品在這個維度上只是程度的不同。《蜻蜓之眼》雖然畫面是監控,但它敘事靠的是旁白。它講的故事其實和監控內容本身相關較弱,更多的是用這些素材拼貼出徐冰老師內心想要表達的一個隱喻。現實對于影片來說更多的是素材,也許替換成另外一種介質也能夠完成。因此《蜻蜓之眼》就是一個作者性很強的影片。《浮生一日》和《煙火人間》的核心區別是前者的素材是征集的。《浮生一日》以“愛與恐懼”為主題,向全世界的YouTube用戶征集他們對于這個主題想要談論的內容以及他們7月24日這一天的日常生活。它從一開始就告訴用戶未來有一天會有一個關于愛與恐懼、關于這一天日常生活的影像呈現。所以它是一個用戶和導演意志的合謀——導演已經設定好了結構,用戶也已經知道了他要用的結構。因此《浮生一日》會有一個預設,制作過程更有目的性,導演的引領性也會更強。《煙火人間》和前面這兩部電影的不同在于,它是一部從素材庫里生長出來的電影。雖然我們會在制作過程當中增加一些作者性的結構呈現,但是這個作者性是從現實本身提煉出來的。具體來說,我們是從快手這個素材庫里查閱了素材,在對素材進行調研后,把素材提煉成奇觀性和日常性這兩個部分,再對它們去進行藝術化處理。所以《煙火人間》是“現實先行,作者后跟”這樣一種創作邏輯和價值選擇。
胡偉:我認為《浮生一日》和《煙火人間》的區別就是《煙火人間》的當代性。所謂當代性就體現在它這種利用現成品的創作方式。我打個簡單的比方。一個雕塑家如果想捏一個牛出來,他會先構思牛的形象,再去想要用什么材料,石膏還是大理石。他是先有一個預設的形象在腦子里的。這是一種傳統的創作方式。而這種利用現成品的創作方式是我用三天時間上街上去撿垃圾,撿完了以后我根據我撿來的這些東西思考我能做出什么東西。這恰恰是今天很多當代藝術的創作方式,許多裝置、雕塑都是這樣來做的,所以我說這樣的一個影像很難得。
觀眾:今天想借此機會請教謝老師,您平常是如何平衡剪輯節奏和音樂的關系?
謝福坤:之前有一個老師跟我說過一個觀點,我覺得很受用,他說你不要覺得剪得不好就拿音樂來湊,很多人是這樣的。但是真正好的剪輯,是在整個片子不放音樂的情況下,故事的節奏照樣能讓人完整地看下去,音樂是錦上添花的一件事。當我們覺得這一塊感情到位了,如果再有一點音樂能讓這個感情更好地抒發,在這種情況下再去把音樂加進去。我們做其他的那種媒體紀錄片的時候,音樂是很晚才加上去的,之前都只是做粗剪。剪到最后的時候我們才會去考慮,某一段我們應該加點緊張的音樂或者別的什么樣的音樂,這一段就會更好,可能本來這一段能打60分,音樂加上去感覺可以再往上加10-15分,這時候我們才加音樂。剪輯的時候要把加音樂的工作往后放,先讓這個故事能看得進去,能吸引人,最后你再挑什么樣音樂。當然如果是像一些預告片或者宣傳片的話,這種你是需要先找一個音樂,然后再把素材按照音樂節奏點拼上去,這樣效率可能會高一點。但如果你是剪一個稍微長一點的紀錄片,我建議音樂都放到最后再加。
觀眾:想請問制片老師,《煙火人間》這種合作式的紀錄片制作形式,它未來會有怎樣的商業化模式探索?
王靜:我們在發起這個項目的時候就是以對于一個學術問題的實踐回應作為目標,確實沒有太多地考慮商業性。《煙火人間》雖然看著好像不怎么花錢,但其實還是有成本的,比如所有聲音的重新制作、歌曲版權購買、短視頻用戶逐個溝通、手機素材重新修復、片尾曲演繹等,這些都還是會涉及不少費用。
這個影片年初已經上映,從商業上來說,它并不是一個成功的嘗試。但如果單純追求商業回報的話,大家肯定不會去投資這樣一個實驗性和挑戰性非常強的項目,大部分出品方一開始也無法想象短視頻如何能剪成大電影。
既然如此,那么我們為什么要去做這件事情呢?因為我們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在這個時代,有很多短視頻大家一閃而過。你可能看到時會會心一笑,因為這是你在當時文化心態之下可能會被觸動到的東西,但是它也必然會淹沒在時間的長河里。我們怎么才能夠讓這些很重要的內容、一閃而過的情緒、有當代性價值的素材在100年之后依然能夠被看見?結論是我們需要一部《煙火人間》這樣的長紀錄片作品把它固定下來。我們的創作目的是想讓百年后的人類看到百年前的中國人在創作什么樣的影像,在如何生活。我們帶著學術探討的精神和一定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去創作,也得到了一批有情懷的出品方的支持,我們希望未來有機會再去復刻這樣的嘗試,當然也希望有理想的資本來支持和鼓勵我們去做下一部。說不定它能做成編年體:2020年,2030年,2040年……每十年去做一部,等到未來回望,會發現不同時代人的生活和影像發生的變化。
觀眾:想請問后期老師,基于這部片子而言,是否能有更好的方式去展示橫屏和豎屏在視覺感官和美學效果呈現上的差異性?
謝福坤:其實片子放映之后我也反思過,這個分屏的形式是不是呈現這個片子的最好方式?我感覺不是。如果你問我會給這個剪輯打幾分,我打60分。我覺得能及格,它能讓一些對它感興趣的人能坐下來看到結束,但也僅限于此了。形式上還是有很多問題。
比如影片上映前我們都是去電影資料館做測試。資料館是一個比較正規的影院,我們坐在正中間看就感覺剛剛好。但是后來我去做第一次公映的映后嘉賓時,我們是在北京的一個小影院里。我當時坐在第一排的邊上,是斜著看的,所以我看電影的時候需要晃頭我才能看到影片的邊邊。再加上那個影院的屏幕離觀眾席很近,那個短視頻的畫面就在眼跟前閃來閃去,沒一會兒就暈了。我之前完全沒有考慮過這種形式會帶來這樣的問題。即便我知道下一個鏡頭出現的是什么,我依然看得很暈。那一場的放映效果不好,至少前排很不好。當時我還和觀眾說大家可以盡量往后坐,因為這樣形式的一個片子,如果你離屏幕太近的話,多少還是會有眩暈感。我覺得這些是我在最開始的時候沒有想好的地方。如果我們還有第二部的話,這些因素要考慮進來。
再比如說有些人是在電視上或者筆記本上看,而我們其實有很多細節是在筆記本這樣的一個小屏幕上不太容易被看到的。比如那個拿一根吸管喝可樂的鏡頭。如果你沒看到那吸管,那這個鏡頭就沒意義了。再比如那個在數九寒天里穿著羽絨服的紡織女工,她其實是光著腿。因為外面很冷,廠房里很熱,她們頻繁出入廠房只來得及套一個羽絨服就往外走。我們希望這些細節能夠在大屏幕上被大家看到,但如果是在相對較小的屏幕的話就不太行了。怎么能把這些東西放進去,是不是可以適當放大一下影片里的一些細節?這也是未來可以考慮的事情。
尹一伊:就我個人而言,每次看完《煙火人間》都還是會很感動。我是做文化研究的,我覺得這部影片除了文獻的意義之外,它在文化方面還存在一種特別的觀照和關懷,它讓很多大家習以為常的東西被提問、被看見。從這個方面來說,我覺得影片在人文關懷方面的意義可能遠大于它的商業價值或形式探索。非常感動能夠在電影院里看到這樣一部作品,也特別感謝各位老師今天帶來的精彩對談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