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憲法大綱》與清帝退位:邁向現代國家的關鍵

《涵變:清末民初的國家建構與現代困境(1895-1917)》
馬勇 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24年10月
1908年,清廷按計劃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僅就文本看,中國將成為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憲政國家,當然是模仿了日本,皇權仍然是至上的,但是輔助皇權的合法機構——議會將要出現,獨立于政府之外,獨立運作。議員將從一半選舉,一半欽定逐步過渡到全部競選,不再欽定,不再有特殊議員。這需要一個過程,但顯然方向是對的,是向現代國家邁出最關鍵的一步,是兩千年帝制的重要轉型。
至于政府,欽定憲法規定向議會負責,享有完整的行政事務處分權,但必須是一個“責任政府”,是一個可以對其行政進行追責的政府。這一點非常重要。
皇帝是國家主權的象征,擁有宣布戰爭、結束戰爭等重大權力。但皇帝實際上只是象征,不再承擔專制體制中事必躬親、事必欽定的角色。皇帝的決定主要來源于議會的辯論,不再是過去內外大臣的奏疏,更不是他們的密折;不是秘密政治,而是透明、陽光,可辯駁、可爭論的票決。
按照欽定憲法,中國除了重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于皇權之下,還有憲政國家普遍擁有的所謂“第四權力”,即開放的媒體。也是這一年,清廷公布了《大清報律》,從制度上規定了新聞出版的自由與限制。什么東西可以自由報道,什么東西必須審查,批準或不批準,都有明確的文本。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新聞出版作為國民合法而不可剝奪的權利,同時也負有對國家利益必須承擔的義務。過去的研究對這個報律持完全的否定態度,其實仔細研究憲政國家體制,不存在完全放任的新聞自由。國家利益,比如軍事情報、軍隊調動,大約現代國家也不會允許毫無約束地報道。至于君主立憲體制中的皇室私密,似乎也不是毫無限制地八卦,畢竟皇室最主要的功能是國民行為示范,荒誕無稽的八卦不僅傷害皇室,而且有害于社會。仔細研讀《大清報律》的放開與限制內容,不以先入為主的偏見自蔽蔽人,我們應該承認這是中國歷史的巨大進步,也是現代國家重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環節。
1908年欽定憲法的公布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這個文件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不論有多少缺陷,都標志著中國向完整的憲政國家邁出了關鍵的不可逆的一步。然而,中國歷史的遺憾總在于突發性事件每每扭轉歷史的方向,或讓順暢的歷史進程陷入一段彎路。
欽定憲法頒布不久,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在不到12小時內相繼去世。這是歷史上不曾見的巧合,因而演繹出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是不管怎么講,兩宮突然去世讓政治變革受到很大的破壞,接替他們的“三人組”是光緒帝的未亡人隆裕太后、光緒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以及載灃幾歲的兒子宣統小皇帝。這個班底從年齡上說,大于1861年慈禧太后、恭親王奕、同治皇帝之三人組,也大于19世紀70年代慈禧太后、恭親王奕或醇親王奕譞、光緒帝三人組。慈禧太后、恭親王奕均屬于強勢領導人,因而他們建構的體制屬于威權體制。攝政王載灃、隆裕太后屬于“弱勢領導人”,缺少大時代政治人物所應具備的決斷力,或者說鐵石心腸,因而讓清帝國已經鋪就的康莊大道在此后幾年被完全廢棄。
攝政王載灃是晚清第一個出國考察過的王爺,到過德國等西歐諸國,知道憲政的意義,也從心里認同慈禧太后、光緒帝預備立憲的選擇,所以在他接班主持朝政時,蕭規曹隨,并沒有影響預備立憲的進程。
問題出在稍后。我們知道,甲午戰爭之后,朝鮮不再是中國的藩屬,兩國關系也降到了冰點。而日本以朝鮮的保護者身份與中國交戰后,也延續先前20年的慣性,與朝鮮的關系日趨緊密。日俄戰爭爆發,朝鮮被綁上日本的戰車,同意日本可以臨時征用朝鮮的資源和土地。
戰后,日朝關系更趨密切,朝鮮實際上成為日本的保護國。1905年,日朝簽署協約,朝鮮將外交權交給日本代為行使,日本成為朝鮮新的宗主。日本在朝鮮設置了統監等機構,朝鮮在實際上成為日本的殖民地。1907年,日朝再簽新約,日本殖民機構統監府有責任掌握朝鮮內政權,朝鮮內政外交均由日本人代理。在中國人的觀察里,朝鮮實際上就是亡國了。
“日朝合邦”本來是日朝之間的事情,但對此時的中國人卻具有無比強烈的刺激并突然產生亡國意識。為防止亡國,中國知識人、中產階級即那些剛剛出現的資產階級憂心忡忡,他們期待清廷加速變革,不要再遵守慈禧太后、光緒帝他們宣布的九年立憲規劃,即刻立憲,明年立憲。
預備立憲是“有計劃的政治”,是仿照日本立憲進程的安排。日本1868年明治維新,1881年宣布憲政,1889年開國會。日本從宣布立憲到開國會,實際過渡時間為八年。但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其實就是以憲政為訴求,以西方先發國家政治架構為自己的摹本。而中國的情形則不然。從立憲進程看,九年預備實際上并不充分,現在如果再縮短,很可能欲速則不達,衍生出許多新的問題。于是在民族資本家階級策動的國會請愿運動爆發之初,攝政王載灃并沒有理會這些請求,強調必須遵照慈禧太后、光緒帝制定的計劃辦。
攝政王不破壞既定的政治日程是對的。但民族資產階級看到了朝鮮被殖民之初的情形不明所以,出于亡國本能的考慮,無法接受攝政王給出的理由。而且,還有一個背景是,《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皇帝擁有至上的權利,這條規定當年是為光緒帝量身定做的,那時的光緒帝年方38歲,屬于有思想有理想的英明君主。現在,換了一個幾歲的娃娃,這個最高權力的行使當然就不讓這批資本家放心。這也是他們堅持呼吁朝廷提前立憲的一個不便明說的理由。
中國資本家階級的堅持終于打動了攝政王。1910年秋,國會請愿團策動第三次請愿活動,動員了國內外各種力量向朝廷施壓。有請愿者拔刀剖腹以明心跡,全國各大中心城市幾乎都有類似活動,一些省區的督撫也被請愿運動感染,聯名上書朝廷建議立即組織內閣,召開國會,盡快步入憲政門檻。
立憲黨人和各省政治領導人的呼吁引起了朝廷的警覺。1910年11月4日,攝政王宣布將原定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大致確定于宣統五年(1913年)召集國會。
攝政王的答應顯然是草率的,由此打開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潘多拉魔盒。江浙等經濟發達、政治變革比較穩健地區的立憲黨人尊重朝廷的穩健風格,但更多的請愿團體則不理解朝廷,反而認為朝廷的讓步是膽怯,主張乘勝追擊,逼迫清廷加快變革,要求速開國會,不必再等三年。激進主義在政治變革關鍵時刻總是容易贏得人們的追慕,但其結果并不必然美好,中外同理,古今如是。
在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時,朝野認為九年預備立憲是一個穩妥的判斷,九年走完日本20多年走過的路,走完英國、法國走了幾百年的路,這已經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現在因為外交危機加大,加快立憲進程,實際上就把步履打亂了,結果引起此后百余年的動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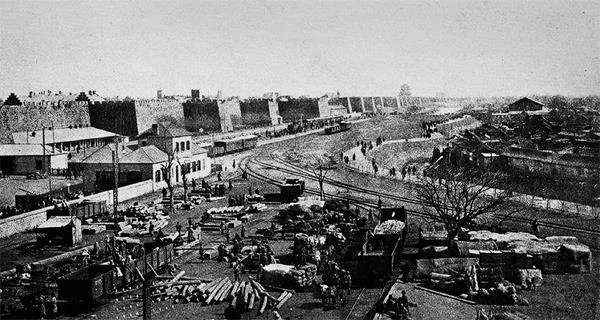
根據調整后的日程,清廷于1911年5月8日成立第一屆責任內閣。這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也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夢寐以求的理想。責任內閣成立,軍機處不廢而廢;內閣總理大臣、協理大臣,以及各部部長,均不再強調滿漢身份,也不再設置滿大臣、漢大臣,每部一大臣,滿漢蒙回諸族一視同仁,量才而用。這個原則當然不錯,然而落實到具體名單則出了問題。慶親王奕劻出任第一屆責任內閣總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為協理大臣,梁敦彥、盛宣懷等十人分任各部尚書。這是巨大進步,不僅優化了行政機構,而且不再以族群身份為用人標準。然而,清廷想不到的是,細心的觀察家發現,十三個閣僚中,竟有九個皇族或滿洲貴族。很顯然,如此人事安排,似乎還不如改革前的滿漢均分,一比一。這是后來引發爭議并最終導致清帝國退出實體統治的原因之一。
導致清帝國結束的第二個原因是新內閣精心準備的新政策“鐵路干線國有化”方案。
中國的鐵路建設在早期被人為耽擱,至甲午戰后,方才因開放外國資本進入各通商口岸而開始鐵路建設。不到十年,基本路網大致完成。如此快速的建設主要就是利用外國資本,基本上與民族資本無緣。
1903年,民族資本看到了鐵路帶來的巨大利潤,因而要求朝廷向民間開放路權。朝廷于是允許民族資本進入鐵路。但不久發現民族資本的進入讓鐵路建設出現標準不統一、融資不規范的問題,不僅有經濟風險,而且弄不好會有巨大的社會風險、政治風險。事實上,清帝國的終結就從這項舉措開始。
為防范風險,清政府進行了審慎的研究,于第一屆責任內閣宣布成立第二天,鄭重宣布“鐵路干線國有化”新政策。這個政策一開始引起巨大震蕩,稍后經過更細致的政策解讀、疏導,大部分省份接受了這個安排。但到了四川,卻遇到巨大障礙,最終將鐵路干線國有化演變為壓死清帝國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川的情形太特殊了,“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出川的路確實不那么容易修建,高山峻嶺,長江大河,技術難度不用說了,而經濟上,出川的路僅僅憑借四川人的融資顯然也是杯水車薪。川漢鐵路總公司在鐵路建設大干快上的氛圍中也融了一大筆資金,只是這筆資金修路顯然不夠,于是拿去保值增值炒股票去了。
但當時的國際市場并不穩定,川漢鐵路公司保值增值的愿望并沒有實現,相反,待清廷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公布,川漢鐵路在股票市場損失慘重,無法接受清廷國有化的要求,于是發動“保路運動”,將清政府的鐵路干線國有化政策解讀成國進民退,與民爭利。于是有四川總督府門前流血事件,于是有湖北新軍入川,于是有武昌空虛,于是湖北新軍乘虛起事,引發我們通常所說的武昌起義、辛亥革命。
武昌新軍的政治訴求極為簡單,就是稍后黎元洪在與袁世凱代表的談判中所期待的,清廷重回憲政改革路徑。然而這一點對于清廷主政者來說似乎又太難了,于是僵持不下。直至十四省宣布獨立,清廷仍然不愿讓步。于是,清帝國過去十年集中國力財力訓練的中央軍實在看不下去了,灤洲兵諫,終于沖開了一個缺口,宣統小皇帝下詔罪己,攝政王載灃退回藩邸,清代政治掀開新的一頁。
重臣袁世凱在光緒帝、慈禧太后去世后不久就退出政治舞臺,回籍養疴。武昌起義后,即受命出山,收拾殘局。稍后,接替慶親王奕劻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全面負責與南方諸省義軍的交涉,答應各省義軍和灤洲兵諫中央軍的要求,重回憲政軌道。清政府于是頒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
然而稍后的南北談判并不順利,清廷內部的滿洲貴族強硬派并不愿意如此輕易丟掉兩百多年所享有的特權,重回憲政軌道,于是南方革命黨和立憲派聯合組建了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推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逼清廷讓步。
孫中山、南京臨時政府的加入,讓問題的性質悄然改變:重回君憲改革路徑、構建一個全新的美國式共和國家,成為兩個并重的政治選擇。
我們知道,十年前清帝國剛剛開始新政時,梁啟超就給出了一個清晰的路徑選擇:君主專制必須改革,美國式的共和則不可取,中國的唯一前途在于君主立憲。這個選擇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十年中國人的基本共識。現在,清帝國內部反對憲政改革的力量越來越多,于是在君主專制還是共和的選擇上,留給中國人的空間實在不多了。
而且,由于列強在武昌起義發生即宣布局外中立,至此幾個月過去了,列強在華利益因為中立而受損,他們似乎也有了不滿的意思。1912年1月20日,南方革命黨、立憲黨人策劃了一個清帝退位的方案,給出了一個極為豐厚的退位優待條件,立憲黨人、袁世凱這些老臣不愿太虧待舊主之孤兒寡母。但這個優待條件實在也害了清帝國。隆裕太后面對滿洲貴族“戰則不行和則不肯”的現實,依然選擇接受這個優待條件,不是沒有原因的。
各方面的變量都在促動中國發生一次巨大的變化。1月22日,英國公使朱爾典會同法俄日公使發布聲明,贊成清帝退位,甚至有為退位協議背書的意思。1月26日,段祺瑞和那些新軍將領47人聯名通電,呼吁朝廷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從根本上化解持續幾個月的政治危機。在各方面壓力的促動下,清廷在2月2日御前會議上決定退位。一個兩百多年的帝國以和平的方式退出中國政治舞臺。這是中國歷史的榮光,是中國的“光榮革命”。
(本文摘自《涵變:清末民初的國家建構與現代困境(1895-1917)》;編輯:許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