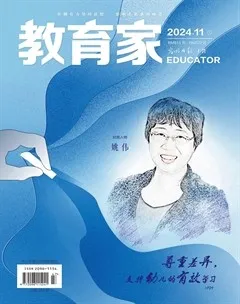戶外游戲,亟待一場科學性與系統性升級

《幼兒園保育教育質量評估指南》指出,幼兒園制定并實施與幼兒身體發展相適應的體格鍛煉計劃,保證每天戶外活動時間不少于2小時,體育活動時間不少于1小時。在“以游戲為基本活動”的共識下,戶外游戲在幼兒園中“蓬勃生長”。然而,在一片欣欣向榮的環境中,戶外游戲仍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
環境受限制,材料受制約。
充足的活動空間是開展戶外游戲的重要保障,但一些幼兒園的活動空間有限,無法滿足幼兒戶外游戲的需求。重慶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教授邵小佩通過調研發現,這一情況在2010年之后新建的城市幼兒園中較為明顯,在場地制約之下,一些幼兒園只能盡可能地利用園中零散的空間組織戶外游戲,限制了開展游戲的種類和參與游戲的幼兒人數,對戶外游戲的質量造成影響。有的幼兒園借用了園外閑置的空地,如何利用這塊空地卻讓幼兒園犯了難:在沒有所有權的情況下建設大量設施,得不償失;寒暑假后還需對其維護整理,也是一筆不小的費用。
空間不足是直觀的難題,而擁有廣闊的游戲空間也不等于高枕無憂。北京市大興區第一幼兒園占地面積逾一萬平方米,戶外游戲大多在園中的操場上進行。對園長白淑新來說,如何分割操場,保證每一個幼兒能夠在適宜的范圍內活動,同時不會互相干擾或引發安全問題,曾讓她頗為困擾。起初,她安排教師將玩具柜放置在操場墻邊,幼兒可以結合材料開展自主游戲。但在游戲時,幼兒取放材料的過程較為混亂,對其他幼兒的游戲產生了不良影響。針對這一情況,白淑新組織了多場教研活動,就確定游戲區域、材料擺放位置等問題與教師展開討論,嘗試將問題合理解決,多次的實驗和探討投入了她和教師的大量心血。
為了讓幼兒擁有更豐富的游戲空間和資源,一些幼兒園將目光放至園外,利用博物館、公園等社會資源開展戶外活動。邵小佩指出,除了潛在的安全風險外,將園外的資源融入游戲實現教育目標,對教師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教師需要設計出既有教育意義,又有趣味的游戲,在干擾因素較多的環境中,不斷調整引導幼兒行為的策略。這極大地挑戰著教師的專業能力。”
戶外環境建設要與時俱進,不斷適應幼兒發展的新需要,但優化環境并不容易。曾經,白淑新到南方參訪幼兒園時,對其環境十分欣賞:“一些幼兒園擁有許多供幼兒玩耍的山坡、草地、滑道,還有的幼兒園擁有一大片水域,幼兒可以在其中游戲。”她有過改造園所的想法,也深知不能照搬照抄,但由于建園時間較早,操場下已經埋藏了許多管線設備,若要改變部分環境,必須考慮這些設備對施工的制約,貿然動工也會影響師幼的正常生活安排。如何不斷滿足幼兒對環境的需要,白淑新仍在進一步探索。
種類豐富、數量充足的游戲材料是戶外游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為了引起幼兒的游戲興趣,幼兒園需要及時更換材料。由于受到經費的限制,部分幼兒園在更換材料時無法足量購入,只能采取分批次投放的方式,先滿足一部分幼兒的興趣和需要,日后再逐步補足。但在輪轉的過程中,適合上一個班級幼兒的材料,不一定適合下一個班級的幼兒。當新材料出現時,教師對于新材料的了解需要時間,對新材料的玩法也有待發掘,在指導幼兒時,難免影響幼兒對新材料的使用。
觀察待改進,介入難把握。
在戶外游戲中,教師是幼兒的觀察者、支持者。通過對幼兒游戲的觀察,教師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幼兒,引導幼兒游戲走向深入。但戶外環境更加多變,為游戲帶來各種偶然因素和突發狀況,需要教師隨機應變。在廣東省深圳市首地幼教集團教師余麗珍看來,如何把握觀察的重點,仍是一個難題:“比如兩名幼兒在游戲中結為伙伴,但突然發生了矛盾,最后他們和好,共同完成了作品。在這一過程中,教師需要重點觀察幼兒的哪些方面?”有時,教師會忽視幼兒短暫的探索行為。“比如幼兒發現了一只昆蟲,短暫地觀察后便離開了,教師可能會把這一過程當作幼兒偶然的行為,忽視了幼兒行為背后的原因。”邵小佩解釋道。此外,戶外游戲中幼兒的非主動社交行為同樣易被教師忽略。教師往往會更關注主動發起游戲、在游戲中充當主導者角色的幼兒,疏忽了對被動參與游戲的幼兒的心理狀態和需求的關注。
觀察的缺位會讓教師難以捕捉戶外游戲的價值點,無法準確解讀幼兒的想法和需求,在幼兒向最近發展區邁進時,無法提供有效的支持。“幼兒在某個器械上的獨特玩法,有可能暗示著他們在創新思維方面有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幼兒在游戲中看似無意義的行為,有可能是一種探索的嘗試。”邵小佩說,“教師若不能捕捉到這些閃光的瞬間,就無法在幼兒現有的水平上繼續引導他們。”
在開展戶外游戲時,教師需要做到“最大程度的放手,最低程度的介入”,但幼兒在游戲中的發展水平呈現出動態變化的趨勢,且分散在戶外環境中,這讓教師愈發難以把握放手和介入的時機。在余麗珍的記憶里,一次組隊拍球接力的游戲中,一名幼兒因等待時間過長,游戲興趣減退。余麗珍通過語言引導,營造了熱烈的團隊氛圍,重新吸引了這名幼兒的興趣。在教研會上,領導稱贊她把握住了介入的時機,給予了幼兒恰當的支持。之后,在幼兒自主游戲時,兩名大班幼兒發生了爭吵,其中一名幼兒情緒激動,余麗珍擔心會發生肢體沖突,于是趕忙制止。之后的教研中,領導給出不同的看法,指出大班幼兒解決問題的能力較強,作為教師應當再耐心些,多給予幼兒一些時間。介入的不同結果讓余麗珍在此后變得謹慎,更多了一份猶疑,“此時介入是否合適呢?”除此之外,在一些具體的場景中,余麗珍仍然感到糾結:“當幼兒不理解游戲規則時,教師是應該向幼兒說明規則,還是讓其在與同伴的互動中理解規則?當幼兒在游戲中產生負面情緒時,教師是應該幫助他們調整情緒,還是應該給予幼兒更多自我調整的時間?”
如果說介入方面的困難是可以被明顯感知的,那么放手方面的問題則更加隱秘。在白淑新看來,把握放手的尺度是一個難點:尺度過松會導致散漫無目的,表現為失去對幼兒發展目標的關注,忽視幼兒個體差異;尺度過緊又導致隱秘的高控,“比如在角色扮演的游戲中,教師過度糾正角色的行為,會限制幼兒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或在搭建游戲中,教師對使用材料的方式做了過多的示范,會讓幼兒對教師的指導產生依賴”。
不恰當的放手和介入,都會阻礙幼兒經驗的深化。白淑新發現,當幼兒提出有挑戰的玩法時,部分教師出于對幼兒安全的考慮會加以否定。“實際上,幼兒有著很強的保護自我意識,在完成有挑戰的動作時,幼兒是十分小心謹慎的,并主動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教師不應該一味否定幼兒,而是在可控的環境下,給予幼兒嘗試的機會。”白淑新道出了她的思考。同時,嚴格的游戲時間阻礙著幼兒經驗的深化。何時熱身、何時整理,游戲過程中每一個階段的時間都有著明確的規定。當游戲時間快要結束時,一些教師會頻繁提醒幼兒,導致游戲匆匆結束或戛然而止,不但幼兒沒有形成經驗的閉環,而且教師也無法觀察到幼兒游戲完整的狀態。
為了更好地開展戶外游戲,幼兒園竭盡所能地為幼兒提供更優質的資源。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微觀視角下,要徹底解決戶外游戲中存在的癥結,幼兒園所要付出的努力似乎永遠沒有盡頭。怎樣突破困局,做到標本兼治,使戶外游戲邁上更高的臺階,還需從整體著眼,發起一場科學與系統的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