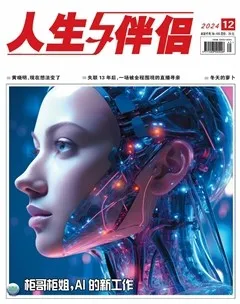皇帝請客你打包,古人也懂光盤行動
提倡節約糧食、主張“光盤行動”,宴席上吃不完的食物要打包帶走,這其實并不是現代人才有的觀念。我國是農業大國,自古以來就以農耕立國,尤其在物品資源并不十分充裕的古代社會,人們更是重視食物、珍惜食物,吃飯時也愛打包帶走。
打包是一種禮儀規范
將剩飯打包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周代的飲食禮儀規范。在匯編春秋戰國時代禮制的《儀禮》一書中,記載了東道主國君宴請他國前來聘問的使臣時要備的公食大夫禮。按照禮制要求,國君應當提前準備好分別盛放不同肉食的七鼎和盛放不同主食的六簋、用于飯前盥洗的盤匜(yí)、宴飲過程中放置食物的俎和豆等,食物除了各種肉食和黍、稷等主食之外,還有醯(xī)醬(類似于今天醋和醬調和而成的調味料)、韭菹(zū)(腌制好的韭菜)、酒水飲品等。宴飲結束后,規定“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也就是說相關負責官員要將宴席上沒有吃完的牛、羊、豬這三牲的肉塊盛裝起來,一起打包送到來使下榻的賓館。如果不將剩飯打包送去,就是本國對于使臣乃至對方國家的失禮,有可能引發國家之間的外交沖突。
除了外交禮儀,在古代儒者心中,打包也是一種日常禮儀的體現。《禮記·雜記下》提到,曾經有人問曾子:“夫既遣而包其余,猶既食而裹其余與?君子既食,則裹其余乎?”認為有德行的君子吃飽之后就不應該再把剩飯打包帶走。曾子回應時征引公食大夫禮中“卷三牲之俎”的禮儀規定,指出國君宴饗之后尚且會將剩飯打包,其他人更不應將打包視作失禮,反而應該認識到“既食而不裹其余”才是不符合禮儀規范的行為。
打包是一種孝心體現
孝老愛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接受宴請時將美味的食物打包帶給家中老人食用是孝心的體現。在《左傳》記載的鄭伯克段于鄢一事中,大夫潁考叔接受鄭莊公宴請時,特意將肉放置在一邊不吃。國君詢問緣故,潁考叔說“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以家中老母沒有吃過國君宴席上的肉為由,懇請鄭莊公允許自己把它打包帶回家。正是這一充滿孝心的行為觸動了鄭莊公,促使他和母親武姜言歸于好。

為家中長輩打包食物,更為有名的要數“二十四孝”中陸績懷橘的故事。據《三國志》所記,陸績六歲時在九江拜見袁術,袁術讓人拿出橘子來招待。陸績在懷里藏了三枚橘子,臨行前拜別袁術,而橘子掉到了地上。袁術問道:“陸郎來做客卻懷揣橘子,這是為什么呢?”陸績跪下回答說:“想要回去送給母親。”于是袁術大為驚奇,認為陸績長大后一定會大有作為。
古代官員赴御宴時,有時會設法悄悄帶回一些肴饌果品,讓家人品嘗。以博通經史著稱的南朝文學家徐孝克生性清素,經常周濟貧困之人,但家中并不富裕。《陳書》記載他:“每侍宴,無所食啖,至席散,當其前膳饈損減。”即每次赴皇家宴會時都不吃什么東西,可散席時面前的食物卻少了。陳宣帝暗中詢問中書舍人管斌是怎么回事,管斌最開始回答不上來,后來留意觀察,見到徐孝克偷偷將食物藏進圍腰的束帶中。管斌當時不理解緣由,后來經過查訪才知,他是將美食拿回去給母親食用,于是如實稟報。陳宣帝感嘆良久,下令:“自今宴享,孝克前饌,并遣將還,以餉其母。”將徐孝克那份食物直接打包讓他帶回去給母親,一時傳為美談。
唐代以后,這種將御宴打包帶回家的大臣逐漸由個例發展成為群體,形成了一股“廷宴余物懷歸”的風氣。明代學者陸深在《金臺紀聞》一書中述及此事時,這樣寫道:
廷宴余物懷歸,起于唐宣宗時。宴百官罷,拜舞遺下果物。怪問,咸曰:“歸獻父母及遺小兒。”上敕太官:今后大宴,文武官結食兩份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余皆聽以帕子懷歸。今此制尚存,然有以懷歸不盡而獲罪者。
意思是說:唐宣宗有次大宴群臣,宴席結束后百官紛紛起身拜謝君恩,忽然掉出來許多果物。唐宣宗不解,詢問緣由,眾人都解釋說準備帶回去給父母和孩子吃。于是唐宣帝下詔今后凡大宴,讓掌管百官之饌的太官專門準備兩份食物讓前來赴宴的文武官員帶給父母食用,再另外賞糕點果子給官員的兒女吃,眾官員自己的食物如果吃不完,也可以用手帕包起來帶走。
這一懷歸余食的制度從唐代一直沿襲下來,明代御筵上吃剩的食物也必須全部打包帶走,否則會被治罪。有時官員被準許“懷歸”的不僅有食物,甚至還有當時使用的餐具。清人孫承澤在《春明夢余錄》中談到明代的情形:“朝廷每賜臣下筵宴,其器皿俱各領回珍貯之,以為傳家祭器。”
這些隨御賜食物一同賜下的器皿能夠成為大臣們的傳家寶物、宗廟祭器,正是出于對“打包”的大力提倡和鼓勵。
打包是一種節儉美德
古代文人士大夫紛紛以自身行動踐行尚儉戒奢,節約食物就要積極將剩飯打包。依據南宋學者胡仔編撰的詩話集《苕溪漁隱叢話》記載,宋神宗在位時大力推行變法,司馬光因政見不合退居洛陽編纂《資治通鑒》,其間與幾位老朋友組織起“真率會”,名字取自率真坦誠之意。與會人員約定:“序齒不序官,為具務簡素,朝夕食不過五味,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真率會”的“會約”講求節儉,對每餐的飯菜、果品數量都有詳細規定,也不允許勸酒,同時還要求“既食而攜其余”,吃剩的食物也要統統打包帶回。如果某位會員違反了這一約定,就要依據約定對他進行處罰。
除了肴饌果品,茶飲也是可以打包的。據《云仙散錄》(又名《云仙雜記》)征引《蠻甌志》記載:“覺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唐代覺林寺僧人志崇飲茶時將茶葉按品第分為三等,最上等的“紫茸香”茶用來供奉神佛,品質中等的“驚雷莢”茶用來招待客人,自己則喝最下等的“萱草帶”。即使是志崇的中等茶也有特別之處,十分珍貴,“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余瀝以歸”。客人們赴他的約會飲茶,臨走時都要用一種稱為油囊的防滲布袋把剩下的茶盛回家去喝,舍不得廢棄。
明末清初的理學家朱用純崇尚勤儉持家,在《朱子家訓》中留下了“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的珍貴教誨,即使是微小的食物和用品,也是來之不易的勞動成果。
勤儉節約、反對浪費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優良作風,在物質生活日漸豐富的今天,更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將“打包”行為中蘊含的道德品質貫徹下去,營造理性消費、簡樸務實的社會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