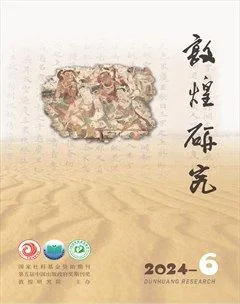敦煌本《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考論




內容摘要:敦煌文書P.2804和P.3040是《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重刊之碑的碑文抄本。原碑旨在紀念天寶元年(742)以來,劉彥偕等人建設藏經閣以及開成三年(838)僧人志明增補寺內大藏經之事。碑文作者志閑擅長撰寫高僧行錄及塔銘,聞名江左。碑文描述了寺中藏經閣的建筑外形和內部結構,為唐代大藏經的收藏提供了珍貴的研究史料。香嚴寺歷史久遠,學僧云集,藏經豐富,尤其是能夠獨立收藏一部大藏經,這在唐代寺院中十分難得。
關鍵詞: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碑;P.2804;P.3040;志閑
中圖分類號:G25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24)06-0076-11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unhuang Version of Records on
Scripture Collections in Xiangyan Temple, Zhuji County,
Yuezhou Prefecture
HE Yif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10)
Abstract:Dunhuang manuscripts P.2804 and P.3040 are both copies of an inscription from a renovated stele entitled Records on Scripture Collections in the Xiangyan Temple, Zhuji County, Yuezhou Prefecture. The original stele was erected to commemo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ripture Library at the Xiangyan Temple, which was accomplished by local figures including Liu Yancheng beginning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Tianbao era of the Tang dynasty (742 CE), as well as to celebrate the completion of a supplementary text to the Tripitaka by the monk Zhiming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Kaicheng era (838 CE). Zhixian, the author of the inscription, was quite accomplished at writing tower inscriptions and records about the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of eminent monks, and was well-known throughout the Jiangzuo region south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tele describes the appearance and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Scripture Library, and thus provides precious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collection of Tripitaka text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The XiangyanTemple commanded a long history and a rich collection of Buddhists scriptures, as well as a thriving community where many monks gathered to study. The fact that the temple was able to gather the Tripitaka independently was very rare among the temples of the Tang dynasty.
Keywords:Zhuji county in Yuezhou Prefecture; Xiangyan Temple; P.2804; P.3040; Zhixia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P.2804比較完整地抄寫了《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以下簡稱為《香嚴寺經藏記》),這是一篇來自浙東越州諸暨香嚴寺的碑文,橫跨東西,原碑早佚,未見著錄,殊為難得。饒宗頤先生從書法價值的角度關注過這一文獻,并認為“可為寫經史及南方經藏源流添一故實”,但遺憾的是,誤以為文獻年代在貞元三年(787)[1]。榮新江先生從寫本樣態的角度觀察,判定此乃碑文,認為此抄本很像是從碑文直接摹錄的[2]。學界對此篇文獻的基本性質已有判斷,然對其進行專題研究管見所及,草此小文,祈教方家。
一 寫本樣態
敦煌保留了兩件《香嚴寺經藏記》抄本,編號為P.2804、P.3040。P.2804由三紙粘連拼接而成,全長80.5厘米,紙寬30.7厘米,首題“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沙門志閑撰,草堂僧守清書”,尾部殘損,存43行,滿行約19字,背面為官文書《宋開寶六年(973)三月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狀》,鈐印[3]{1}。P.3040全長19.5厘米,紙寬15.3厘米,大約是P.2804寬度的一半,尾部殘損,僅存13行,滿行約16字,卷背無字[4]{2}。在相同比例尺下,可以明顯看出二者的大小關系(圖1)。
榮新江先生據首題書式推測P.3040可能抄自P.2804[2]313。進一步詳細對比一些較為特殊的字形,甚至可以看出P.3040的抄寫者在有意模仿P.2804,較為明顯的是“嚴”“沙”“明”“徒”“暫”“牙”“御”“分”“建”“趣”“歸”“拔”“修”“定”等字(圖2)。P.3040的抄寫者文化水平或許不高,但見到一份規整的碑文抄本,有心學習,認真對待。在紙張寶貴的時代,他沒有用廢棄紙張的背面,而是滿懷恭敬地找來新紙,裁剪成正常一紙寬的一半,或許為了做成小卷子,方便攜帶,隨時研學,他耐心地畫上烏絲欄,之后進行模仿抄寫。
二 碑文時代
P.2804所存文字較多,且P.3040當抄自P.2804,遂據P.2804重新釋錄碑文{3}:
1 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沙門志閑撰,草堂僧
2 守清書。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含真空而體寂,鏡妙
3 色以圓明。于一塵中,量出三界。群靈無狀,瞥起情塵;
4 逐浪迷源,背此經體。九十六種異見,■(煜){1}目強生;八萬四千
5 塵勞,狂花亂起。驟生徒而暫出,溺苦海以還沉。如汲
6 井{2}輪,牙為高下。故我釋雄調御,獨運慈光。觀三聚
7 群迷,察萬機差別。三草二木,受潤不同。于一塵中,剖
8 出經卷。分為三藏,建立五乘。囊括四生,牢籠六趣。人乘
9 持三歸十善,下拔泥黎;天乘修八定四禪,上升非想。
10 聲聞乘厭離生死,見諦歸真;獨覺乘欣樂真常,觀
11 緣入道。菩薩乘同塵不染,悲濟生靈。實謂妙啟慈
12 門,巧開方便;怨親同攝,凡圣齊收。五乘既貫于群機,
13 三藏統包于教理。經藏也,廣敷妙義,理契圓常。律
14 藏也,和范{3}毗尼,嚴凈三界。論藏也,研嚴真偽,顯正
15 摧邪。三藏五乘,牙為沙入;猶如寶網,光潔交羅,皆指
16 本心,同歸性海。爰從鹿苑,四諦開摧。降及鷲峰,一
17 乘顯實。五十年內,轉正法輪。故得金文大化于人天,玉
18 ■流輝于沙界。香嚴經藏者,天寶元年檀越主劉
19 彥偕{4}之所建也。錯落貫日,棱層倚山,勢若籠神,捧
20 出金地,當中寶座,八面花龕。玉架以云聯彩鳳,銀函而
21 星布。雖年月寢遠,代不乏賢。上座僧常照、都維那
22 僧孝集、寺主僧慧一,并乃松篁帶雪,秀出庵園。繼踵
23 匡時,彌增壯觀。爰有金仙釋子志明上人,寒玉潔貌,
24 冰壺作心。擬具總持,要探大教。大和六載,因屆香嚴,
25 稽首金仁,獨開寶藏。端居丈室,不舍寸陰。捃摭微
26 言,探尋奧義。手持金字,夜向孤燈。殘卷未終,不覺
27 天曉。一藏寶軸,三年覽終。識浪千花,同歸性海。心珠
28 一顆,頃出衣中。繇是約藏內經題,按開元目錄,欠八百余
29 卷未滿,阿含嗟法寶不圓,因而嘆曰:薝蔔(卜)少花{1},旃檀
30 欠葉;香風不遠,焉能普熏。我須莊嚴,必使圓滿。因
31 立愿力,開信人心。佳以范蠡高蹤,山標諸暨。許君靈跡,
32 巖鎮蕭山。萬古傳芳,清風不墜。山靈地秀,比戶多賢。
33 習東魯儒風,遵{2}西乾釋教。舍潤室金帛,命臨池書
34 人,揮月里兔毫,寫海中龍藏。星霜{3}三變,莊嚴畢功。
35 遂得八百珠圓,十二部足。賈山南面,五色云開。香剎
36 臺頭,一輪月滿。光臨萬戶,分照千門。使百代居人,悉皆回
37 向。可謂內因釋子,外托檀那。二眾同心,五乘教立。若非
38 寔我至德,密契圣心,孰能再闡鴻猷,重昌勝業。貝
39 巖迦葉,結集靈文。蔥嶺摩騰,[
40 傳出千燈。志明上人,還增一崢 {4}[
41 擔如來,其心不二。因旌厥德,永[
42 碑久不存矣,今遂重刊,勒[
43 丁卯歲四月二十八日僧昭義造[
44 □[
據碑文,“志明上人”于文宗大和六年(832)住香嚴寺,用三年時間讀經,又用三年時間校補,至文宗開成三年(838)完成。于是,香嚴寺立碑紀念,碑文由志閑撰寫,但“碑久不存矣”,或許是武宗會昌法難時被毀。“丁卯歲四月二十八日僧昭義造”,知僧人昭義重刊此碑。唐開成三年(838)至宋開寶六年(973)之間共三個丁卯年,大中元年(847)、天祐四年(907)、北宋乾德元年(963),但據碑文所述年號之方式,當屬唐代。宣宗登基恢復佛教,各地寺院多有修寺、補經等活動{5}。碑文未載大中以后之事,故重刊之碑立于大中元年(847)的可能性更大。
要理解寫本的時代背景,其背面書寫的官文書內容也很重要。官文書首書,碑文后抄,法國國家圖書館將碑文視作正面,官文書為背面,故本文因循。P.2804V《宋開寶六年(973)三月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狀》,共有三篇狀文,每狀一紙,書后粘連。落款處鈐右衙都知兵馬使朱印(5.6×5cm){1}。第一篇狀文首略殘,釋文如下:
(前缺)
1 〔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
2" " "右守勳累陳行李[
3" " "臺憧,既捧授已[
4" " "唯將弱植厚□[
5" " "酬恩,況官身[
6" " "之逼迫,須且早回歸路,赴于遣
7" " "差,不是自專,即合察此。謹具狀
8" " "辭,卻乞一字。謹錄狀上。
9" " 牒件狀如前,謹牒。
10" " "開寶六年三月 日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牒{2}。
第二篇狀內容保存完整,釋文如下。
1" 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
2" " "右守勳三曾有狀,一扣
3" " "鈞衡,血淚空垂,肝腸寸斷。蝴蝶之夢,
4" " "夜夜牽心;雁足之書,朝朝役思。昨自
5" " "圣皇差遣,寵陟
6" " "貴州。別鄉土以隔年,每多憶戀。想
7" " "六生之事,富貴貧賤故且一般。其那
8" " "住箔多時,
9" " "州府供給不失。每懷
10" " "感激,慚悚交并。常憂遲滯之僭,恐負
11" " "違功之罪。所已頻申翰墨,察此□端。伏乞
12" " "臺慈,特賜指命。兼具狀申
13" " "辭。謹錄狀上。
14" 牒件狀如前,謹牒。
15" " "開寶六年三月" 日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牒{3}。
第三篇牒文僅存起首,內容可能與第二篇相似。還有P.2985V(2)《宋開寶五年(972)十二月某日右衙都知馬使丁守勳狀》,鈐印位置相同,筆跡相同,當同為丁守勳所書。釋文如下:
1" 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
2" " "右守勳伏蒙
3" " "大王臺造,特垂
4" " "寵喚出臘。謹依
5" " "嚴命祗候訖,謹具狀申
6" " "謝,謹錄狀上。
7" 牒件狀如前,謹牒。
8" " "開寶五年十二月" 日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牒{4}。
此面作廢后,在另一面抄寫諸雜齋文。榮新江先生指出,第三行中的“大王”指曹元忠[乾德二年(964)以后徑稱大王][5],并論及“開寶六年(973)三月,宋朝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乞求早歸,其來沙州已逾年。(P.2804V)”[5]30。丁守勳之狀又見于S.4976,寫狀紙作廢后或被當作包首,粘連于《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之前,背抄《社齋文》。但此件不見紀年,存二月某日,筆跡、鈐印均同。釋文如下:
(前缺)
1" 起居兼申陳
2" 慰。伏惟
3" 照察謹狀。
4" " "二月" 日右衙都知兵馬使丁守〔勳牒〕。[6]
聯系丁守勳諸篇狀文,此篇最有可能寫于開寶五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之間,即開寶六年二月。丁守勳大約在開寶五年(972)十二月受命抵達敦煌,并參與出臘,次年三月仍滯留在此,多次請辭卻不得歸。
丁守勳的五篇狀被廢棄后,被佛教徒重新利用,在背面分別抄寫各種佛教文獻,《香嚴寺經藏記》是其中之一,碑文的抄寫年代在宋開寶六年(973)以后,距立碑之時百年有余,說明香嚴寺興盛時間較長。此碑文在敦煌藏經洞內發現了兩件,都具有閱讀、學習、收藏之用,表明其在敦煌知識階層或佛教僧眾之間有一定的流傳。香嚴寺雖在后世湮沒無聞,但據以上細節推斷,此篇碑文橫跨東西、由唐入宋、傳于敦煌,超越地域與時間的界限,說明香嚴寺在唐宋之際,具有很強的文化輻射力,且維系了不短的時間。
三 作者志閑
《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署名作者志閑,其撰寫碑文的時間在開成三年(志明上人補經完成)至大中元年(僧昭義立碑)之間。現有史料對其生平事跡未有詳載,唯見于《宋高僧傳》卷10《唐婺州五泄山靈默傳》(五泄山在越州諸暨,《宋高僧傳》誤作“婺州”)。靈默禪師貞元初年入天臺山中,住白沙道場,后行次浦陽、盛化,陽靈戍將李望請靈默居五泄,并在暨陽令李胄的幫助下重造禪院。元和十三年(818)卒[6]。《宋高僧傳》在《唐婺州五泄山靈默傳》末附《志閑傳》,言僅一句:“高僧志閑,道行峭拔,文辭婉麗,亦江左之英達,為默《行錄》焉。”[7]可知,大約元和十三年(818)志閑為靈默禪師撰寫行狀,這是志閑在史籍中的最早記錄。此人以文辭見長,在南方頗有名氣。
志閑在元和十五年(820)為江西萍鄉楊岐山甄叔禪師撰寫過塔銘,《宋高僧傳》記載,甄叔禪師元和庚子歲(820)卒,志閑撰碑紀述[7]236。宋代《寶刻類編》著錄:“楊岐山甄寂(叔)大禪碑,沙門至閑撰,僧元幽行書,篆額,太和六年(832)四月三十日建,存。”{1}但作者記為“至閑”。錢大昕首次得到此碑拓片,著錄作者亦為“至閑”[9]。《金石萃編》作“沙門至閑撰”{2}。陳尚君先生認為當從《宋高僧傳》作“志閑”,而“至賢”“至閑”皆誤[10]。宋代著錄以及錢大昕所見拓片均作“至閑”,雖原碑題作“至閑”,但立碑時間距碑文撰寫已逾十二年,立碑之際將“志閑”誤刻作“至閑”亦未可知。綜合考慮撰文時代、文獻產生的地域,以及志閑“江左之英達”的身份,《甄叔大師塔銘》的作者就是《靈默禪師行狀》的撰寫者志閑。
志閑生活的時代,正值越州佛教發展活躍之時,當地的佛學環境以及宣宗對佛教的復興政策為志閑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大約在同時,諸暨佛教的代表性人物禪僧良價就生活于諸暨五泄山寺[11]。此外,越州諸暨的保壽寺也處于復興發展的重要時期。《宋高僧傳》記載著名禪僧神智于大中初年巡游諸暨,后入長安,在宰相裴休的支持下,奏請得到敕賜碑額“大中圣壽”,并由裴休親自書寫,還受賜左神策軍鐘一口、天后繡■、藏經五千卷[12]。同時,越州地方長官多與寺院往來,大約元和年間,諸暨高僧文質于諸暨法樂寺領徒,此后受越州廉使沈貳卿之邀,住會稽呂后山院,咸通二年(861)卒,越州刺史段式為其撰寫《行錄》[13]。當時的越州以及諸暨,佛教興盛,聲名遠播,那么《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碑文傳入敦煌并成為學習范本,就不足為奇了。
根據佛教史籍記錄,另有禪師“志閑”(智閑)可能與唐宣宗有過交往,但在正史中卻無記載。北宋《廬山記》記載:“五巒峰之下有大雄庵,去慧日三里,山勢環聳,屹若城壁,亦別一奧處也。內翰錢易記云:‘貞觀二年(628),梵僧尋山愛其深遠,有若大雄演法之地,故名大雄。’大和中,宣宗避難與僧志閑嘗居焉。”[14]北宋《碧巖錄》(《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引《續咸通傳》云:“武宗即位,常喚大中(宣宗)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致后苑中,以不潔灌,而復蘇,遂潛遁在香嚴閑和尚會下。后剃度為沙彌,未受具戒。后與志閑游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詩云:‘穿云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閑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脈看如何,大中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閑方知不是尋常人,乃默而識之。”[15]南宋《佛祖統紀》所載略同[16]。以上所言志閑當并非《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的作者志閑,而是后梁著名的香嚴閑禪師,名智閑,又稱香嚴和尚,《宋高僧傳》有載,其所住香嚴寺即河南鄧州之香巖寺{1}。
四 古剎藏經
諸暨香嚴寺是一所被后世遺忘的古剎,但它的輝光足以透過歲月厚重的塵埃,以歷史的方式重現。《金石錄》著錄“唐香嚴寺碑,康希銑撰,徐嶠之正書。開元十一年(723)六月”[17]。康希銑,越州會稽人,時遷臺州刺史,文行于世,顏真卿為其撰有神道碑。徐嶠之,越州人,唐代書家徐浩之父。此碑的撰者和書家都是越州本地人,且都是著名的文章家和書法家,可見當時的香嚴寺絕非一般小寺,而是較高等級的寺院。
北宋《寶刻叢編》對香嚴寺碑載有更多信息:“香嚴寺者,本梁賈恩舊宅,其妻舍充梵宇,舊名同惠,神龍中,請而著焉。碑以開元十一年六月立。”{2}據此可知,諸暨香嚴寺歷史久遠,蕭梁時期名同惠寺。唐中宗神龍年間(705—707)奏請更名香嚴寺,說明當時已有不小的規模。南宋時寺碑尚存,寺名已變,《輿地紀勝》載“在諸暨之薦嚴寺”[18]。南宋《嘉泰會稽志》著錄越州山陰縣龍興寺:“宋太(泰)始元年(465)建,號香嚴寺,唐神龍元年(705)改為中興寺,神龍二年(706)改為龍興寺。”{3}山陰縣之香嚴寺與諸暨縣之同惠寺于神龍年間同時更名,并非巧合,當是前者更名之后,后者繼承其名,二者之間或有遷移,于是原諸暨縣的同惠寺就成了香嚴寺。
唐代不少名僧與香嚴寺有密切聯系。大約景云元年(710),諸暨人戚氏,后世稱為高僧惠符,弱冠之時于香嚴寺出家[19]。唐代著名律師玄儼也是諸暨人,以其所撰《輔篇義記》知名,流傳甚廣,如敦煌文書P.2047即《輔篇義記》卷2的內容。玄儼住越州諸暨法華寺,天寶元年(742)卒,其弟子懷節是香嚴寺僧[20]。高僧神邕也是玄儼弟子,也是諸暨人,史載:“開元二十六年(738),敕度隸諸暨香嚴寺名籍。依法華寺玄儼師,通《四分律鈔》。”[21]著名禪師慧忠也是諸暨人,寶應年間奏請在河南淅川白崖山建香嚴長壽寺,慧忠必然知曉自己的故鄉諸暨有一所香嚴寺,這一寺名或許是慧忠為了紀念而有意為之[22]。當時香嚴寺聚集了不少學僧,寺中自然收藏了不少佛教典籍。
香嚴寺的藏經閣是寺內重要建筑。《香嚴寺經藏記》記載:“香嚴經藏者,天寶元年檀越主劉彥偕之所建也。”建造藏經閣的施主劉彥偕,難考此人,但香嚴寺在天寶元年以前一定已經積累了頗多佛教典籍。碑文接著描述藏經閣之宏偉,雖難免溢美,但其建筑規模必然不小,且細節考究。香嚴寺藏經閣應當是復合建筑,所謂“錯落貫日,棱層倚山”,這說明這些建筑依山而建,錯落有致,十分高大,層層分明。又云:“勢若籠神,捧出金地,當中寶座,八面花龕。”說明在建筑群的中央,有類似講經的殿堂,其中有講臺寶座,周圍還有精美裝飾。這符合古人對于在山林中修習佛法的向往圖景。例如莫高窟第209窟初唐壁畫中,西壁南側有人物故事圖,繪有山林殿堂,依山而建,屋檐棱角分明向上翹起。一所堂內,高僧似在說法,屋外俗眾禮拜敬聽。另一所堂內,一人似端坐讀經。西壁北側圖中,遠山重疊、樹木成行[23]。莫高窟第138窟東壁北門晚唐壁畫山城,圖中層巒疊嶂,遠山有寺院樓閣[24]。看來,香嚴寺藏經閣十分符合唐代佛教建筑的審美情趣。
《香嚴寺經藏記》還描述了藏經閣的內部陳設,“玉架以云聯彩鳳,銀函而星布”,說明藏經閣內有很多經架,可能是玉石的顏色,并有彩繪,經架之上遍布裝存佛經的銀匣。這樣的文學表達方式淵源有自,如北周庾信《陜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云:“雖復銀函東度,金■南翻。”{1}志閑的描述為今日物質文化史和書籍史研究保留了重要信息,呈現了唐代寺院藏經閣的內部結構和收藏經卷的方式,即屋內置架,架上列匣,匣內藏卷。白化文先生曾介紹過一種稱為“壁藏”的藏經閣建制,在兩層的藏經閣上層,沿壁立柜櫥安置藏經。在此基礎上,還有“天宮藏”,沿壁建成閣樓式結構以存藏經,香嚴寺藏經閣或與此相類[25]。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藤井惠介先生對于中世紀經藏的收納有過詳細的研究,這里不妨以正倉院圣語藏作為參考。除了入口門的位置以外,圣語藏內側壁面均有木質經架,分為七層,每層之間有隔板,架上擺放木質經匣,匣內收藏經卷(圖3){2}。香嚴寺的藏經方式當與此大同小異。
敦煌壁畫中也有描繪藏經閣的實例,莫高窟第112窟北壁東側中唐壁畫藥師經變中,后殿廡廊頂上有六角藏經閣,內有經架,架上有經帙,經帙內有經卷[26]。莫高窟第85窟南壁晚唐壁畫西方凈土變中,后殿廡廊頂上繪有圓頂藏經閣,樓內有方格經架,架上有經帙若干[24]31。同窟北壁東方藥師經變繪有二層樓閣,上層是六角尖頂藏經閣,樓內有圓形經帙若干[24]41。莫高窟第12窟北壁晚唐東方藥師經變繪有六角雙層塔樓,上懸藏經閣,左右繪有祥云,樓內有經架,架上有圓形經帙若干(圖4){3}。可見,《香嚴寺經藏記》所描述的藏經閣與壁畫中的藏經閣有頗多相似之處,呈現出唐人心中藏經閣的理想化樣態。《香嚴寺經藏記》對藏經閣的描述,對于復原研究藏經閣建筑及經藏收藏方式具有重要意義。
香嚴寺藏經閣建成后,還經歷過翻修和增建,《香嚴寺經藏記》中記載:“雖年月寢遠,代不乏賢。上座僧常照、都維那僧孝集、寺主僧慧一,并乃松篁帶雪,秀出庵園。繼踵匡時,彌增壯觀。”由此推測,當時的香嚴寺藏經閣不論是建筑還是藏經數量,都是十分出眾的。《香嚴寺經藏記》碑文記載,大和六年(832)高僧志明來到香嚴寺“覽經”,很有可能就是慕名而來。
志明在香嚴寺讀經三年后,在大和九年(835)發現經卷缺損情況,“由約藏內經題,按開元目錄,欠八百余卷未滿”,這在寫本時代是十分常見的。《開元釋教錄》的《入藏錄》收錄佛經共五千四十八卷[27-28]。李節所撰《餞潭州疏言禪師詣太原求藏經詩序》中記載,疏言禪師大中九年(855)求藏經五千零四十八卷,顯然也是按照《開元釋教錄》的名目搜集的[29]。志閑據《開元釋教錄》點勘香嚴寺藏經是當時的常見做法。即使缺少八百余卷,那么原藏經大約四千二百余卷,這一體量在寫本時代也是十分驚人的。志明決心補全香嚴寺所缺的藏經,終于在開成三年(838)完成,于是立碑紀念。但原碑被毀,直到大中元年(847)丁卯歲重刊。
唐代寺院雖數量龐大,但除了皇家寺院,獨立收藏一部完整大藏經的寺院并不多見。大約開元年間,佛教圣地五臺山存大藏經,律師守直在此地讀過三遍{1}。寶應年間,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嚴長壽寺受賜藏經一本[22]206。大約元和年間清涼山金閣寺存大藏經[30]。大中初年,僧人清觀為天臺山國清寺請藏經[31]。大約懿宗時期,福壽寺尼繕寫大藏經[32]。寫本時代收藏一部大藏經是不容易的,往往要立碑紀念,實例頗多。如至德至貞元年間,虎邱西寺有顧況撰寫的虎邱西寺經藏碑[33],元和五年(810)北京云居寺韓烈等造藏經記{2}。還有與《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時代相近的明州《唐清泉寺大藏經記》,大和二年(828)立[34]。又如開成五年(840)白居易營建了香山寺經藏堂,并撰文立碑,即《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35]。再如《咸通九年(868)湖北延慶禪院經藏碑銘》{3}。還有山西永濟的《棲巖寺新修舍利塔殿經藏記》,后周顯德六年(959)立{4}。晚唐居多,不待詳陳。
在寫本時代,除了皇家造藏之外,寺院收集、補全一部藏經并非易事,而通覽大藏經則作為一種非凡事跡被記錄在僧傳中。《宋高僧傳》載,約天寶初年,僧靈坦在廬州浮槎寺覽大藏經[7]225。此事被視作一種超凡經歷被寫入僧傳,有趣的是,其他史料證明浮槎寺的大藏經存在諸多問題。唐人李肇所撰《東林寺經藏碑銘》載,約元和年間,僧人義彤曾在浮槎寺覽大藏經:“彤公受具于廬山浮槎寺,嘗討大藏,惡其部帙繁亂,將理之不可,遂發私誓。”此后義彤在廬山東林寺完成藏經的整理,“于是搜遠近之逸函墜卷,目在辭亡者得之,互文合部者兼之,斷品獨行者類之,本同名異者存之,以偽亂真者標之”[36]{1}。這應是當時較為先進的整理藏經的方法,香嚴寺的志明上人或許也是用這種原則校補藏經。大藏經卷帙繁多,文義高深,加之寫本時代書籍的流通能力、復制成本、收藏管理等方面的限制,使得唐代寺院即使收藏一部,也極有可能存在各種缺損、錯亂的情況。
結 語
越州諸暨縣香嚴寺,雖已隱沒,但借助《香嚴寺經藏記》,得以窺見那千年以前的風采。香嚴寺頗有淵源,蕭梁時期名同惠寺,唐神龍年間更名,不少名僧曾在此修學。《越州諸暨縣香嚴寺經藏記》載于寺中的一方石碑上,原碑早佚,以至宋代的金石學家們未得著錄。P.2804和P.3040是僅在敦煌保存下來的碑文抄本,未收入后世文集之中,成為世間孤本,幸有佛教徒們虔誠地抄寫與傳遞,香嚴寺才得以重現于歷史舞臺。敦煌《香嚴寺經藏記》的抄寫者們,面對一篇來自遙遠的諸暨縣的碑文,并沒有地域性的排斥,而是認真抄寫、閱讀、收藏,將其當作撰寫碑文和學習的參考素材,他們眼中的文化,無關朝代、無謂時限、無問西東。
《香嚴寺經藏記》重刊之碑于唐大中元年(847)立,敦煌本的抄寫年代在宋開寶六年(973)以后,相距130余年,在此期間,巡禮朝拜、傳拓抄寫,不曾間斷。此碑雖非寺碑,而是立于藏經閣前的紀念碑,但仍被反復觀摩學習,說明香嚴寺藏經豐富、頗為著名。碑文作者是僧人志閑,其生活的時代,正是越州佛教發展的高峰。《香嚴寺經藏記》不僅記載了藏經閣的外部樣貌,還呈現了內部結構和收藏經卷的方式,屋內置架。架上列匣,匣內藏卷。相關記錄是書籍史研究的重要歷史信息。此篇碑文的流傳,說明唐宋之際的浙東尤其是越州諸暨擁有較強的佛教文化輻射力。前揭越州諸暨保壽院的神智和尚就纂錄了著名的《傅大士頌金剛經》,這在敦煌、吐魯番出土了很多寫本{2}。這都令人重新審視諸暨在中唐以后的文化地位和作用。
參考文獻:
[1]饒宗頤. 法藏敦煌書苑精華:第1冊[M].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277-278.
[2]榮新江. 石碑的力量:從敦煌寫本看碑志的抄寫與流傳[J]. 唐研究,2017(23):312.
[3]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國國家圖書館.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8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19.
[4]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博物館. 法國國家博物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1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8.
[5]榮新江. 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21.
[6]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 英藏敦煌文獻:第7冊[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9.
[7]贊寧. 宋高僧傳:第10卷[M]. 范祥雍, 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231.
[8]道原,景德傳燈錄譯注:第7卷:婺州五泄山靈默禪師[M]. 顧宏義, 譯注. 上海:上海書店,2009:463.
[9]錢大昕.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第8卷:甄叔大師塔銘[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197.
[10]陳尚君, 輯校. 全唐文補編:第74卷:志閑[M]. 北京:中華書局,2005:917.
[11]贊寧. 宋高僧傳:第12卷[M]. 范祥雍, 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280.
[12]贊寧. 宋高僧傳:第25卷[M]. 范祥雍, 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639.
[13]贊寧. 宋高僧傳:第27卷[M]. 范祥雍, 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685—686.
[14]陳舜俞. 廬山記:第2卷[G]//大正藏:第51冊."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1036.
[15]圓悟克勤. 碧巖集:第2卷[G]//大正藏:第49冊.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152.
[16]志磐. 佛祖統紀:第42卷:法運通塞志[G]//大正藏:第49冊.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387.
[17]趙明誠. 金石錄校證:第5卷[M]. 北京:中華書局,2019:98.
[18]王象之. 輿地紀勝:第10卷:兩浙東路:紹興府:碑記[M]. 趙一生,點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406.
[19]贊寧. 宋高僧傳:第19卷[M]. 范祥雍,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477.
[20]贊寧. 宋高僧傳:第14卷[M]. 范祥雍,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342—344.
[21]贊寧. 宋高僧傳:第17卷[M]. 范祥雍,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421.
[22]贊寧. 宋高僧傳:第9卷[M]. 范祥雍,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204—206.
[23]段文杰,樊錦詩. 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第6冊[M]. 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圖187,165.
[24]段文杰,樊錦詩. 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第8冊[M]. 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圖238,190.
[25]白化文. 漢化佛教與佛寺[M].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178.
[26]段文杰,樊錦詩. 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第7冊[M]. 天津:天津美術出版社,2006:圖36,38.
[27]智升. 開元釋教錄:第19卷[M]. 富世平,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8:1287.
[28]方廣锠. 中國寫本大藏經硏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03-418.
[29]董誥,等. 全唐文:第788卷:餞潭州疏言禪師詣太原求藏經詩序[M]. 北京:中華書局,1983:8249-8250.
[30]贊寧. 宋高僧傳:第11卷[M]. 范祥雍,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248.
[31]贊寧. 宋高僧傳:第20卷[M]. 范祥雍,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527.
[32]贊寧. 宋高僧傳:第6卷[M]. 范祥雍,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1987:133.
[33]李昉,等. 文苑英華:第863卷[M]. 北京:中華書局,1966:4556-4557.
[34]趙明誠. 金石錄校證:第9卷[M]. 北京:中華書局,2019:190.
[35]白居易. 白居易文集校注:第34卷:碑記銘吟偈: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M]. 謝思煒, 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1:2012.
[36]李昉,等. 文苑英華:第865卷[M]. 北京:中華書局,1966:4567.
{1} 彩色圖版見https://idp.bl.uk/collection/5C2F68C-
C68F1BC41B0764DB82BB04DBF/?return=%2Fcollection%2F%3Fterm%3D2804
{2} 彩色圖版見http://idp.bl.uk/collection/77FC5EA-
13FF15D40B045F7C9857308C2/?return=%2Fcollection%
2F%3Fpage%3D2%26term%3D3040。
{3} 鄭炳林、鄭怡楠釋讀過P.2804,但部分文字有待商榷。參見鄭炳林、鄭怡楠輯釋《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3—68頁。
{1} “■”,《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作“捏”(第63頁),文義不通,當作“煜”,照耀義。
{2} “井”,P.3040作“一”。
{3} “范”,《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作“規”(第63頁),原卷作“■”,簡化為“范”,規范義。
{4} “偕”,《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作“備”(第63頁),當作“偕”。
{1} “薝蔔(卜)少花”,《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作“蘑蔔少花”(第64頁),誤,“薝蔔花”出自《長阿含經》,也作“瞻蔔華”。
{2} “遵”,《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第64頁)作“導”,當作“遵”。
{3} “星霜”,《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作“呈霜”(第64頁),當作“星霜”,年歲義。
{4} “崢”,《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未錄此字,據殘字劃及韻腳推測,可能是“崢”字。
{5} 史載,宣宗大中元年(847)閏三月,敕:“會昌季年,并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厘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舊唐書》卷18下《宣宗本紀》,中華書局,1975年,第617頁。
{1} 關于此印,參見森安孝夫《河西帰義軍節度使の朱印とその編年》附表,《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5期,中央ユーラシア學研究會,2000年,第120頁;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右衙都知兵馬使”條,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第292頁。
{2} 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8冊,第320頁;錄文參見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4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第515頁。
{3} 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8冊,第320頁;錄文參考《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4輯,第517頁。
{4} 參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0冊,2002年,第322頁;錄文參考《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4輯,第513頁。
{1} 參見《寶刻類編》卷5,葉27b,載《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8475頁上欄。
{2} 參考王昶《金石萃編》卷108《大唐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甄叔大師塔銘并序》,葉29b,載《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3冊,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833頁上欄。
{1} 參考《宋高僧傳》卷13《梁鄧州香嚴山智閑傳》,第303—304頁;參釋靜、釋筠編撰,孫昌武、衣川賢次、西口芳男點校《祖堂集》卷19《香嚴和尚》,中華書局,2007年,第827頁。
{2} 參考《寶刻叢編》卷13《越州》,葉5b,見《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第18282頁上欄。
{3} 參考施宿等撰《嘉泰會稽志》卷7,清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葉40b,見《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6837頁下欄。
{1} 參見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點校《庾子山集注》卷13《碑·陜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中華書局,1980年,第706頁。
{2} 參見藤井恵介《中世の経蔵における聖教·文書の収納狀況》,宮內庁正倉院事務所編《正倉院紀要》第45號,2003年3月,第33—46頁。蒙史睿先生賜告,在此致謝。
{3} 參見《中國敦煌壁畫全集》第8冊,圖76,第55頁。敦煌壁畫中繪有藏經閣的洞窟還有莫高窟第18、154、231、286窟及榆林窟第19窟。
{1} 參考《宋高僧傳》卷14《唐杭州天竺山靈隱寺守直傳》,第351頁;《全唐文》卷918《唐杭州靈隱山天竺寺故大和尚塔銘》,中華書局,1983年,第9560頁。
{2} 繆荃孫著錄:“□展撰。行書。在順天房山小西天接待寺。”原石已佚,拓本存中國國家圖書館。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金石》,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171頁。
{3} 參見張仲炘《湖北金石志》第7卷,葉15a,載《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公司,1977年,第12061頁上欄。
{4} 參見《(光緒)山西通志》卷98《金石記》10《后周棲巖寺新修舍利塔殿經藏記》,三晉出版社,2015年,第4628頁。錄文參見陸心源《唐文續拾》卷7《棲嚴寺新修舍利塔殿經藏記》,中華書局,1983年,第11254—11255頁。
{1} 廬山東林寺藏經由義彤整理之后,還經歷了會昌法難,北宋陳舜俞記載:“會昌之厄,僧道深竊藏之石室,后寺復而經出,然亡失者過半。僧正言稍補之。大中十二年(858),武陽之子宙復世廉察,因施錢再作堂宇,仍志其事。”(參考《廬山記》卷1,《大正藏》第51冊,第1028頁中欄第21行至下欄第6行)“武陽之子宙”即江西觀察使韋丹之子韋宙,韋丹曾資助東林寺建藏經之所。可見唐代寺院收藏一部大藏經的不易。
{2} 具體研究參見陳志遠《傅大士作品早期流傳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21年第2期,第85—96頁。
收稿日期:2023-07-30
基金項目: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項目“法藏敦煌文獻重新整理研究與編目”;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啟”計劃(2024QQJH067)
作者簡介:何亦凡(1992—" ),女,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隋唐史、德政碑、敦煌吐魯番文書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