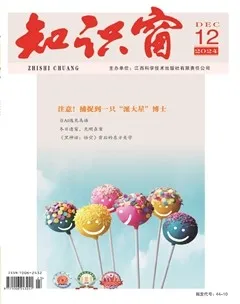“卡林西猜想”的奇妙之旅
在浩渺的人海中,我們與他人的聯系,遠比大多數人想象的更為緊密。這并非一個全新的發現,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真理。早在1929年,匈牙利作家弗里杰斯·卡林西在短篇小說《鏈條》中便揭示了這個秘密:兩個主要角色大膽地猜測,在這個世界的任意兩個角落,人與人之間都可能由不超過五六個人所構成的“橋梁”連接起來。
想象一下,這樣的“橋梁”無處不在,它可能跨越山川大海,也可能穿梭于街巷之間。大多數人都能回想起,那些似乎遙不可及的人,其實只是通過幾個簡單的“橋梁”,便與我們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就是“卡林西猜想”的魔力所在,它揭示了人與人之間微妙而復雜的聯系——幾乎任何兩個人(A與E),都能通過“A認識B,B認識C,C認識D,D又認識E”的鏈條緊密相連。
為了驗證這一猜想,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在20世紀60年代展開了一系列精彩的實驗。他從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的電話號碼簿中隨機抽取了96個普通市民,分別向他們寄送了一個神秘的小包裹,并附上一封信,請求他們通過各自的熟人網絡,將這個包裹轉寄給遠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的一個股票經紀人。這個股票經紀人就是這次實驗的終點,也是所有“橋梁”的匯聚之處。
當然,這96個包裹的命運各不相同。有的包裹可能在收件后,就被擱置在某個角落,有的可能在中途丟失,但令人驚訝的是,最終仍有18個包裹成功抵達那個股票經紀人手中。這18座神奇的“橋梁”的平均鏈接數為5.9,也就是說,它們平均經過了近6個人,才將包裹從起點傳遞到終點。
這一理論的真正普及,還要歸功于約翰·瓜爾在1990年改編的同名戲劇《六度分隔》。這部戲劇在百老匯的舞臺上大放異彩,讓“六度分割”的概念深入人心,而貝肯數是基于“六度分割理論”的概念。到了1994年,美國奧爾布賴特學院的學生推出了一款名為“凱文·貝肯的六度關系”的游戲,讓這一理論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熱門話題。
這款游戲的規則簡單而有趣:參與者需要評估一個演員(無論是在世,還是已經離世)與美國電影明星凱文·貝肯在職業上的接近度。例如,如果某個演員與貝肯出現在同一部電影中,那么這個演員的“貝肯數”就是1;如果另一個演員與“貝肯數”為1的演員合作過,那么他的“貝肯數”就是2,以此類推……經過一系列的推算和統計,實驗者們發現,平均每個演員的“貝肯數”為2.955。這意味著,在這個龐大的電影網絡中,即便是與凱文·貝肯距離最遠的演員,也只需要通過不到3個人的“橋梁”,就能與他產生聯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群演員中,有一個名叫威廉·魯弗斯·沙夫特的演員,他的“貝肯數”是7。沙夫特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一個南部軍隊將軍,他的主要身份與電影行業相去甚遠。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他曾在1898年出演過兩部電影,這使得他與電影圈產生了微妙的聯系。
直到1998年,“六度分隔理論”引起了研究社會聯系的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在這一年,社會學家鄧肯·J.瓦茨和數學家史蒂夫·斯托加茨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小世界”網絡的集體動力學》。這篇論文為社會科學家的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數學基礎,使他們能夠更深入地探索思想和行為在人群中的傳播規律。這篇論文的發表,不僅為“六度分隔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學術支持,還為后來的研究開辟了新的道路。
從“卡林西猜想”,到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再到“六度分隔理論”的廣泛傳播和深入研究,我們不禁感嘆人類社會的聯系之緊密和復雜。在這個充滿聯系的世界里,沒有真正的孤島。我們的每一個行動和選擇,都有可能影響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