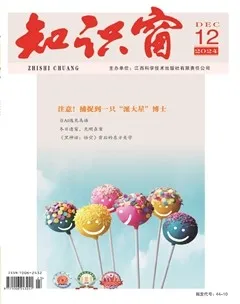史筆刻丹青
春秋時期,魯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齊國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不愿落一個弒君的名頭被后世指責的崔杼,要求前來記載的史官寫齊莊公得瘧疾而死。
崔杼威脅道:“如果不然,吾必殺你!”面對閃著寒光的劍,太史伯拿筆在竹簡上如實記載“崔杼弒其君”。
崔杼很生氣,太史伯死了。
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太史叔先后承擔起了史官職責。崔杼拿起沾血的劍,讓他們寫齊莊公是病死的。太史仲和太史叔接過哥哥的竹簡,用筆寫下了“崔杼弒其君”。
崔杼很生氣,太史仲和太史叔也死了。
太史伯的弟弟太史季就在門外,他和哥哥們一起過來的,太史季接過史筆在竹簡上寫下“崔杼弒其君”。
崔杼放下了劍,太史季撿起竹簡,收殮了哥哥們的尸首,就此退下。
崔杼弒其君的事記載于《左傳》,結尾處寫著這樣一行字:“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即書矣,乃還。”
寥寥數筆,是太史伯四兄弟舍生忘死捍衛的歷史真相,史官是用生命詮釋其對職任之認識,是刀劍在側時的毅然決然,正如千年后身披枷鎖的文天祥一字一字寫下的“時窮節乃見”。每每想到,一種靜穆的悲壯透過《左傳》泛黃的書頁,越千古而來,千百年的讀書人估計都有類似的心情。
在《東周列國志》中記載,太史季在哥哥接連被殺后,說:“據事直書,史氏之職也。失職而生,不如死……某即不書,天下必有書之者,不書不足以蓋相國之丑,而徒貽識者之笑,某是以不愛其死。”此等氣節,殘忍如崔杼也只得長嘆一聲,放下手中的劍。“崔杼弒其君”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史書上的一句話,是萬千看似輕飄飄的記載之一,是萬千不知是以何人之手從鮮血之中寫出,蹚過刀光劍影,沖破波譎云詭,沉淀過百年千年的時光,展開在后人面前的一句話。五個字,三條人命,史筆如刀,垂刻丹青。武將死戰,文官死諫,這是歷史給予的悲壯史詩和豐碑。讀到此處,只有震撼與敬佩。何以中國?“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少年時,我一直有一個問題,崔杼既然有能力殺史官,為什么不殺光史官,或者選一個能聽自己話的史官來寫。
或許答案就在故事的結尾里,“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即書矣,乃還”。
太史季剛出門就碰到了匆匆趕來的南史氏,南史氏怕太史季也被殺了,所以趕來接替他如實記載“崔杼弒其君”。
前面的太史伯兄弟因職就死,南史氏則是主動上前,命運永遠屬于你,躲無可躲,不如捧著竹簡迎上去,所謂前赴后繼,所謂史筆如鐵。兩千年前,南史氏手捧竹簡沿著青石板路直迎上去,一定是猶如彩虹掛天穹的壯麗景象。對歷史的堅守,對信仰的堅守,而面對生命威脅,面不改色,不退一步,如天地正氣,似古道顏色,中國的信仰,就在一片丹青之上。
能如崔杼,最終也死于他人之手。當年的人已然在歷史的漫漫長河中煙消云散,留下的,只是這些秉筆直書的史官對那個時代的記錄,是揮著如刀的史筆刻在丹青史書上的橫平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