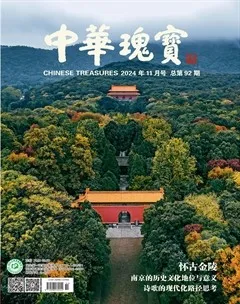清代考證史學的成績


清代乾嘉考證學派在史學上的成績以三部史考為代表,研究它們,有助于考察清代考證史學取得的成績,揭示史學考證方法在中國學術文化發展上獨具的性質和地位。
清代考證學本重在經學,因其鼎盛臻極而延及史學。清代乾嘉考證學派在史學上的成績以三部史考為代表,三部史考即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趙翼《廿二史札記》,乃清代學者對以“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史書體系較全面的研究總結,在中國史學發展上呈超邁前古之功,是清代學者治史方法的一次較全面展示和弘揚,其中頗富可供后來師法借鑒者。由經學考證到史學考證,中國古代經史考證方法日漸成熟,且將垂后而啟迪方來。下面對三部史考分別介紹。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
王鳴盛學問淵博,自視甚高,自稱通“四部”之學,經有《尚書后案》,史有《十七史商榷》,子有《蛾術編》,集有詩文,可敵才高學博的王世貞“弇州四部”。“十七史”乃宋以來舊稱,明末毛晉汲古閣曾匯刻十七史,王鳴盛書還包括《舊唐書》《舊五代史》,共十九史。王氏于其書序中有曰:“商榷者,商度而揚榷之也。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而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為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跡,詮解蒙滯,審核舛駁,以成是書,故名曰商榷也。”即其書以文字考校、典制事實的考證詮釋為主。其書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校勘文字。乾嘉學者多重視并長于校勘,清人常謂書不校不能讀,王氏本有治經的經驗,故《十七史商榷》一書亦表現其長于校勘的特點。除對校、本校法外,王氏還采用了難度較大的理校法。
典制事實的考證。此為本書重點內容。如《史記·老莊申韓列傳》有“刑名”一詞,《十七史商榷》一書詳考相關記載曰:“刑非刑罰之刑,與形同,古字通用。刑名,猶言名實。”考證精當。此書對地理、職官的考證為重點內容。
評論史書內容體例及其作者。王氏認為治經斷不敢駁經,治史則不然,雖司馬遷、班固有過失,不妨對其箴砭批評,故其對各史多有批評議論。如《后漢書》作者范曄在政治斗爭中以謀反罪被誅殺,后沈約《宋書》為范曄作傳亦因妒才而不予褒崇,王氏則為之辨誣,認為《后漢書·黨錮列傳》作得好,讀之激發人,“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亂,必不為也”,又曰“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對范曄人格、史才備加推崇。魏收《魏書》被時人貶為“穢史”,王氏為之鳴不平,說它未必在諸史之下。他認為李延壽《南史》《北史》在記事上有抑南尊北之意,而且在有關人物的褒貶書法上義例不一。這都有助于后人讀史參考。但王氏持才自是,有任意褒貶之處。如王氏謂顏師古注《漢書》,多取其叔父顏游秦《漢書決疑》之義,卻不出其名,乃攘叔父之善而沒其名,為其一蔽,又謂顏師古不通小學。似此皆自視太高,睥睨一切。南宋吳仁杰《兩漢刊誤補遺》自有價值,王氏深相詆議,至有“人生世上,何苦吃飽閑飯,作閑嗑牙”之語,出言刻薄,錢大昕致書勸其要平允謙和。總之,王氏高標自置,在人格學問上不免被人訾議,亦不足怪。
對歷史人物及事件的評論。王氏往往自出胸臆,不附合他人,喜作翻案文章。例如王導在史上被稱為“江左夷吾”,他反對,認為王導“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實乃并無一事,徒有門閥顯榮,子孫官秩而已。所謂翼戴中興,稱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唐代王叔文推行的永貞革新失敗,王氏稱其“忠于謀國”,力斥《新唐書》列傳作者宋祁“但以成敗論人”。綜之,王氏于文字考訂、典制史實考證多有可稱,但負才自是,倨傲一世,致議論看法不免存在偏頗失實之處,此應予注意,但其書內容仍不失為清代史考中的代表作。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
錢大昕一生博學多識,尤重史學。錢氏生當乾嘉之世,治學以史學為主,對其他各種專門知識兼收并蓄,亦通經學,但以通大義為則。他雖以治經方法治史,但并未像王鳴盛那樣專治一經,這在乾嘉學者中乃別開生面。他對當時重經學、輕史學的學風深致不滿。他說自乾嘉考證學盛行于世,學者但治古經,略涉《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錢氏認為經、史本為一體,重經學、輕史學乃陋見。他說:“經與史豈有二學哉!昔宣尼贊修六經,而《尚書》《春秋》實為史家之權輿……初無經、史之別,厥后蘭臺、東觀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創立四部,而經、史始分,然不聞陋史而榮經也。”即孔子所修六經之《尚書》《春秋》為史學濫觴,東漢以后因四部分立,經、史始因目錄學而互相區分,但亦未發生陋史榮經及經精史粗之說。他認為經學、史學同樣重要,《史記》《漢書》當“與六經并傳而不愧”。
阮元曾稱錢氏為清初以來最博贍的學者,他說:“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史學,或言天學,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錢氏以其博學之才治史,故取得不菲的史學成就。除以《廿二史考異》稱于時外,《三史拾遺》《諸史拾遺》亦見重于世。元史向來不被人看重,錢氏于元史多有著作,乃清代元史研究的開山,一些元代史料如《元朝秘史》等,經錢氏提倡始被認識。
《廿二史考異》乃仿照司馬光《通鑒考異》體例撰成。所謂“廿二史”,是從二十四史中除去《舊五代史》與《明史》,又將司馬彪《續漢書》的八志從《后漢書》分出,另立《續漢書》二卷,故其書總目錄上實列出二十三史。其書內容重在文字校勘、典制史實考釋、名物訓詁箋釋等方面。
錢大昕在《廿二史考異·序》中曰:“夫史之難讀久矣。司馬溫公撰《資治通鑒》成,惟王勝之借一讀,它人讀未盡十紙,已欠伸思睡矣。況廿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瞭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佇劣,敢云有得?但涉獵既久,啟悟遂多,著之鉛槧,賢于博奕云爾。且夫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為齮齕前人,實以開導后學。”此指史書歷來即稱難讀,尤其在其文字義例難明、典制史實不通,因此他指摘錯謬,疏通疑難,為助人讀史掃除障礙。
錢氏不僅對二十三部史書及其注釋進行了翔實校訂,改正其錯訛,還考證了史書記載內容,對歷代典制地理職官沿革等進行考釋辨析,使各部史書中疑難不明者得到疏通解釋,為學者研習此二十三部史籍提供了方便。其中對文字聲韻的利用,尤可見其訓詁考證優長。如其考證禿發即拓跋曰:“禿發之先,與元魏同出,禿發即拓跋之轉,無二義也。古讀輕唇音如重唇,故赫連佛佛即勃勃。發從犮得聲,與跋音正相近。魏伯起書尊魏而抑涼,故別而二之,晉史亦承其說。”禿發烏孤建南涼,本河西鮮卑,與北魏同族。錢氏此條考證借助聲韻知識,“古無輕唇音”亦乃錢氏一大發明,見其《十駕齋養新錄》。
錢氏又謂:“予嘗論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族,否則涉筆便誤。”除官職地理之外,族氏制度亦為須關注的問題。殷、周時期實行氏族宗法制,貴族有姓氏,平民無姓氏。秦漢時貴族宗法制解體,平民亦開始有姓氏。魏晉南北朝時,士族門閥制盛行,士庶天隔,士族講究門第郡望,顯示士族地位的氏族譜諜學盛行。與之相關,門閥士族家族地位的變化,往往與其族地位的升降興衰相關;在門閥士族操縱選舉的歷史時期,士族個人的仕途升遷,往往取決于其家族地位的門第高下。錢氏提及“辨氏族”一說,表明他注意到族氏問題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之大。
此外,錢氏還善于在梳理史料的基礎上,集中類比相關史料,作貫通性的綜合性專題研究,有些已成為相當規模的獨立專篇。如其書卷九《侯國考》,詳考《漢書》有關紀志表傳的記載,逐一列舉各侯國封邑所在及始封者姓名,又補《地理志》之失注者二十五人。這已超出一般意義上的考證,成為以考證方法補緝完善原作的續補之作,是其書最有意義的內容。
察《廿二史考異》在文字的訓詁考訂方面的內容,不能不說此乃乾嘉經學家治經風氣在史學上的影響。錢氏通金石文字,往往引金石證史,此亦與以金石證經的學風有關,所以可以說,以考證學為根本,乾嘉史學與經學本相通。錢氏雖專力史學,但未能完全擺脫其時經學研究方法的影響,其治學嚴謹,亦可見經學家的影響。
趙翼《廿二史札記》
乾嘉之世,經學獨盛,史學則相對微弱,當時或以治經余力治史,王鳴盛可為代表。陳寅恪曾對經學盛、史學微的乾嘉學界有所評說:“雖有研治史學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時,始以余力肄及,殆視為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當時史學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誠可哀矣。”陳氏之論對認識乾嘉史學之微末甚有參考意義。趙翼對經學無所建樹,曾自言“資性粗純,不能治經學”,除詩文造詣外,專攻史學,所著《廿二史札記》不同于王、錢二人,在史學上獨步一世。首先,趙氏論及全部“二十四史”,王、錢之書尚有所不及。其次,王、錢之書以考訂文字、典制名物訓詁為主,趙氏之書與此不同,以史書體例得失及史實綜合詮敘為主,即以史法與史實并重,此為其書最大特點。與王、錢二人之書比,趙氏之書史學價值相對更大。
《廿二史札記》遍考“二十四史”,只是未將《舊唐書》《舊五代史》計入,故只稱“廿二史”。清初沿明代有“二十一史”之目,乾隆時刻《明史》,始有“廿二史”之名,繼又刻成殿本“二十四史”,于是“二十四史”之目始定。趙氏以《廿二史札記》為目,是其時“二十四史”之稱尚未流行。《廿二史札記》成書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其時“二十四史”刻成,但“二十四史”之名猶未盛行于世。
其書所論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首先是對各史體例、內容及史料來源的考證評論。此書首先從編纂方面對二十四部紀傳體正史作一番較全面的檢討。在考察每一正史時,先敘述其作者、撰寫經過、成書年代,然后論述各史體例得失、編纂方法優劣、史料來源及其真偽、史料價值高低等。這些對研究“二十四史”的編纂特點很有益處,是研究史學史很有參考價值的內容。
其次是對各史在史實記載方面得失的考證。此書對各史實記載上的互異之處及謬誤、疏漏、增補等,多予指出。如《史記自相歧互處》《宋元二史不符處》指出其記載中的矛盾歧異,《三國志誤處》《宋史各傳錯謬處》指出其史實記載的錯誤,《遼金二史各有疏漏處》《新唐書增舊唐書處》指出其各自的內容疏漏與增補等。這些有助于人們了解“二十四史”在史實記載上的長短得失。
再次是對各時代重要史實、人物及社會歷史特點的綜論評議。此為本書重點,也是區別于王、錢二書的特點所在。這方面除論述某一具體事件或人物功過是非外,大多是對各朝代的歷史記載進行綜合分析,指出和提出重大問題,并予評論。如《唐節度史之禍》《方鎮兵出境即仰度支供饋》《方鎮驕兵》等,這些題目的歸納綜合,涉及唐中后期面臨的嚴重政治問題,并且是導致唐后來衰敗的直接原因。《廿二史札記》往往就歷史記載資料進行綜合分析,歸納出相關專題,以摘引排比史料的形式作出闡示。這些專題歸納往往能反映當時重要的社會歷史及政治問題,因而對讀史者極具啟發引導價值。如“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漢初妃后多出微賤”“東漢功臣多近儒”“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等,多可見其時的社會關系及文化風貌特征等。這說明趙氏已超越對史書及史實的單純考證,直觀處理,開始上升至對社會歷史現象的深入透視,綜合分析,力圖較全面地把握社會實質。此乃趙氏相對王、錢二氏的高明所在,亦為《廿二史札記》的史學價值所在。趙氏在其書《小引》中有曰:“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于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這符合一個史家的胸襟與目光,決非“札記”二字所可范圍。趙氏最喜用類比歸納和貫通綜合史料的研究方法,乃古代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代表,與近代史學方法一脈相通。此書在現代史學研究中參考價值最大,亦最為史學研究者關注。
史家陳垣曾開設“史源學”課程,教學生讀史與作研究的基本功夫,其教材首選是《廿二史札記》,講課時亦提及《廿二史考異》與《十七史商榷》。陳垣認為,錢氏考證最精密,從史源學角度一般不易挑毛病,一般正面引用其論述。王氏目空一切,言辭刻薄,故陳垣往往將其引作反面典型,予以批評。陳垣認為趙氏《廿二史札記》錯誤最多,便于學生從查錯角度做練習,故在史源學教學中將其用作首選教材。由此可見史學上對這三部史考的一般看法。
葛志毅,大連大學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