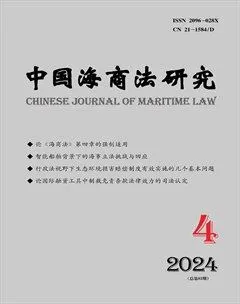行政法視野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有效實施的幾個基本問題
摘要:自2015年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在吉林等七個省市部署開展改革試點,并于2018年在全國范圍內全面試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作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中一項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除需進一步完善自身外,尚需在解決基本問題的基礎上,進一步協調與相關制度之間的關系。其中,明確界定磋商協議的性質、理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環境行政監管之間的關系、協調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行政公益訴訟的關系是幾個最為重要的問題。當下應當基于改革試點的經驗,不斷完善相關法律規定,以實現生態環境損害救濟領域法律制度的有機統一,從而為生態環境法典的制定奠定良好的基礎。
關鍵詞: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磋商協議;行政監管;行政公益訴訟
中圖分類號:D922.68 "文獻標志碼:A
收稿日期:
2024-08-15
基金項目:202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回應型治理視角下街鎮綜合執法改革的法治化研究”(22CFX056)
作者簡介:黃學賢,男,法學博士,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師范大學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研究員,江蘇高校區域法治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人員。
文章編號:2096-028X(2024)04-0061-09
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加強環境監管,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參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求是》2012年第22期,第19頁。】《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以“環境損害—人身權與財產權救濟”的單一模式為基礎構建而成的傳統環境侵權損害賠償制度,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使受害人的人身權或者財產權獲得有效救濟,但導致了生態環境作為侵權損害的介質,仍處于不利狀態。【參見郭海藍、陳德敏:《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的法律性質思辨及展開》,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177頁。】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發布,在吉林、江蘇、山東、湖南、重慶、貴州、云南七個試點省市陸續啟動改革試點項目,成效斐然。2017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再次發布《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簡稱《改革方案》),自2018年1月1日起,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在全國范圍內試行。根據《改革方案》“四、工作內容”部分的規定,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單位或個人為賠償義務人,應當承擔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修復受損生態環境;賠償義務人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無法修復的,賠償權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門或機構根據磋商或判決要求,結合本區域生態環境損害情況開展替代修復。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重要目的就是落實損害擔責的原則,破解“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的困局,提高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水平。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核心是,由省級、市地級政府作為賠償權利人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程序,在與致害人協商不成的情況下由權利人提起訴訟。這一制度的目的是解決實踐中生態環境損害得不到有效救濟的問題。
近年來,隨著行政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法治政府建設不斷推進,環境行政監管日益加強。同時,隨著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以環境公益訴訟為主要內容的環境司法專門化呈現出日益擴張的趨勢。在這種趨勢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面臨著來自多方的挑戰。目前,涉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主要規范除了《改革方案》外,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簡稱《民法典》)等法律、《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試行)》(2020年修正)、《關于推進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此外,還有十幾個省級生態環境保護督察辦法、十幾個省級地方性法規規定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內容。可以預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會成為未來一定時期內中國生態文明建設中一項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目前完善該制度并協調相關關系是最為基礎和重要的工作。其中,明確界定磋商協議的性質、理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環境行政監管的關系、協調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行政公益訴訟的關系,可謂是幾個關鍵點。
黃學賢:行政法視野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有效實施的幾個基本問題
一、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協議的性質
磋商程序是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的核心環節,也是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特色。目前,該制度的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磋商程序本身存在諸多理論上的歧義,如磋商協議的性質、磋商程序的設定、磋商協議的執行等。其中,磋商協議的性質無疑是一個基礎性問題。關于磋商程序,《改革方案》“二、工作原則”部分將其定位為環境損害訴訟之必需的前置條件,對促進“責任明確、途徑暢通、技術規范、保障有力、賠償到位、修復有效”的賠償制度的建立至關重要,【《改革方案》“一、總體要求和目標”部分規定:“……到2020年,力爭在全國范圍內初步構建責任明確、途徑暢通、技術規范、保障有力、賠償到位、修復有效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對提高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和修復的效率、降低行政和司法成本具有突出的功效。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的磋商協議由行政機關主動啟動,并可通過司法確認保障其有效實施,因而其公法色彩非常明顯。但與行政處罰等傳統行政行為不同的是,磋商程序中的談判協商又具有典型的民事私法行為特點。《改革方案》及相關領域司法解釋等涉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文件都沒有從制度層面明確賠償磋商協議的法律屬性,學界對此亦未達成共識,實踐中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導致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協議的性質存在較大的分歧,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實踐中磋商協議的效力及其執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功能也因此受到極大制約。關于磋商協議法律屬性的爭議焦點,尤以民事性和行政性的分野為最。
(一)民事協議說
民事協議說的支持者主張:行政機關代表國家,以自然資源所有權人而非生態環境管理者身份與賠償義務人平等協商,以求達成賠償協議,進而實現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最終目標。【參見陳俊宇、徐瀾波:《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協議之性質厘定與司法效果》,載《當代法學》2022年第6期,第71頁。】無論是從磋商程序中雙方的地位平等,還是從磋商的目的是達成賠償協議來看,磋商協議都符合民事協議的定性本質。《改革方案》中使用的“賠償權利人”與“賠償義務人”,本質上體現了民事賠償請求權的行使。將磋商協議視為民事協議,與磋商失敗后轉為環境民事訴訟程序的制度設計相吻合。在磋商過程中還可以引入第三方調解機構來主持磋商程序,以及對于經調解達成的協議可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等規定,更是強化了磋商協議的民事性。【參見許芝芝:《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制度的基礎理論探討》,載《農村經濟與科技》2019年第7期,第49頁。】將磋商協議定性為民事協議的觀點,實際上是從以《改革方案》為主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文本出發,而不是從問題本身出發所得出的結論。
(二)行政協議說
行政協議說的支持者主張: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磋商過程中,行政機關假以私法領域的協商手段維護公共利益,這符合行政法理論中的“為行政管理”目的論,也體現了新型行政執法模式的協作性和協商性。故此,不能完全用私法理論來解釋這種帶有強烈行政特征的磋商協議,磋商程序只是其外在形式,其本質仍然是為了實現行政職能。【參見黃錫生、韓英夫:《生態損害賠償磋商制度的解釋論分析》,載《政法論叢》2017年第1期,第17頁;郭海藍、陳德敏:《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的法律性質思辨及展開》,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181頁;康京濤:《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的法律性質及規范構造》,載《蘭州學刊》2019年第4期,第54-56頁。】德國學者毛雷爾(Maurer)對行政合同曾經作出過經典的概括:“行政合同是指:以行政法律關系為客體,設立、變更或者消滅行政法權利義務的合同。”“行政合同與其他合同的區別在于客體。……由行政機關簽訂,并且屬于行政法領域。”“如同行政行為,行政合同也是行政法上的、針對個別事件的具有外部法律效果的處理。”【[德]哈特穆特·毛雷爾:《行政法學總論》,高家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349、357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簡稱《行政訴訟法》)(2017年修正)【《行政訴訟法》(2017年修正)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下列訴訟:……(十一)認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或者違法變更、解除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土地房屋征收補償協議等協議的;……”】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已失效)中,立法者就已將行政協議納入行政訴訟的受理范圍并明確行政協議定位。2019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協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行政協議司法解釋》)對行政協議進行了較為全面具體的規定。2023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也在其受案范圍內增加了行政協議。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設計中不應該無視行政訴訟制度的重要發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于2015年在吉林等七個省市開展試點,《改革方案》于2017年出臺、2018年全面實施,其間應該考慮到行政訴訟制度在行政協議問題上的新進展并與之協調。《行政協議司法解釋》第1條從主體、目的、意思、內容四個方面對行政協議作了較為明確的界定,【《行政協議司法解釋》第1條規定:“行政機關為了實現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務目標,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協商訂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屬于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款第十一項規定的行政協議。”】只有同時滿足這四個要件才屬于行政協議,或者說同時滿足這四個要件即屬于行政協議。
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當環境損害發生后,啟動損害的調查取證、評估實際損害、提起磋商程序、簽訂磋商協議等重要程序都以行政機關為主導,每個程序都體現了行政機關在該程序中的職權性。磋商協議的目的是治理與修復生態環境。就意思表示而言,磋商協議的達成是基于行政機關與生態環境損害致害人雙方的協商一致。磋商協議的內容是行政機關管理生態環境職責的延伸,因而自然具有了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內容。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簡稱《環境保護法》)第6條第2款的規定,保護生態環境是各級地方政府應盡的行政職責。【
《環境保護法》第6條第2款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行政區域的環境質量負責。”】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協議可以認為是政府為履行環境保護職責而采取的改善環境質量的措施,表明了行政機關治理生態環境的方式從傳統行政手段向現代行政手段的轉變。這也是行政契約法制從早期的鮮為人知發展至現今行政行為領域中耀眼新星的典型體現。【
參見林明鏘:《行政契約法研究》,翰蘆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頁。】在行政協議典型案例第1號“大英縣永佳紙業有限公司與四川省大英縣人民政府等不履行行政協議再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行政協議實質標準的判斷方式。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是否行使行政職權、履行行政職責是所有要素中最為核心的,而目的要素只是輔助要素。判斷是否行使行政職權,是以行政機關擁有作出單方行政行為的法定權力為基礎,行政協議被視為對單方行政行為的一種替代。【參見凌維慈:《行政協議實質標準的判斷方式——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協議典型案例第1號評析》,載《法律適用》2022年第1期,第118頁。】“準確界定賠償磋商的法律性質應當以正視目的對手段的支配作用為前提,將維護環境公共利益的目的定位作為評判基礎,從而洞曉到賠償磋商實屬在行權方式上有所創新的公權行政行為。這種行權方式的創新主要體現在公私交融的‘混合行政’體制下公共行政權力與私主體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的合作治理轉型以及公法領域的行政管制過程向私法領域平等協商機制的借力。”【
郭海藍、陳德敏:《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的法律性質思辨及展開》,載《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178-179頁。】從對行政合同的理論闡釋、行政訴訟制度的新發展以及《行政協議司法解釋》對行政協議的規定來講,基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要解決的核心問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的磋商協議完全符合行政協議的基本特征和構成要件。因此,將其定性為行政協議更為恰當。
(三)協商行政說、行政事實行為說和雙階論
關于磋商協議的性質,除了民事和行政二元觀點外,還有協商行政說、行政事實行為說和雙階論等觀點。有學者認為,循著行政契約理論的路徑處理賠償磋商行為,可以將生態環境損害磋商行為定性為協商式行政執法行為。協商式行政執法行為的界定更加符合生態環境損害制度構建的初衷。【參見黃錫生、韓英夫:《生態損害賠償磋商制度的解釋論分析》,載《政法論叢》2017年第1期,第17頁;
李姍蔓:《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制度省思——兼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十大典型案例》,載《黃河科技學院學報》2021年第9期,第91頁。】協商行政說沒有真正講清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磋商協議的性質。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磋商行為定性為協商行政,只是表明行政借助了民事的手段,但并沒有改變行政的實質;看似跳出了民事與行政的糾纏,實則仍然沒有擺脫這一紛爭。行政事實行為說則認為無論民事性質論還是行政性質論,二者均無法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制度提供有力的理論基礎。以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行為的構成要件看,將其定位為行政事實行為或具有可行性。【參見李一丁:《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行政磋商性質考辯、意蘊功能解讀與規則改進》,載《河北法學》2020年第7期,第86頁。】隨著行政行為內涵的不斷擴大,行政事實行為已經為行政行為的概念所吸收。所以,行政事實行為說也無法正確表明磋商協議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的性質。雙階論認為,將該磋商協議單一地定義為民事協議抑或行政協議均為不妥。民事協議說忽略了其中調查取證、啟動磋商等重要的主導性程序,僅關注協商的私法屬性。行政協議說則又過分注重了其中的行政屬性。因此,單一的民事協議說或行政協議說均難免失之偏頗,唯有以“前階公法,后階私法”為主要內容的雙階論,才能走出民事協議和行政協議的單一性,為厘清磋商協議的法律屬性提供融貫的解答。【
參見潘佳:《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制度解構》,載《法律適用》2019年第6期,第116頁;劉莉、胡攀:《生態環境損害磋商制度的雙階構造解釋論》,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第39頁。】實際上,起始于德國的雙階論看似全面,但也并不能實質性地界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中磋商協議的性質。生態環境的公共性決定了其不能作為私法治理的對象。基于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憲法》)第26條第1款【
《憲法》第26條第1款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和《環境保護法》第6條第2款規定了國家肩負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的公法責任。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公權力機關只是改變了傳統的行政執法方式,借助了磋商這一私法手段,磋商的公法屬性并未因此而改變。從啟動的行政性、內容的職權性、程序的磋商性、目的的公益性、糾紛解決機制的有效性、執行的實效性等方面來看,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的磋商協議界定為行政協議,不僅符合《行政協議司法解釋》對行政協議的規范,更重要的是在現行行政法律制度體系下能減少制度上的疊床架屋,便于將制度的規范效能轉化為直接的治理效能。
(四)基于行政協議說優勢的發揮
總體而言,從現行行政法體系來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協議的行政協議性質是成立的,其本質是行使行政裁量權而非自主處分其民事權利。【
參見趙鵬:《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行政法分析——兼論相關懲罰性賠償》,載《政治與法律》2023年第10期,第55頁。】但是,就目前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而言,作為行政協議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協議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彌補的漏洞。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簡稱《人民調解法》)第1條為例,該條并未表明司法確認的范圍包括行政協議,這意味著法院調解的適用范圍僅限于民事協議糾紛案件。【
《人民調解法》第1條規定:“為了完善人民調解制度,規范人民調解活動,及時解決民間糾紛,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根據憲法,制定本法。”】故此,應該基于生態環境損害磋商協議的行政協議特征,對該制度作適當調適,排除磋商協議的司法確認。若行政相對人不履行協議,行政機關應按照《行政協議司法解釋》第24條規定的非訴執行方式執行。【《行政協議司法解釋》第24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未按照行政協議約定履行義務,經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機關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協議的書面決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收到書面決定后在法定期限內未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且仍不履行,協議內容具有可執行性的,行政機關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行政機關對行政協議享有監督協議履行的職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未按照約定履行義務,經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機關可以依法作出處理決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收到該處理決定后在法定期限內未申請行政復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且仍不履行,協議內容具有可執行性的,行政機關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如行政機關未能依法履行,未按約定履行或者違法變更、解除磋商協議,行政相對人可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途徑尋求法律救濟。這樣既可以理順糾纏不清的理論,也可以化解諸多制度上的結構性矛盾。正如學者在討論德國行政合同時所指出的:“如今在德國,人們不再爭論行政契約的重要性,而是探討如何明確實現行政契約法的內容。”【
陳慈陽:《行政法總論:基本原理、行政程序及行政行為》,翰蘆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42頁。】時至今日,與其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協議性質問題上作無謂的爭論,不如基于行政協議的本質要求以及相關的制度規定對其作進一步的完善,將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與民事機制的靈活性相結合。【
參見趙鵬:《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行政法分析——兼論相關懲罰性賠償》,載《政治與法律》2023年第10期,第55頁。】這是當代社會行政民主制度尋求更有效、圓滿解決社會問題的智慧選擇。
二、理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環境行政監管之間的關系
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法領域中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建立專門機構、發布規范行使行政力量。侵權機制逐步轉變為發揮“補遺拾遺”的口袋作用。【
參見張寶:《環境規制的法律構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72-73頁。】在中國,以設定環境行政許可、規定禁止性義務、進行環境監督檢查等為主的公法措施,一直是治理環境問題的主要手段。從現有行政法律制度來看,對生態環境損害的救濟機制也并非空白,諸多法律法規授權行政機關以行政強制措施的方式予以救濟。但此種恢復機制由于缺少具體的制度安排等原因而難以實現。【
參見張寶:《生態環境損害政府索賠權與監管權的適用關系辨析》,載《法學論壇》2017年第3期,第15-16頁。】
(一)兩種制度的矛盾體現
有些法律在行政相對人的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與行政監管機關的權力之間存在不匹配的情況。以《環境保護法》為例,第6條第1款作為抽象義務的具體體現,規定環境保護義務主體為一切單位和個人;【
《環境保護法》第6條第1款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第6條第3款具體規定經營者所應承擔的環境損害責任;【
《環境保護法》第6條第3款規定:“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防止、減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對所造成的損害依法承擔責任。”】第30條第1款規定生產經營者有義務保障生態安全,制定和實施生態保護和恢復治理方案;【《環境保護法》第30條第1款規定:“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應當合理開發,保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生態安全,依法制定有關生態保護和恢復治理方案并予以實施。”】第42條第1款規定生產經營者有義務采取措施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和損害。【《環境保護法》第42條第1款規定:“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采取措施,防治在生產建設或者其他活動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廢渣、醫療廢物、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噪聲、振動、光輻射、電磁輻射等對環境的污染和危害。”】此處之“損害”包括人身、財產以及生態環境損害。但從相應法律責任視角看,《環境保護法》卻未授予相關監管部門一般性權力,以通過行政強制措施責令治理與恢復。法律體系不健全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環境行政執法重處罰、輕治理。除了單行法的規定外,《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簡稱《行政處罰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簡稱《行政強制法》)也作了相關規定。《行政處罰法》規定了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時,應當責令當事人改正;【參見《行政處罰法》第28條第1款。】《行政強制法》也明確了當事人不履行行政決定時的代履行機制,甚至還規定了緊急情況下的代履行機制。【參見《行政強制法》第50條至第52條。】但是,實務中多數立法缺乏可操作性,對當事人無法形成具有法律上權利義務關系的嚴格約束,致使一些規定因不具備執行性而被忽視。《改革方案》因此出臺,但其又造成了制度適用上的沖突。由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范圍不同于傳統上的因環境破壞而造成的財產權或生命健康權的損害,這里的損害處于被擴張狀態,導致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被傳統環境行政管制所覆蓋。【參見趙鵬:《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行政法分析——兼論相關懲罰性賠償》,載《政治與法律》2023年第10期,第51頁。】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傳統的環境行政監管之間如何協調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環境行政執法是典型的公法行為自不必說。生態環境損害的政府索賠行為歸根結底是一種新型公法行為,只是其借助了私法手段來實現公法目標。從法學理論來講,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應當與環境行政監管制度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的關系。但事實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現行法律中行政機關施以行政強制措施、必要時施以行政強制執行等或交叉或重疊,二者間的關系亟待協調。【參見張寶:《生態環境損害政府索賠制度的性質與定位》,載《現代法學》2020年第2期,第91頁。】實施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是想通過增加行政權的支點來強化行政權,還是要行政權配合司法權?這個問題涉及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目的以及該制度能否有效運行。應當承認,由于種種原因,中國環境行政監管確實存在監管不力等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定要以司法來取代。即使不得已必須借助司法之力來彌補環境監管制度的不足,也要建立起環境行政監管與司法制度之間的協調互補關系,而不是因司法權的介入使二者之間出現事實上的此消彼長。否則,“不僅不利于環境行政監管的功能改善,還易導致環境司法專門化自身功能定位與發展目標的迷失。”【張璐:《中國環境司法專門化的功能定位與路徑選擇》,載《中州學刊》2020年第2期,第40頁。】由此,理順二者之間的關系尤為重要。
(二)兩種制度的協調方案
自開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工作試點以來,面對生態環境損害時,對于適用行政監管權還是適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程序,各地政府一般都采取回避態度。二者事實上存在責任競合關系。有學者指出,責任競合發生時,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具有自由裁量權。【參見王小鋼、宋麗容:《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訴訟與檢察公益訴訟》,載《中華環境》2018年第6期,第35-38頁。】《關于推進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八、關于鼓勵賠償義務人積極擔責”部分規定:“對積極參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并及時履行賠償協議、開展生態環境修復的賠償義務人,賠償權利人指定的部門或機構可將其履行賠償責任的情況提供給相關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裁量時予以考慮,或提交司法機關,供其在案件審理時參考。”這一規定至少揭示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賠償義務人在履行了賠償責任后,仍要依法承擔行政甚至刑事責任;二是賠償義務人需先行履行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責任;三是行政機關或者司法機關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或者刑事自由裁量權時,對及時履行賠償協議、開展生態環境修復的賠償義務人,要考慮其積極行為的情節。
行政職權并不具有可處分性,其應當作為權力與職責的統一體,具體體現為法律上的支配與職責相統一,因此行政主體無法對職權進行處分即表現為法定職責的基本要求,對于法律賦予的行政職責,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使。行政主體不得隨意放棄行政職權,否則構成行政不作為。【參見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頁。】具體而言,如已有法律明確規定損害方對環境損害的恢復義務和有權機關的行政管理職責,則環境損害發生時有權行政機關應當依法行使行政監管權以維護生態環境利益,而不應當通過磋商制度來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的目標。只有在窮盡行政監管措施后仍不能有效阻止生態環境損害時,才能依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行使政府索賠權。否則,行政機關會因未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而構成行政不作為。因此,并不能簡單地認為政府針對同一生態環境損害行為同時享有行政監管權和索賠權,從而可以選擇性適用。只有在行政監管手段不足時,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制度才得以發揮其補強功能。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認為磋商機制對中國生態管理模式的創新與發展顯著彌補了中國生態管理方面強制性行政措施及公益訴訟的不足。【參見武建華:《從五個方面完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磋商機制》,載《人民法院報》2018年9月12日,第8版。】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簡稱《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101條至第122條可以看出,該法在應對固體廢物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的情況時,首先適用行政監管,其次是對造成重大損失的適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同樣,“從《民法典》所規定的賠償范圍來看,生態環境損害調查、鑒定、治理、修復以及防止損害結果發生和擴大所支出的合理費用與我國《行政強制法》規定相一致。”【趙鵬:《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行政法分析——兼論相關懲罰性賠償》,載《政治與法律》2023年第10期,第50頁。】當然,這并不是說行政機關可以直接依據《行政強制法》行使索賠權,但也說明目前生態環境損害的救濟實際上是“行政執法+政府索賠”的機制,而不是由行政機關選擇適用。隨著法律制度的日益健全,“行政監管—行政措施—強制執行”越來越成為行政主體針對包括生態環境損害在內行為的主要應對方式。當然不能否認,一定時期內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有其存在的現實基礎,但一定要處理好傳統環境行政監管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之間的關系,實現制度上的功能互補、有效銜接,以防止因制度上的疊床架屋而造成事實上的行政機關爭權諉責。從完善法律體系角度講,因為行政權具有主動、高效、事前規制、集中規制的優勢,所以應當盡可能先行政,即賦予行政機關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當事人應有的行政處置權力,同時完善《行政強制法》中的代履行機制并與前者相銜接,以增強治理效能。行政機關應當首先通過行政機制,充分運用行政調查、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行政職能,實現維護生態環境安全的職責。【參見王海晶:《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損失賠償條款適用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160頁。】
在理順環境行政執法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之間的關系時,有一點特別值得關注:當出現生態環境損害時,行政機關首先應當行使環境行政執法權,當窮盡環境行政執法權仍然不足以彌補生態環境損害時,有關政府或行政機關可以運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來追究相關主體的生態修復責任。
【《改革方案》“二、工作原則”部分規定:“……賠償義務人因同一生態環境損害行為需承擔行政責任或刑事責任的,不影響其依法承擔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
這并不違反行政法上的“一事不再罰”原則。基于賠償責任而承擔的賠償金用于生態環境修復,而行政責任中如果有罰款,則要上繳國庫。當然,對生態環境損害者來說,有時會同時面臨賠償金和罰款。如果生態環境損害者無法同時支付賠償金和罰款,應優先支付賠償金,對于罰款可以依據《行政處罰法》第66條第2款的規定,申請暫緩或者分期繳納。【《行政處罰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確有經濟困難,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繳納罰款的,經當事人申請和行政機關批準,可以暫緩或者分期繳納。”】
三、協調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環境行政公益訴訟之間的關系
生態修復責任是生態環境損害者應當承擔的首要責任。作為一種行為責任,首先應當由法定國家機關或授權組織請求生態環境損害者在規定的期限內履行,否則其應承擔生態修復所需費用。問題在于,這里的請求是與《改革方案》銜接、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實現,還是與民事公益訴訟制度銜接?結合《民法典》第1234條【《民法典》第1234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生態環境能夠修復的,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有權請求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承擔修復責任。侵權人在期限內未修復的,國家規定的機關或者法律規定的組織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進行修復,所需費用由侵權人負擔。”】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簡稱《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款【《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款規定:“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規定來看,該請求是與民事公益訴訟制度銜接。但這可能只是基于私法責任體系的制度設計。如果考慮到公法責任體系,《改革方案》《民法典》以及《民事訴訟法》中政府對修復生態環境損害的訴求與政府的行政職責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疊加乃至沖突。
(一)制度沖突的體現
雖然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在其調查、取證等啟動程序上具有明顯的行政性,在其核心程序磋商環節以及賠償協議的簽訂等方面具有明顯的行政協議特征,但《改革方案》規定的政府索賠在實體上還是基于民事侵權法律制度,在程序上也遵循民事訴訟程序。這就勢必造成諸多理論與實踐上的困境,因此應當處理好該制度與行政公益訴訟之間的關系。
如果行政機關不依法行使環境行政監管權,或者違法行使環境行政監管權,檢察機關無疑可基于《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4款的規定行使行政公益訴訟權。【《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4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應當向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督促其依法履行職責。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但如果行政機關不行使生態環境損害索賠權,檢察機關能否行使行政公益訴訟權?行政機關所主張的生態環境損害索賠權并不是一項民事權利,而是其行政權力借由民法的形式,通過雙方磋商協議或者人民法院的司法判決來實現行政目的。這種生態環境治理的新型模式雖然與傳統的環境行政監管存在很大的差異,但行政機關的生態環境損害索賠權本質上屬于行政權,行政機關對該項權力并不能任意選擇,更不能隨意放棄。有民法學者主張,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應歸屬公益訴訟范疇,行政機關作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權利人是否有權處分訴權、達成和解等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參見王利明:《〈民法典〉中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的亮點》,載《廣東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第221頁。】如果行政機關不能有效行使該項權力,檢察機關可以行使行政公益訴訟權,以此來防止“行政活動可能‘遁入私法’,導致對依法行政價值的侵蝕”。【參見趙鵬:《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行政法分析——兼論相關懲罰性賠償》,載《政治與法律》2023年第10期,第55頁。】現行法律規范體系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保護生態環境的職責。如前所述,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的磋商協議確定為行政協議更為準確。根據行政協議的特點,在磋商程序中行政機關所享有的是法律規定的公權力,只不過這種維護環境公益的公權力以《改革方案》所確定的政府啟動賠償磋商程序的形式來實現。假設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中的政府索賠權定義為民事權利而允許其自由處分,那么當政府未能及時履行行政職責時,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將難以對其進行有效制約。“如果將民法上的所有權概念簡單移植到憲法中來,則會將民法所有權蘊含的經濟理性和逐利沖動取代憲法上‘國家所有’預設的責任、約束和國家保護義務。”【王旭:《論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的憲法規制功能》,載《中國法學》2013年第6期,第7頁。】因此,如果存在《改革方案》中所確定的行政機關未履行維護環境公益義務的情況,當然可以適用現行行政公益訴訟程序。以江蘇省為例,《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檢察公益訴訟工作的決定》明確規定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程序與行政公益訴訟之間的關系。【
《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檢察公益訴訟工作的決定》第8條規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權利人啟動磋商或者提起訴訟的,檢察機關可以依法提供法律支持。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權利人不按照國家規定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程序的,檢察機關應當督促其啟動賠償程序。”】
傳統行政權在生態環境遭受損害時,由于實體規則的不健全,比如缺少應有的執法手段,或是由于程序規則的闕如,比如有措施但程序不暢,大大制約了行政效能的有效發揮。司法審判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規則不健全帶來的諸多問題。然而,“如果針對所有的生態環境損害事件,行政機關均需要通過訴訟程序來執法,其管理成本的上升會帶來巨大的治理效能挑戰。”【趙鵬:《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行政法分析——兼論相關懲罰性賠償》,載《政治與法律》2023年第10期,第56頁。】
(二)制度沖突的消解方案
必須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行政公益訴訟之間建立有效銜接。具體而言,一旦出現生態環境損害,行政機關應當首先依法行使環境行政監督權。當行政機關沒有窮盡環境行政監管權就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程序,或者在行政機關窮盡環境行政監管權后仍不足以彌補生態環境損害而又不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程序,或者出現上述兩項權限爭議時,檢察機關就應行使行政公益訴訟權。這樣既可以防止行政機關選擇性行使行政監管權和生態環境損害索賠權,同時也可以防止行政機關因環境行政監管權和生態環境損害索賠權發生紛爭而不作為。
四、結語
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主要理由在于,現行環境保護法律制度中對“環境有價、損害擔責”的救濟存在法律漏洞,“企業污染、群眾受害、政府買單”的現實困境成為難解之題。【參見《破解“企業污染、政府買單”困局——環境保護部有關負責人解讀〈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載《中國應急管理》2015年第12期,第31頁。】然而,《改革方案》因涉及訴訟問題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關于訴訟制度必須嚴格遵守法律保留之規定存在不合,其具體規定也有與現行制度不合之處。長期以來,“以侵權法為代表的私法體系未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作出安排,本質上還是立法者基于私法的規范目的作出的有意缺漏,實際上也宣告了生態環境損害救濟并非私法的任務。”【張寶:《生態環境損害政府索賠制度的性質與定位》,載《現代法學》2020年第2期,第79頁。】但隨著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公益訴訟制度已經確立,《民法典》也已經明確將生態環境損害確立為侵權法上的損害。【參見《民法典》第1234條和第1235條。】因此,現有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在制度構架上已經能夠填補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漏洞。將來可以基于《改革方案》試點的經驗,將現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有關規定充實到具體法律規定中。如此,一方面可以完善具體法律規定以及公益訴訟制度,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制度上的疊床架屋。針對生態環境損害,現行制度主要有四種治理措施,即行政監管、民事公益訴訟、行政公益訴訟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如何處理這四種治理措施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現實問題。如果處理得當會形成制度合力,反之則會消解各自之應有功能。各制度之間不應形成一種競爭關系,而應形成一個有序銜接的制度體系,否則將產生選擇性執法或者不作為。從《改革方案》所規定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范圍來看,現行法律所規定的生態環境損害行政監管方面的公法責任還很不完善。從這個意義來說,《改革方案》在一定時期內尚有存在的現實需要。《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122條第1款增加了有關磋商和訴訟的規定。【
《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122條第1款規定:“固體廢物污染環境、破壞生態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設區的市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門、機構組織與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進行磋商,要求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磋商未達成一致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基于環境立法趨勢的分析,其他有關環境保護單行法的制定和修改也有望增加該制度。【
參見王海晶:《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損失賠償條款適用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2023年版,第159頁。】“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和傳統行政管制在實施主體和制度功能等方面基本重合,但采用了不同的機制和程序構造。我們需要理解不同規制方式的特點,進而推動二者形成一種互補、嵌合的關系,確保整個公共規制架構的內在均衡。”【
趙鵬:《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行政法分析——兼論相關懲罰性賠償》,載《政治與法律》2023年第10期,第53頁。】當下應當基于《改革方案》試點的經驗,不斷完善相關法律規定,以實現生態環境損害救濟領域法律制度的有機統一,從而為生態環境法典的制定奠定良好的基礎。
Several Basic Problems of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Law
HUANG Xuexian
(Kenneth Wang School of Law,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The core of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s to explore 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as the right holders to start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for compensation, and to file the litigation by the right holders if the consultation with the perpetrator fails. The purpose of this system i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in practice whe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s are not effectively remedied. As 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yste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requires not only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itself but also the coordination with related system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clearly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consultation agreement. From both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particularly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the consultation agreements within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fully mee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s. Therefore,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classify the consultation agreement within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as an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Seco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an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needs to be clarified. Since the pilot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generally adopted a cautious approach in deciding whether to apply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 procedure when fac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However, this does not eliminate the de facto overlap of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Specifically, when ecological damage occurs, if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has clearly defined the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responsible for the damage and granted the competent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the power to enforce those obligations,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should exercise its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powers to safeguard ecological interests, rather than rely on the consultation system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Only when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measures have been exhausted and still failed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should the governments seek compensation under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Otherwise,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may be deemed to have failed in its legal duties, resulting in administrative inaction. Thi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and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needs to be coordinated. On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occurs,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should first exercise its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rights. If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nitiates the compensation procedure before exhausting its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powers, or if it fails to initiate the compensation procedure after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has proven insufficient, or if there is a dispute between these two powers, the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should exercise its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rights. This ensur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cannot selectively apply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or compensation rights, and prevents it from avoiding legal responsibility due to disputes over these power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o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legal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remediation.
Key words:compensation system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consultation agreement;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