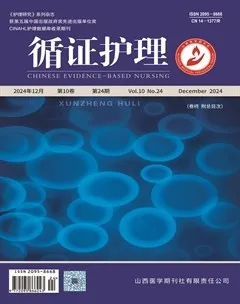腸道菌群介導的飲食干預對結直腸癌病人癥狀改善的研究進展
Research progress of dietary intervention mediated by gut microbiota on symptom improvement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LI Na1,ZENG Jinghui1,SONG Kai1,ZHANG Jing1,YANG Longhui1,HAN Shifan1,2,ZHU Ruifang1,2*1.School of Nursing,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Shanxi 030001 China;2.First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Corresponding" Author ZHU Ruifang,E-mail:ruifang.zhu@sxmu.edu.cn
Keywords colorectal cancer;gut microbiota;dietary;medicine and food share the same origin;non-nutrient;nursing
摘要 闡述腸道菌群介導下的飲食干預防治結直腸癌的作用機制,為結直腸癌的防治提供新的方向,也為進一步研發藥食同源有效成分提供理論基礎。
關鍵詞 結直腸癌;腸道菌群;飲食;藥食同源;非營養素;護理
doi:10.12102/j.issn.2095-8668.2024.24.010
當今世界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轉型正重新定義人類的生活。隨著社會需求和疾病模式的轉變,研究者們需要以一種全局視角來應對這些挑戰。人們對健康的追求已不再局限于治療,而是向預防、治療、修復和康養4個方面發展,形成了一個全方位結合的健康理念。202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的全球腫瘤報告顯示,2020年有近1 000萬例的死亡由癌癥引發,而就癌癥新病例而言,結腸癌和直腸癌占193萬例,排名第3位。美國癌癥學會(ACS)2023年的數據統計顯示,美國有153 020人被診斷為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即結腸癌和直腸癌,該疾病正逐漸成為危害人類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臨床治療結直腸癌常采用手術、放療和化療的方式,而這3種治療方式常會引起病人嚴重的不良反應[1]。有研究表明,對于上述治療方法造成的不良影響通常可以運用飲食干預來改善,即通過藥食同源物質中的非營養素來抑制腫瘤細胞生長、增殖、遷移,以減輕病人炎癥反應,調節免疫功能,進而達到減輕痛苦、降低放化療副作用和防治疾病的目的[2]。隨著基因技術的進步和發展及對腸道菌群的深入研究,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在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中,腸道菌群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3]。在結直腸癌的治療中,腸道菌群介導的飲食干預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為該領域的研究熱點和創新點[3]。本研究旨在闡述腸道菌群介導的飲食干預在增加藥食同源物質生物利用度以及增加益生菌繁殖等方面的機制,從而抑制腫瘤細胞氧化應激,達到防治結直腸癌的目的[4]。
1 結直腸癌概述
結直腸癌一般起源于結腸或直腸的內膜細胞,可同時發生。結直腸癌的病因復雜,可能與飲食習慣、環境因素、體力活動和遺傳等因素有關。其中,飲食習慣與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密不可分[5]。結直腸癌的常見癥狀包括腸道不適、便血、腹痛、腹脹和排便習慣改變等[5]。近年來,結直腸癌的發病率增高,可我國卻一直缺少明確的病理生理機制研究[6]。寄生在腸道的微生物群也被稱為腸道微生物群,它與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存在密切關系。由于它的微小存在,導致經常被人們忽略。其實,在人體結構與機體功能運轉中,其是人類不可分割的“第二大腦”。有相關研究顯示,腸道菌在結直腸癌的發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7]。由于大腸的癌變概率是小腸的12倍,而腸道菌群在大腸中的濃度最高,其內含有繁雜的腸道菌種類和數以萬計的腸道菌數量,且Renuka等[6]的研究也表明,腸道中的病毒也在結直腸癌的發病機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腸道菌群和結直腸癌的關系相輔相成、無法分割。綜上所述,這些研究均可以說明細菌和病毒之間的跨界串擾可能在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7]。炎癥性腸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可以作為結直腸癌的預判標志,包括潰瘍性結腸炎和克羅恩病,也是結直腸癌的危險因素[8-9]。有數據顯示,患有炎癥性腸病的結直腸癌高危人群中,潰瘍性結腸炎病人和克羅恩病病人30年累積結直腸癌發生風險分別為18.4%和8.3%[8]。
2 飲食習慣是結直腸癌的關鍵影響因素
飲食習慣可能是結直腸癌和炎癥性腸病的關鍵影響因素。有報道稱,與亞洲國家相比,西方發達國家的結直腸癌發病率更高,可能與不同國家的飲食模式有關,如西方飲食中以高脂肪為主,而東方飲食則含有種類豐富的蔬菜和大量的碳水化合物[9-10]。也有調查顯示,雖然炎癥性腸病在工業化國家中發病率最高,但其發病率在世界范圍內差異較大,印度和南美洲等新興工業化地區的病例數急速增加,這種增快可能與飲食習慣有關,如加工食品、糖和脂肪的過度攝入,抗生素的過度使用,以及衛生條件和個人衛生不潔等有關[11]。盡管如此,結直腸癌的首次發作和具體病理生理機制尚不清楚。但現有研究顯示,在遺傳易感人群中,炎癥的發生可能與不同國家的環境不同,使炎癥性腸病的易感宿主對腸道微生物抗原產生了免疫反應有關,這也提示腸道菌群參與了炎癥性腸病的發生和發展[5],且在炎癥性腸病和結直腸癌中都存在生態失調,這種生態失調可能引起腸黏膜屏障的破壞,從而導致炎癥和致癌的持續發生,使更多的細菌從腸腔進入到組織內部,導致慢性組織炎癥,炎癥和促癌介質的釋放進一步增加結直腸癌的發生風險[12]。由此追根溯源,飲食在調節腸道菌群結構和微環境失調等方面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4]。保持腸道菌群的動態平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宿主的自身因素,其關系著腸道菌群的種類、數量以及腸道菌群的構成[12]。因此,可以通過飲食干預減少腸道菌群的失調和紊亂,且人體的腸道菌群數量與細胞內的腸道菌群數量相似[13]。由此可見,飲食決定著腸道微生物群的生存和發展。不同飲食模式的人群具有明顯不同的腸道菌種組成,不同微生物組成又與不同的結直腸癌發生風險有關[13]。
3 腸道菌群介導的飲食干預
3.1 理論依據
腸道菌群介導下的飲食干預是以藥食同源物質中非營養素的有效成分為主導,以期達到治療疾病的一種或多種功能配方或組方[2]。追溯歷史,我國自古便有藥食同源的智慧,這一理論強調許多食物不僅可以作為美味佳肴,還能充當良藥,幫助預防和治療疾病。《中國醫學簡史》中便有“醫藥學的最初萌芽源于原始人類的飲食生活,這可以說是人類醫藥學發展的一條普遍規律”。雖然藥食同源這一詞匯是現代才出現的,但其背后的理念早已深深扎根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14]。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對食物、藥物、藥食同源概念的理解是一個由抽象到具體、由簡單到復雜、由實踐到理論的漸進過程;藥食同源的理念并不意味著藥食完全相同,在實際運用中須特別留意藥與食之間的不同之處[14]。中醫學的“藏象學說”致力于研究人體各個臟腑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及其相互關系。這一理論是在歷代醫者的醫療實踐基礎上結合陰陽五行學說的指導,經過總結和提煉而成的,是中醫學理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大眾對于養生保健的理念已經深入骨髓,常把飲食當作一種養生保健和預防疾病的行為措施,甚至運用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論通過食物來達到治病療傷的效果。這正是我國傳統的“以食代藥”的食療智慧。我國有句古語叫“藥補不如食補”,道的就是“以食代藥”“食藥合一”的奧秘[15]。
3.2 作用機制
腸道細菌已成為某些癌癥細胞的重要環境因素,包括結直腸癌、肝癌、膽道癌,甚至是乳腺癌等[16]。在結直腸中約有3×1013個細菌,其無時無刻不在與腸道細胞進行著相互作用,對人體產生一種持久有力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16]。這些微生物可以作用于胃腸道的免疫功能以幫助腸道進行正常的生理運作,而腸道菌數量以及種類的變化也會改變兩者之間的平衡,從而引發腸內或腸外的疾病。在結直腸癌癌變過程中和微生物群相關的成分里,有與潛在的癌癥調節機制相關的成分存在[17]。而且腸道微生物可以和宿主免疫系統通過胃腸道進行相互作用。由此可見,腸道菌在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3.2.1 “乘客驅動”模型和“毒性”腸道細菌模型
唐琳等[18]的研究發現,機體可以運用“乘客驅動”模型和“毒性”腸道細菌模型來調節腸道菌群微環境失調,加快結直腸癌的發生發展。Wong等[17]認為,在結直腸中存在兩種與結直腸癌發生相關的細菌,一種細菌是“引導者”,能夠誘導腸道上皮細胞的脫氧核糖核酸(DNA)受損,而另一種則是“隨行者”,與結直腸癌的發生密切相關;當“引導者”菌群發生變化時會引起腸道微環境的劇烈波動,進而導致“隨行者”菌群的失衡,最終可能引發結直腸癌的發生。“毒性”腸道細菌模型揭示了結直腸癌發生與發展的根本原因,主要源于腸道菌群、腸道免疫系統與結腸上皮細胞之間的復雜作用[17]。具體來說,腸道菌群通過分泌有毒蛋白直接引發腸道上皮細胞的癌變;而由于腸道黏膜的免疫反應異常導致腸道上皮中的癌變細胞數量急劇上升,最終引發了結直腸癌的發生[17]。
3.2.2 免疫調節和抗炎
結腸中最豐富的短鏈脂肪酸是一組由厭氧微生物產生的短鏈脂肪酸,包含醋酸鹽、丙酸鹽和丁酸鹽,其經吸收后具有全身免疫調節和抗炎的特性,可以加快有益菌的增殖,刺激調節性T細胞炎癥介質的降低,可能與結腸上皮細胞耗氧量的增加以及免疫調節和腸道屏障功能增強有關[11]。有研究表明,結直腸癌病人常由于膳食纖維攝入的減少而加快結直腸癌的發生和發展;而如丁酸鹽和丙酸鹽的短鏈脂肪酸是通過腸道微生物對膳食纖維進行發酵而生成的[11]。隨著丁酸鹽濃度的上升,其能產生瓦伯格效應,抑制癌細胞的生長。這是通過抑制組蛋白脫乙酰酶的作用,進而抑制多種致癌信號活性;同時還促進了調節性T細胞的增殖,進而增強了腸道的免疫功能[11]。因此,補充膳食纖維是預防和治療結直腸癌的重要策略。
3.2.3 非營養素通過調節腸道菌群改善結直腸癌癥狀的機制
藥食同源物質中的非營養素成分不僅可以通過調整腸道益生菌與致病菌的比例來糾正腸道菌群失調,從而預防和治療結直腸癌的發生與發展,還能通過多種信號通路對結直腸癌的形成與進展進行干預[4]。在調節腸道菌群相關信號通路的干預措施中,乳桿菌屬F17能夠抑制結腸組織中跨膜受體蛋白(Notch)信號的過度表達[19];而腸道微生物則可以刺激組織蛋白酶K(CTSK)的分泌,進而通過Toll樣受體4(TLR4)、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信號通路促進腫瘤相關巨噬細胞的分化。此外,康美方(CMF)可以調節腸道微生物群降低白細胞介素-17C(IL-17)的表達,從而抑制核轉錄因子(NF-κB)通路的激活;小檗堿則能夠調節Janus激酶(JAK)信號轉導與轉錄激活因子(STAT)、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信號通路[4]。
4 非營養素對結直腸癌癥狀的改善作用
藥食同源物質不僅包括營養素,還涵蓋了非營養素。非營養素是指存在于植物性食物和草藥中的成分,其化學結構與傳統營養素不同,能夠溶解于水或酒精等介質中。這些成分常被用作調節身體健康的活性成分或配方[2]。我國已有專家團隊開展《結直腸癌化療期中醫診療指南》的制定工作,旨在探討中醫藥在結直腸癌化療過程中是否能夠起到協同作用,以提升療效,減少毒副作用[20]。目前與結直腸癌治療有關的藥食同源物質共11種,包括烏梅、黨參、甘草、昆布、茯苓、橘紅、黃芪、蒲公英、薏苡仁、山柰、姜黃。
4.1 修飾后的茯苓多糖可緩解化療不良影響
修飾后的茯苓多糖不但可以調節免疫功能及抵抗或減輕炎癥、氧化應激,還能有效緩解化療藥物的不良影響。Wang等[21]的研究表明,茯苓作為一種重要的傳統非營養素,在我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茯苓的主要成分是茯苓多糖,其抗腫瘤活性很弱。因此,該團隊對茯苓多糖的結構進行了修飾,得到了茯苓聚糖羧甲基化衍生物(carboxymethylated pachyman,CMP),其具有更好的抗腫瘤活性,還具有調節免疫功能及抵抗或減輕炎癥、氧化應激的作用[21],為了探究CMP是否能為接受5-氟尿嘧啶(5-FU)治療的結腸癌小鼠的結腸提供保護,還進行了體外實驗,探討CMP對腸道的保護作用及其優勢作用的潛在機制,并得到了有效證明,即CMP可以作為一種預防和治療化療/放療病人腸道損傷的新藥進行研發,由于化療藥物可以通過引起腸道縮短而導致腸道黏膜炎的發生,這可以提示腸道黏膜屏障被破壞或產生炎癥,也具有明顯的維持結腸長度的作用,減輕了結腸組織病理損傷和炎癥細胞浸潤,揭示了CMP對5-FU誘導的結腸組織損傷的保護作用[1]。然而,腸道微生物群也參與了結直腸癌的多個發展過程,而化療藥物也會造成病人糞便菌群的物種豐富和細菌數量的明顯降低[21]。但CMP通過提高菌群多樣性和有益菌(包括擬桿菌和乳酸菌)的絕對數量可以明顯改善疾病癥狀。這與腸道菌群介導的飲食治療理論不謀而合。
4.2 丹參丹酚酸A(SAA)對炎癥性腸病有保護作用
由于炎癥性腸病是結直腸癌的診斷預判標準,丹參和黨參對炎癥性腸病有保護作用。Bu等[13]的研究表明,中藥中丹參的主要成分是非營養素SAA,通過調整腸道微生物群能夠為由葡聚糖硫酸鈉(DSS)引發的急性結腸炎提供保護。實驗結果表明,經過SAA處理的結腸炎大鼠的炎癥因子[白細胞介素-1(IL-1)、白細胞介素-6(IL-6),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CP-1)]的表達明顯降低,而回腸和結腸中的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則明顯上升。由此可知,SAA通過調節炎癥因子和保護腸道屏障功能來達到治療炎癥性腸病的目的。在腸道菌群方面,使用SAA進行處理的小鼠可以逆轉模型小鼠厚壁菌/擬桿菌(F/B)的升高,增加嗜黏蛋白阿克曼菌的豐度,而嗜黏蛋白阿克曼菌的增加促進了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可以看出,這也運用了腸道菌群介導的飲食干預的原理。結果表明,黨參提取物可以通過調節腸道菌群來緩解小鼠炎癥性腸病的癥狀[22]。黨參提取物增加了雙歧桿菌、乳桿菌和嗜黏桿菌3種重要益生菌的豐度,抑制了致病菌的生長,選擇性地增加了產生短鏈脂肪酸(SCFAs)的細菌,促進了短鏈脂肪酸的產生,增強了其全身和局部功能,減輕了炎癥性腸病小鼠的營養不良癥狀。
4.3 黃芪甲苷可以提高結直腸癌病人的腫瘤緩解率
結直腸癌的主要癥狀是腹瀉。Lin等[23]的Meta分析表明,黃芪類中藥聯合化療可提高結直腸癌病人的腫瘤緩解率,減輕結直腸癌病人的腹瀉。在攝入黃芪時,與化療相關的不良反應出現的頻率更少,反應更輕,這表明黃芪可以提高病人對化療的依從性,常作為臨床補充治療方案。健脾解毒的中藥復方能夠明顯提升結直腸癌病人的化療效果,減少復發和轉移的風險,進而延長病人的生存時間;而黃芪甲苷是健脾解毒方中最為關鍵的活性成分,有強大的抗腫瘤效果[24]。黃芪的核心活性成分包括皂苷、多糖和黃酮等化合物[25]。黃芪皂苷Ⅰ、黃芪皂苷Ⅱ、黃芪皂苷Ⅲ和黃芪甲苷是黃芪皂苷中有一定生物活性且含量較高的4種物質,都比原型生物利用度高,在微生物轉化的過程中,腸道細菌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通過產生β-葡萄糖醛酸酶、β-葡萄糖苷酶和硝基還原酶等各種代謝酶來推動轉化過程[25]。因此,腸道菌群可能對皂苷的生物轉化過程及作用有緊密的聯系。黃芪甲苷能夠調控腫瘤外泌體生成與分泌,進而抑制結直腸癌肝轉移。外泌體是細胞分泌的小型囊泡,其蘊含著豐富的核糖核酸(RNA)和蛋白質,是細胞間溝通的重要橋梁。在腫瘤細胞與其微環境之間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外泌體通過多種方式影響腫瘤轉移,如改變免疫細胞的表型、招募免疫抑制細胞的浸潤、釋放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及調整代謝等,深刻影響腫瘤的發展[25]。
5 小結
綜上所述,我國食療和藥膳在抗癌過程中展現出巨大潛力。藥食同源物質中蘊含著豐富的非營養素成分,其已被證實在防治惡性腫瘤方面具有顯著效果,且能夠減輕放化療的副作用。飲食干預可以作為輔助治療手段貫穿于惡性腫瘤的預防、治療和康復全過程。然而,許多藥食同源物質在人體中的生物利用度低,而如何利用腸道菌來增加藥食同源物質的利用率是目前該領域的難題之一。今后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探究非營養素在臨床實踐中的作用,以期對藥食同源物質進行充分開發,從而為臨床治療疾病提供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1] WONG C C,YU J.Gut microbiota in colorectal cancer development and therapy[J].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2023,20:429-452.
[2] 朱瑞芳,李若蘭,呂亞茹,等.基于病理生理機制的非營養素防治多原發惡性腫瘤的食療護理研究進展[J].護理研究,2023,37(16):2915-2921.
[3] HOU X X,ZHENG Z M,WEI J,et al.Effects of gut microbiota on immune responses and immunotherapy in colorectal cancer[J].Frontiers in Immunology,2022,13:1030745.
[4] 鄒秋萍,李婷,李艷平.中藥及活性成分通過影響腸道菌群干預結直腸癌的研究進展[J].國際藥學研究雜志,2020,47(12):1027-1032.
[5] YANG J,WEI H,ZHOU Y F,et al.High-fat diet promotes colorectal tumorigenesis through modulating gut microbiota and metabolites[J].Gastroenterology,2022,162(1):135-149.e2.
[6] RENUKA,DAHIYA D K.The gut virome:a neglected actor in colon cancer pathogenesis[J].Future Microbiology,2017,12(15):1345-1348.
[7] 徐超,楊曉煉,樂敏,等.細菌促進腸道病毒感染及其機制研究進展[J].浙江大學學報(農業與生命科學版),2018,44(2):140-148.
[8] SAFARPOUR A R,ASKARI H,SHOJAEI-ZARGHANI S,et al.The role of gut microbiota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current stateof the art[J].Mini-Reviews in Medicinal Chemistry,2023,23(13):1376-1389.
[9] LONG D,MAO C H,ZHANG Z S,et al.Visual analy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gut microbiota:a bibliometric analysis from 2002 to 2022[J].Medicine,2023,102(44):e35727.
[10] FOEGEDING N J,JONES Z S,BYNDLOSS M X.Western lifestyle as a driver of dysbiosis in colorectal cancer[J].Disease Models amp; Mechanisms,2021,14(5):59-61.
[11] QUAGLIO A E V,GRILLO T G,DE OLIVEIRA E C S,et al.Gut microbiota,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colorectal cancer[J].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2022,28(30):4053-4060.
[12] CHU J,ZHUANG J,WU Y H,et al.Colorectal cancer and gut viruses:a visualized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knowledge graph[J].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2023,14:1239818.
[13] BU F,ZHANG S H,DUAN Z L,et al.A critical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erbal medicine,Akkermansia muciniphila,and human health[J].Biomedicine amp; Pharmacotherapy,2020,128:110352.
[14] 謝果珍,唐雪陽,梁雪娟,等.藥食同源的源流內涵及定義[J].中國現代中藥,2020,22(9):1423-1427.
[15] 任飛.醫食同源與我國的飲食文化[J].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21(1):24-28.
[16] YAN S S,LIU T,ZHAO H B,et al.Colorectal cancer-specific microbiome in peripheral circulation and cancer tissues[J].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2024,15:1422536.
[17] WONG S H,YU J.Gut microbiota in colorectal cancer:mechanisms of action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J].Nature Reviews Gastroenterology amp; Hepatology,2019,16:690-704.
[18] 唐琳,劉波.腸道菌群在結直腸癌發病與治療中的研究進展[J].山東醫藥,2022,62(10):101-104.
[19] 劉旭偉.益生菌囊泡富集載體的制備及其對小鼠結腸炎的調節作用[D].廣州:華南農業大學,2022.
[20] 李高彪,何斌,梁昌昊,等.基于德爾菲法的《結直腸癌化療期中醫診療指南》臨床問題和結局指標的收集與確定[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22,28(4):565-570.
[21] WANG C H,YANG S X,GAO L,et al.Carboxymethyl pachyman (CMP) reduces intestinal mucositis and regulates the intestinal microflora in 5-fluorouracil-treated CT26 tumour-bearing mice[J].Food amp; Function,2018,9(5):2695-2704.
[22] 黃嬋,張亦,楊榮英.黃芪及黨參破壁飲片改善結直腸癌化療患者不良反應的效果[J].臨床合理用藥雜志,2023,16(10):88-90.
[23] LIN S,AN X X,GUO Y,et al.Meta-analysis of Astragalus-conta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for colorectal cancer:efficacy and safety to tumor response[J].Frontiers in Oncology,2019,9:749.
[24] 浦勻舟,李昊澤,李玲,等.黃芪甲苷調控腫瘤外泌體生成與分泌抑制結直腸癌轉移的作用機制[J].上海中醫藥雜志,2023,57(6):41-49.
[25] 李靜純,龍其雄,馮峰,等.基于網絡藥理學方法探討黃芪-半枝蓮抗結直腸癌的作用機制[J].國際醫藥衛生導報,2023,29(19):2737-2745.
(收稿日期:2024-11-28;修回日期:2024-12-04)
(本文編輯趙奕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