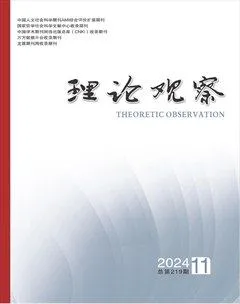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激進解讀
摘 要:為了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實踐開拓理論“空間”,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傳統國家理論做了激進化解讀。這一解讀是通過拓撲學以及斯賓諾莎的理論“迂回”完成的。通過拓撲學,阿爾都塞將馬克思關于社會—國家結構的“大廈”轉變為拓撲學的平面。它遵循斯賓諾莎的內在性線索,以創構性的力量為根基,是多元力量建構的結果。在此意義上,可以說阿爾都塞的國家觀就是一種力量政治學。通過“掏空”國家的“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認識論內容,阿爾都塞凸顯了其國家觀的激進性以及“當代性”。說到底,阿爾都塞的國家觀實際上是一種反國家觀,本質上是一種后結構主義的激進政治模式。
關鍵詞:阿爾都塞;國家;拓撲學;斯賓諾莎;力量
中圖分類號:B565;B0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2234(2024)11 — 0048 — 05
阿爾都塞對馬克思主義傳統國家理論的重釋源于自己哲學觀的改變。早在《保衛馬克思》的著作中,阿爾都塞就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定義為理論實踐的理論。然而,1968年的五月風暴動搖了阿爾都塞的觀念。在經歷了總罷工之后,阿爾都塞開始反思自己的理論。隨著自我反思的展開,他逐漸明確了一個觀點,即“哲學基本上是政治的。”[1]由此,他對哲學的認識從認識論(理論實踐)領域轉向了政治實踐領域。哲學不再是理論實踐的理論,而是“理論領域中的階級斗爭。”[2]在這樣的背景下,阿爾都塞將目光聚焦于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即馬克思主義政治實踐的前沿陣地,意圖通過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理論和實踐的“介入”,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實踐打開一個新的“空間”。
一、“大廈”的空間隱喻和國家的拓撲學平面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指出,“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3]在《論再生產》中,阿爾都塞認為,這里馬克思提出了描繪社會—國家的“一個空間的隱喻,一個地形學的隱喻。”[4]馬克思將社會結構隱喻為一座“大廈”,這座“大廈”由“基礎”(“下層建筑”)和“上層建筑”兩部分構成。一方面,“基礎”(“下層建筑”)對“上層建筑”具有歸根到底決定作用,是整個“大廈”結構中具有決定性的力量;另方面,“上層建筑”雖然不能脫離“基礎”而獨自“漂浮”在空中,但“上層建筑”一旦產生出來就具有相對獨立性,并對“基礎”具有(決定性)反作用。
阿爾都塞承認,“這個隱喻有一個優勢,它使我們直觀地看到社會結構各層的作用指數的大小”。[5]由于“基礎”歸根到底決定著“上層建筑”,所以在“大廈”的整體中,“基礎”的作用指數更大。不僅如此,這個關于社會整體(結構)的隱喻,還將馬克思的整體和黑格爾的總體區別開來。阿爾都塞認為,黑格爾的總體是一種表現性的總體。他的歷史世界中具體生活的所有因素,都根源于“絕對精神”的外化,因而都能夠歸結為一個統一的內在本原。然而,馬克思的總體是一種結構性的總體,復雜性是其社會組織的核心。在馬克思的論述中,社會(國家)整體的統一性是“復雜性構成的、被構成的整體的統一性,因而包含著人們所說的不同的和‘相對獨立’的層次。”[6]
盡管阿爾都塞肯定馬克思這一“大廈”空間隱喻具有一定的理論優勢,但更多強調的是其“描述性的”[7]的性質。所謂“描述性”的,指“大廈”的隱喻未能在理論上說明“上層建筑”的存在和性質的問題,也就是未能在理論上對“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問題以及“上層建筑”對“基礎”的反作用問題做出說明。不僅如此,在阿爾都塞看來,“大廈空間”的隱喻表征了一種“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垂直的作用關系,這種關系將資本主義的社會—國家表述為一個封閉的堡壘。在堡壘的邏輯中,“基礎”通過不斷地生產與再生產產生足夠的、有效支撐上層建筑的可以累加的“量”,而“上層建筑”則在“基礎”的規定下和限度內服務(反作用)于“基礎”的生產和再生產,從而形成了一個“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加強“基礎”的無法爆破的結構。為了突破這種局面,進而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實踐創造理論“空間”,阿爾都塞運用拓撲學對其進行了“改造”。
20世紀40、50年代,許多數學的方法被引入到人文科學領域,這其中就包括拓撲學。“拓撲學”(Topology)是幾何學的一個分支,主要研究幾何圖形或空間在連續改變形狀后還能保持不變的一些性質。它只考慮物體間的位置關系而不考慮它們的形狀、長短、大小、面積、體積等度量性質和數量性質,因此,也稱位置幾何學。在《來日方長》中,阿爾都塞表明,早在獲得巴黎高師教師學銜之前,他就間接得知拉康在搞莫比烏斯圈(拓撲學),以用它來表明精神分析對二元對立觀念的質疑和“穿越幻想”的可能性,并承認拉康對他有一種不可否認的影響。基于此,可以推測,阿爾都塞之所以用拓撲學“改造”馬克思的地形學空間與拉康的啟發是密不可分的。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的主要理論原則呈現出一種‘拓撲學’(topography)的形式,即在拓撲空間中圖形的位置變換,這個空間定義了圖形的拓撲位置以及關系,以使相對外部性、決定等成為‘可見’關系,從而使‘實體’之間的效能成為‘可見’關系,所謂‘實體’即基礎(生產/剝削,因此是經濟的階級斗爭)和‘上層建筑’的要素(法律、國家、意識形態)。”[8]
在阿爾都塞那里,通過拓撲學的引入,盡管“基礎”與“上層建筑”并不具有同樣的認識論內容,不具有同樣的“質”和“量”,但在拓撲學中它們都能夠被“等價變換”為國家這一平面上的具體的點或圖形。或者說,不管“基礎”和“上層建筑”是否具有同樣的層次、位置以及力量,它們都可以經“拓撲變換”(“壓扁”)被“投影”到國家這一平面,成為“異素同構”[9]的相互作用的關系。事實上,為了突破“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堡壘結構,阿爾都塞就是要“抽空”它們的認識論內容,讓它們成為形式化的“基礎”和“上層建筑”。當把它們“抽空”以后,剩下的就是非認識論的、非本質的平面。這個平面就是拓撲學的平面(空間)。如此,“大廈”的空間成為一個純粹的形式化的平面。在這個形式化的平面上,各種因素(力量)不斷地錯位、移置、凝縮,甚至爆炸。也就是不斷地進行著拓撲變換(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經過“拓撲變換”的國家平面,沒有了“作用”(決定)和“反作用”的概念和關系,只有具有各自作用力指數[10]的“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影響、相互重構。至于它們各自作用力指數的大小,不取決于它們的數量,也就是不取決于它們各自在拓撲變換中獲得位置(力量)的累積之和,而是取決于它們在拓撲變換中所獲得位置(力量)的幾何總和。在作用指數的意義上講,無論是經濟、政治還是意識形態都是同等重要的,都對國家這一平面的統一發揮著重要作用。
總的來說,通過拓撲學,阿爾都塞將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的“大廈”(上層建筑和下層建筑)“壓扁”(拓撲變換),構造了一個社會—國家的拓撲學平面,從而取消了“基礎”和“上層建筑”垂直的作用與反作用關系,將它們轉化為在拓撲平面內水平的、異質的因素“相互重構、相互決定” [11]的關系。如此一來,資本主義國家不再是一個堅固的堡壘,而是一個特殊的經由拓撲變換而不斷再生產的平面。通過拓撲變換,“上層建筑”與“下層建筑”成為了“異素同構”[12]的元素。它們在矛盾統一體(國家的拓撲學平面)中相互作用的過程就是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生產條件“再生產”的過程。也可以說,正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地進行“再生產”(拓撲變換),即通過不斷地使“基礎”和“上層建筑”以及它們中的各個要素、結構相互作用、相互重構,資本主義國家作為矛盾的統一體才能夠得以維持而不至于破裂。這就是阿爾都塞發現的資本主義國家得以維持的“再生產”(拓撲變換)的秘密。
二、國家的建構和多元力量的斗爭
在《論再生產》中,阿爾都塞之所以對國家中的各要素做拓撲變換,在于他將國家看作是不斷進行再生產的力量的拓撲學平面,一個力量的動態結構,亦即能量轉化的裝置。如果需要以力量的統一性名義“想象”國家的存在,就必須做大量的“歪曲”(拓撲變換),以便把各個要素都熔進這個統一性的模型中。在這個力量的“統一”裝置,即國家這臺“機器”中,階級斗爭的力量或者暴力,轉化為國家權力,即轉化為國家法律和法權的力量。[13]在將國家看作是一個力量的轉化裝置這方面,斯賓諾莎可謂是阿爾都塞獲得靈感的源泉。關于阿爾都塞和斯賓諾莎的關系,用學者趙文的話講就是“旁邊站著斯賓諾莎的阿爾都塞。”[14]
實體(substantia),也就是神、自然,是斯賓諾莎理論的基礎性概念。在斯賓諾莎那里,實體擁有無限多的屬性,屬性(attributus)是“構成實體本質的東西。”[15]每個屬性都以特定的方式體現著實體的本質。樣式是“實體的分殊(affectiones)”。[16]所謂分殊,也就是實體的具體化、特殊化的變相,即實體的現實效果。用阿爾都塞的話說,整個世界除了效果,別無他物。世界的物性身體就是各種具體的、個別的樣式(事實)“結合”的結果,即“它是諸事物相遇的過程和結果,它本身在它內部進行著‘勢激理易’的‘情動分殊’。”[17]
在阿爾都塞那里,通過斯賓諾莎的理論“迂回”,不僅世界如此,國家更是如此。國家這部“機器”,作為一種“多元決定”的裝置,就各種存在的事實(如經濟、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等)都是它的效果而言,國家的建構與存在正是各種在它之內的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國家“這個統一體是‘復雜的’,那么它也是‘被結構’的。”[18]如果說,思維、廣延以及意識形態一般、生產方式一般、階級斗爭一般等都是世界的屬性,反映世界的本質,那么各種國家機器、具體的生產方式、具體的階級斗爭等等就是世界的種種屬性單獨分殊的樣態或是相互“結合”分殊的樣態。這些具體的樣態在世界之內“情動分殊”,它們“結合”(“偶然相遇”)而成的結構就是國家的整體本身。
由于某種屬性的“情動分殊”并不是必然的,因此任何一種樣式的存在也不是必然的。這就意味著,國家作為各種樣式“結合”的結構同樣不是必然的。具有必然性的只有神,因為只有神是絕對無限力量的存在。存在即力量、能力或者權力,反之亦然。力量或權力是神和萬物賴以存在的東西。“不能夠存在就是無力,反之,能夠存在就是有力”[19]除了神以外,諸多樣態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因此它們都是非必然的存在。所以為了能夠自我保存,它們就必須進行自我保存的努力。這種自我保存的努力是一切樣態的現實本質,是萬物的“自然權利”。國家作為一種力量的動態結構,同樣承襲著這樣的“自然權利”,所以不斷將暴力轉化為人民一致同意的權力以維系自身的存在。
總的來說,在阿爾都塞那里,國家這一整體表現為具有內在性張力以及創構性的拓撲平面。它是一種被多元力量建構的平面,所以也是一種不穩定的平面,無時無刻不處在多元要素的相互作用即不平衡的力量的變化之中。階級鎮壓是一種力量,階級的意識形態化也是一種力量。[20]除了作為國家效果的各種力量,國家的平面上什么也沒有。以至于國家這個平面就像流沙一樣,是一個不斷自我凹陷的“陷阱”。“陷阱”里面究竟是什么是無法知道的。如此,國家的平面是否存在?根據阿爾都塞,國家的平面是一種歸根到底的決定性力量。但是,在阿爾都塞那里,這種歸根到底決定作用自始至終都是作為一種隱含的神秘的作用在起作用,或者作為一種最終的作用而起作用。它總要作為一種最終的、最有力量的統治力量占據一個絕對優勢的位置。說到底,實際上作為隱含的、最終起作用的作用實際上就是經常不起作用,也就是說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力量占據這個位置。所以,實際存在的總是力量和力量之間的斗爭,也只有這種斗爭。換言之,存在的僅僅是多元力量強度的不斷轉移和凝縮。
顯然,力量在阿爾都塞的國家思想中占據重要的理論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阿爾都塞的政治哲學就是一種力量政治學。阿爾都塞總是在強調力量的作用。例如: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組織在資產階級國家的AIE中“得到承認,是由于力量。”[21]在亞、非、拉國家,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組織被完全禁止,也是由于力量。[22]總之,“理性也好,狡計也罷;無能也好,靈活也罷;事實就擺在這里。……事情可能不會以同樣的方式進行,這最終取決于一場歷史性的階級斗爭中的力量對比。”[23]
三、結 語
總的來看,按照阿爾都塞的邏輯,永恒的勝者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無窮的力量的斗爭。結果是,國家是否存在的問題已經不重要。國家的存在需要建構,需要不同的力量建構。這種力量是一種存在的力量,是一種實體表現的力量。它不是歸根到底統治意義上的力量,也就是法權意義上的力量。也就是說,國家并不是被一種超越的力量所決定。這種超越的力量作為另外一種本體的力量通過合法化的暴力轉化為權力。換言之,國家不是被權力所建構、決定的。相反,國家是一種力量的綜合體,世界本身也是一種力量的集合體。這個集合體總是在不斷地進行多元力量的斗爭,不斷地交換“位置”進行拓撲學的(力量的)變換,也就是不斷地進行再生產。這就是事實,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東西。歸根到底的決定(國家)不復存在以后,阿爾都塞下一步的理論邏輯就是:不存在“決定”,存在的只有“非決定”;不存在“國家”,存在的只有“非國家”。“非決定”恰恰是“當代性”的難題性。奈格里正是強調“非決定”,拒絕用“決定”同資本主義國家調情。“非決定”、“反決定”給“諸眾”創造了“聯合”的空間,從而讓“諸眾”擁有一種野蠻的創制的力量。“諸眾”聯合形成力量并通過力量建構國家,就是“諸眾”的實踐過程,實際上也就是群眾創造歷史的過程。然而,按照這種邏輯推演,群眾則成為了一種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概念。這是對唯物史觀的激進化解讀。由此可見,阿爾都塞的國家觀實際上是一種反國家觀。阿爾都塞通過反國家的方式凸顯了他國家思想的激進性,在本質上是一種后結構主義的激進政治模式。
為了反對目的論的國家觀,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實踐開拓理論“空間”,阿爾都塞力圖要突破“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本質性的差別。當“基礎”被掏空以后,“上層建筑”的內容實際上也隨之被掏空了。當“一切”都失去了的時候,就只能通過再生產維持國家這個不可被還原的結構。不可被還原到什么樣的結構?不可被還原到具有歸根到底決定作用的結構。因為,一旦被還原到這樣的結構中,就成為黑格爾的具有同一性的(實際上也就是歸根到底決定的)表現性的總體。一些人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作經濟決定論,顯然遵循的就是黑格爾的同一性的邏輯。然而,這恰恰是阿爾都塞所反對的。在阿爾都塞那里,拓撲變換后的國家的拓撲學平面不再是意識形態的同質的經濟的平面空間。在后者中,占統治地位的是機械的因果關系(直線性的因果關系)。而在前者中,不存在誰先于誰存在的可“追溯”的還原主義問題,更多強調的是共時性的各因素,即各種力量的相互作用。“阿爾都塞堅稱從來沒有一種社會實體是由一個或一組其他的社會實體所決定。相反,社會中的每一個乃至所有的實體總是由所有其他實體的效果同時決定的。換言之,每一個實體都是所有其他實體間相互影響的產物。其由所有這些其他實體共同決定,而不是由某個或某組實體單獨決定。”[24]因此,“基礎”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中法—政治的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之間,甚至“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在同一平面共同貢獻作用指數的意義上,不再存在“作用”與“反作用”的前理論的問題。在國家的拓撲平面中,存在的只有力量以及力量之間的斗爭。也正是由于力量的斗爭,國家才得以建構。這種力量的斗爭歸根到表現為階級之間的斗爭。
可見,通過對斯賓諾莎的理論“迂回”,阿爾都塞的國家觀具有了“當代性”。用阿爾都塞“當代性”的問題式來解讀馬克思,恰恰就產生了奈格里的“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阿爾都塞晚期和奈格里一樣,都走上了“訣別”馬克思的道路。可以說,阿爾都塞的思想中一直存在激進的成分。這也正是阿爾都塞合乎邏輯地走向了“當代”的理論根本。阿爾都塞也因此成為當代斯賓諾莎復興,包括用斯賓諾莎解讀馬克思的理論先驅。他的思想直接影響了德勒茲、馬舍雷、奈格里和巴里巴爾等人。正是在此理論意義上,阿爾都塞不是一個純粹的結構主義者,他是一個后結構主義者的先驅,即后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驅,是當代法國激進左翼話語的先驅。
〔參 考 文 獻〕
[1][法]阿爾都塞.哲學是革命的武器[C]//莫徒,譯.中共中央著作編譯局.馬列主義研究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05):160.
[2] [法]阿圖塞.答劉易斯(自我批評)[C]//杜章智,沈起予,譯.自我批評論文集(補卷),臺灣:遠流出版公司,1991:83.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
[4] [法]阿爾都塞.論再生產[M].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134.
[5]吳子楓.阿爾都塞的國家理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05):112.
[6] [法]阿爾都塞,[法]巴里巴爾.讀《資本論》[M].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107-108.
[7] [法]阿爾都塞.論再生產[M].吳子楓,譯.陜西: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135.
[8]Althusser. Marx in his Limits[A]. Francois Matheron, Oliver Corpet.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1978-87[C]. London & New York:Verso,2006:47.
[9]姚云帆.重繪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地形學構造:《論再生產》讀后[J].東方學刊,2020(01):115.
[10] [法]阿爾都塞.論再生產[M].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134.
[11]姚云帆.重繪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地形學構造:《論再生產》讀后[J].東方學刊,2020(01):115.
[12]姚云帆.重繪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地形學構造:《論再生產》讀后[J].東方學刊,2020(01):115.
[13]Althusser. Marx in his Limits[A]. Francois Matheron, Oliver Corpet. Philosophy of the Encounter Later Writings,1978-87[C]. London & New York:Verso,2006:108.
[14]趙文.力量政治學與群眾的自我啟蒙:阿爾都塞的斯賓諾莎及其難題性[J].東方學刊,2021(01):94.
[15]斯賓諾莎文集:第4卷[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
[16]斯賓諾莎文集:第4卷[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
[17]趙文.力量政治學與群眾的自我啟蒙:阿爾都塞的斯賓諾莎及其難題性[J].東方學刊,2021(01):99.
[18][美]沃倫·蒙塔格.結構與表現難題:阿爾都塞早期的“相遇的唯物主義”[J].趙文,蘭麗英,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01):151.
[19]斯賓諾莎文集:第4卷[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10.
[20] [法]阿爾都塞.論再生產[M].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 299.
[21][法]阿爾都塞.論再生產[M].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208.
[22][法]阿爾都塞.論再生產[M].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212.
[23][法]阿爾都塞.論再生產[M].吳子楓,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219-220.
[24][美]斯蒂芬·A·雷斯尼克,[美]理查德·D·沃爾夫.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新起點[M].王虎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88.
〔責任編輯:侯慶海,周浩〕